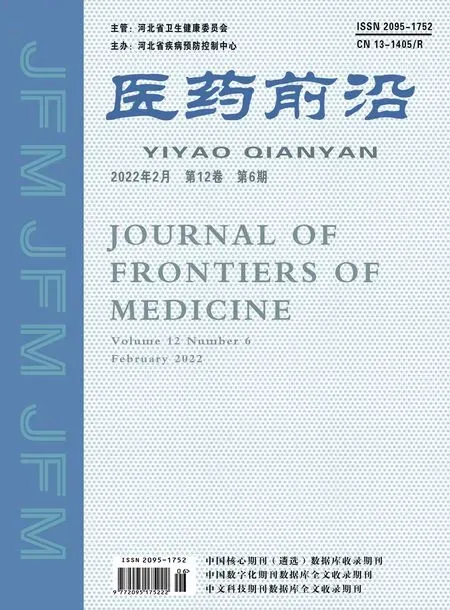原發性肝癌外科治療進展
郭程昊,吳曉瑋,王 軒(通信作者)
(1 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八一醫院腫瘤外科 江蘇 南京 210000)
(2 南京中醫藥大學 江蘇 南京 210000)
(3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總醫院秦淮醫療區腫瘤外科 江蘇 南京 210000)
原發性肝癌是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患病率在全球惡性腫瘤中排第7 位,死亡比例則高居第3 位。而我國是世界上肝癌發病率最高的國家,發病率在我國常見惡性腫瘤中排第4 位,病死率排第2 位[1-3],病情形勢嚴峻。目前多學科綜合療法已成為我國肝癌防治的主流模式和發展方向,可以制定出最佳的個體化治療方案,進而有效提升肝癌患者的個體及總體生存率。雖然目前肝癌的治療手段不斷更新,尤其近年來生物免疫療法發展迅速,是唯一有望徹底消滅癌細胞的方法,但手術治療仍是早期肝癌的首選治療方法,是延長肝癌患者生存期的最有力手段[4]。本文將通過對肝癌的術前精準評估、手術方案制定、降期轉化、術中止血技術及術后輔助治療等領域的臨床科研熱點展開論述,以求深入了解肝癌外科治療的最新進展。原發性肝癌主要包含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內膽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HCC 和ICC混合型3 個不同的病理學類型,因三者在發病機制、生物行為、組織學形態、診療方式及其預后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別,而其中HCC 占85%~90%[3],因此本文中所指的“肝癌”均指肝細胞癌。
1.術前精準評估
由于肝癌手術的復雜性,進行精準的術前評估是十分必要的,不僅僅是最基本的判斷患者手術施行的可能性,其對手術方案的制定、評估手術安全性、降低術后并發癥發生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只有建好了術前的“地基”,才能更好保證術中效果及患者術后的長期獲益。
通過解讀《原發性肝癌診療規范(2019 年版)》并結合臨床實踐,作者認為肝癌的綜合術前評估應當以下列因素為重點。(1)全身系統狀況評估:詳細詢問并了解患者的既往病史,并通過心臟彩超、肺功能檢測等檢查判斷是否有其他重要器官的嚴重病變,以評估患者能否耐受手術治療。(2)肝功能評估:目前國內外較為常見的評估方法是按照Child-Pugh 分級,通過評估患者肝性腦病分期、腹水情況、總膽紅素、白蛋白、凝血酶原時間延長這五項指標來進行打分,一般來說肝功能處于A 級的患者手術風險較小,預后較佳。(3)肝臟儲備功能評估:常用的肝臟儲備功能評估方法主要為吲哚氰綠(indocyanine green,ICG)清除實驗,同時筆者所在科室會根據上腹部CT 等影像學手段評估肝硬化程度,來綜合評價患者的肝臟儲備功能。通常認為肝功能Child-Pugh A 級、吲哚氰綠15 min 滯留率<30%是能成功實施手術切除的必要條件[4]。(4)病毒學評估:有肝炎病史的病人通過測定肝炎病毒DNA 定量評估病毒性肝炎的活躍程度,若肝炎病毒活躍,須先行抗病毒治療。(5)門靜脈高壓評估:由于門靜脈高壓癥患者的術后并發癥發生概率明顯增高,需在術前通過肝臟瞬時彈性檢查結果評價門靜脈高壓程度,以制定術中方案及綜合評估預后。(6)影像學評估:得益于臨床數字化技術的顯著發展,可以通過術前CT 及MRI 三維重建技術制定手術方案。這樣不僅能更直觀地觀察患者肝臟情況,有助于設計更為精準的切除范圍和手術路徑,還能在保證腫瘤切除完整性的前提下,保護剩余肝臟的管道。近年來3D 打印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三維重建技術在臨床上有了更廣泛的應用,不僅僅局限于術前,對于術中方案的制定也有非常重要的輔助意義。
2.外科治療相關領域的進展
2.1 手術方案的制定
研究表明,肝切除術的切除范圍越大,術后發生肝功能衰竭的幾率就越大;另一方面,若切除范圍有限,則腫瘤復發的機會就越大[5]。有外國學者通過對患者MELD 評分及血清鈉水平進行危險分層,以探求肝硬化患者所能耐受的肝切除范圍上限[6]。肝硬化病人因其肝臟基本功能受損,往往需要更加精準地劃定手術范圍,盡可能多的保留殘肝體積,以減少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目前,我國指南認為[3]手術切緣距離腫瘤邊界>1 cm可定為切緣陰性,若切緣≤1 cm,則需根據病理學檢查指示切除面是否有腫瘤細胞殘留來判斷切緣是否為陰性。而韓國最新指南認為[7]切緣>2 cm 能獲得更好的長期療效,目前國內外對于手術切緣的范圍界定尚未有一個統一的規范。由于肝癌術后復發與否由原發肝癌大小、微血管有無侵犯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決定,切緣陰性并不能說明復發可能低,所以筆者認為切除范圍的制定還需以保證殘肝功能為先。
2.2 精準肝切除理論的發展
2006 年由董家鴻教授首次提出精準肝臟外科概念,并在此概念基礎上,提出了精準肝切除的新理念[8-9]。精準肝切除理念專注于提供全面的術前評估、個性化的手術方案、細致的術中操作和完善的術后管理等方面,同時也對治療成本及安全性保持一定的重視程度,成為了目前肝臟外科發展的主流方向[10]。
2.3 中晚期肝癌的降期轉化
由于肝癌發病隱匿的特點,大部分肝癌患者確診時已至中晚期,錯過了手術治療的最佳時機,但外科治療仍是目前肝癌患者能夠獲得長期生存的最佳方法。因此,探討如何將中晚期肝癌轉化為可手術切除的狀態成為近期的熱門話題。降期治療以縮小腫瘤體積,縮小或滅活大血管癌栓及增加剩余肝臟體積為主要目的[11]。肝癌的降期轉化處理雖然可以為中晚期肝癌患者創造手術切除的機會,但對于如何提高降期成功率、預測降期處理效果的優劣、減少術中及術后風險等方面,都值得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
2.4 出血控制
由于肝臟具有血液供應豐富、管路分布復雜等特點,如何在術中有效控制出血并及時止血成為了手術成敗的關鍵。
2.4.1 肝門血流阻斷技術:該技術是肝癌切除術中用于控制出血的最主要措施,目前在臨床應用上最常見的有間歇性全入肝血流阻斷術、選擇性半肝血流阻斷術以及保留半肝動脈血供的入肝血流阻斷術[12]。其中間歇性全入肝血流阻斷術即Pringle 法,是一種最簡便的控制肝臟血流的方法,被廣泛用于各種肝臟切除術,雖然其操作簡單,但是會極大增加發生肝臟缺血/再灌注損傷的風險[13]。
2.4.2 控制門靜脈壓力:在術中,控制門靜脈壓力也是減少出血的有效手段。當肝門血管被阻斷后, 分離肝實質過程中的肝短靜脈和肝靜脈出血是術中出血的主要風險,降低門靜脈壓力能有效控制靜脈血流從而減少出血。Li 等[14]研究表明,在肝癌切除的手術過程中控制門靜脈壓力,是一種簡單有效地控制術中出血的方法,并且對患者的肝腎功能幾乎沒有不利影響。
2.4.3 止血材料:因肝癌切除手術的特殊性,具有切口深、切口附近有更多血管神經等特點,常規術中止血方法常常無法達到很好的預期。目前,纖維蛋白膠、吸收性明膠海綿、氧化(可再生)纖維素、α 氰基丙烯酸酯類組織膠、殼聚糖等均為常用的止血材料[15]。
2.5 手術方式的選擇
目前手術方法的選擇以開放手術、腹腔鏡手術及達芬奇機器人手術等為主。近年來,隨著達芬奇機器人手術系統的不斷完善,雖然還未能成為主流的手術方式,但也漸漸在全國各地有所開展。我國學者陳燕凌等統計后分析發現[16],達芬奇機器人手術相較于腹腔鏡手術,雖然在手術時間及安全性上沒有明顯差異,但在術中處理血管破口及斷端的時間上有明顯縮短,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術后并發癥的發生,讓患者有更好的預后。Choi GH 等[17]學者研究表明,在學習時間上,達芬奇機器人手術較腹腔鏡手術更短,使得醫生能夠更快地在臨床上應用此技術。
2.6 肝移植
肝移植一向是終末期肝病治療中的首要手段。由于臨床上采用廣泛的米蘭標準條件過于嚴苛[18],我國學者經過不斷地探索,提出了上海復旦標準及杭州標準,大大增加了獲益人群。但考慮到國情,肝源的供給仍然緊缺,筆者認為仍需嚴格把控受體的選擇標準,同時兼顧評價患者經濟條件,這樣才能保證手術利益最大化。
3.術后輔助治療
肝癌術后的高復發率是一直以來影響肝癌患者術后生存率的最大原因,為此,在保證肝癌術前評估精準,術中切除腫瘤完整的前提下,術后輔助治療方案的選擇也極其重要。目前,肝癌術后輔助治療的選擇主要有TACE,TARE,靶向治療,免疫治療,抗病毒治療,中醫藥治療等,但目前尚無制定輔助治療方案的統一規范[19-20]。
筆者認為,中醫所提倡的“治未病”概念在肝癌的診治上可以有所運用[21]。在減輕放化療不良反應,改善癥狀,以及提高患者生存率上,已有很多研究可以證實中醫藥的療效[22-25]。術后運用中醫方法治療,由于其辨證論治的特殊性,可以根據患者的病情變化及時的調整治療方案,在病程不同階段提供符合病情所需要的治療,在這一點上,很多西醫輔助治療有所欠缺,也是中醫治療的獨特優勢所在。通過一段時間的定期反饋,也能堅定患者的治療信心,對醫患雙方都有著正向影響。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肝癌的外科治療有著其特有的復雜性,不管是術前、術中還是術后都有著大大小小的難題等待臨床上去解決,但總的來說,盡早地預防、發現及治療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患者獲得更加積極的治療效果。我國多個研究團隊聯合[26]提出了一種運用深度學習基于患者術前多期造影增強CT 和臨床數據對肝臟惡性腫瘤進行判別的智能診斷系統,在該系統輔助下,放射科醫生診斷準確率平均可提高8.3%,使肝癌的診治更加精準。筆者相信,隨著手術技術、傳染病、腫瘤學、醫學材料、數字化等多學科的發展,臨床上多學科合作體系的不斷完善,能使肝癌患者獲得更長久的生存期及更佳的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