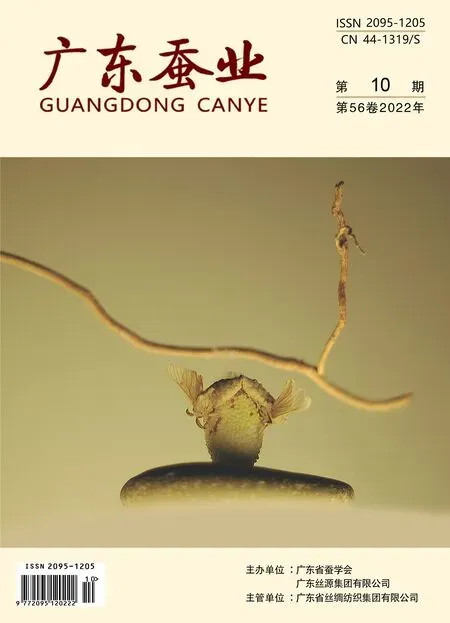稻田種養結合模式的功能研究進展與發展展望
陳明杰 梁 龍 孫 凱
稻田種養結合模式的功能研究進展與發展展望
陳明杰梁龍孫凱
(貴州財經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貴州貴陽550025)
稻田種養作為我國重要傳統農業文化遺產,在糧食安全、生態環境和文化價值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正確認識傳統稻田種養生態經濟系統的生產、生活和生態功能,有利于實現農業糧食供給與低碳發展的雙贏。
稻田種養;農業文化遺產;可持續農業;糧食安全;低碳生態
自2019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許多國家開始限制糧食出口,全球農業供應嚴重不穩定,糧食安全再次成為全球熱議的話題。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2021年7月發布的《2021年世界糧食安全與營養狀況》報告,估計2020年有近7.68億人口處于饑餓狀態,占世界總人口的19.2%,比2019年增加了約1.18億人口,這距離2030年結束糧食不安全狀態,實現人口零饑餓的目標仍然遙遠。糧食安全問題一直是人類發展面臨的諸多困境之一。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為解決國內饑荒和改善農業生產現狀,印度率先發起了農業綠色革命并成功推向亞洲和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1],但生產效率提高的同時,卻忽視了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農業生產開始過度依賴化肥、農藥及其他農用化學藥品的投入,變得更加能源密集,以至農業的高碳排、低效率問題凸顯。因此,如何在保證經濟生產的同時兼顧生態環境成為世界共同關注的焦點。
如今人類的頻繁活動被認為是影響和導致全球氣候變暖的根源。2018年,人為產生的溫室氣體(GHG)排放量超過500億t,全球地表平均溫度相比工業化前已上升了1.1 ℃的水平[2]。農業作為陸地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來源,全球三分之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來自糧食生產系統,糧食生產對人為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貢獻達到34%[3]。我國是世界糧食生產大國,以僅有8%的可耕土地養活了全球約20%的人口,然而糧食生產的碳排放卻占全球總糧食系統碳排放的13.5%。因此,為減小人為活動帶來的環境壓力,保證發展的可持續性,我國承諾在2030年之前達到碳峰值,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低碳農業發展勢在必行。
目前,我國水稻種植面積3 007.6萬hm2,產量近2億t,在糧食供給方面具有突出貢獻,但水稻種植也是我國農業生態系統四大碳排放源之一,稻田溫室氣體甲烷(CH4)、氧化亞氮(N2O)等對大氣環境的影響不容忽視,應采取有效的稻田減排策略,以阻止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Liu等研究發現水稻生產中氮肥的投入處于過量狀態,化肥用量的增加不利于作物對氮素的利用[4],而適當減少施氮,配合有機肥替代,能夠促進清潔生產[5-7]。夏仕明等認為水和肥是影響CH4和N2O排放的兩大主控因素[8],通過氮肥減施和間歇灌溉能夠分別降低稻田38%、48.7%的潛在增溫趨勢[9]。可見,水分管理也是稻作系統減排的重要農藝措施。稻田節水灌溉具有促進根系發育,改善土壤通氣條件,抑制厭氧菌活動等優勢[10-11]。Li等通過實驗研究發現,節水灌溉條件下優化氮肥管理,在保持水稻產量、提高氮素利用率和減少稻田氮流失方面具有交互效應,但要注意的是,節水決不能以犧牲水稻產量為代價[12]。此外,張藝、孫會峰等、張衛建等還發現改良水稻品種能夠顯著幫助增產和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強度[13-15]。Yao等認為覆膜栽培在保產甚至增產的前提下,能夠顯著降低稻田CH4和N2O排放總量的54%[16]。
盡管現代更新的農藝措施和不斷發展的低碳稻作技術,能穩定糧食產量并減少環境足跡,但是我國作為歷史上最早探索和實踐稻田種養結合的國家,經過千余年發展已經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農耕文化,這種以稻為主,以養促稻的共生模式將糧食安全、生態環境和文化傳統緊密關聯,亦是我國水稻產業實現低碳生態,綠色可持續發展的方案。表1總結了我國稻田種養結合模式的多重功能、面臨的機遇以及今后發展的方向,并在下文進行了詳細闡釋。

表1 稻田種養結合模式的功能、發展機遇及展望
1 稻田種養結合模式多重功能的研究進展
1.1 稻田種養結合模式的糧食安全功能
糧食安全一直以來都是全球面臨的重大問題,而近年來極端天氣的頻發直接導致糧食減產,威脅到糧食生產系統,世界農業開始重新審視糧食安全、膳食營養以及環境可持續的發展目標。
過去集約化的稻田單作系統極大地增加了全球糧食供應,但無意中也對自然環境和農業生態系統產生了負面影響,糧食生產需要更可持續的方法。稻田種養是一種運用生物共生原理,將水稻種植與動物養殖相結合的生態農業技術。目前我國稻田種養的總面積已突破233萬hm2,占水稻種植總面積的7%以上[17]。相比單一的水稻種植,稻田養魚、蝦、蟹、鰍、鴨等模式,允許農民在有限的土地和水資源利用上實現一田雙收,而合理地設置稻田養殖密度甚至可以達到水稻穩產、增產的效果,即當養殖產量低于理論閾值時,水稻生長并不會因為空間擠占而減產[18-19]。Zhang等以稻鱉系統為例,通過6年的田間調查和2年的試驗發現,即使不施用化肥和農藥,稻鱉模式的水稻產量也不會低于單作模式,稻田種養并未降低水稻產量,甚至還增加了水稻產量[20]。Hu等以稻蟹為研究對象,通過田間調查和實驗表明,盡管稻蟹擠占了10%的稻田活動空間,但水稻產量并未受到影響,相反略有增加[21]。鄭華斌等認為稻田飼養動物促成影響水稻產量的直接因素(水稻穗長、有效穗數、總粒數、實粒數等)發生變化,使得產量提高[22]。王晨等對稻魚、稻鱉、稻蝦、稻蟹和稻鰍5種種養類型的153個規模農場的調查表明,相比水稻單作,稻漁種養在產出一定數量水產品的同時,表現出穩產或增產效應[23]。Jin等采用糧食當量法和耕地當量法對江蘇省稻田種養的試驗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相比常規單一稻作,稻魚、稻蝦、稻鴨模式單位面積的水稻產量更高[24]。
事實證明,稻田中引入水產或水禽并未威脅到水稻的產量,相反科學合理的種養結合,能促進水稻產量的增加,穩定糧食生產。
1.2 稻田種養結合模式的經濟社會保障功能
過去,現代農業技術及外源性農用生產資料的應用將水稻種植引向集約化,額外的化肥和農藥購買成本阻礙了農戶的增收。稻田種養結合作為一種節肥、節藥和一田雙收的農業管理實踐模式,在提高農戶經濟收入方面具有較大潛力。丁偉華通過分析稻魚、稻蝦、稻鱉、稻蟹、稻鰍的經濟投入和產出發現,相比水稻單作系統,稻田水產養殖的化肥、農藥投入成本顯著降低了22%~31%[25]。雖然稻漁共生系統增加了飼養動物的投入成本,但從產投比來看,產投比一般為1.30∶1到2.97∶1[26],其經濟產出價值顯著高于常規水稻單作。此外,稻田種養系統同時生產出的綠色有機大米和水產品,能增加商品附加值。Wang等通過調查發現,相比常規大米,國內消費者購買稻田種養產出的大米溢價約是41%,高收入及有孩子的家庭更愿意為“生態”大米支付費用[27]。Yi也認為稻田共育產出的大米能夠被消費者所接受,其價格溢價高于有機稻和常規稻[28]。Karim等還將稻田生態種養模式強調為實現收入多樣化的一種手段,其生產的靈活性可用于改善農村社區生計和減少貧困發生[29]。
1.3 稻田種養結合模式的生態環境保護功能
從低碳高效,可持續的角度來看,稻田種養模式利用水稻與水產(禽)間的協同作用,耦合了環境與生產之間的關系,被認為是減少農業環境負面影響的重要途徑之一。
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稻田種養混合系統的能量輸入較低且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大,產出能量更是大于傳統單一稻作。Liu等認為稻田養魚、養鱉的化學品投入依賴更小,資源配置更合理,是一種高能效、可持續的農業生產系統[30]。Li等運用能值分析法,對水稻單作、稻田養魚、稻田養鴨三種不同耕作模式進行可持續評價,結果表明稻魚、稻鴨系統的能值轉化率分別比單作系統高65.5%和49.9%[31]。稻田養殖表現出較低的環境負荷和較高的資源可持續利用率。
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水稻單一種植是溫室氣體CH4和N2O的重要排放源,而稻田生態種養是固碳減排的重要措施。王強盛認為稻田種養結合模式對減緩農業潛在增溫趨勢(GWP)具有顯著作用[32]。Sheng等通過水稻單作與稻鴨共作的田間對比試驗,發現稻鴨種養系統的增溫趨勢(GWP)和溫室氣體排放強度(GHGI)分別顯著降低了28%和30.2%[33]。許國春等認為將鴨引入稻田,促進了水稻植株的固碳能力,使稻田生態系統的碳氮循環更穩定可控,整體表現為碳“匯”[34]。Muhammad以稻蟹系統為研究對象,結果表明稻蟹共作也具有減少GHG排放和緩解GWP的能力[35]。同樣,崔文超等以全球首批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青田稻魚為例,運用生命周期評價法核算其碳足跡,發現相比當地單作系統,稻魚共生系統排放的溫室氣體更少,環境影響更小,生態效益更高[36]。基于現有文獻說明,稻田種養結合是一種高效、低碳、生態的可持續農業模式。
2 發展稻田種養結合模式面臨的機遇
2.1 聯合國各組織呼吁保護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IAHS)項目是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在全球環境基金(GEF)的支持下,會同包括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等,于2002年合作發起的全球性重大項目[37]。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概念和動態保護理念已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成為今后世界各國保護農業文化和自然遺產的重要手段。目前,自項目發起已經過去了20年,在此期間,東亞等國積極參與其中,中國作為有著數千年傳統農耕文化和長期農業實踐的國家,是最早響應并參與GIAHS項目的成員之一。
聯合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倡議,最初主要關注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農作情況,而隨著GIAHS項目參與者的不斷增加,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農業文化遺產的確定項已占有68%以上,到2020年年底,我國已擁有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15項,居世界之首,其中傳統稻—魚種養和稻—魚—鴨共生模式分別在2005年和2011年被列入全球農業文化遺產名錄。“稻+水產”“稻+水禽”的傳統種養模式體現了原始生產與生態循環的邏輯,創造了農業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生態經濟系統,是生態農業、循環農業和低碳農業的典型代表,為我國現代低碳生態農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2.2 世界范圍內廣泛采用稻田種養結合模式
稻田共作模式并不是中國獨有,在印度、孟加拉國、埃及、印度尼西亞、泰國、越南和菲律賓等其他國家均有報道。幾十年來,稻田種養模式在保證糧食生產、減少環境負載和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越來越受到各國農業發展的關注。日本和韓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中葉相繼意識到稻田共作制度的重要性,非洲也在看到稻田種養結合模式良好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后,開始引入并實踐。盡管在世界范圍內,稻田種養結合模式已被廣泛認同并采用,但其中最著名和最成功的可持續實踐仍在中國。
隨著漁業資源利用與生態保護的矛盾日益突出,2019年《國務院關于促進鄉村產業振興的指導意見》提出,要“推進規模種植與林牧漁融合,發展稻漁共生、林下種養等”。我國農業農村部也已經意識到稻畜共育的重要性,開始大力推廣“稻田養魚(蝦、蟹)”“稻鴨共生”等種養模式,以實現農業資源的最大化利用,保證糧食和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目前,我國已形成低碳生態、循環可持續的稻田種養總體發展思路。
3 我國稻田種養結合模式的發展展望
3.1 積極推廣和擴大稻田種養結合模式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為我國發展稻田種養農業提供了絕佳的機會,雖然稻漁(禽)種養具有不與糧爭、一田雙收、生態循環等諸多優勢[38],但農田操作和管理技術的復雜性,使其并沒有被大規模地廣泛使用。同時,由于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勞動力大量從農業轉移到第二、三產業,許多農村家庭選擇了易于管理且收獲簡單的蔬菜種植或水稻單一種植,而不是稻田種養結合模式。而高經濟利潤驅動下的集約化池塘養魚,更是威脅到山區的許多傳統稻田共作系統。因此,在農村地區積極推廣稻田種養并擴大規模對我國堅持大食物安全觀,實現農業“三生”(生產、生活、生態)共贏具有重要意義,但推廣和擴張必須控制化肥、農藥增施,稻米、水產、水禽價格下降的潛在風險和注意農民重漁(牧)輕稻米的危機。
3.2 重視我國稻田種養文化遺產保護
中國稻作文化源遠流長,在漫長的農業發展過程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農耕文化使得稻田種養在我國東南部省份和西南山區盛行。這種巧妙的技術組合和稻田管理做法,幫助了在邊緣和極端條件下農業生態系統的恢復。稻作文化遺產是中華農業文明傳承的基礎,在稻田種養結合模式被各國高度關注和廣泛采用的今天,重視我國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制度建設和文化傳承普及,對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增加遺產地農民收入、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和傳播中華文明具有重要作用。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起步較晚,未來我國在世界范圍內,應繼續加強與FAO等國際組織的合作,依靠GIAHS項目搭建良好的國際文化遺產保護交流平臺,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在國內,應積極建立農業文化遺產管理和保護機制,加快建設一批懂技術、善管理、愛文化的稻田共生專業研究隊伍,重視稻作文化的宣傳和教育。
3.3 開發稻田種養的生態旅游潛力
作為城市化、工業化的對立面,農業生態旅游無論是娛樂還是體驗,都能為游客帶來精神和心理上的放松。稻田種養作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既有自然屬性又有文化屬性,是人類長期勞動與自然演化的共同結果,是中國數千年農耕文化不斷傳承和創新的事實,在生態、文化和美學方面具有獨特的價值。當前,旅游開發作為實現對農業文化遺產動態保護的有效途徑,已得到普遍認可。農業文化遺產是特殊的旅游資源,重點開發稻田共作文化遺產的生態旅游潛力是吸引游客來到農村,了解農耕,學習農史的核心內生要求。以文化為導向,以教育、休閑為目的,利用和開發稻田種養的生態旅游潛力,不僅能為人們提供了解農業和學習農業文化的機會,而且能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但由于農業文化遺產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對其進行旅游價值的開發時應正確處理好長遠利益與當前利益、旅游發展與遺產保護之間的關系[39],爭取在為每位游客講好“農業故事”的同時,重視文化遺產的脆弱性。
4 意義
正確認識到傳統稻田種養生態經濟系統的生產、生活和生態功能,有利于保護主要農業文化遺產。同時迎合國家計劃、方針和政策,助力鄉村振興和農業現代化建設實現,為農業生產新模式的創新和開發提供參考,實現農業糧食供給與低碳發展的雙贏。
[1]陳培彬,張精,朱朝枝.印度“綠色革命”經驗對我國發展生態農業的啟示[J].農業經濟,2020(6):11-13.
[2]CHEN X H, MA C C, ZHOU H C,et al.Identifying the main crops and key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crop production in China, 2001-2018[J].Resources,Con-servation&Recycling,2021,172:1-17.
[3]CRIPPA M,SOLAZZO E,GUIZZARDI D,et al.Food syst-ems are responsible for a third of global anthropogenic GHG emissions[J].Nature Food,2021,2(3):198-209.
[4]LIU T Q,HUANG J F,CHAI K B,et al.Effects of N fer-tilizer sources and tillage practices on NH3volatilization, grain yield, and N use efficiency of rice fields in central China[J].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2018,9:385.
[5]馮靖儀.稻田作物生產的碳足跡及化肥減施的溫室氣體減排潛力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20.
[6]楊丹,葉祝弘,肖珣,等.化肥減量配施有機肥對早稻田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18,37(11):2443-2450.
[7]黃璐璐,金海洋,王站付,等.化肥減量配施有機肥對水稻產量及氮肥利用率的影響[J].安徽農業科學,2021,49(1):138-142.
[8]陳松文,劉天奇,曹湊貴,等.水稻生產碳中和現狀及低碳稻作技術策略[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2021,40(3):3-12.
[9]夏仕明,陳潔,蔣玉蘭,等.稻田N2O排放影響因素與減排研究進展[J].中國稻米,2017,23(2):5-9.
[10]WANG H,ZHANG Y,ZHANG Y,et al.Water-saving irri-gation is a 'win-win' management strategy in rice paddies-With both reduce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enhanced water use efficiency[J].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2020,228.
[11]李思宇,陳云,李婷婷,等.水分養分管理對稻田溫室氣體排放影響的研究進展[J].揚州大學學報(農業與生命科學版),2019,40(6):16-23.
[12]LI J L,LI Y E,WAN Y F,et al.Combination of modified nitrogen fertilizers and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can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increase rice yield[J].Geoderma,2018,315:1-10.
[13]張藝.我國稻作技術演變對水稻單產和稻田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研究[D].南京:南京農業大學,2015.
[14]孫會峰,周勝,陳桂發,等.水稻品種對稻田CH4和N2O排放的影響[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15,34(8):1595-1602.
[15]張衛建,張藝,鄧艾興,等.我國水稻品種更新與稻作技術改進對碳排放的綜合影響及趨勢分析[J].中國稻米,2021,27(4):53-57.
[16]YAO Z S,ZHENG X H,LIU C Y,et al.Improving rice production sustainability by reducing water demand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ith biodegradable films[J].Scientific Reports,2017,7:39855.
[17]車陽,程爽,田晉鈺,等.不同稻田綜合種養模式下水稻產量形成特點及其稻米品質和經濟效益差異[J].作物學報,2021,47(10):1953-1965.
[18]HU L L,ZHANG J,REN W Z,et al.Can the co-cultivation of rice and fish help sustain rice production?[J].Scientific Reports,2016,6:28728.
[19]唐建軍,李巍,呂修濤,等.中國稻漁綜合種養產業的發展現狀與若干思考[J].中國稻米,2020,26(5):1-10.
[20]ZHANG J,HU L L,REN W Z,et al.Rice-soft shell turtle coculture effects on yield and its environment[J].Agriculture,Ecosystems & Environment,2016,224:116-122.
[21]HU L L,GUO L,ZHAO L F,et al.Productivity and the complementary use of nitrogen in the coupled rice-crab system[J].Agricultural Systems,2020,178:102742.
[22]鄭華斌,賀慧,姚林,等.稻田飼養動物的生態經濟效應及其應用前景[J].濕地科學,2015,13(4):510-517.
[23]王晨,胡亮亮,唐建軍,等.稻魚種養型農場的特征與效應分析[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8,39(5):875-882.
[24]JIN T,GE C D,GAO H,et al.Evaluation and screening of co-culture farming models in rice field based on food productivity[J].Sustainability,2020,12(6):2173.
[25]丁偉華.中國稻田水產養殖的潛力和經濟效益分析[D].杭州:浙江大學,2014.
[26]胡亮亮,趙璐峰,唐建軍,等.稻魚共生系統的推廣潛力分析:以中國南方10省為例[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中英文),2019,27(7):981-993.
[27]WANG E P,GAO Z F.Chinese consumer quality perce-ption and preference of traditional sustainable rice produced by the integrated rice–fish system[J].Sustainability,2017,9(12):2282.
[28]YI S C.Contingent valuation of sustainable integrated agriculture–aquaculture products:The case of rice–fish farming systems in South Korea[J].Agronomy,2019,9(10):601.
[29]KARIM M,AHMED M,TALUKDER R K,et al.Dynamic agribusiness-focused aquaculture for 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Bangladesh[J].The WorldFish Center,2006:36884.
[30]LIU G,HUANG H,ZHOU J.Energy analysis and economic assessment of a rice-turtle-fish co-culture system[J].Agro-ecology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2019,43(3):299-309.
[31]LI J,LAI X,LIU H,et al.Emergy evaluation of three rice wetland farming systems in the Taihu Lake catchment of China[J].Wetlands,2017,38(6):1121–1132.
[32]王強盛.稻田種養結合循環農業溫室氣體排放的調控與機制[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18,26(5):633-642.
[33]SHENG F,CAO C G,LI C F.Integrated rice-duck farming decreases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and increases net ecos-ystem economic budget in central China[J].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2018,25(23):22744–22753.
[34]許國春,劉欣,王強盛,等.稻鴨種養生態系統的碳氮效應及其循環特征[J].江蘇農業科學,2015,43(10):393-396.
[35]MUHAMMAD A B.稻蟹共生系統對生產力,土壤肥力和環境的影響研究[D].北京:中國農業科學院,2019.
[36]崔文超,焦雯珺,閔慶文,等.基于碳足跡的傳統農業系統環境影響評價:以青田稻魚共生系統為例[J].生態學報,2020,40(13):4362-4370.
[37]閔慶文,史媛媛,何露,等.傳承歷史守護未來:記聯合國糧農組織—全球環境基金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2009—2013)[J].世界農業,2014(6):215-218,221.
[38]王斌,孫業紅,焦雯珺.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生態效益評估:以青田稻魚共生系統為例(英文)[J].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2021,12(4):489-497.
[39]閔慶文,孫業紅,成升魁,等.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旅游資源特征與開發[J].經濟地理,2007(5):856-859.
S511
A
2095-1205(2022)10-18-04
貴州省省級科技計劃項目“構建碳足跡大數據推動貴州特色農業全產業鏈綠色發展研究”[黔科合基礎(2020)1Z057];2021年新農科建設項目“‘校企+’發展‘特綠’功能農業及合作育人研究與示范”(黔財教【2021】48號)
陳明杰(2001- ),男,漢族,貴州黔南人,本科,研究方向為農村發展。
梁龍(1973- ),男,漢族,湖南郴州人,博士研究生,教授,研究方向為生態農業與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