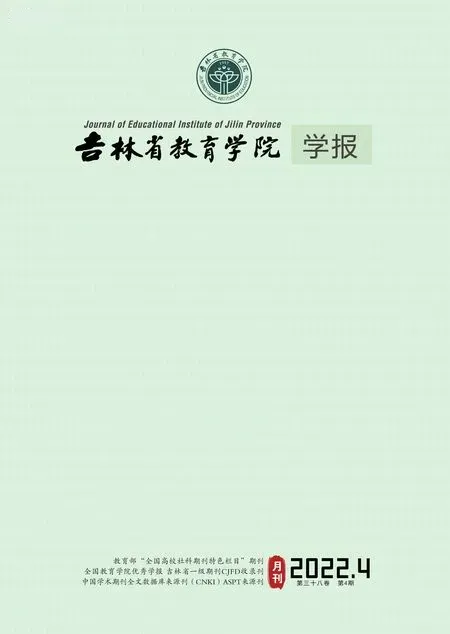英語教師的課堂省略式疑問功能的知識論闡釋
彭 卓,許映嫻
在英語課堂互動中,教師的提問話語頻繁出現。據統計,接近70%的課堂話語都是師生的問答話語。[1]可見,提問是英語課堂教學的重要方式,是師生課堂互動中凸顯的語言現象。[2]目前,一些學者探究了教師課堂提問的策略、話語特點以及功能,如宋曉英[3]、董明[4]、華麗、凌永剛[5]等人的研究。但是較少學者對教師的課堂省略式疑問展開研究,依據會話分析的關聯規則,某一話輪的出現會對其后續話輪產生一種關聯性限制,不是任何話語都能作為前面話輪的相鄰對后件(the second pair part),前面話輪構成后續話輪的語境,而這些后續話輪繼而又構成其后話輪的語境,會話就是按照這樣的模式發展下去的。[6]
由此可知,教師的課堂省略式疑問出現的語境肯定與完整式疑問所在的語境不同,因而前者在互動語境中的功能也必定有特殊之處。同時,問答必然涉及互動雙方的知識流通問題。[7]因此,知識論(Epistemics)能為問答互動做出較為貼切的解釋。鑒于此,本文將從知識論視角分析英語教師的課堂省略式疑問的結構類型與互動功能,有助于洞悉此類疑問功能的知識性本質,為教師有效使用此類課堂提問提供啟示。
一、知識論
知識論由西方會話分析界的領軍人物Heritage提出,主要探究互動者話語所體現的誰擁有什么知識的問題。[8]
知識論包含兩個維度:知識地位(epistemic status)和知識站位(epistemic stance)。前者指互動者心理預設互動雙方在某一知識領域的相對地位,后者指互動者通過話語表達的自身在某一知識領域的即時性相對地位。[9]兩者可存在不一致性,因為知識地位高者可通過話語設計故意降低自己的知識站位。互動雙方在某一話題上的知識站位的高低差異會形成知識的不對稱性(knowledge asymmetry),后者被稱作知識梯度(epistemic gradient)。[10]知識梯度往往是驅動會話互動發展的內在動力。知識就是從知識站位高者流向知識站位低者,直至雙方在某一話題中的知識站位趨于對等,會話互動才會終結。[11]
由于知識站位的判定只以話語為線索,不受先設的觀念和心理影響,因而在問答互動中,提問者往往體現為較低的知識站位,而回答者則體現為較高的知識站位,知識由回答者流向提問者。當前,知識論是西方會話分析界的熱點理論,主要關注(不)禮貌、同意、疑問及指令等語言現象。[12]但目前,較少學者借助知識論來分析英語教師的課堂省略式疑問的功能。在課堂問答中,教師通過提問來降低自身的知識站位,從而讓學生處于相對較高的知識站位,繼而在師生間形成知識梯度,最終致使學生有輸出問題答案的壓力。當學生成功回應了教師的提問,師生間的知識梯度被消解,此微觀話題的問答互動也就趨于終結。
二、英語課堂提問研究綜述
關于英語教師課堂提問的研究大致可分為3種研究取向:教師提問的策略、話語特點以及功能。
在教師提問策略的研究方面,一些學者介紹了高效的提問策略,并列舉了失當的提問方式。教師可針對實施教學的不同環節采取不同的提問策略,如導入式提問、新知呈現式提問、語言操練式提問、拓展運用式提問等。[13]同時,教師要善于變換提問句式、明確提問對象、以提問激發學生思維,避免長期采用一種提問模式、過于泛化提問對象和口頭禪式的提問。[14]這類研究能為教師的課堂提問提供指引,但是它們更多是一種理性的構想,未深入到真實課堂中的提問實踐和效能。
在教師提問的話語特點研究方面,一些研究者基于真實微觀的課堂問答互動,分析教師提問所具有的特點。董明揭示了教師課堂提問會體現鮮明的語部性,教師會借助拓展性問題來引導學生輸出答案,同時,教師的提問還具有即時性特點。[15]同時,課堂提問存在4種認知層級發展特征:平級發展、向下發展、向上發展和波形發展。[16]這些研究都探討了真實微觀的課堂提問話語特點,但是提問話語特點也許是由提問的功能所決定的,因而提問功能更應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在教師提問的功能研究方面,Michalovich和Netz分析了在真實的課堂互動中,教師疑問話語在會話片段的不同位置所起的助學和抑學功能。[17]同時,教師提問還具有請求學生重復話語、確認學生理解知識以及獲取學生觀點等功能。[18]這些研究聚焦教師課堂提問的功能,對課堂教學有切實的指導意義。但是這類研究一般不將疑問形式和疑問功能關聯,而不同形式的疑問往往會具有不同的功能,如一般疑問句比特殊疑問句對回應有更大的限制性。
綜上所述,首先,關于教師提問策略的研究往往得出一種理性構想的結果,例證是一種靜態的孤立句子,常常未提供課堂會話中微觀動態的互動理據。其次,關于教師提問話語的特點研究關注了課堂互動的微觀話語,但對于話語特點背后的動因關注不夠,話語功能也許是話語特點外顯的內驅力。第三,關于教師提問功能的研究能深入揭示提問話語的成因,但這類研究一般忽略疑問形式和疑問功能的關聯性,以致功能研究可能缺乏全面性和系統性。最后,問答必然涉及互動雙方的知識流通問題[19],因而知識論能為問答互動做出較為貼切和深入的解釋,同時,知識論在西方會話分析界方興未艾[20],它能為課堂提問提供新的理論視角和解釋。鑒于以上各種原因,本文將聚焦英語教師的課堂省略式疑問的結構類型與互動功能,并從知識論視角對這些功能做深入的闡釋。
三、研究設計
本文從知識論視角分析英語教師的課堂省略式疑問的功能,具體探究以下問題:英語教師的課堂省略式疑問有什么結構類型?以上課堂省略式疑問具有什么功能?從知識論視角看,為什么課堂省略式疑問會具有以上功能?
研究者從優酷網隨機下載4名中國大學英語教師的教學視頻,分別為“外教社杯”全國高校外語教學大賽一等獎和三等獎的教學視頻以及重點本科院校和高職高專的大學英語精品課程錄像。選取這些視頻做研究,旨在包含不同性別、不同學校層次的教師和相異教學環境的師生互動。這些視頻包含自然發生的課堂會話,它們未經刪節,滿足了會話分析的語料選取標準。筆者依據Jefferson的轉寫規則[21],將總時長約128分鐘的教學視頻錄音轉寫為文本,隨后依據話題的一致性來截取教師的省略式疑問會話序列,共得此類序列122個。筆者借助會話分析方法,分析英語教師的課堂省略式疑問的結構類型與互動功能,并借助知識論對這些功能進行闡釋。
四、語料分析
(一)省略式疑問的結構類型
研究者對所收集的教師省略式疑問話語進行整理和歸類,依據原型范疇化理論[22]的觀點,從例子間的家族相似性來劃分類別范疇,總結出4種結構類型,具體類型如下。
第1類為陳述句式縮略。英語教師可使用省略助動詞、賓語或表語的陳述句縮略形式來提問,例如“Other people go somewhere?”“It means?”“That song is from?”等。第2類為疑問句式縮略。英語教師可使用省略謂語或賓語的疑問句來提問,有時疑問句被縮略為一個疑問詞,其他成分都被省略,例如“What kind of performance?”“Do you agree?”“Why?”“Who?”等。第3類為連接詞式疑問。英語教師延續先前的提問以讓學生提供更多的答案,前者將相關疑問句省略,只使用連接詞來提問,例如“And?”“Then?”“So?”等。第4類為獨立實詞結構式疑問。英語教師可使用單一的實詞(詞組)來提問,例如“Right?”“The fourth one?”“Only happy?”“Sung by-?”“How to pronounce it?”等。
(二)省略式疑問的互動功能
在知識論中,知識是較為寬泛的概念,涵蓋信息、經驗、感受、想法、希望和期待等,可被分為元認知知識、概念性知識、事實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4類。[23]省略式疑問的互動功能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引導學生提供知識
例a(教師針對課文內容提問)
01 T:How did the author describe the architecture of this city?
02(2.0)
03→T:She said that the city i:s?
04 S:Well-planned and practical in design.
05 T:Er hm.
教師在01行針對課文作者對城市建筑的描繪內容提問,體現教師主動降低自身在此話題上的知識站位,讓師生間形成知識梯度。但02行出現2秒鐘的沉默,說明學生未接管話語權,未能提供問題所涉及的知識。教師在03行借助省略式疑問再次提問,此疑問重述了課文句子的某些部分,因而降低了回答難度,換言之,教師通過此省略式疑問隱性地為學生提供了回應01行疑問的部分知識,降低了教師在話語層面展現的“無知”程度,提高了教師的知識站位,縮小了師生間的知識差異,因而減少了師生間的知識梯度,使學生較易完成回答任務,最終學生在04行成功地輸出知識。學生實現了知識由自身流向教師。可見,03行的省略式疑問具有引導學生提供知識的功能。
2.誘導學生補充知識
例b(教師針對課文內容提問)
01 T:How does the author describe the people there?(.)She thinks that there:-
02(1.0)
03 T:Okay people there were openin:g=
04 S:=Friendly.=
05→T:=Friendly and?
06(1.0)
07→T:And?
08 S:They are eager to talk about-=
09 T:=Yeah okay.(.)They are eager to talk about the(.)life and no
10 matter how the economy is.(.)Right.
教師在01行針對課文作者對人們的描述內容提問,教師降低了自身在此話題上的知識站位,師生間形成知識梯度。但是02行出現1秒鐘的沉默,說明學生未接管話語權,未能提供問題所涉及的知識。教師在03行準備提供相關知識,但話語未說完,就被學生搶占了話語權。學生在04行提供了問題所涉及的知識,從而減少了師生間在疑問話題上的知識梯度。但教師認為此回應不夠充分,因而在05行使用省略式的疑問誘導學生補充問題的相關知識,此疑問增加了師生間的知識梯度,給學生輸出性壓力。但06行出現1秒的沉默,表明學生未接管話語權。因此,教師在07行再次使用省略式的疑問誘導學生補充相關知識。學生在08行補充了知識,并在09和10行得到教師的正面評價。可見,在學生提供了部分答案的情況下,05和07行的省略式疑問能再次降低教師的知識站位,增加師生間的知識梯度,給學生施加輸出壓力,驅使學生補充相關知識。綜上所述,05和07行的省略式疑問具有誘導學生補充知識的功能。
3.驅使學生延展知識
例c(教師針對所播放的歌曲提問)
01 T:Do you know the name of the song?
02 S: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03→T:Very good.(.)That’s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Sung by-?
04(1.0)
05→T:Who sang the song?(.)Of course not me.(.)Who?
06 S:Er Elton John.
07 T:Very good.
教師在01行針對課堂播放的歌曲提問,體現教師相對于學生的較低知識站位,師生間產生知識梯度,驅使學生在02行輸出與問題相關的知識。教師在03行給予正面評價“Very good”,并且以重述的方式確認了學生的回應。這說明教師認為學生02行的回應是充分的,師生就歌名方面持有對等的知識,即02行話語實則實現了師生就歌名方面的知識對稱性,兩者在此話題上的知識梯度趨于零。隨后,教師在03行最后一個話輪建構單位(TCU)中,使用省略式疑問欲讓學生提供此首歌曲的演唱者姓名,重塑師生間的知識梯度。但04行出現1秒的沉默,學生未接管話語權。隨后,教師在05行首先使用完整的疑問句做相同議題的提問,然后在05行的最后一個TCU中,再次使用省略式疑問來提問。最終在知識輸出壓力下,學生在06行提供了問題的相關知識,并在07行得到教師的認同,師生間的知識梯度再次被消除。綜上,學生在02行已很好地完成01行疑問所投射的回應任務,教師在03和05行的省略式疑問實則是對01行疑問的關聯拓展,具有延展學生相關知識的功能。
4.尋求學生認同知識
例d(教師請學生談論關于圖片描繪的運動會的感受)
01 T: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sport meeting one?
02 S:Er exciting.
03 T:Exciting?(.)That’s all?
04 S:En en.
05 T:Do you feel inspired?
06 S:Yeah.
07 T:Okay.(.)Do you feel proud?
08 S:Yeah.
09→T:Okay(.)so you have other feeling too(.)right?
10 S:Mm.
從05、07和09行可知,教師在03行的省略式疑問實則欲引導學生對02行的答案做補充,因而03行的省略式疑問的功能實則與例b相似,這里不再贅述。教師在05和07行主動為學生提供關于運動會的感受后,在09行做了總結,并使用省略式疑問“right”來降低自身的知識站位,使師生間形成知識梯度,驅使學生在10行做出認同09行知識總結的回應。可見,09行的省略式疑問具有尋求學生認同知識的功能。
5.邀請第三方加入知識討論
例e(教師詢問學生五一假期的去向)
01 T:So where did you go:?
02 S1:Nanshan Park.
03 T:Oh.You go to Nanshan Park.(.)Yeah one of the plant
04 park in Chongqing.(.)Okay do you like it?
05 S1:Yes.
06 T:Yes.
07 S1:Very much.=
08→T:=Er(.)er he.(.)And other people go somewhere?
09 S2:Ihave been to the city of Luoyang.
10 T:Luoyang.(.)Oh.it is quite a long distance.
教師在01和04行分別向某一學生問了兩個不同的問題,并且均得到此學生的關聯性回應。教師在08行首先使用認同性回應“er he”,接受了此學生在07行的回應。然后,教師采用省略式疑問降低自身的知識站位,并且將會話對象錨定為其他學生,構建師生間的知識梯度,對其他學生的知識輸出施壓,最終使另一名學生在09行回應了問題。可見,08行的省略式疑問具有邀請第三方加入知識討論的功能。
(三)功能的知識論闡釋
由上節可知,英語教師的課堂省略式疑問具有5種互動功能:引導學生提供知識、誘導學生補充知識、驅使學生延展知識、尋求學生認同知識以及邀請第三方加入知識討論。知識梯度往往是驅動會話互動發展的內在動力。知識就是從知識站位高者流向知識站位低者,直至雙方在某一話題中的知識站位趨于對等,會話互動才會終結。[24]以上省略式疑問均出現在教師首次提問之后。教師在首次提問時,實則已降低了自身的知識站位,構建了師生間的知識梯度,讓學生成為知識輸出方,對學生的知識輸出施壓。但是問答互動過程充滿偶然性,學生可能回答不了問題、只提供問題的部分答案,或者教師想要學生繼續深入討論與首次提問相關的另一問題或欲邀請更多學生加入到問題的討論中。那么教師的省略式疑問就是解決以上互動困境的最直接、簡單、快捷和高效的話語手段。
當遇到這些互動困境時,教師的省略式疑問能對師生間的知識梯度做調節,以使互動向前推進,最終實現教師的交際目的。
例如在例a中,教師的首次提問構建了師生間的知識梯度,但學生無法輸出知識,因此,教師通過省略式疑問隱性為學生提供了回應疑問的部分知識,在話語層面提高了自身的知識站位,減少了師生間的知識梯度,最終使學生成功輸出與問題相關的知識。
在例b、c和d中,師生成功完成了至少1輪的問答互動后,兩者間的知識梯度本應減少,但教師通過省略式疑問增加了師生間的知識梯度,驅使學生再次輸出相關知識。
在例e中,師生在完成2輪問答互動后,教師使用帶受眾指向性的省略式疑問,構建教師與特定受眾之間的知識梯度,從而實現邀請第三方加入知識討論的功能。綜上所述,教師的省略式疑問能對師生間的知識梯度起調節作用,這是實現此類疑問5種互動功能的原因。
五、討論
本文探討了英語教師的課堂省略式疑問句,揭示此類疑問句存在4種結構類型和5種互動功能,它們對師生間知識梯度的調節作用是以上互動功能的內在成因。在知識論中,知識地位指互動者心理預設互動雙方在某一知識領域的相對地位,知識站位指互動者通過話語表達的自身在某一知識領域的即時性相對地位。[25]前者與互動者的經歷、文化和機構性預設相關,后者與互動者的即時性語言表達相關。[26]在通常情況下,人們會預設性地認為教師擁有豐富的知識,因而他們具有比學生高的知識地位。但知識站位的情況則不同,它是通過話語表達來體現的,因而知識地位高者可將自己描述或展現為知識地位低者,反之亦然。知識地位與知識站位可以存在不一致性。
教師的課堂省略式疑問在話語層面展現的是較低的知識站位,這是因為疑問話語讓教師成為知識的接收方,而學生則是知識的輸出方,知識是由學生流向教師的。教師在獲得學生的回應后,在話語層面體現為接收或接受學生輸出的知識,如教師的反饋語(er hm、er he、yes、yeah、okay、oh)、評價話語、重述學生的答案以表確認等。這些話語展現了教師獲取了學生提供的知識,因而提升了自身的知識站位,消解了教師先前發出的疑問句所構建的教師低而學生高的知識梯度,平衡了師生間的知識站位,因而問答互動片段也就趨于終結。
省略性疑問比完整的疑問形式更為靈活和更有針對性,這是因為前者被省略的部分往往就是教師想讓學生說出的答案,學生不需用復雜的句法來表達問題的答案,只需輸出最核心的信息來回應此類疑問。
一些省略式的疑問句直接就是課文句子的約略結構,隱性地告知學生答案的出處,因此它們能降低學生尋找答案和回答問題的難度。換言之,教師利用省略式疑問將自己需尋求的知識量縮減,降低了話語層面展現的“無知”程度,提高了自身的知識站位,因而省略式疑問能減少師生間的知識梯度,如例a所示。
一些省略式疑問句出現在師生成功實施了1輪或多輪問答互動之后,這些問句被教師用于再次降低自身的知識站位,以建構教師低而學生高的知識梯度,從而對學生的知識輸出再次施壓,借此實現問答互動的延續,如例b、c和d所示。
還有一些省略式疑問句不僅降低了教師的知識站位,而且能構建教師與特定學生群體間的知識梯度,教師能借此順勢將上一問答議題指派給特定受眾,從而實現在特定學生群體中延續問答互動,如例e。
綜上所述,省略式疑問能調節師生間知識梯度,而知識梯度的增加、減少或質變(構建知識梯度的群體變換)會驅使問答互動產生各種發展軌跡,從而體現省略式疑問的不同功能。
六、結語
本文探究了英語教師的課堂省略式疑問結構類型,并從知識論視角分析這些疑問的互動功能及其成因,通過揭示教師省略式疑問的結構和功能,洞悉此類疑問功能的知識性本質,為教師有效使用此類疑問提供啟示。同時,本文也表明研究者在做會話分析時,要避免先驗預設對會話分析過程的影響,盡可能讓所有分析都聚焦于話語證據本身。隨著語料收集過程的不斷發展,也許教師省略式疑問的功能類型會有所增加,它們需要得到進一步的闡釋,省略式疑問的結構類型與功能的使用頻率也有待進一步分析,這些問題將在后續研究中得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