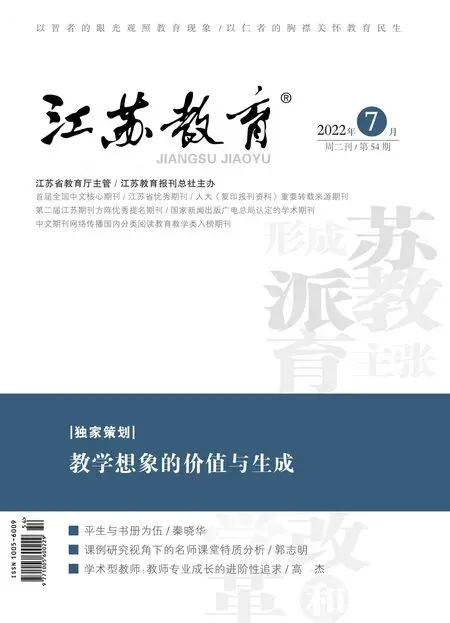教學想象的限制與突破
馮 毅 張樂群
一、教學想象是在想象什么
1.對“學生發展形象”的預想
以色列教育專家艾互德·沙克拉先生在報告《怎么著眼未來世界設計教育方案》中提出一個問題:舊時代出生的教師如何才能為將在新時代工作的學生做好準備?特別是他們將來的職業現在可能并不存在。在這一問題的背后,我們看到教育者對受教育者未來形象的預想對今天的教育所起到的導向性作用。
教育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擔負這一重任的教學就一定要做到“眼中有人”。這里所說的“人”,既是身邊“現實的兒童”,也是想象中“理想的兒童”;既是這一個孩子現在的樣子,也是他(她)未來發展的姿態。從某種程度上說,教育者正是按照心中的學生形象來開展教育教學活動的。教學想象的一個重要價值,就在于將學生的培養目標以發展形象的方式勾畫出來。對“人”的想象使得教學有了強烈的對象感,學生的發展形象越鮮活,具體表現越清晰,教學的指向就越明確。
2.對“學科教學何為”的創想
學科教學究竟何為?當然要傳授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但是要做的遠遠不止于此。2022年頒發的《義務教育課程方案(2022 年版)》強化了課程育人導向,各課程標準基于義務教育培養目標,將黨的教育方針細化為本課程應著力培養的核心素養,體現正確價值觀念、必備品格和關鍵能力的培養要求。
如何發揮學科教學的育人價值?加德納的觀點極具啟發性。他倡導“注重品行的學科教育”,并指出“學科教育是傳遞真、善、美觀念最有效的渠道”[1]。這樣的傳遞當然不是簡單的說教或直接的灌輸,而是伴隨著學科觀念和思想方法深度學習、理解的涵育過程。“學科的內涵存在于該領域專家人士發展出的特定思考方式。借著這種思考方式,他們可以從特定的而非直覺的角度了解這個世界。如果能夠讓學生通過各種不同的角度觀察這個世界,這就是成功的教育。”[2]
在學科育人的立意上,教學想象引導每一個教師建立一種思考方式,即所任教學科能夠為學生形成正確價值觀念、必備品格和關鍵能力貢獻什么。這樣的構想,將教師的教學導向正確的軌道,向著高遠的理想前進。
3.對“我怎么做、能做成什么”的構想
對教師來說,教學想象并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而是對教學有著實實在在指導意義的主體創造性活動。有研究者從能力角度對“教學想象力”進行界定:“它具體是指教學思維、教學情感、教學方式和教學內容的靈活性,即教師在教學活動展開前應預計到教學活動的效果,在教學活動結束后要辯證地評價教學活動的結果,在教學過程展開時須依據教學情境條件,充分調動各種感官要素、情緒要素以及智能要素,在多種教學思維方式和教學情感方式之間自由切換,以便高效率地完成教學實踐活動的綜合性的心理能力。”[3]據此可見,在教學的全過程,教學想象力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有著豐富創造意蘊的教學想象,通過創造新的教學意向或觀念,對教學發揮導向作用。不僅如此,教師通過教學想象對自己如何開展教學進行構想,包括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幫助學生達成學習目標,如何促進每一個學生的學習真正發生,并且對自己的做法是否能達成預期效果、在多大程度上達成效果作出預判,預估學生品質的發展和個性的形成,確保教學能夠很好地施行。
二、哪些因素可能會限制教學想象
很多教師在聆聽大師級教師的公開課時,會發出這樣的慨嘆:“簡直超出了想象。”那種看似不可企及的高度與自身現實之間的落差引發我們反思——是什么限制了一個教師的教學想象呢?
我們認為,教學想象是一個具有濃厚個人色彩的概念,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教師對教學抱有的態度,對教學持有的理解,對教學擁有的體驗等。這些方面的缺失、異化,在一定程度上會限制教學想象如預期般打開,需要我們加以關注。
1.教師對教學抱有的態度
教師對教育越是抱有積極的態度,主導的意識就越發凸顯,內心的力量就越發彰顯。理想的教師是思想的主人、決策的主人、實踐的主人。擁有主人意識是前提條件。這里的“主人意識”,是指教師個人對自己、對自己所經歷生活意義的覺察,包括個人的身份、角色、特點、權利、義務等,在此基礎上決定自己的言行舉止,選擇朝什么方向去做和怎么做。覺察是將外在的要求與內在的自我建立聯系的過程。如果一個教師覺察到教學是自己精神生活的重要構成,他就會在強烈的內在動機驅使下主動去做這件事;反之,就只會被動地應付。教師對教學是否抱有主人翁的態度決定了他會做出何種選擇。一個視教好學生為己任的教師會想方設法創造各種條件助力學生的學習。
2.教師對教學持有的理解
教學是專業性的實踐活動,教師對專業知識的掌握程度決定了其專業實踐的深度和廣度,在一些教學基本問題上所持的不同理解也會影響其在處理問題時做出何種選擇和采取何種方法。一個教師如果總是試圖將教學設計做到“毫無瑕疵”,甚至將師生交流的每一句話都寫在教案中,而認識不到“作為一種理性活動的教學設計存在有限性”[4],那么,他的教學方案就不會保持必要的彈性和開放度;一個教師如果認為試卷中會出現的知識才是有用的、才是值得教的,反之則是無用的、不值得教的,而認識不到一些知識在學生思維發展、素養提升上的潛在價值,那么,他的教學就可能陷入短視和僵化;一個教師如果認為只有知識是可教的,思維是不可教的,認識不到“為思維而教”是一種重要的教學主張,那么,他就不會有意識地去開發各種激發學生思維的教學策略,也就會錯失許多在課堂上守候精彩觀念誕生的悸動和喜悅;一個教師如果認為教學必須強調標準答案、追求立竿見影,而不能包容暫時的混亂和不確定,他就一定不能容忍某些學生的暫時掉隊,不會給學生充分表達自己想法的機會……由此可見,想象的窗常常是被教師自己關上的,而能再次推開這扇窗的,只有教師自己。
3.教師對教學擁有的體驗
站在課堂中的教師擁有豐富的教學體驗,這些體驗不僅會影響教學活動的進程,還會影響其對教學活動的自我意識。試想,一個以“灌輸”為主要教學方式且屢試不爽的教師,他的教學想象恐怕也就只限于如何才能更快、更好地“灌輸”,而不大可能去主動調整自己認識教學的心智模式。可能影響乃至限制教師教學想象的體驗包括:教師對教學過程的體察,如是否完成了教學目標,教學方法是否適切,教學策略是否有效等;教師在課堂教學中的情緒體驗,如成功的體驗、失敗的體驗、焦慮的體驗、沮喪的體驗等;課堂上教師對學生學習狀態的體驗,譬如學生的課堂反應,學生回答問題的情況,整體上達成目標的情況等。這些體驗都會影響教師對教學活動的自我監控、調節和管理,致使教師修正或更換教學方案,對教學進程、教學難度和教學方法做出調整。一個缺乏自我效能感的教師,往往會因為一次小小的失敗體驗就喪失了自信,抽身退回到“舒適地帶”而裹足不前。當這樣的現象一再發生,是否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呢?
三、如何才能突破限制并放飛想象
上文分析了可能會對教師的教學想象造成影響乃至限制的三個關鍵因素,這同時也指向了突破限制的三個著力點,分別是主體態度、個體知識和教學勇氣。主體態度解決的是愿不愿意展開教學想象的問題,個體知識解決的是能不能展開教學想象的問題,教學勇氣解決的是敢不敢、能不能持續地展開教學想象的問題。
1.確立主體態度:建構“我”的教學想象
教學想象要求教師對自己、對教學有很好的自我概念。在心理學上,“自我概念”是指一個人對自身存在的體驗。通俗地說,“自我概念”就是指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和感受自己,包括對自己身份的界定(我是誰),對自己能力的認識(我可以做什么),以及對自己的理想或要求(我應該是什么樣子)。一個人自我概念越強,他的自發性和創造性就越強。
良好的自我概念能轉化為積極的主體態度。在哲學上,僅僅具有人的身份未必一定具有主體身份。主體是起能動性的、主動性的和創造性的作用的人。[5]對于教師來說,要以自己的主體性活動使自己成為主體:我是誰?我是教師,但我也是“我”,是“這一個”教師;我的學生是學生,但也是作為其自身的“我”。還原師生雙方共有的“我”這一主格,敞亮豐富的主體性是第一步要做的。教師可以做什么?教師應該堅信有能力為自己的教學打上深深的“我”的烙印,有能力幫助學生在學科學習中刻下“我”的印痕。“我的教學應該是什么樣子?”或許這個問題一時沒有辦法完全想明白,但是凸顯師生雙方的主體性,使得教學中的師生關系重新回到主體間的對話關系上,這是教學想象建構的起點,也是閃爍其間的人性光芒。
2.修煉個體知識:豐富“我”的教學想象
想象建立在已有知識的基礎上。我們對知識的掌握越牢固,領悟得越深刻,想象就越有生成的可能。相反,當我們對某個對象一無所知的時候,就很難對其產生想象。因此,在考量教學想象差異之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不同教師所擁有的知識背景。
教學想象要建立在對學科的精準理解之上。教師應該努力掌握所教學科的學科觀念、核心概念和基礎知識,要有成為學科專家的自信。為此,教師不能僅僅滿足于自己以前所經受的專業訓練,還要有強烈的與時俱進的意識和能力。教學想象要建立在對教育、教學的正確看法之上,對諸如“預設與生成”“有用與無用”“可教與不可教”“確定與不確定”等教學基本問題要有自己準確的研判以及合理的解讀,并將積極的行動落實在課堂上。教學想象要扎根于教師個體知識的土壤中。個體知識是與教師的課堂教學實踐緊密聯系著的實踐性知識,是教師專業發展最有價值的知識成果。作為教師,我們應該擁有怎樣的個體知識呢?我們要將學科教育的現場、教師的教學實踐活動視為教師知識構成的重要來源,即在實踐中修煉個體知識,這是教學想象得以不斷豐富的必經之路。
3.提升教學勇氣:堅守“我”的教學想象
教學想象是需要堅守的,而這一份堅守需要勇氣。教師要相信,對自己的認同和隨之煥發的心靈的力量能夠帶來好的教學。帕爾默認為,好的教師具有聯合能力,他會去編織一個他們自己的世界。教學的勇氣就在于保持心靈的開放,即使力不從心也仍然能夠堅持,那樣,教師、學生和學科才能被編織到學習和生活所需要的共同體結構中。[6]
教學想象是每一個教師都必須堅守的。作為一個有理想、有情懷、有擔當的教師,要不斷提升自我效能感,對自己的教學能力信心滿滿,敢于挑戰高層次的目標,并且對自己能夠最終達到目標深信不疑;要堅信開放的心靈才能真正接近教育教學的真諦所在,篤信只有坦誠的心靈才能得到心靈默契的回應,只有心靈才能成就心靈。這一切,無不需要身為教師的我們擁有巨大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