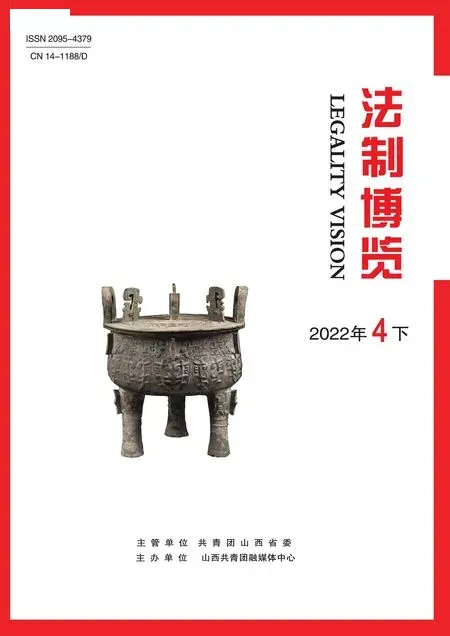房地產企業的待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解除權的法律界定
董學全
山東德衡(煙臺)律師事務所,山東 煙臺 264000
近些年,為了穩定房地產市場,國家加大了對房地產行業的調控力度,使得不少房地產企業陷入發展危機,甚至面臨著破產重整的困境。房地產企業破產重整中常見的問題是未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問題。對于這類合同的處理問題,不僅關系到破產企業重整工作的開展,還影響著購房者的直接權益,甚至還會給社會發展帶來不穩定因素。為了解決房地產企業破產中待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以下簡稱《破產法》)第十八條賦予管理人對未履行完畢合同選擇繼續履行或者解除合同的權利。考慮到待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解除權的特殊性,以及破產解除權的公平性原則、比例性原則,需要對待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解除權分情況理解和分析,來保障合同解除后購房者的基本權益,以及對破產企業財產保增值的協調性,再根據實際情況對相關權益人進行合同解除的受損權益進行救濟。當前,國內房地產破產企業中待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問題是房地產企業破產重整中面臨的重點難點問題。研究該課題對合理解決房地產企業破產重整事務處理操作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破產法》中關于解除權的界定
破產企業進入破產程序,在首次債權人會議正式開始前2~4個月期間,企業需通過維持經營保有一定的現金流,確保職工的穩定。因此破產程序開始時,房地產企業需維持一段周期的工程建設,以確保企業破產重整工作的有序推進。《破產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規定,管理人在首次債權人會議召開前,管理人決定繼續營業或暫停服務[1]。在此期間,若管理人發現繼續經營會加劇對企業的損害,不利于企業財產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可選擇不履行合同。面對房地產企業破產重整,管理人同時面臨著以下多種合同情況:1.進入破產程序時企業與合同相對人中僅有一方存在未履行合同的情況;2.破產企業與合同相對人同時未履行完合同的情況。前者可依據《破產法》關于破產財產控債權的規定,對已履行完畢的合同進行解除,應根據《民法典》合同編關于合同解除的規定進行約束。后者則根據《破產法》的一般規定處理。在處理后者破產企業與合同相對人均未履行完成合同的情況時,管理人又面臨著繼續要求合同相對人履行合同的情況和在繼續承擔原先義務的同時要求管理人提供適當擔保的情況。對于繼續履行合同的情況,合同相對人有權根據《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五條規定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對于要求管理人提供適當擔保的,依據《破產法》第十六條,“破產程序禁止向個別債權人清償債務為由拒絕履行”的規定,管理人不能完全保證在破產程序中對任何人提供擔保。針對該問題,我國《破產法》第十八條遂規定管理人對未履行合同具有選擇權。該規定的設置主要是考慮到破產企業財產保值增值的需求[2]。
關于破產企業破產解除權的法律界定,大致分為以下有幾種情況:1.破產解除權的特殊性。《破產法》第十八條賦予管理人破產解除權的選擇權利,實際上是針對管理人處理破產解除權的行使權。它包含管理人在規定時間通知合同解除和不通知或在合同向對方催告規定時間內不答復的方式解除合同。這本質上與《民法典》合同編第五百六十二條、第五百六十三條規定的約定解除權、法定解除權不同,因此管理人的破產合同解除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是獨立于約定解除權、法定解除權之外的合法的解除權,且優先于《民法典》中規定的解除權。在破產企業重整中就待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的解除權,它作為特別法具有優先適用的法律效力。2.破產解除權原則上不具有溯及力。就此,有學者持肯定觀點,認為破產解除權有溯及力會增加合同解除權與破產解除權的邏輯矛盾,影響約定解除權的法律效力,同時還會影響破產交易安全及破產企業財產保護的原則。有學者持否定觀點,認為破產解除權具有溯及力,合同雙方具有恢復原狀或返還不正當得利的請求權。實際上,破產解除權作為特別法,與合同解除權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關于是否認定破產解除權具有溯及力,還需要考慮我國立法的實際。考慮到破產解除合同保護破產企業財產保值增值的目的,以及維護市場穩定性的需求,對破產解除權是否具有溯及力應靈活規定,考慮破產企業合同履行完畢和未履行完畢的情況。對于合同解除后未履行的,應終止履行;對于已履行的合同,則應根據合同履行完成情況、合同性質及合同當事人要求而定,來保護當事人的權利和破產企業財產價值最大化。當事人有權要求請求損失賠償。合同解除權的目的是實現對違約方的制裁,穩定市場秩序。二者的價值取向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需要根據案情實際分析破產解除權。從破產解除權保護破產企業重整財產利益最大化目標而言,它不具有溯及力。而不考慮對破產企業財產價值的保值增值目的時可認定為破產解除權具有溯及力。從《民法典》視角分析,雙方在訂立合同時存在可預見的債權請求風險。這又違背了破產企業重整中關于企業財產保值增值的原則,也違背了《民法典》的公平性原則。因此,破產解除權是否具有溯及力還應該根據行使合同相對人的權益及是否受到損害等方面進行詳細分析。3.破產解除權的行使規范。《破產法》第十八條規定管理人具有選擇破產解除合同或繼續履行合同的權利。從《破產法》的視角分析,該規定對債權人的權益與破產企業財產價值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為了確保破產解除權形式的規范性,《破產法》又重新對破產解除權做出了如下規定:(1)《破產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管理人決定履行未履行完成的合同時,應向人民法院或債權人委員會報告。第二十六條規定,首次債權人會議召開前,管理人對繼續或者停止債務人營業的情況也需要向人民法院報告。(2)《破產法》第十八條規定,管理人決定履行合同可根據情況向對方當事人提供擔保。對方當事人提出擔保,管理人不予以擔保的情況認定為未履行合同的解除。(3)部分國家針對破產解除權的規定考慮司法實踐的公平性原則,以尋求當事人公平與破產企業財產價值最大化間的平衡為原則。這是出于行使破產合同解除權在司法實際中的公平性需求而言的[3]。
二、待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的認定
(一)待履行消費型購房合同的認定
現階段我國司法實踐中,關于房地產企業破產重整中消費性購房合同的認定還存在一定的學術與實務爭議。未履行消費性購房合同中當事人的權益受到的影響極大。對于一些家庭收入狀況一般、貸款借款買房的家庭,待履行消費型購房承載的是一個家庭的希望,解除合同則會直接影響到當事人的生存權益。對于家庭收入狀況好,名下有其他住房的當事人而言的生存影響相對較小。考慮到當事人購買消費性住房的差異性,對消費型購房合同的界定也就存在了差異性。在沒有統一的標準界定下,待履行消費型購房合同的認定遵循法定原則、公平性原則。其中法定原則具有優先性[4]。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發布了《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2015執行異議復議規定》)第二十九條中對消費型購房合同租出進行了界定。雖然為消費型購房合同的司法認定提供了參考依據,但未對買受人做出詳細的分類界定,就不能單純地將買受人界定為消費者。在沒有其他更好參照標準的情況下,只能以該標準作為認定消費型購房合同的基礎法定標準,再根據購房人實際情況,如家庭背景、收入、住房持有量等綜合考慮是否將當事人購房認定為消費者購房,來保證待履行消費型購房合同認定的法定性及相對的公平性。在司法實踐中,還需要考慮雙方合同“待履行”的程度,分析購房人購房款的給付情況和商品房的交付情況,綜合考慮多種情況認定管理人對待履行合同的解除權。分析多因素認定的目的是確保個案破產解除權行使的公平性原則,在保證破產企業財產價值最大化的同時,還要防止破產解除權行使對購房當事人生存問題造成的危害[5]。
(二)待履行非消費型購房合同的認定
待履行非消費型購房包括普通型購房、以房抵債型購房、投資型購房等。認定待履行非消費型購房合同的難點在于合同界定投資型購房等。住房的投資性質在以多子女大家庭背景下是很難標準化界定的。如果僅將一個家庭擁有一套住房作為剛需,將再購房認定為投資性質,這顯然是不符合多子女大家庭的住房實際需求的。關于投資性住房的認定,可參照《2015執行異議復議規定》第二十九條對于消費型購房的界定,并由此推定是否是投資性住房。這種認定方式放在個案中用于行使合同解除權違背了《破產法》的公平性原則。因此,對于個人需要在司法實踐中管理人根據房地產企業進入破產程序時商品房建成與交付情況,以及購房人房款給付的實際情況而定是否就待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進行解除[6]。
(三)待履行以房抵債型購房合同的認定
房地產企業因資金周轉緊張而在合同中約定以房抵債的情況的本質是讓與擔保的關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民間借貸若干規定》)第二十四條對讓與擔保進行了規定。在這兩種關系中,房地產企業破產中待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解除的本質都是為了消除原有債務關系,并消滅合同。理論上以房抵債與讓與擔保有著相似的概念,要求擔保標的物的所有權移轉給擔保權人,將擔保權人控制在擔保范圍內,在債務清償后再將擔保標的物歸還給債務人或者第三人。不履行債務的情況,擔保權人有優先受償權。但在司法實踐中,以房抵債形式具有多樣性,法律關系較讓與擔保的關系更加復雜,無法通過讓與擔保的關系對以房抵債合同情況進行認定。事實上,大部分房地產企業宣告破產時均存有未建成商品房的問題,司法實踐中也不涉及已辦理物權轉移等問題。對于待履行以房抵債型購房合同,管理人應該從清查以房抵債協議的形成與債務清償期屆滿的順序開始,再依次確定以房抵貸的法律效力,再根據《破產法》第三十一條行使破產撤銷權,無須通過破產解除權[7]。
三、結語
《破產法》第十八條就管理人對破產申請受理前成立而債務人和對方當事人待履行合同有選擇解除合同或繼續履行的權利,實際上是提供了選擇權。管理人對待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解除與履行的選擇,需要根據待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的實際情況和《破產法》規定的不同情形做出認定,對破產合同解除權進行限制或解除,做出有利于使債務人財產最大化的原則,同時還要充分考慮和保障當事人的利益,體現管理人處理待履行商品買賣合同的公平性、協調性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