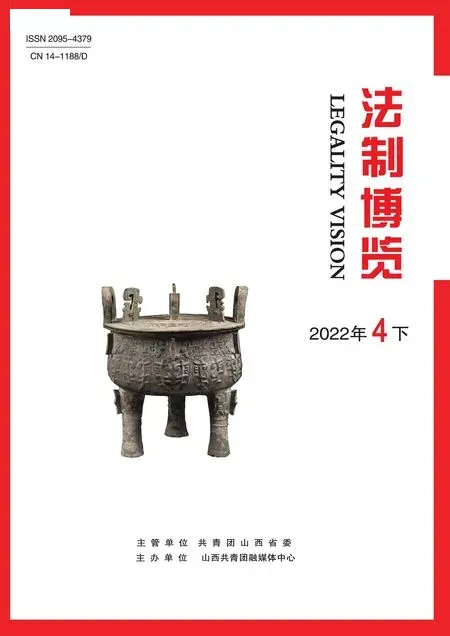《安全生產法》法律責任規定方面存在的若干問題
王朝陽
北京大成(廣州)律師事務所,廣東 廣州 510623
一、《安全生產法》規定的行政強制執行存在的問題
(一)行政強制執行可否二次或多次的問題。《安全生產法》第九十四條、九十七條、九十八條、九十九條、一百零一條、一百零九條規定的基本模式為責令限期改正并罰款,逾期未改正的,處罰款(金額比前一個罰款的金額多)。按《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以下簡稱《行政強制法》)第十二條的規定,加息罰款性質上屬于行政強制執行,即后一個罰款是對逾期未改正行為的行政強制執行,不同于對違法行為進行的行政罰款。而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的按日連續罰款性質上也屬于行政強制執行①《安全生產法》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生產經營單位違反本法規定,被責令改正且受到罰款處罰,拒不改正的,負有安全生產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可以自作出責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處罰數額按日連續處罰。,上述條文規定的行政強制執行與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的行政強制執行均基于一個違法行為,條文的組合構成兩個行政強制執行行為。針對一個違法行為施加兩個行政強制執行存在是否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問題。若施加兩個行政強制執行都無法使行政相對人改正違法行為,有必要考慮其他的行政強制執行方式。安全生產關系到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對安全生產領域的違法行為進行處罰,往往針對的是生產過程中的安全隱患或管理缺陷,兩者均可能導致生產安全事故的發生,從而導致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后果。而且,無論是安全隱患的整改或管理缺陷的糾正均具有時間方面的緊迫性,延遲處理,將使安全生產處于不確定性狀態,屬于不可接受的風險,也需要采取一定的強制措施。基于上述理由,無論是行政罰款還是行政強制執行,雖然加重了違法主體的違法成本,但在違法主體不糾正其違法行為時,金錢方面的處罰對其失效,法律上應當考慮其他的行政強制措施,如查封設備、設施、場所或代改履行等。
(二)無論是《安全生產法》第九十四條、九十七條、九十八條、九十九條、一百零一條、一百零九條的加處罰款還是第一百一十二條的按日處罰,均突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和《行政強制法》)規定的加處罰款的數額。《行政處罰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到期不繳納罰款的,每日按罰款數額的3%加處罰款,加處罰款的數額不得超出罰款的數額。《行政強制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的數額不得超出金錢給付義務的數額。顯然《安全生產法》上述條款規定的行政強制執行都突破了《行政處罰法》和《行政強制法》規定的加處罰款的數額。
二、一個違法行為可能導致二次行政罰款,違反《行政處罰法》二十九條規定① 《行政處罰法》二十九條規定,對當事人的同一個違法行為,不得給予兩次以上罰款的行政處罰。同一個違法行為違反多個法律規范應當給予罰款處罰的,按照罰款數額高的規定處罰。
《安全生產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與第一百一十四條的規定存在部分重合,可能構成一事再罰。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與第一百一十四條均以發生安全事故為前提,個人經營的投資人應當理解為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個體工商戶、個人獨資企業等,這些生產經營單位與個人投資人在法律上被認為是一個主體。若因未能保證安全生產所必需的資金投入而導致發生生產安全事故時,均滿足這兩條規定的處罰前提條件,如果按這兩條規定同時進行罰款處罰,顯然構成了一事二罰。
三、法律適用的問題
(一)《安全生產法》第九十四條、九十七條、九十八條、九十九條、一百零一條、一百零九條與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的適用問題。《安全生產法》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從文義解釋方面來說存在模糊地帶,首先,使用的是“責令改正”,而第九十四條、九十七條、九十八條、九十九條、一百零一條、一百零九條中使用的是“責令限期改正”,語義并不完全相同;其次,罰款開始時間是“自作出責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從文義解釋上可理解為行政機關作出責令改正和罰款決定之日的次日起開始按日連續處罰。將在九十四條、九十七條、九十八條、九十九條、一百零一條、一百零九條規定的對生產經營單位違法行為予以基礎處罰的同時,不給予生產經營單位改正時間便再次處罰,顯然不合理。探求立法者對一百一十二條規定的本意,按日連續處罰的時點應該是指責令限期改正之日中的限期屆滿之日起的次日。需要注意的是,《安全生產法》第九十四條、九十七條、九十八條、九十九條、一百零一條、一百零九條使用的是“逾期未改正的”用語,而一百一十二條使用的是“拒不改正的”用語,二者在用語方面并不完全相同。逾期未改正包括生產經營單位主觀不愿改正和客觀不能改正兩種情形,而拒不改正更多強調的是生產經營單位主觀不愿改正,二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屬于屬種關系。“逾期未改正的”的情形包括了“拒不改正的”情形。既然二者是屬于屬種關系,就可能存在重合的情形,遇到這種情況時,監管部門在進行處罰時就面臨著法律適用的問題。是擇一條款處罰還是按兩條規定同時處罰?“拒不改正”如果按前述方式理解,從邏輯上還可解決法律適用問題,即生產經營單位明確表示拒絕改正的,按第一百一十二條處罰,其他情形按上述條款中逾期未改正的情形處罰。即對逾期未改正的情形進行限縮解釋,排除拒不改正的情形。但考察《安全生產法》第九十四條、九十七條、九十八條、九十九條、一百零一條、一百零九條的規定,所規定的違法行為并不存在客觀上不能改正的情形。也就是說前述條款中的“逾期未改正的”與一百一十二條中的“拒不改正的”基本為同義。之所以說基本為同義,逾期不改正的情形尚包括生產經營單位愿意改正只是未能在限定的期限內完成改正的情形。若按兩個條文規定同時處罰,則明顯偏離了行政處罰的比例原則、合理性原則規定,若擇一處罰,將虛置,條文得不到適用的機會。
(二)《安全生產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適用問題。《安全生產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對生產經營單位中的個人經營投資人與其他類型的公司、企業在處罰上采取了區別對待。單獨將個人經營的生產經營單位列出的立法目的是什么,修正草案并未說明,同一種違法行為區別不同的主體而采取不同的處罰顯然構成了主體的歧視,不符合公平的法律原則。此外,個人經營的投資人也可能是生產經營單位的主要負責人,按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也需要給予撤職處分,但相對于法人類型的生產經營單位,個人經營的投資人附加了額外的罰款處罰。
四、生產經營單位主要負責人職業禁入規定不合理的問題
《安全生產法》九十四條第三款規定的生產經營單位主要負責人職業禁入罰存在不合理的問題。《安全生產法》事實上規定了高危行業和一般行業的安全生產,礦山、金屬冶煉及危險化學品生產經營單位等高危行業其安全管理的要求、人員的配備、安全生產責任險的投保等均與一般行業有區別,或者說在安全生產方面的要求是高于一般行業。九十四條第三款規定,對重大、特別重大生產安全事故負有責任的,終身不得擔任本行業生產經營單位的主要負責人。重大、特別重大生產安全事故可能發生的單位是一般行業,如機械加工行業,也就是說,對發生了重大、特別重大生產安全事故負有責任的機械加工行業的主要負責人,其不能擔任機械加工行業的生產經營單位的主要負責人,但并未限制其擔任高危行業的生產經營單位的主要負責人,這顯然不太合理。職業禁入罰的目的,一方面是對負有責任的人員進行處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應該是防止這些人擔任其他生產經營單位主要負責人再次發生生產安全事故。對發生重大事故或特別重大事故負有責任的生產經營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其再次擔任生產經營單位的主要負責人是否更容易發生生產安全事故,目前并未看到統計數據的支持。但法律既然作出規定,至少表明立法者認為其擔任主要負責人對其任職的生產經營單位生產安全事故的發生的可能性更大,按此邏輯,若其從一般風險行業進入高風險行業,發生事故的可能性可能相同,但高危行業的生產經營單位發生事故的嚴重程度比一般行業更大。第九十四條第三款未能細分不同行業危險程度,而粗略地作出這樣的規定,可能并不能實現立法的目的。故筆者認為,該條可調整為“對發生重大事故或特別重大事故負有責任的生產經營單位的主要負責人終身不得擔任生產經營單位的主要負責人”。
五、生產安全事故發生時及事故調查處理期間的違法行為的處罰存在的問題
《安全生產法》第一百一十條規定的法律責任存在的問題。該條規定主要針對生產經營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在發生生產安全事故時及事故調查處理期間的違法行為進行處罰。存在的問題表現在:
(一)僅對主要負責人在事故調查處理期間逃匿的行為處以拘留處罰,對性質更嚴重的事故發生時不組織搶救的行為沒有規定拘留處罰。發生生產安全事故時不組織搶救,其危害性顯然比事故調查期間逃匿的危害性更為嚴重。迅速組織應急救援能有效減少甚至避免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而事故調查期間意味著搶救工作已經結束,事故后果已經確定,其逃匿行為并不會加重生產安全事故的后果。故更有必要的是加重對事故發生時不組織搶救行為的處罰。
(二)“給予降級、撤職處分”的規定不夠明晰。是同時處以兩個處分還是選擇其中之一進行處分,若為后者,何種情形處降級處分,何種情形處撤職處分?若是同時處分,可能對國有性質的生產經營單位才有意義,對非國有性質的生產經營單位無意義。
(三)第一百一十條第二款中依照“依照前款規定處罰”不明確。第二款規定針對的是對主要負責人隱瞞不報、謊報、遲報生產安全事故的行為進行處罰,而第一款規定的處罰包括降級、撤職、罰款、拘留四種處罰,第二款規定的“依照前款規定處罰”應當按這四種處分形式中的哪種或哪幾種處分進行處罰未予明確。
六、涉及民事責任的規定存在歧義及與民事法律規定沖突的問題
《安全生產法》第一百一十六條規定存在的問題。本條規定了發生生產安全事故后民事責任的承擔。
(一)生產安全事故民事責任的承擔是否需要經過人民法院的審判程序后再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該條沒有規定,而是直接規定了由人民法院依法強制執行。關鍵在于對“由人民法院依法強制執行”中的“法”的理解,依《安全生產法》的本條規定,受害人可無須經過民事訴訟程序,直接申請人民法院執行,若依民法和民事訴訟法,受害人則必須先經過法院審判程序,判決生效后方可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前一種情況顛覆了民法體系的制度安排,后一種情形,《民法典》已有規定,此處規定沒有意義,僅余告知或恐嚇的意義。
(二)第二款規定中的“受害人發現責任人有其他財產的,可隨時請求人民法院執行”存在的問題。在民事訴訟中,事故的賠償責任本質上是一種侵權賠償責任,根據《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條的規定,用人單位的工作人員因執行工作任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用人單位承擔侵權責任。且生產安全事故的責任主體一般是較多的,可能包括生產經營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安全管理人員、違章操作的人員,甚至還包括監管部門的工作人員,這些人都可稱作責任人,是否都要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條規定也突破了民事法律關于民事責任承擔的規定。
七、結語
安全生產事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加大對安全生產領域的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提高違法成本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安全生產法》自身法律責任規定之間的內部協調,《安全生產法》與民事法律、行政處罰法律等其他部門法之間的協調也是落實《安全生產法》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