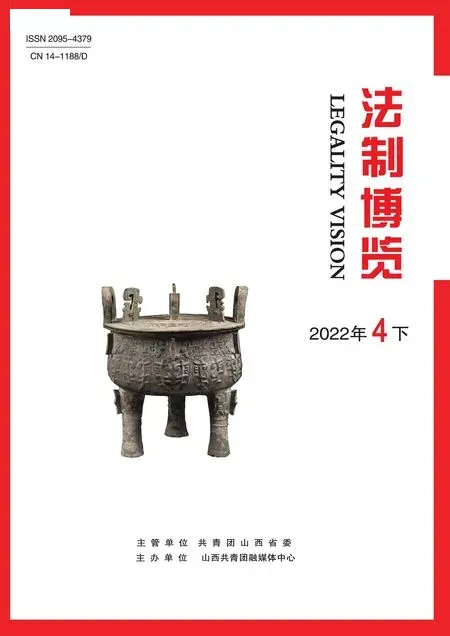環境公益訴訟領域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解釋論分析
蒙厚紅 余 艷
陜西理工大學,陜西 漢中 723001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條規定,“侵權人違反法律規定故意污染環境、破壞生態造成嚴重后果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這是我國首次在環境侵權領域引進懲罰性賠償。環境侵權問題不同于其他侵權,其損害對象一般包括私益損害和公益損害,針對私益損害,鑒于《民法典》的私法性質以及此次《民法典》的新規,環境私益侵權適用懲罰性賠償毫無疑問,但是對于環境公益訴訟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目前在學術界仍然存在爭議。鑒于此,筆者將基于解釋論的立場,試分析環境公益訴訟中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理論基礎與現實選擇。
一、環境公益訴訟與懲罰性賠償的本質探究
(一)環境公益訴訟的私法性質
環境公益訴訟在我國發展的數十年間,學者對環境污染損害的利益主要劃分為私益損害和公益損害,其中私益損害包括單一人損害、特定多數人損害以及不特定多數人損害,公益損害主要包括社會損害和國家損害[1],私益損害毋庸置疑。但是提起公益損害的環境公益訴訟到底屬于私法性質還是公法性質學界仍舊存在爭議。
普遍認為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主要依據利益保護重心、調整對象的不同。首先利益保護重心主要包括公益保護和私益保護,公法以維護公共利益即公益為核心,私法以維護私人利益即私益為核心,單從這點上看,提起公益損害的環境公益訴訟因保護利益為公益,故學者認為可以將其列為公法性質。其次根據調整對象而言,公法調整的是國家與公民、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而私法調整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和財產關系,因為提起公益損害的環境公益訴訟原告主要包括符合一定條件的社會組織和代表國家權力的檢察機關和負有環境資源保護管理職責的部門以及其他機關,故學者認為可以將其列為公法性質。
根據以上兩點,提起公益損害的環境公益訴訟勢必歸屬于公法性質更為恰當,但筆者認為以上兩點皆存在明顯漏洞,第一,提起公益損害的環境公益訴訟所損害的對象即公益損害并非公私法性質上的公益損害。人與環境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環境問題的優劣直接關系到人類的生存問題,任何一類環境污染所造成的損害都是以損害人和環境為共同代價的。人類和環境從本質上來講已經是一個利益共同體,損害環境最終損害的還是人類的居住利益,人有生活在綠色、健康的環境里的權利,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便是人類的生存權。所以環境公益損害的最終對象還是人的私益。第二,提起公益損害的公益訴訟原告主體并非公私法意義上的不平等對象。符合一定條件的社會組織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組織,而法人和非法人組織與自然人是處于平等地位,故此時的符合一定條件的社會組織即原告仍舊與被告是平等關系,此外檢察機關和負有環境資源保護管理職責的部門以及其他機關,雖然是國家權力的代表,明顯屬于國家機關,但在具體行使職能時也要分而論之。2020年新修訂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和負有環境資源保護管理職責的部門以及其他機關依據《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的規定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由此可見,檢察機關和負有環境資源保護管理職責的部門以及其他機關在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時所依據的是《民事訴訟法》,而《民事訴訟法》上的原告和被告屬于平等地位,所以即便是這兩類國家機關在提起此類訴訟時的原告身份仍舊與被告是平等的。根據公私法的權利保護重心和調整對象,筆者認為將環境公益訴訟歸屬于私法性質更為恰當。
(二)懲罰性賠償的私法性質、公法責任
懲罰性賠償是相對于補償性賠償而言的,其突破了“同質賠償”規則,旨在對惡意侵權人進行嚴厲打擊,懲罰性賠償從誕生之初就是為了解決私主體之間的民商事糾紛,且私主體之間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懲罰性賠償只是為了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財產關系,故從公私法的性質上來講,懲罰性賠償明顯屬于私法性質。[2]
懲罰性賠償中的受損害人突破了“同質賠償”規則而向侵權人主張懲罰性賠償便是典型的公法責任,從表面上看違背了法理,但卻符合實質法治。法治分為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法哲學家認為實質法治才是法律的最終目的,懲罰性賠償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維持正常的交易秩序,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故懲罰性賠償雖歸屬于私法性質,卻帶有明顯的公法責任。
二、環境公益訴訟與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性質、價值契合
(一)環境公益訴訟與懲罰性賠償皆為私法性質
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是在《民事訴訟法》的基礎上進行的,即便訴訟主體一方為公權力機關也不影響環境公益訴訟的本質為私法性質。懲罰性賠償制度不管是在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主要適用于私主體之間的民商事糾紛,懲罰性賠償是相對于補償性賠償而言的,其突破了“填平規則”,旨在遏制惡意侵權人的直接或者間接侵權行為。[3]我國法律體系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但其基本框架還是大陸法系,懲罰權這一概念在我國主要被刑法和行政法等公法壟斷,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立法者賦予了平等主體之間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要求數倍賠償的權利,這便是懲罰性賠償,其作用機理和目的偏向于公法,但本質還是屬于私法,是典型的私法性質、公法責任的體現。
環境公益訴訟與懲罰性賠償在公私法的性質上來講皆屬于私法性質,在性質上二者是契合的。《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條規定了環境污染懲罰性賠償制度,雖然暫時沒有司法解釋規定環境公益訴訟可以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但是基于環境公益訴訟與懲罰性賠償的本質,從制度本身的性質解釋上來講二者結合適用并不沖突,尚未突破公私法交叉適用的弊端。
(二)環境公益訴訟與懲罰性賠償的目的、功能相符
環境侵權不同于普通侵權,其所帶來的損害一般較大,持續時間較長,且修復成本高,污染波及的范圍廣,除危害私人利益外還會危害公共利益。大型企業造成的環境污染成本相對于其獲利而言不值一提,因此在沒有懲罰性賠償制度之前,侵權人只需要承擔修復環境污染的費用以及流于形式的行政罰款,暫時的污染雖然可以制止,但是潛在的污染卻是絡繹不絕。[4]
治理環境污染的最終目的是修復現有污染和遏制潛在污染,補償性賠償可以修復現有污染,但是對于潛在污染卻效果不大,雖然《刑法》早將環境污染入罪,但其制裁的還是造成環境污染的行為人,對于修復環境《刑法》也鞭長莫及。懲罰性賠償是市場經濟的產物,針對環境污染問題,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長久保護環境,而環境污染領域的懲罰性賠償暫時是沒有規定上限的,針對財力雄厚的大型企業,如果不對其施加懲罰性賠償,則難以遏制潛在污染,故環境公益訴訟與懲罰性賠償在目的和功能上都是契合的,二者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保護環境,防止潛在的環境污染事故,在環境公益訴訟領域適用懲罰性賠償能夠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最大化地保護岌岌可危的生態環境。[5]
三、解讀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體系
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規定在《民法典》第七編第七章,而侵犯知識產權、產品責任的懲罰性賠償規定也同樣規定在《民法典》第七編第七章,分別為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一千二百零七條,與環境污染懲罰性賠償都隸屬于《民法典》侵權責任編。[6]而《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了環境污染、侵害消費者權益等類型的公益訴訟,由于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是新增制度,但是侵犯知識產權的懲罰性賠償最早出現在2013年修訂的《商標法》,隨后在2019年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2020年修訂的《專利法》《著作權法》中都規定了懲罰性賠償。
侵犯消費者權益的懲罰性賠償最早規定在2014年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并且規定了消費公益訴訟制度,《民法典》及最高院于2021年3月出臺的《關于審理侵害知識產權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中并沒有規定侵犯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公益訴訟,故筆者不再討論此類型。消費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在《民法典》出臺之前已經存在,《民法典》出臺后也規定了產品責任的懲罰性賠償,同時《民事訴訟法》也規定了產品責任的公益訴訟,且產品責任公益訴訟也分為針對私益損害的產品責任和針對公益損害的產品責任,但此二者都同樣適用懲罰性賠償,所以基于體系解釋,環境污染與產品責任同時規定在《民法典》中,《民事訴訟法》中也都規定了針對此類型的公益訴訟,環境公益訴訟也同樣包括針對私益損害的環境公益訴訟和針對公益損害的環境公益訴訟,既然產品責任的兩種公益訴訟類型的都能適用懲罰性賠償,那么環境公益訴訟也同樣能適用懲罰性賠償,這是體系解釋的必然性。
四、環境公益訴訟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現實選擇
按照規定,《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2021年1月4日在江西某縣人民法院環境資源法庭公開審理了全國首例適用《民法典》環境污染懲罰性賠償案件,此案件中,公益訴訟起訴人為某縣人民檢察院,被告人為浙江某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法院經審理認為,浙江某化工集團有限公司自2018年3月3日至7月31日,連續將該公司生產的1124.1噸硫酸鈉廢液傾倒在浮梁縣八角井、洞口村周邊,造成八角井周邊約8.08畝范圍內環境和洞口村洞口組的地表水受到污染,1000多名群眾用水受到妨礙。此案雖然發生在《民法典》實施之前,但造成的損害卻持續到《民法典》實施之后,故法院依法判處被告浙江某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承擔生態修復費、環境功能性損失費等全部費用,并判處其承擔環境污染懲罰性賠償金11406.35萬元。
雖然《民法典》及現有的司法解釋并沒有規定懲罰性賠償可以在環境公益訴訟中適用,但是基于現實選擇的困境,很多法院已經在一些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中選擇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以此來制裁惡意侵權人肆意污染環境的客觀事實。筆者認為理論和現實選擇的共同需要造就了個別先行法官預見性地在此類案件中適用懲罰性賠償。
五、結語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條并沒有詳細說明環境公益訴訟領域能否適用懲罰性賠償,但是基于前文的解釋分析,筆者認為不管是基于學理解釋還是體系解釋,環境公益訴訟與懲罰性賠償都是私法上的產物,二者結合起來適用并無不當。學者的爭議和全國首例環境公益訴訟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案件共同折射出法學理論與司法實踐之間的差距,法律的制定與適用應當考慮法律、社會和生態效果之間的關系,環境公益訴訟領域適用懲罰性賠償雖然暫時沒有法律及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但是現實的選擇促成了此制度的適用,解釋論的分析也足以破解理論上的適用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