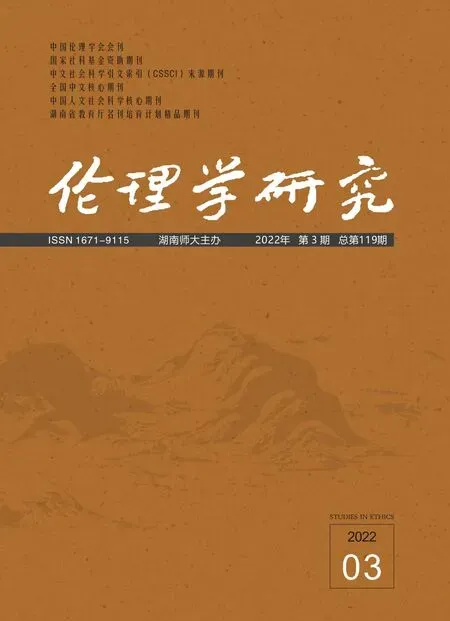論愛國義務的證成問題
高景柱
一、問題的提出
無論人們從哪個角度理解愛國主義,對國家的熱愛與忠誠應該是愛國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然而,為了進一步厘清愛國主義的內涵,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追問一些帶有本質性的問題,例如,熱愛和忠誠的內涵是什么,如何體現對國家的熱愛與忠誠?進一步思考,我們就會發現,愛國主義強調的“熱愛”和“忠誠”是以對國家和同胞的特殊關心和特殊義務表達出來的。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愛國義務都關涉到人們應該如何對待本國和同胞這一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愛國義務意味著優先關注本國的福祉,特別是關心同胞的利益。我們可以用“本國優先”和“同胞優先”這兩個命題來概括愛國義務的基本內涵。就“本國優先命題”來說,對國家的偏袒體現為特別關注本國的利益,當本國的利益與他國的利益之間出現沖突時,愛國者通常會優先關注本國的利益。同樣,就“同胞優先命題”而言,特別關注同胞的利益是對同胞的偏袒的主要體現形式,當同胞的利益與非同胞的利益發生矛盾時,愛國者通常也會強調優先滿足同胞的利益。
人們通常認為,公民擁有愛國義務,應該偏袒自己的國家和同胞,然而,這一觀點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質疑。對自己國家和同胞的偏愛超過了對其他國家及其人民的偏愛,這種做法的正當性并不是不言而喻的,過度的偏袒就會帶來道德上的問題。如果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擁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和道德價值,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為偏袒本國和同胞的行為進行辯護呢?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就根據道德普遍主義的立場質疑了愛國主義的偏袒立場,認為這種愛國主義是一種惡德。托爾斯泰指出,雖然愛國主義可能因在古代世界使得人們獻身于祖國,使之免受野蠻人的攻擊,從而成為一種美德和自然的情感,但是如今的情況恰恰相反,“如今愛國主義要求人們有一個與我們的宗教和道德完全相反的理想——并不承認所有人的平等和博愛,而是承認一個國家或民族對所有其他國家和民族的統治,這怎么可能是一種美德呢?然而,在我們的時代,這種感情不僅不是美德,而且毫無疑問是一種罪惡;這種愛國主義情緒現在不可能存在,因為它的概念既沒有物質基礎,又沒有道德基礎”[1](75)。在托爾斯泰那里,這種愛國主義不僅是愚蠢的,而且是不道德的,違背了道德平等的基本原則,已經成為戰爭的不折不扣的根源,不斷威脅著人類的和平與安寧。查爾斯·瓊斯(Charles Jones)從全球正義的立場出發質疑了對本國人的特殊義務,她認為對本國人的特殊義務這一愛國主義的偏袒行為明顯缺乏任何普遍的、能夠站得住腳的理由[2](134)。喬治·凱特布(George Kateb)曾試圖指出愛國主義的內在錯誤。在他看來,雖然愛國主義意味著對國家的熱愛,但是它是一種隨時準備為自己的國家而犧牲和進行殺戮的立場,這與道德原則是相沖突的,一個有道德的人應當在堅持道德原則和對自己國家的忠誠之間做出抉擇。凱特布還強調,愛國主義是一個永久的道德節日,一旦它變得充滿活力,它總是會變成犯罪。“愛國主義不僅是一種抽象,也是一種理想;但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它將國家這個實體理想化了,人們覺得這是他們的。愛國主義因此把某種自愛變成了理想。這是一種自我關注,不可避免地會變成一種被許可的自我偏愛,這種偏愛從事物的本質出發,必須反過來試圖破壞其他國家,而很少是為了捍衛人們的有形利益。”[3](9)在凱特布那里,愛國主義與那種信奉普遍主義的道德原則是沖突的,是一種自我理想化,由于國家手中掌握著武裝力量,在愛國主義的激發之下,國家之間經常會存在沖突。托爾斯泰和凱特布在質疑愛國主義時,無疑都指向了愛國義務問題,強調愛國義務會帶來一些惡劣的后果。
可見,雖然人們通常承認愛國義務的存在,但是愛國義務的正當性仍然需要進一步的證明。為了回應上述質疑,我們必須關注愛國義務的證成問題,思考公民對其國家和同胞的特殊義務的基礎,關注人們能否為這種特殊義務提供一種有說服力的理由。為了下文論述的方便,我們應當首先進一步界定本文關注的問題。愛國主義并不只有一種,而是有多種形式,并不是所有形式的愛國義務都擁有可以被證成的可能性。例如,依照愛國主義立場的激進程度,我們可以將愛國主義分為“極端的愛國主義”和“溫和的愛國主義”。極端愛國主義具有極端的排外性,只關心自己的國家和同胞,認為自己的國家是最優秀的,對國家有一種無條件的積極評價,強調一切手段都可以被用于實現自己國家的利益。與之不同,溫和愛國主義并不像極端愛國主義那樣排外,它除了關心自己的國家和同胞,也會關心其他國家及其人民,對國家并不擁有一種無條件的積極評價,強調國家在實現自身利益的過程中所采取的手段必須受到某些限制,至少不能侵犯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顯而易見,極端愛國主義拒絕道德本身,否認所有人的基本平等,極易淪為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與這種愛國主義有關的特殊義務難以獲得證成。因此,我們應該首先排除極端愛國義務,重點關注那種受到某種道德原則限制的愛國義務的合理基礎問題。一種有可能獲得證成的愛國義務應當是與溫和的愛國主義有關的特殊義務,這種特殊義務不會傷害其他國家及其人民,我們接下來談及的愛國義務均指向與溫和的愛國主義相關的義務。愛國義務能否得到合理的辯護?愛國義務如何獲得證成?也就是說,那種優先關注自己國家和同胞的利益(而不是優先關注其他國家及其人民的利益)的做法的正當性何在?這將是本文關注的主要問題。本文第二節歸納目前學界用于證成愛國義務的三種代表性的觀點,即共同體主義、感激和相互性的論證方式,第三節指出上述三種用于證成愛國義務的代表性觀點存在的值得商榷之處,第四節試圖提出一種可能用于證成愛國義務的方法,即“規則后果主義”(Ruleconsequentialism)的方法。
二、用于證成愛國義務的三種代表性觀點
不少學者關注愛國義務的證成問題,并為此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見解,較具代表性的觀點有如下三種。第一種觀點是由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為愛國義務提供的“共同體主義”論證方式。麥金太爾在為愛國主義是一種美德這一立場辯護的過程中明確強調了愛國義務,認為愛國主義是一種對本國以及本國獨有的特征、優點和成就的關切,然而,愛國者并不同等地重視其他國家類似的特征、優點和成就,“愛國主義屬于展現忠誠的那類美德之一(如果它確實是一種美德的話),這類美德還包括夫妻間的忠貞、對家人和親友的愛和友誼,以及對像學校、板球或棒球俱樂部這類機構的忠誠。所有這些態度都展現出一種會引發行動的對特定的人、機構或團體的獨特關切,一種建立在表現這種關切之人同相關的人、機構或團體間特定的歷史性聯合關系之上的關切”[4](248)。言下之意,在麥金太爾那里,愛國主義強調公民應該對自己的國家和同胞展現出獨特的關切和偏袒。然而,上述愛國義務立場所強調的公民對自己的國家和同胞所表現出的偏倚性,與不偏不倚的道德立場之間貌似存在一種沖突。麥金太爾認為這兩種立場之間不一定存在沖突,只要愛國主義處于某些道德立場的約束范圍之內。某些自由主義者所信奉的愛國主義即是如此。然而,麥金太爾并不認可這一做法,認為如此受到限制的愛國主義就像是被閹割了一樣,變成了一套幾乎空洞的口號,他通過兩個例子展現了這種觀點。在其中的一個例子中,兩個共同體爭奪森林、土地、礦產等稀缺資源,這些資源對這兩個共同體的生存都是至關重要的,此時沖突就有可能出現。當沖突出現時,自由主義信奉的非個人化的道德立場強調每個個體只能算作一個。麥金太爾當然不認可這種做法,而是強調“愛國立場要求的是:我為我的共同體力爭更多利益,而你為你的力爭更多。理所當然,在一個共同體的生存處于危急關頭的地方,有時甚至只是在一個共同體的重大利益遭受威脅時,愛國主義將激起以本共同體名義開戰的意愿”[4](249)。麥金太爾還提出了一種試圖替代自由主義的愛國主義解釋,即共同體主義的解釋,“愛國主義作為一種美德,它現在或過去之被奠立,首先縛系于一個政治的或道德的共同體,其次才縛系于該共同體的政府;然而現在,作為一種特征,愛國主義之被踐行是要在這樣的政府中對這樣的政府盡職”[5](324)。自由主義道德通常強調人們從哪里學習以及從誰那里學習道德的原理,與道德的內容是不相關的,而根據麥金太爾的共同體主義的道德觀念,一個人在哪里習得道德、從誰那里習得道德,對于道德信仰的內容和性質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一個人在各種共同體中的不同的成員資格“并不是偶然屬于人們的特性,不是為了發現‘真實自我’而須剝除的東西。作為我的實體的一部分,它們至少是部分地,有時甚至是完全地確定了我的職責和義務。每個個體都在相互聯結的社會關系中繼承了某個獨特的位置;沒有這種位置,他就什么也不是,或者至多是一個陌生人或被放逐者”[5](42)。基于這種共同體主義的道德觀,一個人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共同體中,才能領會道德規則的內容,對道德的辯護必須以在特定共同體的生活中享受的特定善為依據,倘若一個人失去了其共同體,這個人將會失去真正的判斷標準,同時,依據這種道德觀,愛國主義(以及與其相似的忠誠)也就成為一種美德,自由主義強調的那種受到不偏不倚原則限制的愛國主義將是過于空洞的。可見,麥金太爾訴諸共同體主義立場為愛國義務進行辯護,強調愛國主義的特殊主義道德扎根于一個特定的共同體,并與那個共同體的社會生活聯系在一起,其所處的共同體和同胞是其所擔負義務的主要對象。
有些學者強調個人出于對從國家和同胞那里獲取的利益的“感激”而對自己的國家和同胞負有特殊義務,例如,共和愛國主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毛里齊奧·維羅里(Maurizio Viroli)就在其共和愛國主義理論中為愛國義務提供了一種“感激”論證方式,這也是本文探討的用于證成愛國義務的第二種觀點。維羅里構建了一種共和愛國主義理論,共和愛國主義所言說的對祖國的熱愛意味著熱愛那種基于共同自由、擁有共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共和國。維羅里偏愛的共和愛國主義是一種沒有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強調通過政治參與等政治手段來實現的愛國主義,“這種愛國主義使好的共和國所需的公民美德得以可能。理解恰當的話,公民美德是對共和國或祖國的熱愛,它表現為一種允許公民為了共同善而行動、反對共同自由的敵人的道德活力。與所有美德一樣,公民美德也要求努力;它要求豐富私人生活,而不是把它帶入到公共承諾中去”[6](171)。依照這種共和愛國主義理論,愛國主義是人民對其祖國的一種情感,這種情感意味著特殊義務,它表現為公民對特殊的人、目標和地方的熱愛,表現為公民對自己的國家和同胞的福祉的關注。關于公民為什么有關心其國家和同胞福祉的特殊義務,維羅里曾言,“講述愛國主義故事是符合道義的,但并未提供我們對民族共同自由作出承諾的道德理由。共和主義思想家給予的答案是眾所周知的:因為我們欠她的,所以我們對國家有道德義務。我們的生命、教育、語言以及在大多數幸運的情況下的自由,都歸因于祖國。如果我們期望成為有道德的人,就必須對我們的所得作出回報,至少是部分的回報,而那就是為公益服務”[6](7-8)。也就是說,人們可以從國家那里獲取利益,因此,人們必須作出回報,即擔負愛國義務。
在維羅里那里,共和愛國主義可以成為民族主義的解毒劑,強調各種團結的紐帶可以被用于維護自由,而非像民族主義那樣將其變成煽動排外或侵略的力量,同時,人們也要確定愛國義務的邊界,辨別源自國家的命令中哪些是可以被接受的、哪些是應當被拒絕的。伊戈爾·普利莫拉茲(Igor Primoratz)認為,當被問及為什么人們認為自己應該特別關心自己的國家和同胞時,感激可能是愛國義務中最受歡迎的理由之一,許多愛國者就談到了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感激之情,維羅里的立場就是如此[7](28)。也就是說,依普利莫拉茲之見,維羅里是從感激的角度來探討愛國義務的代表之一。
第三種觀點是有些學者試圖從“相互性”的視角為愛國義務提供一種合理的基礎,理查德·達格爾(Richard Dagger)是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達格爾在從相互性的視角為同胞優先這一觀點進行辯護時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即一方面,人們強調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生命權或生存權是不分國界的;另一方面,人們又強調同胞優先的觀念,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必須在兩者之間做出某種非此即彼的選擇呢?在達格爾那里,基于權利的政治理論會要求我們認識到政治共同體成員之間的特殊關系,相互性的觀點強調人們應該給予其同胞以優先權,因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人們虧欠其同胞,在一個政治共同體中,那些有著相同公民身份的人有著特殊的關系,這種特殊的關系意味著特殊的權利和義務。為了證明這一點,達格爾強調,那些有著相同公民身份的人之所以處于一種特殊關系中,原因在于,一方面,他們從事的是一項合作事業,這項合作事業會給他們帶來利益,使人們能夠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能夠和平地追求他們的私人利益;另一方面,政治共同體的存續依賴于人們遵守政治秩序的規則,倘若政治共同體的成員在進行相互合作時不遵守這些規則,這些規則將是毫無用處的。“那些從事合作事業的成員之間有一種相互性關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義務遵守法律。因為我們有義務這樣做,這是政治組織的合作成員的責任。它們有要求我們服從的權利,因為通過對它們的服從,使我們能夠享受政治秩序的好處。換言之,只要國家可以被合理地視為一個合作事業,它們就可以對我們提出要求,這一要求延伸到包括同胞優先的概念。”[8](443)也就是說,依達格爾之見,公民之間有一種社會合作關系,凡是參與該合作體系的人都有義務對其他人承擔公平份額的負擔,從而換取公平份額的利益,否則,不公平就會出現。達格爾在從相互性的視角為愛國義務進行辯護時曾總結道:“同胞優先,是因為我們出于相互性的原因而虧欠他們的。每個人,不管是否是同胞,都有權得到我們的尊重和關心——這種權利是建立在自主權的基礎上的,但那些與我們一起參加合作事業的人有權得到特別的承認。他們的合作使我們能夠享受事業的好處,公平要求我們回報。當政治組織可以被合理地視為一種合作行為時,那么,我們必須給予我們的同胞一種特殊的地位,一種優先于那些站在由政治事業構成的特殊關系之外的人的地位。”[8](446)當然,達格爾在為同胞優先的觀點進行辯護時,最后還指出同胞的優先地位并不是絕對的,倘若同胞優先的觀點能夠成立,它需要滿足一個前提條件,即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
三、對證成愛國義務的既有觀點的反思
在歸納了目前學界用于證成愛國義務的三種代表性觀點之后,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些觀點能夠為愛國義務提供合理的基礎嗎?本文認為上述三種觀點都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一些有待澄清的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麥金太爾為愛國義務提供的共同體主義證成方式是否合理。雖然麥金太爾的共同體主義理論本身極具爭議性,但是我們在此不準備質疑麥金太爾的共同體主義理論本身,只關注麥金太爾以共同體主義來述說愛國義務的嘗試是否可行。麥金太爾的立場至少存在三點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麥金太爾忽視了愛國主義與普遍主義之間存在相容的可能性。上文曾言,麥金太爾強調那種受到非個人化的道德立場等普遍主義立場約束的愛國主義已經被閹割了,相當于一套空洞的口號。在麥金太爾那里,愛國主義所信奉的偏袒與普遍主義所強調的不偏不倚之間的沖突是難以調和的,在愛國主義的偏袒和普遍主義的不偏不倚之間缺乏一種中間的立場,人們不得不在愛國主義和普遍主義之間做出一種非此即彼的抉擇。實際上,麥金太爾對普遍主義道德的不偏不倚理念采取了一種過于簡單化的理解,忽視了普遍主義道德允許人們偏袒自己的國家和同胞的可能性。愛國主義的偏袒和普遍主義的不偏不倚不應該被視為要么全有要么全無的東西,人們可以在認可某些普遍主義原則的情況下為愛國義務進行辯護。偏袒和不偏不倚并不是完全對立的,它們之間存在相容的可能性,只要人們在表達偏袒的過程中仍然遵循某些道德原則的限制及其背景性條件是正義的。例如,“公民應該熱愛自己的國家”這條原則的普遍適用性與這條原則所允諾的特殊義務并不沖突。“公民應該熱愛自己的國家”是一種可以被普遍化的原則,所有人都可以熱愛自己的國家,同時,只要人們在踐行愛國義務時的背景性條件是正義的,它允許人們對自己的國家和同胞表示偏袒。
第二,在麥金太爾的兩個國家爭奪資源的例子中,麥金太爾認為雙方不得不訴諸戰爭,這種做法不僅忽視了存在其他解決方案(如通過談判從而尋求和解)的可能性,也使得麥金太爾的愛國主義理論極有可能變成我們在第一節曾提及的極端愛國主義。對于麥金太爾的為共同體而戰的觀點,維基·斯賓塞(Vicki A.Spencer)曾言:“盡管自衛即使從和平主義者的立場來看也是正當的,但是在這里,愛國主義和國際關系中的現實主義立場驚人地相似,后者認為國家是沒有任何倫理考慮的自我最大化的行為者。相關的是,盡管麥金太爾認為國家是個人道德的唯一真正來源,但是當涉及群體間的關系時,道德就消失了。”[9](202)也就是說,此時愛國主義與國際關系中的現實主義幾乎不存在區別。實際上,雖然國與國之間難免會存在利益沖突,有時存在一種非常激烈的利益沖突,但是戰爭并不是僅存的解決利益沖突的手段,人們在訴諸戰爭手段之前,應該積極尋找調和沖突的和平解決方式,更好地進行權衡,尋找一種合乎道德的立場。即使戰爭是難以避免的,人們也必須關注戰爭的正義性本身,在對戰爭進行反思之前,并不存在一種明確的、固定的解決利益沖突的手段。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麥金太爾所主張的愛國主義中的非理性的特征就會使其蛻變為一種極端的愛國主義。當然,這種極端愛國主義并不像麥金太爾所認為的那樣會成為一種美德。
第三,在麥金太爾那里,真正的愛國主義是一種以人們所處的共同體為基礎的美德,這種做法過于強調公民所處的共同體對一個人接受的道德教育、認可的道德觀念以及擁有的道德能力的影響。麥金太爾只是將道德理解為人們所處共同體的道德,忽視了存在那種可以超越各個具體共同體的普遍主義道德的可能性。雖然我們不能否認人們在某共同體中接受的道德教育,會影響其認可的道德觀念以及擁有的道德能力,但是我們同樣不能忽視人們擁有道德反思的能力,不能忽視人們擁有道德進步的可能性。在關注愛國主義的情感及其引發的行動時,人們不能只關注自身所處共同體認可的道德規范。一方面,人們需要進行道德反思,需要反思自己所處的共同體信奉和踐行的道德規范的正當性,當自己所處的共同體信奉的道德規范明顯侵犯其他共同體的利益時,人們應該明確指出來;另一方面,這些道德反思本身就是愛國義務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道德反思,人們會遠離盲目性的愛國主義忠誠。否則,這也會影響麥金太爾為愛國主義是一種美德這一立場進行的道德辯護。
接下來我們來看維羅里為愛國義務提供的感激論證方式是否恰當,本文認為這種論證方式也是不恰當的。其一,愛國義務的感激論證方式側重于人們從國家那里獲取的“利益”,然而,利益不一定會引發感激,感激的出現是需要條件的。弗雷德·伯杰(Fred R.Berger)對感激的深入分析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反思愛國義務的感激論證方式。在伯杰那里,表達感激之情并不僅僅是對他人對我們做了有益的事情的回應,我們除了考慮利益對接受者的價值以及給予者做出的犧牲或讓步的程度,還需要考慮其他因素。伯杰主要強調了兩點因素:一是利益給予者在給予利益時是否是自愿的,倘若利益給予者是在被脅迫的情況下給予利益的,感激就是不應該的;二是利益給予者在給予利益時是否擁有明確的意圖,雖然利益給予者對人們做了某些有益的事情,但是他是在沒有任何意識的情形下做出的,或者這些利益只是利益給予者的某些行為的副產品,此時人們也不應該表達感激之情,“如果行為的發生僅僅是因為行為者選擇了兩害相權取其輕而犧牲自己,或者沒有任何知識或想法認為它會給我們帶來利益,或者僅僅是因為它會給行為者自己帶來利益,那么感激也不存在,因為沒有做任何事情來幫助我們。因此,感激不是出于對利益的回報,而是出于對仁慈的回應;這是出于幫助我們的愿望,對給予的利益(或試圖使我們受益)的回應”[10](299)。也就是說,感激的表達是對他人的仁慈的回應。我們在判斷是否應該對某個人或群體的行為表達感激之情時,我們必須注意利益給予行為的背后的動機是什么,倘若我們無法判斷行為背后的動機是什么,我們就不能確定感激是否應該出現。聯系到愛國義務問題,我們可能無法簡單地判斷國家給予我們利益這一行為背后的動機是什么;同樣,對那些參與社會合作體系的同胞給予的一些利益的背后動機是什么,我們也難以做出準確的判斷。在沒有弄清楚這些動機之前,我們不能簡單地試圖用感激來證成愛國義務。
其二,即使感激是對利益的回應(而不是對仁慈的回應),倘若這種利益是免費給予我們的,我們有表達感激的可能性,然而,我們在從國家那里獲取某些東西時是需要滿足某些前提條件的。普利莫拉茲對此曾分析道:“感激只適用于作為禮物免費贈送的利益,而不適用于已經支付的東西。然而,一個人從自己的國家或政治組織中獲得的大部分利益都屬于后一種:由守法行為,特別是通過稅收支付而獲得的利益。”[7](29)也就是說,倘若公民不納稅、不服從法律,公民很難從國家那里獲取利益,相反,公民還要遭受相應的懲罰。我們確實從國家那里獲得了不少利益,例如,國家制定了法律,提供了安全、和平、教育和醫療等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然而,這些利益的獲取并不是不需要支付成本的。維羅里強調我們從國家那里獲取一定的利益這一做法無可厚非,然而,維羅里不能忽視我們從中獲取利益時需要滿足的前提條件。對于感激的論證方式,我們還需要注意的是,倘若只試圖通過感激來證成愛國義務,愛國義務就有可能變得根基不穩,因為依照這種觀點的內在邏輯,人們對國家和同胞負有義務的基礎是因為公民從國家和同胞那里獲得了某些利益而心懷感激之情,從而負有愛國義務,然而,一旦這些利益消減了,這種愛國義務貌似就不存在了。這與人們的直覺相悖,依照人們的直覺,這種愛國義務應該存在。當然,本文質疑從感激的角度為愛國義務進行的論證,這并不意味著公民不應該感激國家,公民應該感激國家,其背后的緣由應該不只是因為公民從國家那里獲取的某些利益,我們還應該從其他地方尋求其內在的緣由。
有些學者從相互性視角出發為愛國義務提供論證方式這一做法,也同樣存在值得商榷之處。第三種證成愛國義務的方式非常強調社會合作體系的重要性,在國家的協調之下,公民從與同胞共同參與的社會合作體系那里獲取了一定的利益,倘若沒有這種社會合作體系,這種利益是不可能獲得的。當然,這種社會合作體系也會帶來一定的負擔,此時就要求公民對國家和同胞擔負一定的愛國義務,由于外國人沒有參與這種社會合作體系,這種愛國義務就不應該針對他們。然而,情況果真如此嗎?我們可以考慮兩類特殊的群體:一是殘疾同胞;二是居住在某國的外國人。就殘疾同胞(如精神病患者、植物人等)而言,這些人對社會合作體系的貢獻相對較少,按照這種相互性的證成方式的內在邏輯,這些人就不應該獲得任何回報,也不應該成為愛國主義偏袒的對象,然而,這明顯是有違道德直覺的,任何國家都不可能也不應該忽視殘疾同胞的需求;就居住在某國的外國人來說,這些人居住在某個國家內,通過消費等形式間接地納稅,遵守法律,換言之,這些人也與同胞一樣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社會合作體系,與同胞一樣處于相互性的關系之中。按照愛國主義的相互性的證成方式的內在邏輯,這些人也應該成為愛國義務關注的對象,然而,這些人卻被排除在愛國義務之外。因此,上述兩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都凸顯出愛國義務的相互性的證成方式難以自圓其說,缺乏自洽性。
四、一種用于證成愛國義務的可能路徑
本文最后從道德平等的立場出發,試圖為愛國義務提供一種規則后果主義的證成方式。依照道德平等的基本理念,雖然人們在財富狀況、教育程度、社會地位、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但是從道德意義上來說,這些差異并不意味著人們是不平等的,實際上,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內在價值和道德地位,沒有一個人在本質上優越于其他人,同時,每個人都擁有一些不可被剝奪的基本權利,任何人都無權侵犯這些權利。雖然很多學者在一些價值問題上持有很多不同的觀點,但是道德平等已經獲得了普遍認可,是人們的基本共識之一,因此,它也適合我們作為述說愛國義務的正當性的起點。道德平等意味著每個人都應該獲得平等的尊重,這一立場意味著人們彼此之間至少要承擔一些義務,這些義務可以被稱為“一般義務”。一般義務包含的內容眾多,既包括消極義務,又包括積極義務,例如,人們不應該互相傷害,應該尊重彼此的人格和權利,應該互相幫助,等等,無論對誰來說,這種義務都是同樣的。一般義務通常可以被細分為一個個特殊義務,一般義務往往是通過特殊義務的履行來加以實現的,我們在本文中言及的愛國義務就屬于一種特殊義務。雖然我們剛才從道德平等出發引出了一般義務的存在,但是道德平等不會排除特殊義務,例如,道德平等原則并不會排除愛國義務這一特殊義務的存在。
愛國義務如何獲得證成呢?我們可以嘗試著為其構建一種規則后果主義的證成路徑。“后果”是后果主義重點關注的對象,后果主義將后果(而非動機)與道德正確性密切關聯在一起,依照后果對行為等內容進行道德評價,力圖實現好的后果的最大化。后果主義的類型眾多,其中行為后果主義和規則后果主義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對于規則后果主義的內涵,布拉德·胡克(Brad Hooker)曾言:“規則后果主義主張,當且僅當某行為由規則所準許,而這個規則能夠合理地被預想到所產生的善與任何其他可識別的規則能夠合理地被預想到所產生的善一樣多,該行為就是得到許可的。”[11](219)換言之,在判斷某行為的正當與否時,規則后果主義并不像行為后果主義那樣依據某行為產生的后果而對其進行道德評價,而是依據某行為是否符合某種能夠帶來總體上好的后果的一般規則來對其進行道德評價。我們在試圖依照規則后果主義來為愛國義務辯護時依賴的是何種規則呢?我們依賴的是“分工是一種實現目標的有效手段”這一規則。對于分工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借鑒羅伯特·古丁(Robert E.Goodin)的觀點。在探討特殊義務的正當性問題時,古丁強調,特殊義務僅僅是一些人們用來把道德共同體的一般義務分配給特定的行為者的手段,例如,在一個海灘上,有很多人看著溺水的游泳者在水中掙扎,沒有一個圍觀者是這個人的親近者,也沒有人是更擅長游泳的人,如果所有的圍觀者都試圖提供幫助,那么這只會造成更大的混亂,此時被正式任命的救生員是更適合拯救溺水者的人,“這似乎為我們許多所謂的特殊義務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模式。出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許多一般義務倘若被細分,并且給特定的人分配特定義務以適應這部分任務的需要,就會更有效地完成這些任務。有時這樣做的原因與專業化和分工的優勢有關。有時候它與做好一件事情所需的大量信息有關,也與人們同時處理大量事情所需的大量信息的能力的有限有關”[12](681)。在現實社會中,很多事情是極為復雜的,這對人們處理這些事情的知識和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挑戰。然而,人們有時在知識和能力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這就需要將一些復雜的事情進一步細化,通過分工的方式,讓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分工能夠帶來更大的善,從長遠看能夠帶來更大的利益。依照愛國主義的同心圓模型,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系列的同心圓中,同胞處于同心圓的核心位置,那些處于同心圓模型最核心位置的人是家人和親屬等與人們有著最親密關系的人,與其緊密相鄰的人應該是好朋友或同事等與人們關系較為密切的人,依此類推,處于同心圓模型其他位置的人應該是其他同胞。人們對同胞的需求更為了解,也會更為關注同胞的利益,在背景性正義存在的情況下,依照分工原則,履行對同胞的特殊義務這一做法也將有助于實現人類的利益,這種特殊義務的履行有助于一般義務的落實。
在依照規則后果主義為愛國義務進行辯護時,一個尚需解決的問題是,什么是分工的重要工具?公民身份的確定就是進行分工的重要工具,因此,我們還需要強調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公民身份主要強調公民作為國家這一共同體的成員所擁有的地位,意味著所有擁有這種地位的人擁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公民身份是當今世界各國用于確立每個人的特殊身份的重要手段,我們既要認識到公民身份所體現的將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涵蓋在內的平等性,又要認識到公民身份本身的重要價值。在國家中,公民擁有共同的公民身份,這種共同的公民身份就是一種特殊的關系,涉及公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公民之間的關系。共同的公民身份意味著國家是自己的國家,意味著公民與國家之間以及同胞之間的特殊關系,意味著公民應該優先關注自己的國家和同胞的利益以及需求,這種特殊關系在某種程度上為愛國義務提供了基礎,塞繆爾·謝弗勒(Samuel Scheffler)的“關系性義務”(associative duties)概念可以給我們帶來一種有啟發性的描述。在謝弗勒那里,當今社會有著融合和分化這兩種不同的趨勢:隨著經濟、技術和政治的一體化,融合的趨勢出現了;然而,伴隨著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民族主義的復蘇以及多元文化主義思想的興起,分化的趨勢也在不斷顯現。在這兩種沖突的趨勢中,各種各樣的義務問題就出現了,尤其是如何理解人們對不同的人的義務。謝弗勒認為,常識性道德常常強調,人們除了對有些人擁有一定的一般義務,對某些社會群體的成員和親密關系的參與者還擁有額外的、更大的義務,即關系性義務,“根據一個熟悉的區分,一般義務是我們對一般的人負有的義務,而特殊義務是我們只對那些與我們有某種重要互動或與我們有某種重要聯系的特定的人負有的義務。根據這種區別,關系性義務當然是一種特殊義務。在這個意義上,其他被廣泛認可的特殊義務包括契約性義務(指由承諾、契約或協議產生的義務)、賠償性義務(或對受委屈、傷害或虐待的人的義務)以及感激的義務(或對恩人的義務)”[13](49)。關系性義務存在于各種群體中,人們通常對其家人、朋友、鄰居、同學以及同一共同體的成員能夠產生這種關系性義務,依照謝弗勒立場的內在邏輯我們可以推斷出,愛國義務就是一種關系性義務。這也使得愛國義務成為一種特殊義務,這種特殊義務與每個人對他人的一般義務有所不同。當人們對自己國家和同胞的“特殊義務”與對其他國家及其人民的“一般義務”發生沖突時,這種特殊義務應當占據優先地位,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這種特殊義務應當首先被履行。
我們在關注愛國義務的正當性時主要關注愛國主義的特殊性問題,這種特殊性與同胞關系以及公民身份的重要性有著密切的關系。公民身份是一種擁有內在價值的關系,當人們漠視同胞這種特殊關系時,我們很難說人們仍然重視同胞這一觀念的作用。作為一種關系性義務,愛國義務會帶來某些善,這種特殊關系構成了福祉的基礎。愛國義務的特殊性源于一個人擁有某個國家的公民身份的事實以及公民之間關系的特殊性。在國家中,人們都是國家這個政治共同體的成員,擁有相同的政治權利,他們的命運是密切相關的,共同受到國家的諸多行為的深刻影響,同時,他們又有機會參與國家的公共生活,影響政策的制定。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人們有義務支持其所處的共同體以及偏袒自己的同胞。在愛國義務中,人們通常渴望自己的國家能夠強大,擁有關心國家的福祉和參與公共生活的義務,這些愛國義務對國家本身有著重要的作用,對維系國家這一共同體的生存和繁榮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當然,國家也會影響和保護公民的福祉,為公民提供歸屬感和認同感,提供和平與秩序。
在為愛國義務提供一種規則后果主義的論證方式時,我們是從道德平等出發的,這種證成愛國義務的正當性的做法,可以避免第二節提到的某些學者試圖從相互性的視角出發為愛國義務的正當性進行辯護時面臨的由殘疾同胞引發的問題。無論其身體狀況如何,無論其是否為共同體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和道德價值,都應該得到平等的尊重,這種做法并沒有將殘障同胞置于愛國主義的偏袒范圍之外。道德平等與我們強調的分工原則并不矛盾,在背景性正義存在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可以關心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都可以關心自己的同胞,每個人都有關心他人的特殊義務。另外,在依照規則后果主義來證成愛國義務時,除了明確強調“分工是一種實現目標的有效手段”這一規則的重要性,我們還強調公民身份是一個尤為重要的概念。由公民身份這種特殊關系所產生的義務與道德平等并不矛盾。公民身份與道德平等是兩個相通的概念,平等性是公民身份的重要特征之一,擁有一個國家的公民身份意味著公民擁有平等的地位(包括道德平等、法律平等、政治平等和機會平等等內容)。愛國主義強調公民應該熱愛和忠誠于自己的國家,這一原則允許人們偏袒自己的國家,然而,它也是一種可以被普遍化的原則,只要人們在背景性正義存在的情況下表達愛國義務,任何人都可以熱愛和忠誠于自己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