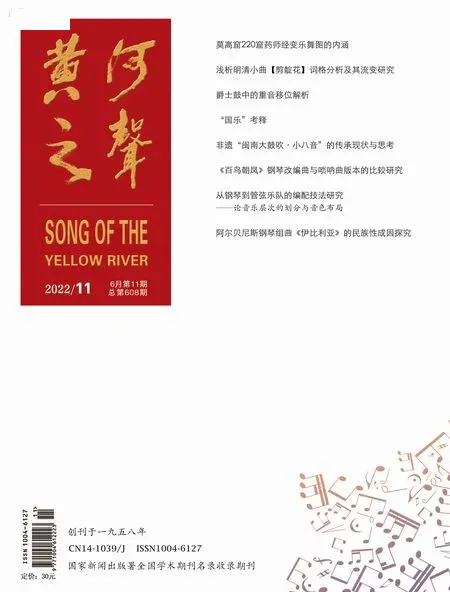非物質文化遺產下膠州秧歌的傳承與保護
胡慧杰
引 言
膠州,是一座有著較為悠長歷史的古城,建成距今已有五千余年。自宋元以來,膠州的港口文化就甚是繁榮。經濟和文化的繁榮活躍,也帶動了膠州音樂和舞蹈藝術的發展,以其獨特的人文底蘊孕育了獨具魅力膠州秧歌。
被譽為山東三大秧歌之一的膠州秧歌,就是一朵在膠州沃土上滋潤成長起來的傳統民間舞蹈藝術的奇葩,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藝術特色,據記載已有近三百年的歷史了。膠州秧歌在其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舞蹈動態和神態,被人們譽為深得人民大眾的喜歡。膠州秧歌不同于“鼓子秧歌”的氣勢磅礴,粗獷豪放,也不同于“海陽秧歌”的熱烈奔放。膠州秧歌以動作中的男剛女柔形成強烈的對比而具有藝術魅力,這個特點正是由于膠州作為一個商貿出口的口岸,匯集了大江南北的優秀品質而成,男子的剛毅正是我國北方民族豪放、剛毅的特征,而女子的柔美正是融入了江南水鄉女子的委婉,秀麗的姿態而獨具魅力,正是這種強烈的對比,才使得膠州秧歌有如此豐富的角色和動律特征,也正是這種強烈的對比,才能更讓欣賞的人們產生強烈的震撼和共鳴。
膠州秧歌起源并流行于膠州地區,以其獨特的舞蹈動態和技藝,廣受贊譽,被當地人稱為“三道彎”、“扭斷腰”。膠州秧歌的藝術特色跟別的秧歌不太一樣,不是單一地強調粗獷豪放,而是強調通過男子的剛強與女子的柔弱形成對比來放大自身的藝術特點。這與膠州當地人民生活習慣、環境條件等因素的影響有關。因為膠州是北方一個重要的港口城市,所以自古以來都是南北文化交流比較密集的地方,自然在生活和勞動中就逐漸吸納了江南的柔美,在結合北方原有的豪放,逐漸形成了膠州秧歌這樣一種剛柔并濟、對比強烈的音樂舞蹈藝術形態。正因為膠州秧歌兼容南北文化,所以更加能夠讓觀眾產生共鳴和強烈的興趣,由此得以百年流傳至今。
但目前,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展,我國音樂和舞蹈藝術受到了越來越多來自國外藝術審美的影響,大眾審美逐漸向流行音樂和街舞、韓舞等方向傾斜。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的傳統音樂和舞蹈藝術,如秧歌戲等,就漸漸淡出大眾的視野,生存的發展的空間也越來越狹小。膠州秧歌作為一類非常傳統的地方戲曲,其目前的傳承狀況就特別令人擔憂。是以本文希望通過全面剖析膠州秧歌的藝術特征和歷史文化,進一步探尋促進其保護和傳承的有效途徑。
一、膠州秧歌的發展歷程
膠州秧歌作為我國本土傳統的一類戲曲,它具有著悠長的發展歷史,其形成背景與演變歷程皆與膠州當地的歷史人文息息相關,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一)膠州秧歌的起源說
1、清朝詞本起源說
關于膠州秧歌的起源,有較多歷史資料佐證的一種說法,就是清朝詞本起源說。相傳在清朝咸豐年間,有一位叫宋觀煒的才子,將膠州當地口頭傳唱的民謠秧歌匯總,進行二次創作,編制成了《秧歌詞》一書,詳細記錄了十一首膠州秧歌的唱詞和舞蹈表演技法,并連帶著對當時膠州秧歌的角色和服裝等一一作出了詳細的描述,自此膠州秧歌方成體系,逐漸流傳下來。這一段歷史在《膠州市文化志》中便有記載。
而在此前乾隆年間的《膠州志》中記載的膠州秧歌成為雜劇,還沒有明顯的舞蹈表演元素和劇情設置,而在《秧歌詞》中就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劇目設計。由此也可以推測,膠州秧歌約莫就是在清朝乾隆年間到咸豐年間這一段時間內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就是清朝詞本起源說。
2、宋元文化起源說
一種觀點認為,膠州秧歌的雛形,形成于宋元時期,是當地勞動人民在農忙時即興傳唱的小,供農民們勞作時消遣放松用調。而且膠州秧歌之所以有南方秧歌的元素,正是因為宋元時期膠州作為重要港口,商貿發達,南來北往的就形成了文化的交融,因而南方秧歌傳入膠州,經當地百姓的改良后成為自成一派的膠州秧歌。
而除此之外,宋元文化起源說還認為膠州秧歌的劇目編排與元雜劇關系緊密。膠州秧歌共分六個行當——膏藥客、鼓子、小嫚、扇女、翠花、棒槌,與元雜劇中的角色分類比較相似,正好可以對應生、旦、凈、末、丑。膠州秧歌表演的戲臺子與宋元時期的戲臺構造也是相似,皆為立柱四方臺,四面通透。可見膠州秧歌確與宋元時期的雜劇文化也有所關聯。但筆者認為,僅僅憑借形式上的相似和契合就說膠州秧歌起源自宋元時期的港口文化和雜劇藝術,還不夠嚴謹,有待進一步考究[1]。
(二)膠州秧歌的發展沿革
1、小調秧歌時期
小調秧歌時期,是膠州秧歌發展的初始時期,主要是由膠州秧歌藝人將農民田間農忙哼唱的小調進行提煉、加工,不斷改良演變成具有特定音律和唱詞的小調秧歌。這樣的膠州秧歌表演形式也越來越多地被應用到節日慶典的表演中去,進而得到了更深、更廣的發展。這一時期的膠州秧歌,以唱為主,輔以簡單的舞蹈表演,主題以展現鄉土風情和生活瑣事為風格特征,廣受地方百姓喜愛。
2、小戲秧歌時期
戲秧歌時期,是繼小調秧歌之后的又一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膠州秧歌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膠州秧歌中戲目表演的成分占比加重,唱戲演出的角色行當也逐漸細分出來,出現了開戲前跑場、暖場的角色設計,即后來的膏藥客串角色,這一環節稱為“墊戲”[2]。
小戲秧歌時期的膠州秧歌主題圍繞展現民風民俗的小戲目展開,整體故事情節和人物塑造都已初成體系,整個表演嚴格由劇情、角色、曲牌構成,已經慢慢從村民們自娛自樂形式的表演轉變為具有商業性質的演出,逐漸成了一項手藝人賴以營生的藝術[3]。
3、文武秧歌時期
文武秧歌時期,是膠州秧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一時期膠州秧歌的特征是出現了一定的風格分化,延伸出了文派和武派兩個體系。其中,文派善辭賦,故事多以倫理、愛情等為主題,曲風也比較婉轉悠揚,人物塑造以溫婉的扇女和靈動的小嫚為主,武打動作設計較少;而武派則恰恰相反,尤以花式繁多、難度較大的武打動作為戲目亮點,故事情節簡單,人物形象塑造愛憎分明,有明顯的北方豪放大氣的戲曲風格[4]。
在文武秧歌時期,文派和武派多有藝術方面的切磋,也各自擁有不同的受眾群體。可以說,在這兩派的不斷切磋發展下,膠州秧歌藝術也相應得到了更多的改良發展,在我國的戲曲文化歷史中逐漸嶄露頭角,釋放出屬于自己獨特風格的光芒。
二、膠州秧歌的藝術特征
(一)角色風格特征
膠州秧歌中有六個角色,其中三個男性角色分別是膏藥客、鼓子、棒槌,三個女性角色分別是翠花、扇女、小嫚。每個角色在表演中都有固定的形象定位,其中膏藥客是作為暖場主持一樣的存在,負責插科打諢,逗觀眾開心,以此來調節表演開場的氣氛,一般都由略有文化和生活經驗的口齒伶俐的人來扮演;鼓子則是扮演家庭中年紀較長的男性角色,對應老生的行當,角色特點詼諧、豪放;棒槌則是扮演年輕男性的角色,舞蹈動作技巧最為復雜難學,以身手敏捷、英勇聰穎為主要人物特征;而女性角色中,翠花與鼓子對應,扮演家中年長女性,人物性格潑辣而有威嚴;扇女則是扮演青年女性,角色溫順嬌婉,多出演媳婦、嫂子的角色;小嫚則是膠州地區對于待嫁閨女的統稱,人物形象天真爛漫、活潑善良[5]。
(二)服飾風格特征
膠州秧歌的這六個角色,分別有著各自獨特的服飾造型風格,具體梳理如下。
一是膏藥客。膏藥客的服飾大體以清朝時期男子的便裝款式為主,手執雨傘和串鈴,從外形上看頗似一個江湖術士。有時還會戴上一副墨鏡,以增加詼諧之感。
二是鼓子。鼓子的角色一般比較沉穩,身著對襟上衣,根據不同邊沿的需要,色彩搭配略微會有調整,但不變的是頭上要戴黑色或藍色的帽子,并在右邊髪角處插大紅色絨球,嘴上粘短胡須,清末民初時腰間還需別鼓,后換成長煙槍,儼然一個威嚴老者的形象。
三是棒槌。棒槌同樣戴帽,但絨球別于帽子正中,身穿紅色對襟上衣,下穿綠色燈籠褲,腦后還別一條長邊,腰間系一對棒槌。
四是翠花。翠花頭戴兩條簇花緞帶,前額扎一朵繡花,身穿與鼓子同色的對襟上衣,袖口鑲白邊,腰間系黑色繡花圍腰,清末民初時身背“翠花包”,即一種沿街兜售小飾品的布包,后來簡化過就不背了。
五是扇女。扇女手執折扇和一條長方巾,多為綠色,搭配粉紅的簪花綢子頭飾;上身穿粉紅色大襟上衣,胸前系繡花肚兜。
六是小嫚。小嫚的服飾顏色比較艷麗,頭上簪花戴綢,以大紅和黃色為主,前額系珠簾,后腦留一根長辮子,著裝對照清朝時期未出閣的女子裝束。
(三)動作風格特征
在膠州秧歌的中額六個角色中,一般來講,膏藥客作為暖場角色,并沒有過多的表演動作,主要的動作技術還是集中在其他五個角色上。
其中,鼓子作為年長男性的角色,其舞蹈動作主要是掌握一個甩袖的技巧,以此來顯示自身角色的粗獷豪放,搭配的要掌握弓箭步、舞花步等,通過步子和甩袖的結合來塑造一個睿智而不失風趣的長者形象。
棒槌與鼓子相似,在舞蹈動作風格塑造中都追求力量感和控制力,其最主要的動作技巧就是舞棒花,即利用棒槌來舞出腰花、腿花、懷花等不同的花式招數,加上前后空翻、掃堂腿、撲打等動作,來塑造一個孔武有力的年輕男子形象。
而女性角色中,扇女舞扇,配以提鞋、劈線等動作,與生活勞動息息相關;翠花的動作與扇女相似,遵循基本的扭步和搖手;小嫚則相對來講要更活潑靈動些,除了扭步、搖手,還有一些小碎步跑跳的動作,塑造人物天真爛漫的性格。
隨著時代的發展,膠州秧歌的動作風格隨機本保有傳統的元素,但很多技術要求較高的武打動作,如弓箭步翻身跳馬、凌空于腿下擊打棒子等,已經或多或少地被簡化或者刪去,很難看到如當年一般精彩的打斗場景了。
(四)曲牌唱腔特征
膠州秧歌是一種地方性的戲曲歌舞表演,其曲牌唱腔的特征,也是其藝術特色的一部分。其中,曲牌分為伴奏曲和演唱曲,伴奏曲一般由鑼、鼓、嗩吶等來進行演奏。而在演唱曲中則加入了更多的民族樂器,如鐃鈸等,同時也應用小白馬、得勝令、趕集、繡花燈等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間小調來進行演唱,融入劇情編排,以豐富舞臺表演效果。
至于唱腔方面,膠州秧歌素來以剛柔并濟,豪放而不失婉轉而著稱。伴隨著劇情的發展,和人物角色的轉換,伴奏曲牌會有粗獷和柔情兩個方面的轉化,而角色的唱腔先后也會有所改變。其中,最明顯的一個特征是節奏的變化,急促而穩健的鼓點、一氣呵成而咬字清晰的唱腔,配之以熱烈奔放的舞蹈動作,共同展現出了膠州秧歌獨特的感染力和舞臺表現力。
三、膠州秧歌的發展現狀
(一)膠州秧歌目前的演出現狀
近年來,隨著我國非遺保護工作的推進,膠州秧歌傳統戲曲音樂和舞蹈藝術的傳承與發展也重新引起了人們的重視,開始進行了一系列的實踐活動。其中,傳播和舉行的比較廣泛的要數“膠州市秧歌大賽”及秧歌節的表演。2009年,在膠州市文化局和文化館的協助下,膠州民間秧歌隊得到較好的組織,隆重舉辦了“膠州市秧歌大賽”,獲得了較好的宣傳和表演效果。但從這些表演中也不難發現,隨著老一輩藝人的老去,膠州秧歌高難度的舞蹈動作和表演技藝得不到傳承,現在的表演動作難度明顯降低,遠不如當年那般精彩絕倫。
除了像這樣由政府牽頭舉辦起來的大型節日表演和競賽活動之外,膠州秧歌現在比較活躍的表演的其實是膠州當地城區的廣場等休閑場所。截至目前,膠州的許多城區,都已經相繼建立起來可供居民休閑娛樂的文化廣場。這些廣場也成了當地居民表演膠州秧歌的一個重要場所。據筆者實地考察結果顯示,日常在廣場上跳擺手舞的人群中,有79.6%是中老年人,而且跳舞的時間段集中在晚飯后的一兩個小時。雖然看似膠州秧歌在廣場舞體系中得到了所謂“活態化”的發展,但實際上因為跳舞的都是中老年人,思想比較固化,不愿意接受新花樣,只是跳著固化而有些變形的舞蹈動作,能否持續發展下來也是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
(二)膠州秧歌在學校課程開設的情況
目前,在膠州多個地區的小學校園中,順應國家關于非遺入小學校園的實踐政策號召,開展了一系列學習和表演膠州秧歌的主題活動,有些學校還以膠州秧歌為教學內容開設了拓展性課程。由于不同地區非遺保護的側重點不同,所以從實施現狀上來看,只有膠州秧歌資源比較集中且突出的幾個地區是真正的嘗試將膠州秧歌藝術帶入學校課堂,但其實踐效果也是良莠不齊。如有些課程開設只側重膠州秧歌相關知識的程式化普及,而不注重藝術的實踐體驗,難以激發學生們的學習興趣,長此以往,膠州秧歌非遺課程的開設難免流于形式。
也就是說,在學校,膠州秧歌的課程化傳承只是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但在其推進的過程中也難免遇到一些困難和阻力,暴露出來一些問題,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以期進一步完善解決。
四、膠州秧歌的傳承與保護
(一)膠州秧歌的傳承與保護面臨的問題
1、外來文化沖擊,生存環境受限
隨著時代的發展,山東地區許多廣泛流傳和發展膠州秧歌的村落已經不再是原來環境閉塞的情況了,因為跟外界的接觸多了起來,所以這些村落中年輕一代的想法和審美也漸漸發生了轉變。對于舞蹈藝術來說,其魅力的所在,是源于觀眾的審美、文化的內涵等多個方面的,具有隨著環境改變而改變的特性。也就是說,在外部環境有較大改變的情況下,人們的審美改變了,膠州秧歌如果繼續保持傳統一成不變的話,其生存環境必然受限。
因為外來文化對于膠州秧歌起源地年輕一代的沖擊比較大,所以他們對膠州秧歌的美感和價值有了新的體驗和判斷,各種不同的角度和標準相結合,創造出了膠州秧歌在新時代的新定位。他們傾向于將其作為歷史遺跡一般的內容圈起來,認為這是具有歷史內涵的一種藝術形態,但不認為膠州秧歌可以再次成為符合時代審美和發展的舞蹈藝術。從目前來看,也只有少部分的人真正在關注和關心膠州秧歌活態化的傳承和發展。可見膠州秧歌因外來文化的滲透,而喪失了原本生存和發展的有利環境,下一步需努力改善。
2、社會發展迅速,傳承隊伍銳減
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我國各個地區的交通和經濟日漸發展起來,由此,原本經濟落后的村莊也改變了原來交通閉塞的情況。年輕人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走出鄉村,去接觸更加發達的城市文化,漸漸地沖淡了他們身上對于原有鄉土藝術文化的認知和意識。在這樣的背景下,膠州秧歌的社會價值得不到明顯的體現,所以也逐漸失去了對年輕一代的吸引力。尤其是在膠州秧歌原流傳地的年輕人接受了現代化的生活理念和價值觀之后,就很少有人愿意繼續留在鄉村,固守一方水土和文化。就這樣,膠州秧歌的傳承隊伍銳減,越來越難找到愿意學習膠州秧歌的后人,就連膠州秧歌的服飾改良創作都后繼乏力,更別將膠州秧歌提作為事業來發展,極大限制了其在新時代的活態化傳承。
而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舞蹈藝術來說,一定的群眾基礎是其得以繼續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在膠州秧歌的傳承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其實是人,只有擁有能夠欣賞、認同,并且愿意學習膠州秧歌的群眾,膠州秧歌才能繼續傳承下去。否則,即便是舞蹈的視頻、唱詞的音頻等資料保存得再好,也難以實現活態化的發展。就目前來看,膠州當地的膠州秧歌舞者,很少有成規模的、體系化的表演隊伍,很多都是由年齡、水平等參差不齊的群眾組成,靈活性和規范性欠缺,同時可以看出來年輕人的比例較少,存在傳承斷層的現象。很多年輕人認為膠州秧歌近年來的蓬勃發展,只不過是借著國家大力倡導促進傳統藝術發展政策的支持,暫時性的繁榮一陣子,并不認為具有深入學習甚至是當作職業的價值。可見,在群眾基礎這方面,膠州秧歌還是相對薄弱一些,亟需政府及媒體等進行正確的思想觀念引導。
3、保護方向偏移,忽略活態傳承
近些年來,膠州秧歌的保護與傳承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但是目前已有的對于膠州秧歌的舞蹈動作、戲曲唱腔和歷史發展過程大多都被整理和保存為書面及影像資料,進行館藏展覽。就目前來看,膠州秧歌相關展示資料的保存工作已經做得比較完善了,但同時我們也發現這樣物化的、固態的保存方式,會讓膠州秧歌這一項舞蹈和戲曲藝術慢慢脫離現實社會活動,成為被封存在博物館中的藏品,進而喪失其原本的社會價值。
在膠州秧歌的保護與傳承中,只有活態化的傳承是能夠適應時代變化的科學的方式。其實我們保護膠州秧歌藝術的最終目標,應該是讓它能夠繼續流傳下去,如果只是重視資料的保存而不管其動態的發展,那么注定是難以達到應有的保護效果。此外,筆者在調研中也發現了,目前在膠州秧歌藝術的傳承中,比較多的人還是持有固化的觀念,認為應該保存膠州秧歌最原始的表演形態和服飾造型,而一味地拒絕現代化的改編和創新。這樣的觀念,或多或少也影響了膠州秧歌在新時代的活態化傳承和保護進度。
(二)膠州秧歌的傳承與保護面臨問題的解決策略
1、促進膠州秧歌藝術的創新發展
對膠州秧歌藝術進行創新發展,是對其進行活態傳承的核心步驟。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在舞蹈動作方面進行改編創新。膠州秧歌作為廣泛流傳于山東膠州一帶的一種歷史悠長的舞蹈藝術文化,其發展本身就是由先民經過歷代的不斷實踐改良出來的,具有活態化的性質。我們在傳承的時候,固然要重視膠州秧歌舞蹈表演形態中一脈相承的傳統元素,但也大可不必故步自封,不敢進行創新。恰恰相反,只有不斷地基于現代化審美對膠州秧歌的舞蹈動作進行創新和改良,才能讓它與社會發展同步,繼續在當前的文化環境中尋求自身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和機會,實現活態化的有效傳承與保護。
二是在曲牌唱腔方面進行融匯創新。傳統的膠州秧歌曲牌唱腔,有著濃濃的地方特色和歷史特點,在新時代具有區別于其他樂曲的魅力所在,但同時也與現代大眾的音樂審美有一定的距離。要實現膠州秧歌唱曲的活態化的傳承,就是要讓其在新時代找到全新的發展土壤。盡管膠州秧歌在當代的生存環境已經發生的較大的變化,但其傳承多年的唱腔藝術,必然還存在著能夠在新時代繼續發揚光大的充滿魅力的元素。只需要結合新時代的審美和文化的交流,積極融入創新,就能夠更好地放大這些元素,讓年輕人重新對膠州秧歌產生興趣,以幫助其適應時代發展,達到傳承目的。
三是在服飾造型方面進行改良發展。傳統的膠州秧歌服飾造型比較固化,喜用大面積撞色搭配,色彩飽和度較高,在當時可以更好地突出人物形象,但以現代的審美來看不免有些俗氣而缺乏時尚感。針對當下年輕人喜歡帶有一點灰調的“莫蘭迪”服飾色彩搭配,膠州秧歌藝術可以在服化道上下點功夫,進行改良創新,以引起年輕人的注意和喜愛,實現其在新時代的自發傳承。
2、完善膠州秧歌當前活態化傳承機制
膠州秧歌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就目前來看,膠州當地雖對其有采取一定的保護策略,但總體來看都偏向于靜態的、物化的保存,缺乏科學的活態化傳承機制。要想更好地把膠州秧歌藝術傳承下去,就要盡快完善膠州秧歌當前的活態化傳承機制。這主要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一是要轉變偏向于保存膠州秧歌藝術的保護觀念,重點探索其活態傳承的方法。一方面,政府要加強投資和管理,建立和完善保存膠州秧歌藝術現存資料的相關機構,不斷提高工作人員的水平和質量。同時,另一方面,要將重心放在現實中膠州秧歌活態的表演創新發展,積極對公眾進行正確的引導,樹立活態傳承膠州秧歌的觀念。
二是要健全傳承人保護機制,不斷壯大傳承人隊伍。這個保護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要為傳承人創造更好地發展膠州秧歌的客觀環境和物質環境,讓傳承人可以專心地致力于膠州秧歌活態化傳承的相關研究和實踐;另一方面,要重視宣傳機制的建立和維護,宣傳膠州秧歌的創新成果,擴大膠州秧歌的影響,給傳承人信心,吸引更多的年輕人來學習,不斷壯大傳承人隊伍,以保護膠州秧歌傳承人隊伍的延展性和可持續性。
3、推動膠州秧歌非遺入校園教育活動
非遺入校園,是我國為了更好地促進各類為物質文化遺產而制定的一項政策。近年來,膠州及附近地區各學校響應政策的號召,圍繞膠州秧歌展開了課程實踐,雖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果,但還有較大的進步空間。因為青少年是傳承膠州秧歌的好苗子,可以說,要切實完成膠州秧歌藝術的活態化傳承,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推動膠州秧歌非遺入校園的教育活動,建立理論與實踐并重的膠州秧歌藝術鑒賞和體驗課程,并編制與推行鄉土特色教材,讓膠州秧歌在課堂中實現創新性的可持續的發展。同時,也可以鼓勵教師進行與膠州秧歌活態化傳承相關的教育教學研究,促進科研成果產出,推動膠州秧歌在新時代的傳承發展。
總的來說,為了實現膠州秧歌藝術的創新發展,首先要轉變人們固化的觀念,激起膠州秧歌愛好者及傳承人的創新意識。其次,可以多研究膠州秧歌藝術的核心元素,并進行提取保留,至于其他的輔助表演形式,可以順應時代的發展做出改變。最后,觀眾的欣賞和體驗效果,是檢驗膠州秧歌藝術創新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建議結合校園課程的推進,多聯合學校和地方舉辦改編的擺手舞表演活動,通過觀眾的反饋信息,進一步驗證創新效果,不斷完善、提升,以實現擺手舞在新時代迅速實現活態化傳承。
結 語
膠州秧歌,是山東三大秧歌之一,也是膠州音樂舞蹈藝術文化中突出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當地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有著較大的傳承和保護價值。隨著時代的發展,傳統的舞蹈藝術在不斷流逝,這也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在傳統與現代、國內與國外的舞蹈文化交融和沖擊下,膠州秧歌藝術如何實現活態化傳承與發展還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探索推進。針對目前膠州秧歌傳承缺乏活態觀念和舉措的現狀,本文通過剖析膠州秧歌的歷史起源、藝術特征及發展現狀,進一步挖掘了其在學校中作為非遺課程實現再發展的可行路徑,希望引起各界的重視,推動膠州秧歌活態化傳承的實踐,讓其在新時代繼續釋放獨特的魅力和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