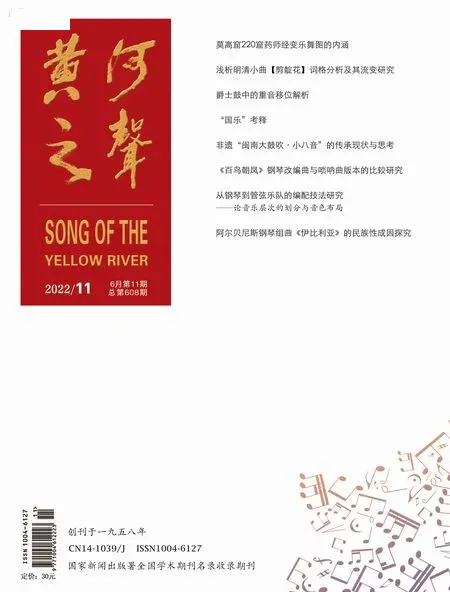論歌劇《江姐》的藝術(shù)特征
單文群 / 李勝男
引 言
歌劇是一種綜合藝術(shù)的表現(xiàn)形式發(fā)展到現(xiàn)在逐漸形成較為完整的體系,許多經(jīng)典歌劇呈現(xiàn)于世界。中國歌劇受到所處時(shí)代、中外文化的影響。在融合和融合文化選擇方面,審美追求,精神內(nèi)涵,審美功能等因素的過程中,審美風(fēng)格形成并逐步完善。
歌劇《江姐》整部戲劇講述了中國共產(chǎn)黨與反動(dòng)派之間在矛盾和勇敢的斗爭中,涌現(xiàn)的英雄人物及其愛國精神。
這部歌劇將四川民歌為主。以中國傳統(tǒng)戲曲藝術(shù)作為根基,它融入西方歌劇的藝術(shù)形式還有歌唱技巧,將京劇、戲劇、越劇等與西方歌劇相融合。令人震驚的是他不僅成為一個(gè)紅色經(jīng)典,還成為教導(dǎo)后人的一個(gè)文化藝術(shù)模式。1964年《江姐》于北京進(jìn)行首演。屆時(shí),歌劇《江姐》口口相傳,仿佛變得家喻戶曉,并于1964-1965年,進(jìn)行了近乎286場的演出,創(chuàng)造中國戲曲史上的一個(gè)奇跡。通過理解和實(shí)踐,了解歌劇中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特色,便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其內(nèi)容,更加生動(dòng)地詮釋其情感。
一、歌劇《江姐》的發(fā)展?fàn)顩r
(一)我國民族歌劇的發(fā)展
因?yàn)槭艿叫挛幕\(yùn)動(dòng)背景的影響,中國的早期民族歌劇在10年的時(shí)間,創(chuàng)作編排了36部兒童歌舞劇。雖然作品簡單而缺乏更多的元素,但它已經(jīng)具有歌劇的特點(diǎn)和模樣,基本符合了其對于歌劇所要必備的藝術(shù)要求。1935年,《揚(yáng)子江風(fēng)暴》由田漢和聶耳創(chuàng)作受到人民的高度評(píng)價(jià),其形式與兒童歌舞的形式大不相同,語氣源于勞動(dòng)人民的生活,民族特色明顯。從以往的兒童舞劇到《揚(yáng)子江風(fēng)暴》,都是中國早期民族歌劇探索的結(jié)果,風(fēng)格和內(nèi)容與真正的歌劇有所不同。現(xiàn)代戲曲原型或歌舞劇,但它為后來的現(xiàn)代戲曲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chǔ),為后來的民族歌劇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chǔ),提供了較好的客觀條件。
1942年,進(jìn)行了大規(guī)模的生產(chǎn)運(yùn)動(dòng),廣大民眾參加了“秧歌運(yùn)動(dòng)”,出現(xiàn)了具有群眾基礎(chǔ)和時(shí)代氣息的歌劇。解放區(qū)士兵和人民的和諧生活為素材,真實(shí)動(dòng)人,輕快活潑條件。抗戰(zhàn)時(shí)期,延安進(jìn)行“文藝整風(fēng)”,在中國共產(chǎn)黨對文化藝術(shù)的重視下,中國民族新歌劇由小變大,創(chuàng)作出眾多有中國民族獨(dú)立風(fēng)格,中國民族獨(dú)立氣質(zhì)的新歌劇藝術(shù)作品。
(二)《江姐》的創(chuàng)作背景和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
就近代歌劇作品來看,《江姐》算是其中最為意義重大,最有藝術(shù)價(jià)值的一部民族歌劇。“江姐”用自己的音樂內(nèi)涵,證明了自己的強(qiáng)大生命力。它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藝術(shù)舞臺(tái)上,從未被遺忘,并且不斷得到改進(jìn)。同時(shí)戲劇中也加入了激烈沖突,樹立“江姐”英雄形象。
二、《江姐》的音樂創(chuàng)作特點(diǎn)
音樂創(chuàng)作這樣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來自審美體驗(yàn)。音樂的創(chuàng)作實(shí)際上是打破了作者的思想意境,掰開了揉碎了然后具象化,然后形象地讓人們聽到歌劇是否可以讓人們記住,這取決于音樂本身的生命。自我的生命是否能夠“聲入人心”,可以表達(dá)社會(huì)意義和時(shí)代精神。
創(chuàng)作是實(shí)踐的根本,表演和欣賞都是以創(chuàng)作為前提。作為一部歌劇,它更注重音樂創(chuàng)作的質(zhì)量。由于音樂創(chuàng)作的卓越表現(xiàn),世界上涌現(xiàn)出不少經(jīng)典膾炙人口的好劇,如《塞維利亞的理發(fā)師》、《卡門》、《圖蘭朵》不僅僅是通過舞蹈,燈光和服裝這些因素讓人們記住。不變只為音樂本身魅力。音樂賦予它們強(qiáng)大的生命力。喬治克拉姆說:“我相信音樂反映了人類靈魂甚至超越語言的最深層的能力。”歷史向我們證明了,好的音樂創(chuàng)作帶來的有生命力的音樂深受不同時(shí)代的大眾喜愛,并跨越國家。歷史證明,《江姐》是一部凝結(jié)了當(dāng)代音樂創(chuàng)作者智慧的具有強(qiáng)大藝術(shù)生命力的民族特色歌劇。
(一)歌曲和曲式結(jié)構(gòu)的特點(diǎn):以《紅梅贊》為例
1、《紅梅贊》歌詞的寫作特點(diǎn)
從題目《紅梅贊》可以看出,在詞曲的創(chuàng)作中同時(shí)包含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對作品和人物形象刻畫的思考。“比興”是一種古代詩詞寫作的常用技巧,意在以自然景物比擬其他事物,早在周朝《詩經(jīng)周南桃夭》這首詩中將桃花比擬為新嫁娘,這一首新娘賀詞大概意思為:詩人看到桃花盛開柔嫩的枝丫,待放的花骨朵,好似新娘年輕貌美婀娜翩翩,這種手法就是比興的手法。同樣,《紅梅贊》就運(yùn)用了比興的寫作技巧,把人物“江姐”比作紅梅,從剛開始革命同志一起奮斗的欣喜,到抗戰(zhàn)的不卑不亢,再到之后就義的寧死不屈,塑造了人物江姐如同“獨(dú)立寒天報(bào)早春,一縷香魂慰世人”的革命精神。
為何要將江姐比作“梅”呢,其實(shí)這里也點(diǎn)出了我們中華傳統(tǒng)文化,早在明代,黃鳳池輯有《梅竹蘭菊四譜》,梅、竹、蘭、菊作為四君子,已成為中國畫的傳統(tǒng)題材,在歷代的詠物詩中,梅花這個(gè)意象是經(jīng)常被使用的,梅花有一種自足中的孤傲和冷靜,淡定而不招搖,迎寒開放美麗絕俗,把人比擬做自然植物,我們由此也可以理解人格與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多用托物言志的手法,與古代的文人騷客不同的是,江姐的境遇不是懷才不遇的孤傲,而是對于革命勝利的渴望以及必死必勝的決心。也就是如此,從《紅梅贊》的歌詞寫作方面,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核心象征,歌詞是吸收了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來進(jìn)行寫作的。
2、《紅梅贊》的曲式以及音樂特點(diǎn)
歌曲可以分為兩個(gè)部分,結(jié)構(gòu)較為方整。唱段中采用大量的戲曲拖腔技法,速度較為緩慢,使旋律整體上給人一種娓娓動(dòng)聽的感覺。在調(diào)性上,該曲是民族七聲F徵調(diào)式,這種調(diào)式從聽覺上具有強(qiáng)烈的民族氣息。從織體上來看,該曲使用了較多的十六分音符和裝飾音,使旋律更加豐富,細(xì)節(jié)處理細(xì)微,增加作品流動(dòng)性。
3、“板腔體”的借鑒
在創(chuàng)作上模仿了西方歌劇藝術(shù)的詠嘆調(diào)框架。其中還融入了板腔體的元素,融合了西方聲樂演唱的元素。使用慢板并與當(dāng)時(shí)的場景相連,反映出主角的情感特征。在音樂上表現(xiàn)出情緒上升,逐漸推向高潮,引出主題,與群眾產(chǎn)生強(qiáng)烈共鳴。不斷出現(xiàn)的重復(fù)樂句也表示江姐最后就義之前對無法對祖國繼續(xù)效力的無奈之感和遺憾。
有些部分采用了中國板腔體形式,自由緊密的伴奏織體將音樂藝術(shù)情感和共鳴推向高潮。與之前不同的是,迅速從善良的母親的角色轉(zhuǎn)變?yōu)閷ψ鎳聵I(yè)的英雄奉獻(xiàn)的革命形象。這首作品一直是在高音徘徊,最后樂句末尾是整首歌的最高音,基于B宮徵調(diào)式上運(yùn)用拖腔,感情豐富綿長。
其實(shí)中國民族歌劇就是要在不斷創(chuàng)新中不斷回歸,《江姐》在遵循原作的基礎(chǔ)上由于反復(fù)運(yùn)用穿插了板腔體,聽覺上給觀眾帶來的東西更為豐富飽滿。這種緊拉慢唱的節(jié)奏將人們更好的代入故事環(huán)境,讓人們仿佛置于故事中發(fā)現(xiàn)和表達(dá)作者想要表達(dá)的東西。
5、川劇“幫腔”的運(yùn)用
《江姐》歌劇中借鑒了很多川劇元素,其特點(diǎn)是:織體自由,行腔自由,使用拍板和鼓點(diǎn)進(jìn)行基本伴奏用于歌唱。高腔一般以幫,打,唱三者同時(shí)進(jìn)行,一唱一和兩兩相和,綿長有力,高亢恢宏。內(nèi)心的感受,或作為第三者評(píng)價(jià)扮演的角色。幫腔在整部歌劇中起到了相當(dāng)大的貫穿輔助作用。
(二)音樂風(fēng)格的對比
審美價(jià)值的種類在本歌劇中可分為優(yōu)美、壯美。從基本的邏輯和直觀的感受來看,這兩者是最早實(shí)現(xiàn)最為客觀的審美價(jià)值和標(biāo)準(zhǔn)。他們萌生于物質(zhì)實(shí)踐和精神實(shí)踐領(lǐng)域,人類可以自由地控制,自由創(chuàng)造,輕松地讓人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帶來心理和精神上的愉悅。從價(jià)值載體中,讓人感覺到輕柔、安逸、緊密,甚至于讓人有昏昏欲睡的特點(diǎn)的事物為標(biāo)準(zhǔn)。優(yōu)美一般具有靜謐,和諧,安逸等特征。美好的心理特征體現(xiàn)了客體與主體的和諧。在審美活動(dòng)中,優(yōu)美客體一般用自身表現(xiàn)出的審美價(jià)值體現(xiàn)來與觀看者產(chǎn)生共鳴。主體幾乎以一種溫柔的感情接受它們并感受它們。因此,美感來自對象本身的和諧和完美的感覺,以及對象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把握。
在《江姐》這部優(yōu)秀歌劇中,通過四次復(fù)排,對音樂編曲與和聲進(jìn)行了一些調(diào)整,音樂的發(fā)展更加完善。在觀賞音樂中,優(yōu)美和壯美的結(jié)合飽滿體現(xiàn),滿足了觀眾的審美需求。
(三)音樂與戲劇的結(jié)合
歌劇的兩個(gè)重要組成部分,一是音樂,二是戲劇,兩者結(jié)合的藝術(shù)表演形式,被稱為歌劇。這些歌曲的比例和地位并不重要,而且后代所理解的歌劇實(shí)際上是完全不同的。把它們稱為音樂的戲劇。在歷史的推動(dòng)和人們審美要求漸漸提高的前提下,音樂在歌劇中的所占部分也變得尤為重要。雖然戲劇性的特征已經(jīng)部分曲折和短暫,但它仍然主要是沿著保持和加強(qiáng)歌劇藝術(shù)的戲劇性特征為前提前進(jìn)的。
三、由《江姐》引發(fā)的對近代民族歌劇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思考
(一)以民族音樂為根基
相比西方歌劇藝術(shù)來說,中國民族歌劇中融入了較多的中國戲曲技法,中國戲曲板腔中集成有“唱念做打”四要點(diǎn)為表演亮點(diǎn)和特色,相比起西方藝術(shù)作品的浪漫風(fēng)格,中國民族戲曲舞臺(tái)中表達(dá)多為程序化虛擬化,寫詩寫意,以表達(dá)情感和宣揚(yáng)精神為主,即通過豐富的情感藝術(shù)表達(dá)人與人之間或處于當(dāng)時(shí)背景之下的道德精神,在歌劇《江姐》中,為符合國人審美和秉承民族文化傳統(tǒng),藝術(shù)家同樣將川劇,板腔之類有機(jī)結(jié)合,在創(chuàng)作中,使用板腔技法,在樂曲中起到情感的連接變化,引申發(fā)展,運(yùn)用音樂樂段塑造形象,同時(shí)作為鋪墊,形成發(fā)展。
當(dāng)“歌劇之風(fēng)”吹進(jìn)中國的時(shí)候,人們漸漸接受了這個(gè)外來藝術(shù)形式,中國獨(dú)有的民族藝術(shù)情懷特色鑄就了中國歌劇。其實(shí)就是將傳統(tǒng)的中國戲劇表現(xiàn)形式“戲曲”作為獨(dú)特舞臺(tái)表現(xiàn)形式,將這一方式作為基礎(chǔ),把西方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模式和中國寫意美學(xué)放在一起堆砌起來,有機(jī)結(jié)合。其實(shí)盡管國情和人民生活的差別很大,但是西方所有的音樂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在我們的舞臺(tái)上也可以呈現(xiàn),甚至更多。從舞臺(tái)上的展現(xiàn)東方貼切人們生活得舞美,加上演員情緒的相互烘托,又有人物的塑造,從藝術(shù)審美的角度上拉近了演員和觀眾的距離。這就是民族歌劇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本體的回歸,對傳統(tǒng)美學(xué)的回歸。
其實(shí)對于當(dāng)代的民族歌劇來說,應(yīng)當(dāng)摒棄絕對傳統(tǒng)和中庸的創(chuàng)作手法,因?yàn)檫@樣客觀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表達(dá)沒有“顏色”,沒有“新鮮血液”,過于嚴(yán)肅的同時(shí)不符合當(dāng)下的審美意識(shí),當(dāng)代歌劇音樂的創(chuàng)作,在遵從“音樂至上”的情況下應(yīng)當(dāng)更注重色彩和速度上的變化,才能拒絕歌劇音樂的“平面化”表達(dá)。
(二)走多元化的創(chuàng)新道路
對于經(jīng)典歌劇,應(yīng)該進(jìn)行定期地改變和長期的表演。不能用一整不變的創(chuàng)作思想應(yīng)對隨著時(shí)間變化而變化的審美。因?yàn)楦鑴〉闹鞒绷鬟€是以西方的歌劇藝術(shù)形式為主。與此同時(shí),文化全球化是必然的,所謂文化是世界的,不僅僅在于經(jīng)濟(jì)政治方面,更在于各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歷史沿革,藝術(shù)作品等方面。
對于當(dāng)代中國歌劇音樂創(chuàng)作,有一種說法是把西方歌劇音樂創(chuàng)作從歌頌神話人物的寫意引進(jìn)中國音樂創(chuàng)作中,通過這一客觀媒介進(jìn)行改編排演從而改進(jìn)了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傳播形式。其實(shí)這一說法存在主次問題,本人認(rèn)為,是當(dāng)前背景下的中國歌劇音樂創(chuàng)作者根據(jù)本土的音樂形式,運(yùn)用板腔技法或是融合戲曲的觀念,對于歌劇這一藝術(shù)形式的重新塑造和詮釋。
何為“多元發(fā)展”,之前的歌劇創(chuàng)作和表現(xiàn)形式為歌曲,經(jīng)過一度創(chuàng)作之后再進(jìn)行排演、拓展,歌劇其實(shí)更是一個(gè)大的工程,更需要“精耕細(xì)作”,歌劇舞臺(tái)是舞臺(tái)和文化、音樂、精神的集大成者。分工很重要,比如一度創(chuàng)作中的文學(xué)賞析和體現(xiàn),二度創(chuàng)作中使用音樂進(jìn)行的人物刻畫,亦或者舞臺(tái)表現(xiàn)的動(dòng)作神態(tài),故事情景化的連接和代入,都需要文學(xué)家一度創(chuàng)作和作曲家、演員、編導(dǎo)的二度創(chuàng)作的緊密配合,讓所有創(chuàng)作者在主觀意識(shí)上對本劇的理解和想法達(dá)成一致,也就相當(dāng)于一次“頭腦風(fēng)暴”,在藝術(shù)體特質(zhì)上產(chǎn)生共鳴,這樣嚴(yán)密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音樂創(chuàng)作,才能使民族歌劇魅力最大化。
在歌曲的創(chuàng)作上,有人批評(píng)近年來中國排演的民族歌劇是“舶來”,反復(fù)排練是在湊篇幅,而我認(rèn)為這是近代民族歌劇在幾十年來不斷摸索過程中的一種“尋根”,是當(dāng)代創(chuàng)作藝術(shù)家們的一種回歸,一種回歸民族本體的現(xiàn)象,只有將我們自己民族的東西,反復(fù)打磨,因?yàn)楦鑴〉闹鞒绷鬟€是以西方歌劇藝術(shù)形式為主,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一種對新的理論的實(shí)踐打磨和論證。對于中國民族歌劇的傳播,更重要的是易懂易接受,面向大眾尤其是面對年輕的群體,擺脫西方歌劇音樂的束縛自成一派,用“中國面貌”站立國際歌劇舞臺(tái),在尊重音樂發(fā)展的同時(shí),接納融合,多元發(fā)展,精耕細(xì)作,吸引年輕的力量去感受,去創(chuàng)造,去傳承,不斷摸索,中國民族歌劇之路定將越走越寬廣明亮。
結(jié) 語
總之歌劇《江姐》多次復(fù)排,是歌劇藝術(shù)家在民族藝術(shù)音樂回歸中,探尋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之路的過程。對地方劇種的穿插融合也好,對唱腔技法的研究結(jié)合牙好,對西方歌劇藝術(shù)配器和舞臺(tái)表演的借鑒也好,都是對傳統(tǒng)中國國學(xué)的一種傳播和回歸。讓音樂藝術(shù)和歌劇藝術(shù)更加飽滿,更加充滿豐富的語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