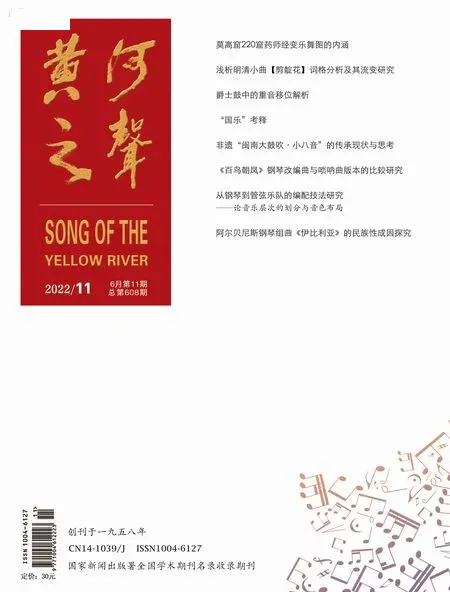《春天的故事》大合唱與交響詩分析比較研究
伊文博
引 言
我國進入近現代音樂時期后,音樂作品體裁逐漸豐富,交響音樂與大合唱音樂體裁也日趨成熟。大合唱體裁自“學堂樂歌”之后傳入我國逐漸衍變成合唱形式,代表作:《黃河大合唱》、《鳳凰涅槃》等。中國交響樂體裁在新中國成立后創作出在世界上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作品,代表作:《梁山伯與祝英臺》、《紅色娘子軍》等。
一、作品背后的故事
大合唱版本《春天的故事》由蔣開儒創作于1994年,最初,蔣開儒得知廣東省將舉辦青春歌曲創作大賽的消息后,找到王佑貴為其譜曲,但最后遺憾落選。之后又與葉旭全一起完善樂曲,最終創作出這種耳熟能詳的作品。本文以王世光改編的合唱曲為研究對象,音響選用國家大劇院合唱團版本,四部混聲合唱用鋼琴伴奏。
交響詩版本《春天的故事》由杜鳴心先生編曲,作于1999年。以王佑貴先生的原曲《春天的故事》旋律創編而成,此作品是中國音樂家協會委約作品。杜鳴心加了一段快速、熱情的中部,描繪中國人民響應鄧小平同志的號召,意氣風發,用智慧與汗水投入到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本文選用杜鳴心先生的交響詩曲譜為研究對象,音響選用中國愛樂樂團版本。
二、兩部作品音樂本體研究
(一)大合唱《春天的故事》
該曲的曲式結構為單二部曲式,以降A調貫穿其中。作品分為A與B兩部分。前奏為10小節,在前奏中以男聲部進入,嘆詞用mi的八度關系襯托情感從中音區進入到高音區部,之后緊接著用三個春天在三個聲部上的不同重復,以此作為對主題的引入和對語氣詞的一個回答。5—10小節中旋律多以三度以內的級進和節奏以三連音與長音符結合的形式進行,對前奏進行表達主題顯現及引出A段。
A段由兩句組成,降A大調,為a+b(5+4),都在屬音上結束。在a句中旋律起伏較大,多用密集的節奏型來表達樂句內容,但每句歌詞結束時大多選用長時值音符,以此來緩解樂句中緊密排列音樂造成的緊張感,使樂曲增加抒情效果。A句中15小節女低聲部采用屬關系內的和聲,旋律用經過音的方式解決到16小節的主音上過渡至b句旋律,使其適應合唱音樂效果。
B段由c句與d句組成,c+d(4+13),延續降A調。c句中自20小節進入后主要旋律聲部由女生聲部擔任,男生聲部主要起襯托以及增加合唱音響效果并與A段形成對比。C句在男生聲部的處理上主要集中在承接女生聲部主旋律之外的和聲音響,d句中的音響又與c句相區別,除26-27小節以外男生聲部作為襯詞與女生聲部相呼應以外,其余部分都是在各自音區旋律中以齊唱的形式進行,增加音響的厚重并增加氣勢,與A段抒情性音樂形成鮮明的色彩對比。這本文選取的譜例及音響版本中,A段與B段結束后又重復演唱了一次,相同的旋律不同的歌詞,d句結尾時從33小節直接進入37小節,此為d1句,共11小節。
尾聲為8小節,偏向頌歌的形式,重復強調“中國”、“春天”這兩句歌詞,在音樂節奏上多以長音符出現延長音響效果。尾聲中用“啊”的這個嘆詞作為過渡與收尾,處理這個字的音樂時采用跳進四度及五度跳進和相比其他尾聲部音樂旋律的稍密集節奏型流動用以渲染情緒氣氛,尾聲部分緊扣主題又使音樂進行思想內涵上的升華。這首作品的鋼琴伴奏多以柱式和弦音型為主,為音樂旋律增加縱向和聲支撐,在整體音樂效果上雖不及交響樂隆重但也足夠滿足合唱音樂效果。
(二)交響詩《春天的故事》
這首樂曲采用交響音樂中較慣用的奏鳴曲式結構,由于是以歌曲《春天的故事》中旋律改編的作品,所以在奏鳴曲式的安排上不是傳統的奏鳴曲式結構,而是以旋律為主要依據根據奏鳴曲式原則進行的曲式安排。由引子、呈示部、展開部、再現部、尾聲構成。引子1-6小節,為D大調,呈示部:主部7-19小節、副部20-27小節、連接28-34小節、主部35-47小節、連接48-50小節、結束部51-59小節。除結束部在G大調轉至C大調以外其余部分都在D大調上發展。展開部:引入60-65小節(G大調)、中心一66-93小節(G-E-C-D-A-?B-G)、中心二94-108小節(G-D-?D-?E-?f-A),在展開部調性變化比較復雜。再現部:主部119-131小節、連接132-135小節,再現部調性的回歸到D大調上,尾聲136-144小節,在D大調上終止。
引子部分選用以音色較明亮的短笛與單簧管進入旋律,大管與大提琴低音厚重音色相輔、三角鐵音色的點綴,在前兩小節完成交互。后交由第一、二小提琴、中提、長笛和單簧管、圓號進行旋律直至引子結束,以圓號聲部的下行音階的進行加以輔助音結尾形成溫和終止的音響效果。
主部旋律主要由弦樂組完成,在主題部分音樂色彩并不復雜,主要以敘述為主。作為一首純器樂作品,在主部的前兩句中,弦樂組中音區的中提琴與大提琴相配合完成陳述主要音樂材料,第三句中加入銅管與木管組對弦樂組的旋律進行和聲填充以此來增加音樂音響色彩并推進情緒進行。20小節開始進入副部旋律,在開始的兩小節樂匯上旋律放在長笛聲部上出現而后在提琴聲部的銜接,通過兩種樂器音色上的對比使這個樂句產生了呼應的效果,這是以配器變化來處理音樂的。在22小節的樂句結尾處用短笛、長笛、單簧管聲部運用復調的形式進行了一小節旋律擴充。
28-34小節連接部分中使用引子的音樂材料,la la la si la si la la,這個小節可以看作整首樂曲的主要動機,在引子、連接、結尾部、尾聲等具有銜接功能的部分都有出現,用以貫穿全曲使其前后呼應并緊扣主題。28-32小節采用了這樣的動機但作者將其分配在不同樂器上出現,在聽覺上出現音色區別且不覺單調。32、33小節中用連續的二度上行音階將音樂推向下一個主部主題的出現,在動機上模仿了la si si la 的關系。34小節的la音表示這個樂句的半終止結束在屬音上,四個四分的音符的以分解和弦的形式出現以強調在調內屬和弦的收束感,配器上運用了定音鼓與小軍鼓的音響同樣也是為了增加終止效果。但為了引出在35小節出現的主部旋律,34小節上用豎琴進行了從大字組la音到小字二組la音刮奏,這樣的音樂處理是為了中和終止的強硬,使連接部與主題部銜接緊密。35-47小節的主部主題雖然與7-19小節的主題部分旋律一致但運用了不同的配器手法,為典型的浪漫主義風格。其中每個樂句的樂器配置都有所不同,樂隊音色愈來愈豐滿,濃重。這種配器不但構成音樂形式上的差異同時也造成音色的細膩變化,反映出浪漫主義配器風格對作者創作的深刻影響。
結束部選用主部主題音樂材料,兩個小節為一個樂句發展。小提、中提、大提琴、長笛、單簧管、大管為主旋律的基礎上,短笛、英國管與小號這些音色明亮的樂器做旋律擴充與襯托,定音鼓在樂句結尾加強音響。四個小節在G大調的基礎上進行發展后進入C大調至59小節,以四個樂器組齊奏的形式展現,將旋律推入展開部。
中部是杜鳴心先生在原曲旋律的基礎上新增加的一部分內容,本文作為展開部呈現。引入部分以向高音區快速跑動的半音階為過渡,與前方結束部中的終止音全音符形成動靜結合之態,為后面展開部中大量密集音符的跑動做鋪墊。61-65小節豎琴與中提琴的半音進行是引入部分的核心內容,小二度Fa到?sol的進行形成不穩定之感。中心一從65小節出現大量輔助音與經過音的進行,圍繞著G音以16分音符的節奏密集出現,其他聲部輔以四度、五度的和聲襯托。以幾次離調的進行轉入E大調。半音模進是作曲家掌握最為透徹、得心應手的作曲技法之一,多種半音手法的綜合運用使音樂呈現半音化調性布局和音樂半音化發展態勢。70-80小節運用具有嚴密的邏輯、可移動的調中心寫作手法有機貫穿,經過快節奏的和聲轉換,達到片段性、結構性的頻繁調整變化。配器主要集中在弦樂組的小提、中提、大提琴上。73-79小節在小提琴聲部采用十六分音符琶音形式結合四分音符的寫作手法,四分音符處于調式主音高位,先緊后松造成節奏傾向性,配合中提與大提琴上的循環音型,在明確調性的同時給以轉換的余地。
在配器上依舊遵循以弦樂組作為主旋律進行的寫作手法,銅管、木管組作為和聲支撐,單簧管與大管配以分解和弦豐富和聲效果。在中心一的旋律進行中音高逐步遞增表現急切地想要為祖國的美好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的心情,這段音樂是熱情的、充滿朝氣的,與呈示部抒情細膩的旋律形成對比。在中心一的終止處92、93小節選擇了下行音階走向,既是為了使旋律線回到中音區做必要準備也是給樂段的一個喘息機會,以便于中心二持續上升的音組推動音樂發展,升華音樂思想及內涵。中心二與中心一的旋律相似,但在117、118小節時做出改變,117小節同音sol降低16度回到中音區后隨即上行音階將旋律推入再現部,這樣的音樂處理方式避免了展開部與再現部的旋律架構斷裂,雖說是兩個對比鮮明的樂段,但是杜先生用過渡性的旋律交接來塑造整體性、一氣呵成。中心部分布局上以小結構為主并且忽視主調性,調式主音的斷續、調性游移手法設置在長樂句中,看似自由隨意,其實依然可以看出明確的調性指向,遵循縝密邏輯思維的理性控制。
再現部的主部主題是全曲最輝煌的部分,119-122小節調動了木管樂器組與弦樂器組共同擔任旋律演奏,銅管樂器與打擊樂進行和聲支撐以及旋律加花,123-127小節銅管樂器組圓號負責旋律聲部,木管與弦樂組配合分解和弦的和聲,改變音色建立多聲部立體結構。128-132小節四個主要樂器組相互配合進入高潮階段,在音響效果擴大到最大化的同時旋律上選擇具有歌頌性的段落抒發音樂思想。133、134小節的銅管組半音進行與92、93小節的音樂處理有異段同工之妙,這也是杜鳴心先生較為典型的音樂處理方式。在尾聲中以輝煌的音樂效果結尾,上行琶音音型的密集跑動,半音模進變形、四五度疊置、分解和弦的低聲部和聲支撐,打擊樂器的情緒渲染,體現出作曲家結合民族音樂風格與西方浪漫主義風格的交響化音樂思維,樂曲效果恢宏大氣、振奮人心。
三、兩首作品比較研究
兩首作品雖都以歌曲《春天的故事》為創作根本,但音樂家在創作時賦予其音樂體裁、創作觀念等方面有著很大區別。
音樂體裁方面,一個采用的是人聲與器樂結合的大合唱形式,單二部曲式,在創作思想上秉持著對于原作品的尊重。去掉獨唱部分,將旋律分配在男高、男低、女高、女低的四個不同聲部中,在使用歌曲旋律改編時充分考慮了語境與意境,通過不同的聲部表達音樂情感。另一個采用了純器樂形式的交響詩體裁,奏鳴曲式,雖同樣采用原歌曲的旋律但是在樂曲音樂內容上有所增加,在展開部有新的音樂材料,脫離了歌曲的歌唱方式但沒有改變旋律的歌唱性。
音樂創作以及樂曲配器方面兩者有著各自的特點與優勢。音樂創作方面大合唱采用的鋼琴伴奏,織體多以分解和弦與柱式和弦為主,在和聲結構上起到對演唱聲部的支撐,也是合唱作品慣用的寫作手法,交響詩以四個樂器組配器為主加入豎琴的元素,在整體音響效果方面更顯磅礴大氣,音樂表現形式豐富。相同樂段的不同配器造成彼此各部分的差異并在其中加以具有作曲家個人藝術風格的中段,抒發感性情感的同時用理性作曲思維加以約束,達到收放自如的狀態,正如民族音樂理論家田青所言:“‘出去’是‘放’,‘回來’是‘收’,收放自如才是藝術。”通過交響詩《春天的故事》這首作品,體現了作曲家在旋律寫作上有強烈的個人風格很高的藝術造詣。旋律的走向、演變、主題旋律多聲部銜接、過渡句的巧妙運用、聲部間的應答等,給有限的旋律無限的發展空間,看似呈示部主題與展開部毫無關聯,實則通過頻繁的調性轉換,游離音等方式將展開部融入到整個作品中,不僅不顯得突兀等有升華思想情感的絕佳效果。
結 語
本文以大合唱《春天的故事》與交響詩《春天的故事》為研究對象,在分析作品音樂本體的同時,也對兩首作品在音樂體裁和音樂創作等方面做了比較研究,發現在音樂處理上有其各自的特點也有對原歌曲旋律的共通之處。筆者意圖通過本文兩首作品之間的比較為更多的音樂家提供可借鑒之處和理論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