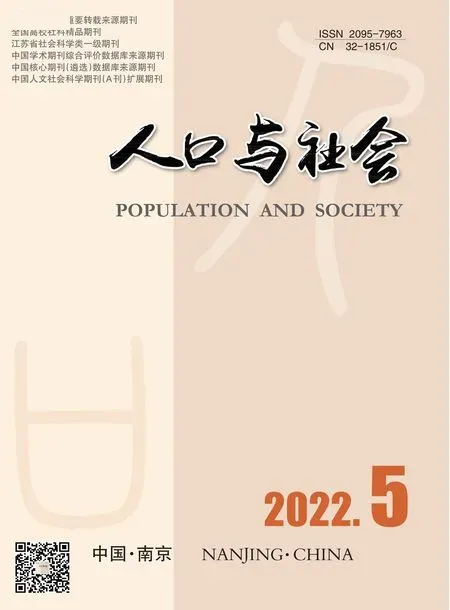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對城市居民健康的影響
——基于社會交往和主觀階層的多重中介效應
陳維超,曾小晉
(湖南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健康作為一種重要的人力資本,不僅是個人生存和發(fā)展的基礎,而且是現(xiàn)代化社會的重要標志。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其逐漸從一種娛樂方式變?yōu)樯a(chǎn)和生活方式。互聯(lián)網(wǎng)與健康、醫(yī)療產(chǎn)業(yè)的深度融合,為人們在網(wǎng)絡搜尋健康信息和尋求醫(yī)療服務提供了極大便利。國內(nèi)關于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與健康效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群體,對影響機制的分析多從互聯(lián)網(wǎng)功能出發(fā)探討社交、娛樂、學習等方面的中介效應,鮮有從社會學角度研究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與城市居民健康效應。鑒于此,本文采用鏈式多重中介效應檢測方法,分析社會交往和階層認同在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與城市居民健康狀況之間發(fā)揮的中介效應。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與城市居民健康關系的研究
關于互聯(lián)網(wǎng)與使用者健康的相關研究,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互聯(lián)網(wǎng)給使用者健康帶來負面影響,Gilleard等發(fā)現(xiàn)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減少了老年群體的社會參與,導致其產(chǎn)生孤獨感與隔離感等心理健康問題[1]。Gross 等發(fā)現(xiàn)封閉的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環(huán)境會造成青少年群體情緒上的低落和孤獨感[2]。二是互聯(lián)網(wǎng)有助于提升使用者的健康水平,主要體現(xiàn)為使用者可以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緩解精神壓力和獲取健康信息。公眾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進行娛樂社交、網(wǎng)絡游戲以及自我表達等行為,能夠極大緩解精神壓力,降低自我的孤獨感[3-4]。健康信息獲取方面,Dutta-Bergman研究證實,與未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搜索醫(yī)療新聞的消費者相比,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尋找醫(yī)療信息的消費者顯示了更高水平的健康信息導向和更強烈的健康信念[5]。Hyun Jung Oh等研究發(fā)現(xiàn),人們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能夠有效獲取健康信息和社會支持[6]。在國內(nèi),陳亮和李瑩基于CGSS2015數(shù)據(jù)分析,發(fā)現(xiàn)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對居民健康具有顯著正向影響[7]。趙穎智和李星穎基于CFPS2014數(shù)據(jù),證實互聯(lián)網(wǎng)作為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通過傳遞健康知識對個體健康水平的提高具有顯著作用[8]。徐延輝和賴東鵬基于CSS2013數(shù)據(jù)引入風險感知變量,不僅證實了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和居民健康的正相關關系,而且揭示了風險感知對居民健康情況的遮掩效應[9]。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對城市居民健康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社會網(wǎng)絡: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影響群體健康的中介機制
互聯(lián)網(wǎng)為人們溝通交流和情感維系提供了便利,而社會交往有助于緩解孤獨和焦慮情緒。關于互聯(lián)網(wǎng)與社會網(wǎng)絡的關系,主要有兩種論調(diào)。一是互聯(lián)網(wǎng)抑制了線下社交。普特南(R. Putnam)認為互聯(lián)網(wǎng)最初是用來娛樂而非交往的,上網(wǎng)對社會活動的抑制會導致個體產(chǎn)生孤獨感[10]。二是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從一種娛樂工具轉(zhuǎn)化為社交平臺,線上交往擴展了個體的社會網(wǎng)絡。漢普頓(K. Hampton)研究發(fā)現(xiàn),加拿大居民的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會加強鄰里之間的聯(lián)系以及公共事務參與[11]。有的學者從弱關系和強關系兩個層面分別探討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與社會網(wǎng)絡之間的關系。Kraut等發(fā)現(xiàn)公眾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進行交往互動會提升家庭成員交流頻率,改善家庭關系[12]。付曉燕證實,使用者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獲得情感支持和拓寬基于“弱關系”的社交圈群,提升自己的橋梁型社會資本[13]。
關于社會網(wǎng)絡與公眾健康狀況的關系,一方面,社會網(wǎng)絡有助于健康信息共享,幫助個體規(guī)避健康風險[14],另一方面,社會交往有助于營造互信的社會環(huán)境,緩解個體的生活壓力[15]。Helliwell和Putnam發(fā)現(xiàn)朋友關系、鄰居關系、職場關系與居民健康狀態(tài)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16]。郭小弦和王建發(fā)現(xiàn)與高地位群體交往會增強用戶的社會比較心理,致使其產(chǎn)生自卑感與挫敗感,而與低地位群體交往則能增強居民的自我滿足感[17]。楊璐研究發(fā)現(xiàn),居民通過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強化社會交往進而提升自身健康水平[18]。據(jù)此提出假設:
H2:社會網(wǎng)絡在互聯(lián)網(wǎng)影響城市居民健康狀況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三)主觀階層: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影響群體健康的中介機制
階層認同主要受到客觀經(jīng)濟地位和個體主觀特質(zhì)影響。美國社會學家杰克曼夫婦認為,階層認同指的是“個人對自己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占據(jù)位置的感知”[19]。本文從微觀層面切入,認為階層認同是一種個人主觀性的感知判斷。階層認同會影響社會成員的態(tài)度和努力程度,進而影響到社會和諧與社會穩(wěn)定,因此研究個體的階層認同具有重要意義[20]。本文將主觀階層感知作為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影響城市居民健康的中介機制進行研究。
首先,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與主觀階層之間的關系。周葆華以上海城市居民為調(diào)查對象,發(fā)現(xiàn)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與社會成員的階層地位感知顯著正相關[21]。黃麗娜基于CGSS2013數(shù)據(jù)分析發(fā)現(xiàn),互聯(lián)網(wǎng)不僅正向影響城市居民的階層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并重塑了城市居民的主觀社會分層[22]。其次,主觀階層與健康效應之間的關系。主觀階層感知較低者往往伴隨著焦慮、壓力大以及不平等等心理,致使其產(chǎn)生健康問題[23]。Roos等以芬蘭青少年群體為研究對象,發(fā)現(xiàn)對家庭有著較低主觀階層感知的青少年,其健康狀況往往更差[24]。吳青熹與陳云松的研究表明,主觀階層感知對自評健康的影響顯著,且高主觀階層感知人群的自評健康狀況更好[25]。據(jù)此提出以下假設:
H3:主觀階層認同在互聯(lián)網(wǎng)影響城市居民健康狀況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客觀階層不是影響個體主觀階層感知的唯一要素[26-27]。Sayer認為階層不只包含經(jīng)濟差異,還包括文化和社會資本的差異[28]。Bucciol等的研究表明,美國老年人的社會資本與主觀社會地位顯著正相關[29]。Ji Hye Kim等基于2012年東亞社會調(diào)查數(shù)據(jù)(East Asian Social Survey)研究個體社會資本(包括黏結型資本、橋梁型資本、認知型社會資本)和主觀階層感知的關系,發(fā)現(xiàn)中國民眾和高社會階層的人交往越頻繁,主觀階層感知越高;而在中國臺灣地區(qū)和韓國,與親屬和朋友之間交往越頻繁,主觀階層感知越高[30]。據(jù)此提出以下假設:
H4:社會交往與主觀階層聯(lián)動在互聯(lián)網(wǎng)影響城市居民健康狀況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二、數(shù)據(jù)來源與變量設定
(一)數(shù)據(jù)來源
本文的實證研究采用了中國人民大學“2017年中國綜合社會調(diào)查數(shù)據(jù)”(CGSS 2017)。根據(jù)研究需要,本研究剔除了農(nóng)村居民樣本以及關鍵變量缺失樣本,最終獲得居住地為城市的被訪者有效樣本4850個。
(二)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
借鑒熊艾倫等[31]、趙建國和劉子瓊[32]的研究設定,本文使用了三個測量不同維度健康水平的指標,包括“自評健康”“生理健康”“心理健康”。自評健康(self-rated health)表示個體對自我健康狀況的感知狀況。近年來大量文獻研究發(fā)現(xiàn),自評健康是發(fā)病率和死亡率的重要預測因子,可作為評估個體健康狀況的有效指標[33]。采用問卷“您覺得您目前的身體健康狀況如何”來反映城市居民自評健康水平。生理健康通過問題“在過去的四周中,健康問題影響到您的工作或其他日常活動的頻繁程度”來測度。心理健康通過問題“在過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喪的頻繁程度”獲得。三個維度的賦值越低,說明個體受健康問題影響越大。
2.核心解釋變量
本文核心解釋變量為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根據(jù)問卷“過去一年,您的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情況如何”來測度,得分范圍為1~5(1=從不,2=很少,3=有時,4=經(jīng)常,5=非常頻繁)。
3.中介變量
借鑒蘇林森和程思琪等[34]的研究設定,選取問卷中“與鄰居進行社交娛樂活動”以及“與朋友進行社交娛樂活動”兩個問題,對兩個問題選項賦值進行累加再平均,得到“社會交往”的分值,從“從不”到“非常頻繁”,分別賦值1~5。
主觀階層認同以問卷選項“綜合看來,在目前這個社會上,您本人處于社會的哪一層?”來測量,選項包含10個等級。將10個等級分為5組:下層(1、2)、中下層(3、4)、中層(5、6)、中上層(7、8)和上層(9、10),占比分別為16.59%、36.53%、42.51%、4.00%、0.37%。可以看出,當前城市居民階層認同偏向于中層和中下層。
4.控制變量
依據(jù)CGSS2017問卷,并參考過往健康效應的相關研究,本文將一系列控制變量納入后文的實證分析。如表1所示,所選取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態(tài)、家庭年收入、社會心理感知、區(qū)域特征等。

表1 變量定義及描述性統(tǒng)計結果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各變量的相關性系數(shù)
考慮到影響城市居民健康的變量間可能存在相關性過高引發(fā)的結果精準性問題,為保障指標選擇的合理性和科學性,采用Pearson相關系數(shù)方法對所選指標間的相關系數(shù)進行了初步分析。圖1所示為變量之間Pearson相關性系數(shù),深色表示正相關,淺色表示負相關。可見,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與自評健康的正相關性較強,年齡與自評健康的負相關性較強,而婚姻與自評健康不存在相關性。同時,利用方差膨脹因子檢驗可知,自變量的VIF均值為1.419,最大VIF為1.9543,故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能獨立反映不同維度的健康信息。

圖1 變量間Pearson相關性系數(shù)圖
(二)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如表2所示,模型1、模型2、模型3的被解釋變量分別為自評健康、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以模型1為例,性別、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社會評價、社會信任、主觀幸福感均與自評健康顯著正相關,即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認為社會越公平、對社會信任感越高主觀幸福感越強的城市居民自評健康水平更高,而年齡與城市居民自評健康狀況顯著負相關。婚姻狀況在三個模型中的回歸系數(shù)均不顯著。三個模型回歸結果表明,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對城市居民健康水平具有正向影響,即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頻率越高,城市居民的健康水平越高,H1得到驗證。

表2 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和城市居民的健康效應
(三)內(nèi)生性處理:工具變量法
本研究采用工具變量法來消除遺漏變量、測量誤差以及變量的反向因果等導致的內(nèi)生性問題。參照陳世香和曾鳴[35]的研究設定,選取“主要信息來源”作為工具變量,將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主要消息渠道的群體賦值為1,選擇其他信息接收渠道的賦值為0。陳云松認為偏愛使用電腦、手機等電子產(chǎn)品獲取信息的居民,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或手機上網(wǎng)的概率更大[36],故滿足相關性。同時,媒介渠道選擇與使用偏好是個體異質(zhì)性的體現(xiàn),與城市居民健康水平并沒有直接影響關系,故滿足外生性。
針對回歸模型的內(nèi)生性問題,通常采用2SLS方法來分析模型的內(nèi)生性以及工具變量的有效性[37]。本文也借鑒這種方法對工具變量進行檢驗,使用工具變量的前提是模型存在內(nèi)生性。首先對模型進行內(nèi)生性檢驗,Wald檢驗顯示P值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是外生變量的原假設,表明原模型存在內(nèi)生性問題,使用工具變量是合理的。其次,弱工具變量檢驗下的F統(tǒng)計量為890.78,明顯大于10,表明“主要信息來源”這一工具變量有著較好解釋效果(見表3)。
根據(jù)表3,一階段工具變量“主要信息來源為互聯(lián)網(wǎng)”的系數(shù)為1.6729,在1%水平上顯著,二階段回歸中內(nèi)生變量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的系數(shù)為0.1057,同時,偏R2為0.6282,說明工具變量對內(nèi)生變量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有著較強的解釋力度。綜上所述,基于工具變量的回歸結果是有效的。

表3 內(nèi)生性分析結果(2SLS模型)
(四)異質(zhì)性分析
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對不同個體特征的城市居民產(chǎn)生的影響存在異質(zhì)性,本文從性別、年齡和區(qū)域等角度來進行異質(zhì)性檢驗。如表4所示,性別方面,男性群體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的健康提升效應高于女性群體。年齡方面,青年、中年與老年城市居民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的回歸系數(shù)均顯著為正,然而系數(shù)值差距較大,青年與老年城市居民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的健康提升效應更顯著。區(qū)域方面,西部和中部城市居民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的健康提升效應更顯著。

表4 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對城市居民自評健康影響的異質(zhì)性檢驗
(五)穩(wěn)健性分析
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還存在其他測量指標,即“空閑時間上網(wǎng)頻率”和“主要消息來源”,因此本文以“空閑時間上網(wǎng)”和“是否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主要消息來源”替換核心解釋變量“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進行穩(wěn)健性檢驗。(1)替換變量。如表5所示,模型4將核心解釋變量替換為“空閑時間上網(wǎng)頻率”,模型5將核心解釋變量替換為“是否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主要消息來源”,分析結果均支持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對城市居民自評健康的顯著正向效應。(2)改變模型設定形式。模型6將Probit模型換為OLS回歸模型,回歸系數(shù)依然顯著。(3)改變變量設定形式。模型7將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設定為虛擬變量(不使用為0,使用為1)的形式后,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仍然會提升健康水平,證明結果穩(wěn)健。分析結果進一步證實,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給城市居民帶來的健康效應是穩(wěn)健、可信的。

表5 穩(wěn)健性檢驗(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
(六)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中介效應的檢測方法一般包含逐步檢驗法、Sobel Goodman檢驗、Bootstrap 法。由于本文有兩個中介變量,溫忠麟和葉寶娟認為檢驗多重中介效應比較好的方法是Bootstrap法[38],因此選取Bootstrap法來測量中介效應。多步多重中介模型,也稱為鏈式多重中介模型,是指中介變量之間存在影響關系,中介變量表現(xiàn)出順序性特征,形成中介鏈。
1.特定路徑的中介效應。用路徑1表示“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社會交往→自評健康水平”,路徑2表示“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主觀階層→自評健康水平”,路徑3表示“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社會交往→主觀階層→自評健康水平”。根據(jù)表6,從路徑1看,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經(jīng)由社會交往的中介效應95%置信區(qū)間不包含0,說明中介效應顯著,這意味著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可以通過強化社會交往這一途徑對城市居民自評健康狀況施加影響,H2得到驗證。從路徑2看,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經(jīng)由主觀階層的中介效應為0.005,且在1%水平上顯著,這意味著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通過提升主觀階層感知對健康水平產(chǎn)生了正向影響,H3得到驗證。從路徑3看,置信區(qū)間不包含0,說明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經(jīng)由社會交往、主觀階層的鏈式中介效應存在,意味著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通過促進社會交往進而提升主觀階層感知對健康產(chǎn)生正向影響,H4得到驗證。

表6 社會交往與主觀階層的中介效應分析結果
2.總體中介效應。將上述特定中介效應加總可得到總體中介效應0.008,且在1%水平上顯著,這說明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通過主觀階層、社會交往與主觀階層聯(lián)動三條路徑對健康效應產(chǎn)生總體的正向影響。
四、結語
本文基于最新公開的CGSS2017的微觀數(shù)據(jù),運用有序Probit計量方法,試圖探討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與城市居民健康水平的關系。結果表明:
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對城市居民健康水平有顯著正向影響,并且通過了穩(wěn)健性檢驗。異質(zhì)性檢驗分析結果表明,男性、青年以及中西部地區(qū)城市居民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的健康提升效應更為顯著。在控制人口統(tǒng)計變量的情況下,利用鏈式中介效應檢測方法,引入社會交往和主觀階層變量探討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對城市居民健康水平的影響機制。其中,社會網(wǎng)絡和主觀階層認同均通過了中介效應檢測,增強了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對城市居民健康水平的正向影響。
此外,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經(jīng)由社會交往與主觀階層聯(lián)動的鏈式中介效應顯著存在,即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通過促進社會交往進而提升主觀階層感知對健康產(chǎn)生正向影響。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社交功能的凸顯和社交化產(chǎn)品的日益增多,人們在網(wǎng)絡進行社會交往的成本越來越低。互聯(lián)網(wǎng)社交互動的匿名性消弭了城市居民的現(xiàn)實身份區(qū)隔,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居民的主觀階層感知,同時,網(wǎng)絡社交對現(xiàn)實社會交往的促進作用有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主觀階層感知,而高主觀階層感知的人自評健康狀況往往更好。
本文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在研究方法上,通過選取工具變量消解了回歸模型的內(nèi)生性問題,使得模型估計結果更為科學;內(nèi)容方面,鑒于互聯(lián)網(wǎng)已經(jīng)滲入社會各個領域,對人們的健康也產(chǎn)生了多元化影響,分析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與城市居民健康之間的關系及具體的作用路徑,有助于最大化發(fā)揮互聯(lián)網(wǎng)對城市居民的健康激勵效應。
然而,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受制于數(shù)據(jù)測量變量的可獲取性,對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測量沒有對具體使用類型加以細分,僅以一個籠統(tǒng)的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作為代理指標,因此難以測度不同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類型給城市居民健康狀況帶來影響的差異性。未來可以考慮進一步細化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類型開展相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