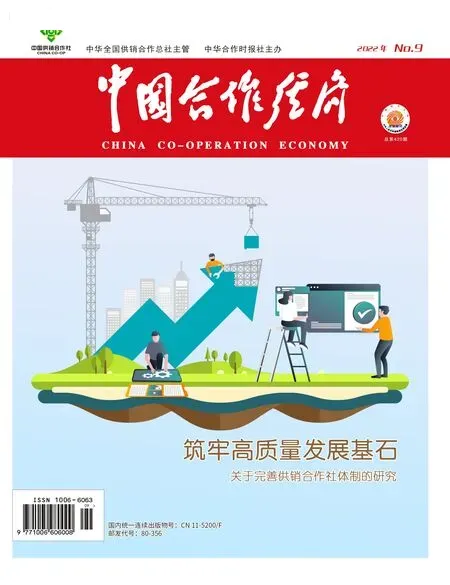從“小農”到“大農”
——簡論張謇對農業的貢獻
文 葛志華
在近代歷史人物中,張謇是獨樹一幟的。他既有全國性的作為,在諸多歷史風口留下了或顯或隱的身影,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又有區域性的貢獻,在家鄉江蘇省南通市開創了諸多事業,奠定了“中國第一”的歷史地位。他既有獨特的理論,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又有豐富的實踐,成為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開拓者之一。他既熱衷于工業化,成為毛澤東眼中“不能忘記的四人”之一,又致力于推進農業現代化,為現代農業發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
張謇(1853—1926),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清末狀元。張謇在致力工業化的同時,又與農業結下了不解之緣。這種不解之緣主要表現為認識層面的先人一拍、實踐層面的快人一步、行政層面的勝人一籌等,從而奠定了張謇在中國農業現代化史上的歷史地位。
認識層面的先人一拍
農業是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基礎,但農業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農業社會,農業雖是決定性的生產部門,卻是“小農”形態,諸如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工具簡陋、經營規模狹小、生產力低下,既脆弱又易再生等,其本質特征就是物質與能量的封閉循環。到了工業社會,農業占比日漸縮小,但發展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在農業生產技術、經營規模、經營機制、要素投入、功能作用等多方面呈現出新變化,其本質特征就是物質與能量循環由“封閉”轉向“開放”、由“小農”轉型為“大農”。因此,“小農”與“大農”雖只是一字之差,卻是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式。前者是農業社會的產物,后者卻是現代化的結果。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創造了燦爛的農業文明。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就告別了刀耕火種,形成了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在此后的2000多年,雖然朝代更替不斷,但農業生產力水平提高不快,家庭分散經營形式基本不變,呈現出內卷化特征。資料顯示,先秦時期我國小麥畝產已達51公斤,經兩漢到隋唐時期仍只有53公斤,1000年左右只提高了兩公斤。明清時期,我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鴉片戰爭后的五口通商又被迫卷入現代化的漩渦,繼而又有洋務運動與民族資本主義的興起,但這些都沒有動搖小農經濟的根基。與之相適應,統治者仍把以農為本、重農輕商作為基本國策,知識界對農業的認識仍是以不變應萬變,信奉傳統文化定義的重農抑商、重利輕義的那套說教。
張謇所處的年代,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猶如一塊魔方,由四個不同側面,或者是四個不同的過程相互交織相互激蕩而成。這個過程包括統治集團自身衰敗的過程、半殖民地化的過程、革命化的過程、現代化的過程。因此,近代中國既面臨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又面臨現代化的時代潮流。順應這一潮流,扛起歷史任務,就成為所有仁人志士的共同選擇。正如張謇所說,“謇不幸而生中國,不幸而生今之時代,尤不幸而抱欲為中國伸眉書生吐氣之意愿,致以皭然自待之身,溷穢濁不倫之俗”(《為實業致錢新之函》)。因此,“捐棄所持,舍身喂虎”就成為張謇的人生選擇。
張謇“家世務農”,在科場蹉跎了幾十年,具有扎實的傳統文化功底,終于“大魁天下”,獲得“天子門生”的殊榮。但張謇又不同于一般的士大夫,更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腐儒,而是繼承了顧炎武等人經世致用思想,主張“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并告誡世人“雄節不忘田子泰,書生莫笑顧亭林”(《張季子九錄·詩錄》)。
在與社會各界的接觸中,在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中,在致力于早期現代化實踐中,張謇逐漸脫離了傳統文化軌道,對農業有了新的認識,揚棄了傳統的小農理論,形成了自己的“大農論”。
縱觀張謇的文稿,他并沒有就大農的概念與內涵作系統的闡述,而是從不同側面豐富自己的“大農論”。擇其要點有:
——農業不再是一個封閉的部門,而是實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實業救國”是張謇的一貫主張與不懈追求,而實業并不是專指工業或商業,也包括農業。工業也不專指傳統手工業,也包括機器大生產。張謇認為,所謂“實業者,西人賅農工商之名,義兼本末,較中國漢以后儒者重農抑商之說為完善,無工商則農困塞”。可見,張謇并不是就農業說農業,而是把農業作為實業的有機組成部分,進而提出“父教育、母實業”的主張。
——農工商三者是有機聯系的。張謇非常重視農業,“凡有國家者,立國之本不在兵也,立國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與農,農為尤要”(《張謇全集》第二卷第13 頁)。但是,張謇重農并不抑商。張謇認為,“本對未而言,猶言原委,文有先后而無輕重”。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重農抑商的說教。他舉例說:“棉之始,農之事;棉之終,商之事,其中則工之事。”在張謇眼中,農工商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形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產業循環鏈,“蓋農不生則工無所作,工不作則商無所鬻。相應之勢,理所固然”(《請興農會奏》)。因此,“農工商必兼計而后能相救”(《張謇全集》第二卷第800頁)。
——“大農”與“小農”有諸多不同。張謇認為,“實業在農工商,在大農大工大商”。“大農”與“小農”有明顯區別:在經營形式上,小農是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而大農則是“仿泰西公司集資堤之”,“凡有大業者,皆以公司為之”;在生產工具上,“小農”是人力加畜力,而“大農”主要是“用機器墾植”;在生產目的上,“小農”是自給自足,“大農”主要進行商品化生產,為工業化提供原料;在經營方式上,“小農”是分散的小規模經營,只能從事簡單再生產,“大農”則是規模化經營,可進行擴大再生產。所謂“擴充棉產,獎勵大農,非大農不能有此擴張之能力”“種植棉花,需倚大農”;在要素投入上,發展大農需要金融等社會化支持,“非大農足以收宏效,然行大農法,必有一金融機構為之后援,乃可措手”(《張謇全集》,第二卷第238頁)。
當同時代官僚士大夫圍繞“中體西用”與“全盤西化”、圍繞“以農立國”與“以商立國”等爭論不休時,張謇已率先把目光轉向農業轉型,形成了自己的“大農論”,豐富了我國的農業發展思想寶庫。
實踐層面的快人一步
張謇不僅在理論層面上提出“大農論”,還在實踐層面率先實踐“大農論”,為引領農業轉型發展樹立了典型。
張謇的大農實踐始于1901 年。該年5 月,張謇等集資創辦的通海墾牧公司正式成立。墾區總面積232平方公里,合12.5萬畝,其中可墾地11.5萬畝。經過十年的艱苦創業,歷經“四難”,即與天斗(雨澇)、與地斗(鹽堿)、與海斗(風潮)、與人斗(地權),有計劃地修筑海堤、興修水利、招募墾戶、建造農舍、改良土壤,引進良種,終于建成。1911年公司開始盈利,當年給股東分紅31425兩。從1911年到1925年,公司所獲純利高達84 萬兩,幾乎為原始投資的3 倍。張謇在《墾牧鄉志》記曰:“各堤之內,棲人有屋,待客有堂,儲物有倉,種蔬有圃,佃有廬社,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一小世界矣。”(《張謇全集》第三卷第395頁)。
通海墾牧公司的成功帶來了興辦墾牧公司的熱潮。資料顯示,到1920 年止,張謇先后成立了大有晉、大豫、中孚、通遂、大豐、通興、華成等公司。上述公司共投入資本2199萬元,所占土地面積455萬畝,已開墾土地70萬畝之多。
在張謇的帶領與影響下,江蘇東部沿海北起阜寧、南至南通,綿延600多里的沖擊帶上,迅速崛起了眾多鹽墾公司,其中屬于大生系統的有16家。這些公司進行大規模的廢灶興墾,改良土壤,興修水利、引進馴化良種,在荒涼的鹽堿地上譜寫了墾荒史上雄偉、悲壯的樂章。截至20 世紀20 年代,這些公司已擁有土地2000余萬畝、植棉400余萬畝,年產棉花60余萬擔。
雖然墾牧公司投資總額、所占面積、股東構成不同,但有以下共同點:在經營形式上,“份泰西公司集資堤之”,如通海墾牧公司“集股股本的規銀二十二萬兩為準”,每股規銀一萬兩,共二千二萬股;在經營機制上,采用“公司+農戶”的形式,農戶主要負責生產管理,公司主要負責規劃、水利等任務;在生產目的上,主要為棉紡工業提供優質棉花,從事商品生產。因此,張謇的農業實踐已明顯脫離了傳統的小農軌道,既開墾了大量荒地,緩和了人地矛盾,增加了政府收入,支持了工業化,又成為我國農業現代化的有益探索,也可以說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發軔。
從現有史料來看,張謇的大農實踐固然保留了不少傳統性,但更多地體現了現代性:
從要素投入來看,農業增長的貢獻主要依靠土地、勞動力等傳統要素更明顯地轉向依靠資本、科技等現代要素。農業的發展離不開土地與勞動力,也就是所謂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小農”如此,“大農”也是如此。兩者的區別在于小農只是土地與勞動力的簡單結合,一塊土地與一個家庭就可進行周而復始的生產。大農也離不開土地與勞動力,更離不開資本與科技等現代要素,張謇通過股份制這一全新的組織形式,把社會閑散資金匯集為巨額資本,滾動開發鹽堿荒地,不僅獲得了大量土地,緩和了人地矛盾,還有力地支持了早期工業化。在產前環節,墾牧公司投入大量資金圍墾造田,開展水利工程建設與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在產中環節,又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土壤改良、設立農校、棉紡試驗場、推廣新技術、引進馴化新品種,有效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在產后環節,又用大量資金收購棉花,引導農民進行商品生產,促進了農業的內部分工,擴大了農業多樣化聯系,加快傳統農業與農民的轉型發展。可見,資本與科技在張謇的大農實踐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從經營機制來看,生產經營的形式由千家萬戶的分散經營轉向“公司+農戶”的產業化經營,形成了較為完善的農業經營模式。家庭分散經營是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征。這種經營方式是一種“全把式”的小農業,內部沒有分工,外部缺失聯系。這種小農經濟十分脆弱,又極易再生,是傳統專制政治的經濟基礎。張謇的大農實踐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公司這一市場主體,形成了“公司+農戶”的新模式。就土地權限而言,張謇將墾牧公司的土地劃分為“田底權”與“田面權”,公司擁有田面權,負責水利工程和農田基本建設,向政府繳納田賦,承諾進行建設時優先雇傭佃戶,代建農舍(收費)等。公司將20 畝為一窕出租給農戶,佃戶擁有“田面權”,只要交付“頂首”(押金)每畝6元,佃戶就可獲得“田面權”。且佃戶一旦獲得“田面權”,田主不可收回租佃權,實際上就是“永佃制”,擁有了處置土地的轉租、典押、傳給后代等權益,還可獲得土地改良后部分地價升值收益。這種土地關系與當時南通地區通行的“活佃制”相比,對公司與農戶都有利,實現了“雙贏”。農戶多交了一倍的押金,但獲得了永佃權,有了穩定的經濟預期,且每年可少交一半田租;而公司通過“伸佃頂”獲得了更多資金,緩解資金困難,可以進行滾動開發。
就分配關系而言,在公司的引導下,農戶以家庭經營方式進行生產經營,一年兩熟,上半年種植谷類、豆類,下半年種植棉花。到收獲時,由公司派人估產(議租),收獲物按四六分成,公司為四、農戶為六,納稅的棉花交給公司,多余的棉花也按市場價格以現金形式兌付給農戶。這種議租分成制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歉年時,業佃雙方共擔損失;豐年時,業佃雙方共享其成。
就雙方權責而言,公司負責水利建設、農田基本建設、新品種的引進與推廣、棉花的收購、代建農舍等工作。公司還承擔墾區內堤渠、涵洞、道路、橋梁工程公共設施的維修,所需人工則優先雇傭佃戶。農戶主要職責是生產經營,以家庭為單位進行農業生產。
由此可見,公司與農戶建立了一種特殊的生產關系。公司決定農戶生產什么,負責將其產品變成工業原料,把農戶納入現代經濟軌道;農戶則按照公司的要求,組織農業生產,為家庭增加經濟收入。農戶與公司是一種互利關系,公司增加了現金流,有了穩定的工業原料基地;農戶則提高了生產積極性,產品有了穩定的銷路。土地為公司與農戶共有,這與地主封建所有制有本質區別。
從功能作用來看,農業產業發展由單一的食品供給轉向多功能拓展。在張謇的大農實踐中,農業不再是封閉的循環,而是現代實業的一部分,與其他部門的聯系越發緊密。就農業與工業的關系而言,大生公司與墾牧公司相互支持,融為一體。大生公司為墾牧公司提供資金支持,墾牧公司則為大生公司提供價廉質優的工業原料;在大生轉盈為虧時,又給大生以可觀的經濟回報。就生態環境而言,張謇的大農實踐改變了墾區的面貌,白茫茫的荒灘變成了良田與相對繁榮的村鎮,成為“新世界的雛形”。就功能而言,農業產業的多功能作用日益明顯,農業的產品貢獻、要素貢獻、市場貢獻、外匯貢獻等基本功能持續存在并得到加強,旅游觀光、江海文化傳承等新的功能逐漸顯現。就產業發展而言,農業產業橫向與縱向聯系不斷加強,產前、產中、產后緊密銜接,產加銷、貿工農環環相扣,形成了多元化的產業形態與產業體系,初步形成農業經營的新局面。
與那些負氣、空言的官僚士大夫相比,張謇的大農實踐無疑是有價值的,不僅開墾了大量荒地。增加了物質財富,支持了工業化,還成為我國早期農業現代化的典型。但張謇的大農實踐又是不可能成功的,這不僅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缺乏現代化的環境與條件,還因為張謇的大農實踐是一個“早產兒”。中國工業化處于初始時期,自身力量十分弱小,沒有也不可能形成改造傳統農業的動力。因此,當大生集團進入下行通道后,墾牧公司也就搖搖欲墜了。
行政推動層面的勝人一籌
張謇的一生是豐富多彩的,有時居廟堂之高,身居“總長”等要職;有時又處江湖之遠,致力于“村落主義”;更多是以“通官商之郵”的特殊地位為踐行“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夢想嘔心瀝血。
張謇當過幕僚、翰林院修撰、實業總長、農林工商總長等職,擁有“天子門生”的光環,與當朝重臣翁同龢、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擁有豐富的行政資源。他與執政當局的關系很復雜,有依賴的一面,比如張謇“奉旨總理通海商務”,請兩江總督派兵駐守墾區,打擊“沙棍”與土匪,維護農業生產秩序等;也有抗爭的一面,比如張謇對一些官僚不識時務表示失望,對政府的苛捐雜稅進行抵制,對軍閥混戰進行批評等。
雖然居官的時間不長,但張謇長袖善舞,抓住“窗口期”,綜合運用組織、行政、立法、經濟等手段扶持大農、改造小農,并獲得了一定的成效。
——提出設立農會。發展大農離不開農會。為了有效發展大農,張謇多次建議設立農會,加強對農業生產的研究、管理與指導。他提出,應在上海設立總會,各地設立分會,農會應開設農學堂,延聘外國農業人才。他還明確農會的三大任務,即辨土壤、考物產、籌資本。張謇還參考英國、美國農會的經驗,提出了農會的創辦方法、經濟來源、功能作用等。
——強化行政推動。張謇在擔任實業總長與農林工商總長期間,主持起草了一系列促進實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倡導興農墾殖、廢除苛捐雜稅、制訂銀行條例、發布《商業注冊章程》。他還發布了《關于征集植物病蟲及害蟲給各省民政長官的訓令》,頒發《勸農員章程》。張謇還以總長身份對改良土壤、病蟲害防治、種子改良、農具改進、金融服務等提出了具體要求,為大農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推動農業立法。張謇以為,農林工商部第一計劃,“即在立法”。在總長任職兩年中,親自主持修訂頒布了“二十余種農商部法規”(《九錄·政聞錄》卷七),諸如《森林法》《國有荒地承墾條例》《造林獎勵條例》《植棉制糖牧羊條例施行細則》等,為農業發展特別是大農發展創造了法制條件。
——運用經濟手段扶持大農。無論是墾荒還是種植,張謇都把大農作為重點,在獎勵方面向大農傾斜,支持建立規模化的生產基地。
張謇綜合運用多種手段扶持大農發展,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有效促成了民國初年墾荒高潮,加速了民國初年農業現代化進程。但因當時的歷史條件,有的文件成為了一紙空文。
改進傳統小農,發展現代大農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沒有也不可能在張謇手中完成。但張謇的先人一拍、快人一步、勝人一籌,無疑奠定了他在農業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因此,研究中國工業發展史,不能不提到張謇;研究中國農業發展史,不能忽略張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