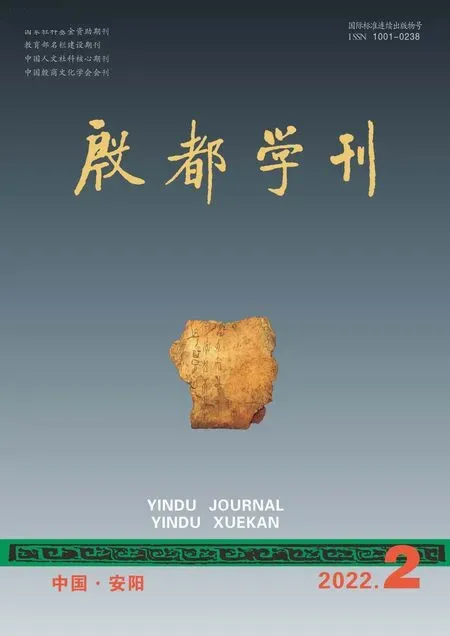“桑林祈雨”及其相關問題研究
李銀良
(安陽師范學院 甲骨學與殷商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安陽 455000)
夏商之際,持續幾年干旱,危及了剛剛建立的商政權。商王統治集團采取了積極救災措施,諸如鑄造金幣、推廣“區田法”等,此外還有著名的“桑林祈雨”等。根據文獻記載,“桑林祈雨”是在干旱持續數年后才采取的祭祀活動。但是,后世對“桑林祈雨”故事津津樂道、大書特書,而真正起到實質性作用的“區田法”以及其他措施被有意或無意地淡化了!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通過分析,本文認為“桑林祈雨”滲透了天命觀,突出商王擁有與神溝通的能力,反映了“君權神授”的思想,統治者借此說明商朝建立和商湯統治的正當性,目的是鞏固王權。
一、桑林祈雨
(一)旱災連年
夏商之際,旱災盛行,史書上亦有記載,如《國語·周語上》“昔伊洛竭而夏亡。”(1)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第27頁。《墨子·非攻下》“逮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谷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余。”(2)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間詁》,中華書局,2001年,第147-148頁。《呂氏春秋·慎大》也有“商涸旱,湯猶發師”的記載(3)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中華書局,2009年,第356頁。。
此次旱災持續時間很長,波及面很廣。旱災時間或有“五年之說”,如《墨子·七患》“《殷書》曰:‘湯五年旱’。”(4)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間詁》,第28頁。《呂氏春秋·順民》“五年不收”(5)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第200頁。。除“五年之說”外,還有“七年之說”,如《莊子·秋水》“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6)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第1300頁。《荀子·富國》“湯七年旱。”(7)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第150頁。《左傳正義》引《書傳》“湯伐桀之后,大旱七年。”(8)《春秋左傳正義》卷31,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1947頁。《文選·思玄賦》李善注引《淮南子》亦云“湯時大旱七年。”(9)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65頁。今本《竹書紀年》也有類似記載(10)今本《竹書紀年》記載:“十八年癸亥,王(商湯)即位,居亳。”“十九年,大旱。”“ 二十年,大旱。”“二十一年,大旱。”“二十二年,大旱。”“二十三年,大旱。”“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參見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卷上,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17頁。。
可見,夏末,天下大旱,商湯滅夏后,旱災仍然肆虐橫行。面對如此困境,在大旱五年或七年后,商湯舉行了隆重的祈雨祭祀活動,這就是著名的“桑林祈雨”。
(二)“桑林祈雨”活動
“桑林祈雨”的故事,史書屢見。如《荀子·大略》:“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11)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595頁。《尸子·君治》:“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著布衣,嬰白茅,以身為牲,禱于桑林之野。當此時也,弦歌鼓舞者禁之。”(12)汪繼培輯:《尸子》卷下,清嘉慶十七年刻本(湖海樓叢書),第12頁。《呂氏春秋·順民》對之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翦其發,磨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13)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第201頁。
《文選·思玄賦》李善注引《淮南子》也有類似記載:
湯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曰:我本卜祭為民,豈乎自當之。乃使人積薪,剪發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燃,即降大雨。(14)蕭統編,李善注:《文選》,第665頁
商湯通過隆重的祭祀活動,感動了天帝,最終求得大雨。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以下信息:商湯祈雨的地點是桑林,祭品是自己(人牲),祭祀方式是焚燒,祭祀對象是上帝鬼神。對之,我們逐一加以分析。
(三)“桑林祈雨”探析
1.桑林之社
商湯祈雨于桑林,“桑林”在何地?《左傳·襄公十年》正義引《書傳》作“湯禱于桑林之社。”(15)《春秋左傳正義》卷31,《十三經注疏》,第1947頁。《帝王世紀》也有湯“禱于桑林之社。”(16)皇甫謐撰,徐宗元輯存:《帝王世紀輯存》,中華書局,1964年,第65頁。可見,桑林是商人之社(17)魏建震:《先秦社祀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6-90頁。。
“社”的起源很早,它的最早形態是先民們對自然土地的崇拜。土地生育萬物,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根本,故而先民會定期向土地報德祭祀。正如《白虎通·社稷》所記載的“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18)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2013年,第83頁。《春秋公羊傳·莊公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東漢何休注曰:“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故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19)《春秋公羊傳注疏》卷8,《十三經注疏》,第2237頁。但是,土地廣闊,不能遍祭,于是,先民就“封土為社”,以之代表土地之神,正所謂“土地廣博,不可遍敬也。五谷眾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20)《白虎通疏證》,第83頁。。
正是基于此,人們往往在“社”中舉行祭祀活動,以祈求農業豐收(21)魏建震:《先秦社祀研究》,第253-267頁。,如《史記·封禪書》所云“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谷”(22)《史記》卷28《封禪書》,中華書局,1959年,第1392頁。。農業的收成與雨水的多少有直接關系,故而遇到干旱或水災,人們往往在“社”里舉行祭祀,祈求“降雨”或“止雨”(“寧雨”)。商代甲骨卜辭中屢見此類活動,如下:
(1)乙卯卜,王求雨于土。《合集》34493 (第四期)
(2)癸丑卜,甲寅又宅土燎牢,雨。《屯南》4400(第四期)
(3)辛巳,貞,雨不既,其燎于亳土。《屯南》1105(第四期)
卜辭中的“土”即“社”,“土”是“社”的初文(23)孫海波:《甲骨文編》,中華書局,1996年,第518頁。。這種用法后世文獻屢見,如《詩·大雅·緜》“廼立冢土”,毛傳曰“冢土,大社也。”(24)《毛詩正義》卷16,《十三經注疏》,第511頁上。《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諸侯祭土”,杜注曰“土謂社也。”(25)《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2,《十三經注疏》,第2263頁。以上即為其證。辭(1)大意是:乙卯日占卜詢問,商王向社祈雨?辭(2)大意是:癸丑日占卜詢問,甲寅日在“又宅”(右邊的房子)用經過特殊飼養的牛燎祭社神,能否降雨?辭(3)大意是:辛巳日占卜詢問,雨水不足,是否燎祭亳社?以上卜辭說明祭祀土地神可以祈求降雨。在“社”里“祈雨”的習俗一直延續到后世,如《春秋繁露·求雨》記載漢代“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山川。”(26)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第426頁。
雨水多了,產生澇災。有時商人也在“社”里舉行“止雨”(“寧雨”)祭祀活動,卜辭如:
(4)翌辛亥燎。(正)
燎土,不延雨。(反)《合集》14393(第一期)
辭(4)是占卜詢問在未來的辛亥日舉行燎祭,占卜詢問舉行燎祭社神,雨不會連續下嗎?在“社”里舉行“止雨”(“寧雨”)”活動的習俗,后世也有,如《左傳·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27)《春秋左傳正義》卷10,《十三經注疏》,第1780頁。《春秋繁露·止雨》“雨太多……令縣、鄉、里皆掃社下。”(28)《春秋繁露義證》,第437頁。
2.烄祭祈雨
商湯以己為犧牲,采用焚燒的祭祀方式來祈雨。在商代,通過用人牲(有時是動物牲)放到木柴堆上進行焚燒,以此來達到與天帝神靈的溝通,促使有關神靈布施雨水(29)陳夢家先生認為“烄”字“以人立于火上以求雨”,張秉權先生“象一個人交股被火焚燒的形狀……在甲骨文時代,烄是專門用來求雨的一種風俗。”詳見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中華書局,1988年,第602頁;張秉權:《殷代的農業與氣象》,《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第2分,1970年,第317頁。,這一祭祀活動稱為“烄祭”(30)“烄”字,有學者認為是“焚”字,該字甲骨文字形像尪在火上,是專指“焚巫尪”之“焚”的異體(裘錫圭)。詳見裘錫圭:《說卜辭的焚巫尪與作土龍》,胡厚宣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33頁。。所謂的“烄”,《說文》“交木然也”之說“非其本義”,后世文獻所記“暴巫”之俗“猶烄之遺風”(31)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姚孝遂按語”,中華書局,1996年,第1123頁。。“烄”在甲骨卜辭中,可作祭名,也可表示用牲方法。甲骨卜辭屢見,茲錄代表性如下:
(5)貞,烄,有雨。
勿烄,亡其雨。《合集》12842正(第一期)
(6)于甲烄凡。
弜烄凡,不雨。《合集》32296 (第四期)
(7)戊申卜,其烄泳女。
勿烄,雨。《合集》32298(第四期)
辭(5)是正反對貞,大意是:貞問,舉行烄祭,會有雨嗎?不舉行烄祭,不會下雨嗎?凡,人名;泳女,泳地之女。辭(6)和(7)均說明了用人牲進行烄祭,辭(6)大意是:占卜詢問在甲日是否用凡(人牲)舉行烄祭,是否會下雨嗎?辭(7)大意是:戊申日占卜詢問是否用泳女(人牲)舉行烄祭,是否會下雨嗎?
烄祭祈雨的方法一直延續后代。如《左傳·僖公二十一年》記載“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諫曰:‘非旱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杜注:“巫,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32)《春秋左傳正義》卷14,《十三經注疏》,第1811頁。《太平御覽》卷十引《莊子》春秋“宋景公時,大旱三年,云:以人祀,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吾所求雨者,為人,今殺人,不可。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33)李昉等:《太平御覽》卷10,中華書局,1960年,第51頁下。《春秋繁露·求雨》云:“春旱求雨……暴巫聚尪八日。……秋暴巫尪至九日。”(34)《春秋繁露義證》,第426-427、434頁。
3.向上帝鬼神求雨
桑林祈雨,商湯祭祀對象是上帝天神。上帝,或作帝,是天神。在商人的意識中,“上帝(帝)是高高地居于天上的天神”,是“統領雨、雷、雹、風等自然神商王主神”,“操縱著下雨與不下雨的大權”(35)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國社會出版社,2010年,第28、32頁。。商人祈雨于上帝,甲骨卜辭屢見,如下:
(8)辛亥,內貞,今一月帝令雨。四日甲寅夕[允雨]。
辛亥卜,內貞,今一月[帝]不其令雨。《合集》14295正(第一期)
(9)辛未卜,爭貞,生八月帝令多雨。
貞,生八月帝不其令多雨。
丁酉雨至于甲寅,旬有八日。九月。《合集》10976正(第一期)
令,即命令。辭(8)和(9)均是占卜詢問帝(上帝)是否命令雨神下雨或多下雨的。根據驗辭情況,有時祭祀上帝天神后,會有降雨,如辭(8)中有“允雨”的驗辭。
二、“區田法”與“鑄金幣”
如前文所述,商湯是在大旱持續五年或七年后才舉行了“桑林祈雨”活動,那么在持續干旱的幾年中,商湯是怎樣帶領民眾進行自救的呢?或許與“區田法”和“鑄金幣”等措施有密切關系。
(一)“區田法”
所謂的“區田法”是一種抗旱豐產的耕作方法。《氾勝之書·區田法》記載:“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36)萬國鼎輯釋:《氾勝之書輯釋》,中華書局,1957年,第62-63頁。
“區田法”非常適合我國北方地區干旱少雨的自然條件,主要有以下特點和優勢(37)參見郭文韜:《中國北方旱地耕作的歷史經驗》,《中國科技史料》1987年第4期;范楚玉:《漢代的區田法和代田法》,《文史知識》1988年第2期。:一是抗旱“保墑保肥”。由于區田要深翻作區,便于小面積的澆灌,糞肥集中,并且水分蒸發和流失少,所以,非常適合旱作物種植,這也是度過旱災的理想選擇。二是區田對土地質量要求不高(38)范楚玉:《漢代的區田法和代田法》,《文史知識》1988年第2期。,正如上文所言“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因此,適合做區田的地方很多,“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這樣以來區田就便于推廣。三是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由于區田一般面積較小,有利于集中供水和肥料,單位面積的產量會大幅度提高(39)《北堂書鈔》卷39《興利》:“氾勝之區田云:昔湯有旱災,伊尹作區田云云。乃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為之,收至畝四十石。”據《太平御覽》卷821《資產部·田》也有類似記載。參見虞世南:《北堂書鈔》,中國書店,1989年,第108頁上;《太平御覽》卷821,第3658頁下。。正是由于以上特點和優勢,伊尹推廣了區田,這樣至少可以解決口糧問題,使得民眾度過持續的旱災。
至于伊尹是否是發明“區田法”第一人,無法給出確切的回答,或者說很有可能“區田法”早已有之,作為卿士的伊尹只不過加以改進,然后在大面積干旱區域內進行提倡和推行。伊尹推廣的“區田法”幫助民眾度過了旱災,故而人們以伊尹發明“區田法”以示紀念。但無論如何,在這次持續旱災中,伊尹推廣的“區田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穩定了生產,安定了民心,維護和鞏固了新生政權。
(二)“鑄金幣”
除了“區田法”外,還有其他方法,如鑄金幣等。在古代,如果遇到天災之年,國家往往通過鑄造貴金屬貨幣方法,來加強物資流通和控制物價,借此賑濟災民。如《周禮·地官·司市》:“國兇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鄭注曰:“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為民乏困也。金銅無兇年。物貴,大鑄泉以饒民。”(40)《周禮注疏》卷14,《十三經注疏》,第735頁。《周禮·地官·賈師》《國語·周語》也有類似記載(41)《周禮·地官·賈師》載“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國語·周語下》也有類似記載: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參見《周禮注疏》卷15,《十三經注疏》,第738頁;《國語集解》,第106頁。。
面對持續的旱災,成湯就采取了鑄造貴金屬貨幣方法,緩和社會矛盾,度過了天災。如《管子·輕重》“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42)《管子校注》,第1300頁。《鹽鐵論·力耕》也有“湯以莊山之銅,鑄幣以贖其民,而天下稱仁。”(43)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第27頁。今本《竹書紀年》也有成湯二十一年“鑄金幣”記載(44)《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卷上,第17頁。。商湯通過鑄造發行貴金屬貨幣的方法,調控物資供求,促進商品流通,調配有余、補給不足,穩定物價,贏得民心(45)《鹽鐵論·力耕》對災年鑄幣的舉措有較為詳細的表述,其文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兇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余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參見《鹽鐵論校注》,第27頁。。
“區田法”與“鑄幣”措施在商初旱災中均起到了積極作用。“區田法”增加了糧食產量,起到了“開源”的作用,是國家政權安全的重要基礎;“鑄幣”的措施促進了商品流通,調節了物資分配。
三、桑林祈雨與商王統治的正當性
與“區田法”“鑄金幣”等措施相比,“桑林祈雨”卻為后世關注和廣為宣傳,之所以如此,這與商王統治的正當性以及王權鞏固有關。討論這一問題,首先要理清我國古代王權的來源和組成。
(一)我國古代王權的重要來源和組成之一——宗教祭祀權
我國古代王權有三個來源和組成:宗教祭祀權、軍事指揮權、族權,這三個方面的發展構成了王權發展的三個重要機制。(46)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6-372頁。就宗教祭祀權來說,對于大部分“原生形態的國家,在其形成的過程中,既產生了掌握祭祀、行政和軍事的最高統治者或執政,也形成了一個輔佐統治的祭司或巫師階層,這也是當時唯一的知識階層,我國古代稱之為‘宗祝卜史’。”(47)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第369頁。這一集團隨著社會的分化和發展,逐漸形成了管理階層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我國三代時期,王權往往會帶有一種神圣性,而且王權的神圣性和宗教性是一致的(48)王震中先生提出中國古代國家形態演進:邦國——王國——帝國三階段和三種形態,其中夏商周三代屬于王國時代。夏商國家結構屬于多元一體的、以王國為“國上之國”的“復合制國家體系”,作為“天下共主”的王,既直接統治著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謂的“王畿”地區(王直接控制的直轄地),也間接支配著臣服或服屬于他的若干邦國。參閱王震中:《邦國、王國與帝國》,《河南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王震中:《夏代“復合型”國家形態簡論》,《文史哲》2010年第1期;王震中:《論商代復合制國家結構》,《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3期;王震中:《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59-66頁。。也就是說,“王權中含有濃厚的神權”,這充分說明了“對于最高神靈和王族祖先神靈的宗教祭祀的獨占,是王權獲得發展和加強的又一機制”。(49)王震中:《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第470頁。
(二)王權行使的重要體現之一——宗教祭祀權
如前文所述,宗教祭祀權是王權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反過來,宗教祭祀權也是王權行使的一個重要體現。三代之王自稱代“天”或“帝”來統治天下,特別強調“君權神授”,借此來構建統治的正當性。商代也不例外,商湯在滅夏活動以及商朝建立過程中,對政權正當性的建構做了一系列努力,其中之一就是爭奪和獨占最高宗教祭祀權。
首先,商王標榜自己有能力代表“天”或“帝”。商王借助先祖的神圣性,來說明自己擁有非凡的能力,如《詩·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50)《毛詩正義》卷20,《十三經注疏》,第622頁。《史記·殷本紀》記載商人始祖之母簡狄“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51)《史記》卷3《殷本紀》,第91頁。。簡狄因吞玄鳥卵而生商始祖契,正如所謂的“圣人皆無父,感天而生”(52)《詩·大雅·生民》孔穎達疏引《五經異義》說“《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圣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詳見《毛詩正義》卷17,《十三經注疏》,第529頁。,以此突出商代祖先的神圣性,商王借此標榜自己有能力代表“天”或“帝”。
其次,商王一般通過戰爭征伐和祭祀等活動來代表“天”或“帝”。商王可以借助“天”“帝”之名征伐,如《書·湯誓》《詩·商頌·玄鳥》等均有記載(53)如《書·湯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詩·商頌·玄鳥》也有“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商湯把征伐夏桀的行動冠以“上天”或“帝”命令,除了鼓舞士氣外,還說明商湯也可像夏王一樣代“天”和“帝”行使權力。參見《尚書正義》卷8,《十三經注疏》,第160頁;《毛詩正義》卷20,《十三經注疏》,第622頁。除了戰爭征伐外,商王還充分利用祭祀活動建構新生政權的正當性,如“桑林祈雨”。“桑林祈雨”的成功,不僅緩解了長期的旱情,收到了民心。同時,商湯借此宣傳自己有能力與天帝神溝通,傳達天帝之命。既然商湯擁有與神溝通的能力,那么,商湯就可以代表天或帝在人間行使權力,借助天或帝命以立威嚴、成人事、制臣民。商湯所擁有的權力是天然合理性,而由他所建立政權的正當性也被廣大民眾所認同。
(三)突出商王的威信,王權至上
與“桑林祈雨”相比,在長期干旱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區田法”以及“鑄金幣”等措施被有意或無意地淡化了,客觀上來說,這也是為了鞏固王權的需要。“桑林祈雨”是以商湯(王)為主體的主動行為,而“區田法”可能是以伊尹作為“卿士”(臣)的行為。比較而言,商王是第一位的,或者說“桑林祈雨”故事更容易被利用。
商湯統治集團借助“桑林祈雨”的成功以及天帝的神秘性,對當時民眾來說具有一定的感召力和迷惑性(54)這種行為影響深遠,“就直到二千年后的今天,對于‘老天爺’的信仰也依然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民間,只要有一‘替天行道’的狂信者出現,便立刻可以造成一種教派”。參見郭沫若:《青銅時代》,《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2頁。。這樣使得商湯的威信進一步提高,王權至上的觀念更加鞏固。史書對“桑林祈雨”的大書特書、經久不衰,目的是凸顯“君權神授”觀念,也是為了鞏固王權需要。
結語
王權時代,王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也是國家的代表和象征,王的一些舉措是為了突出王權的唯一性和獨尊性。商湯立國后,從不同角度來建構政權的正當性,其中之一就是借助上帝天神的威靈和力量。“桑林祈雨”祭祀活動滲透了天命觀念,商人借此宣揚商王擁有與天帝神溝通的能力,營造王權的神秘化,凸顯了“君權神授”的思想,以此來說明夏亡商興乃是天命所致,商王朝建立和商湯統治是正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