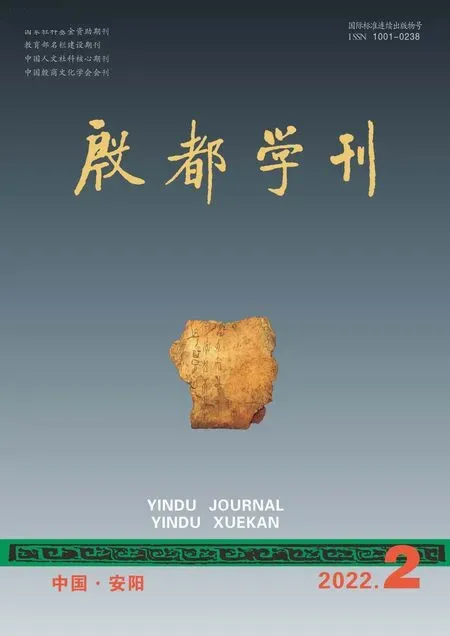記憶中的元上都
——《灤京雜詠》《元宮詞百章》對元上都的三重書寫
武 君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北京100732)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1358),肇建于元憲宗六年(1256)的草原都城——元上都(1)元朝實行兩都制,以今之北京為大都,又在灤河之陽建上都(在今內蒙古正藍旗境內)。上都,在元代又稱“上京”“灤京”等。元憲宗六年忽必烈在灤河龍岡建開平府,為其藩府駐地。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于開平稱帝,四年定開平府為上都。,燃起熊熊烈火。上都毀之一炬,不但預示著經歷近百年輝煌的大元王朝即將謝幕,也標示了有元一代,那些扈從圣駕,親歷上都壯麗宮闕,享受盛世華宴的文人,關于上都的現場書寫就此封筆。(2)從忽必烈時期始,實行兩都巡幸制,上都為夏都,皇帝車駕每年春天從大都啟程前往上都,秋季返回,后宮、宗藩、百司、館閣文臣皆扈從隨行。由此催生出元代創作最盛、歷時最久、范圍最廣的詩歌類型——上京紀行詩。據劉宏英、吳小婷《元代上京紀行詩的研究狀況及意義》,元代上京紀行詩作約千余首。《河北北方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此外元人也大量創作宮體詩,在上京紀行詩與宮體詩中有大量描寫上都宮闕、風光、宴飲、活動等詩歌。明朝初年,歸老故山的遺民楊允孚和明皇室周憲王朱有燉(3)楊允孚,字和吉,號西云,江西吉水人。顧嗣立《元詩選》錄其小傳。關于《元宮詞百章》的作者,王福利《〈元宮詞百章〉的作者考辨》(《河池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及黃凌云、汪如潤《朱橚〈元宮詞〉的史詩意蘊和價值》(《天中學刊》2015年第5期)認定為明周定王朱橚。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后序,劉禎《〈元宮詞百首〉的作者》(《中國文學研究》1986年第2期)認定周憲王朱有燉。后者考辨較實,今從之。,分別作《灤京雜詠》《元宮詞》各百余首,以大量筆墨書寫上都,用詩作勾勒個人意中的“記憶之城”。
記憶是《灤京雜詠》和《元宮詞百章》最基本的書寫方式,而這里所謂的“記憶”,是關于記憶的表述,是記憶的文學文本化表現。從記憶到記憶文本,記憶主體經歷了在場—不在場—再在場的轉變,記憶客體也經歷了喚回—重構—理解的過程,而其間發揮更為關鍵作用的是存在于記憶主、客體之間的文本書寫者,他們與記憶主體構成間性關系。如此,對記憶文本的研究,似乎更要走出文化記憶研究者所提出的“誰來記憶”“記憶什么”“如何記憶”的內容,進而叩問“記憶如何表述”“記憶被誰表述”“怎樣理解表述的記憶”的問題。即如德國學者阿斯特莉特·埃爾(Astrid Erll)所謂的“文學中的記憶”,探索文學作品對記憶的描寫和表現,考察文本在處理和演繹記憶內容及運作方式時所采用的手段。(4)阿斯特莉特·埃爾和安斯卡·紐寧認為記憶理論在文學中的應用有三個方向:“文學的記憶”(文學作為象征系統和社會系統)、“文學作為記憶的媒介”(文學作品的記憶媒介性)和“文學中的記憶”。阿斯特莉特·埃爾、馮亞琳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需要更加關注記憶文本的形成方式,記憶主體和書寫主體的間性關系,以及記憶文本的真實性及有效性問題。因此,從記憶到記憶文本的實現,主要體現在重現、重構、解釋三個方面。那么,一座已成煨燼的昔日都城如何被記憶和書寫?記憶文本書寫者的身份差異如何影響其使用不同的藝術處理方式,使這座都城再現于詩歌作品中?又會產生什么樣的情感與價值向度,賦予其何種不同的意義,進而重塑后人對故城的認知?本文擬將討論《灤京雜詠》《元宮詞百章》中的元上都書寫,于此探求其中之意。(5)對兩部詩集的研究大多據作序者所交代的“可備史乘”的意義加以考察,考證元上都歷史及風土民俗。李嘉瑜《記憶之城·虛構之城:〈灤京雜詠〉中的上京空間書寫》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分析《灤京雜詠》,認為元上都包含集體記憶和個人私密記憶的文化內涵。《文與哲》2011年第19期。劉偉楠《朱有燉〈元宮詞百章〉的思想傾向及其產生原因》認為朱氏對上都宮廷景致、建筑和生活的描寫不帶批評色彩,是出于對元正統論和文化自由的認同。《赤峰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而以《灤京雜詠》《元宮詞百章》為記憶文本,展開對其書寫方式、藝術處理、文化意義的同異分析顯然仍有待開掘。
一、期待的記憶與上都實景喚回
回憶是對既往的追溯。在回憶中,人們總是期待記憶的東西可以最大程度、盡量客觀地還原往事,消解因時空跨度而帶來的遺忘,讓過往的或已然消逝的事物可以清晰、完整地重現。重現(representation)是記憶的核心問題,它是文本的真實性表征。即便能夠回憶起的東西也許只是一些零散的碎片,甚至有些許失實,然而,無論對于回憶者,還是傾聽者來說,寧愿相信,記憶總是真實的,這種真實感或本真性首先來自于回憶者的親身經歷。
兵燹過后,一位老者回歸故里,在頹檐敗壁下“滌瓦榼,倒鄰釀”“回視曩游”(羅大巳《灤京雜詠跋》)(6)楊允孚:《灤京雜詠》,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用回憶的方式為鄉鄰知己講述一段過往的、真實的都城生活體驗。明人金幼孜《灤京百詠集序》云:“先生(楊允孚)在元時以布衣職供奉,嘗載筆屬車,之后因得備述當時所見,而播諸歌詠。”(7)金幼孜:《金文靖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22頁。無獨有偶,一位舊朝宮女經歷易代滄桑,輾轉流落到新朝王府中,為主人備陳宮中往事,朱有燉《元宮詞序》說:“永樂元年,欽賜予家一老嫗,年七十矣,乃元后之乳母女,常居宮中……知元宮事最悉,間常細訪之。”(8)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2頁。通過記憶線條,楊允孚和元宮女將早已莽為丘墟的元上都重新勾勒。而回憶者——一位曾出仕元廷的勝國舊臣和一位常居元宮又通曉蒙古族語言、宮中秘事的宮女,作為上都生活的親歷者,他們對這座草原都城、宮苑盛景的紀實講述,形成回憶者及傾聽者對于回憶期許的基礎。
親歷,勾連和印證了記憶與真實的關系,將記憶文本帶入到傳統意義上具有相對紀實性的文體中獲取“信認”。除卻《元宮詞》本身顯現的“宮詞”性質,《灤京雜詠》也以存典、自注的方式,歷來被視為體裁本自王建《宮詞》,是“自成體系的元宮詞”和“最后的上京紀行詩”。(9)楊鐮:《元代文學編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06頁。可以說,親歷是宮詞和紀行兩種詩歌體裁本有的內質,宮詞往往是轉述和表達親見者的見聞,張昱《宮中詞序》云:“大抵宮中詞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不可以文章工拙稱。必非想象,必親見,皆非閭巷之士可擬而賦者。”(10)柯九思:《遼金元宮詞》,陳高華點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18頁。“親見”“真實性”在宮詞的寫作中成為超越“工拙”的藝術標準。紀行是對實景的抒寫,王思誠題胡助《上京紀行》詩曰:“煌煌兩京城,關城阻千里。扈圣從鄒枚,紀行富詩史。”(11)胡助:《純白齋類稿》(附錄卷一),中華書局,1985年,第202頁。認為紀行可以充實詩歌作為史實的內容。《灤京雜詠》《元宮詞》的創作在某種意義上便是在提示和強調著這種“真實性”的存在,表達對存史的強烈欲望。
對于記憶真實性的期待,讓人有理由相信,有關回憶的內容可以作為佐證上都歷史的材料。金幼孜《灤京百詠集序》云:“然則后之君子,欲求有元兩京之故實……尚于先生之言有征乎!”(12)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722頁。朱有燉《元宮詞序》亦自言:“予詩百篇皆元宮中實事。”(13)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第2頁。實景、實況的記錄,在寫作者和閱讀者那里,都將其視為創作的原動力,它對詩歌解讀者的影響,也往往因之而集中于對其中史未曾載之掌故和風土景物的挖掘與考辨。箋注《元宮詞百章》的傅樂淑先生坦言:“余年來研究元史,頗注意當時宮廷之生活狀況,參證此書,時有悟解。”(14)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第1頁。記憶引人入勝的地方,就在于本體論范疇的可靠性,它能夠記錄歷史,竭力充當最接近本真、原貌的“親歷者”和“見證者”。
然而,記憶是獲取信息、編碼、存儲、提取的過程,記憶的內容在某種程度上并不能等同于歷史。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認為,歷史是“未被居住的記憶”,即記憶所面對的是紛亂的和未被整理的“史料”。(15)阿斯特莉特·埃爾,馮亞琳:《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7頁。《灤京雜詠》《元宮詞》成為考征元上都的史料,完成回憶期許,其實現方式是通過編碼、存儲、提取,使無序的材料變為符號。記憶便是對符號的處理,使之成為“被居住的記憶”,重現于記憶文本中。這里的重現更體現在語言符號作為中間環節對文本和真實的邏輯溝通,從而喚回一座記憶中的“真實”上都。喚回,是回憶的重要方式,在往事的凝視中,重新進入記憶現場,填補記憶空白,努力構筑一種實景的再現,由此構成《灤京雜詠》《元宮詞》對元上都最表層的書寫結構。那么,返回記憶現場,元上都在《灤京雜詠》《元宮詞》的書寫中呈現出怎樣的形象?
多年過后,回到江南故鄉的楊允孚和寄居新朝王府的元宮女,存留在他們記憶中的上都依舊呈現出一派壯麗和繁盛的景象,充滿了對這座草原都城異域景致和生活的驚艷,“耳目所及,窮西北之勝,具江山人物之形,狀殊產異俗之瑰怪,朝廷禮樂之偉麗”(羅大巳《灤京雜詠跋》)(16)楊允孚:《灤京雜詠》,第1頁。。言都邑:“圣祖初臨建國城,風飛雷動蟄龍驚。月生滄海千山白,日出扶桑萬國明。”(《灤京雜詠》)(17)楊允孚:《灤京雜詠》,第3頁。以龍居的傳說描述上都的神秘色彩,“日出”“月生”,異常光亮,極力渲染上都作為王城、圣城的空前壯大;言宮闕:“五云樓閣翠如流”(《灤京雜詠》),“上都樓閣靄云煙”(《元宮詞》)(18)楊允孚:《灤京雜詠》,第3頁。,極言宮闕之雄麗,大安閣、水晶宮、合香殿、棕毛殿、清寧殿等宮闕成為上都地標性建筑;言宴會:“錦衣行處狻猊習,詐馬筵開虎豹良。”(《灤京雜詠》)“棕殿巍巍西內中,御宴簫鼓奏熏風。”(《元宮詞》)(19)楊允孚:《灤京雜詠》,第4頁。極力描繪詐馬宴的盛容和宴會場景及食物的豐腴繁盛;言異域風光感受:“灤京九月雪花飛,香壓萸囊與夢違。”(《灤京雜詠》)“信是上京無暑氣,行裝五月載貂裘。”(《元宮詞》)(20)楊允孚:《灤京雜詠》,第10頁。竭力陳說上都寒冷的感官體驗;言殊產異俗:黃羊、黃鼠、白翎、金蓮、紫菊、地椒、芍藥、野韭、奶酒、奶酪、羊酥等異域物產不厭其煩地成為二者歌詠及標注的奇異物象。都邑之壯大、宮闕之雄麗與異域的殊產異俗、奇節詭行通過記憶隧道,成為回憶者在記憶中不斷“感知”和“捕捉”的上都意象。
意象,作為“詩人感知的物象”,是經作者情感和意識加工,“由一個或多個語象(物象是語象的一種,由具體名物構成)組成”,從而“具有某種意義自足性的語象結構”,而它的組成元素(語象)本就是具有心理表象的文字符號。(21)蔣寅:《語象·物象·意象·意境》,《文學評論》2002年第3期。關于記憶與意象的關系可參閱張宇慧《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記憶》,《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17年第5期。上都都邑、宮苑以及獨特的異域風土景物作為意象,其實在元代的上都文學書寫中已然形成。其表現便在于將上都物象與詩人主體經驗和意識作有意聯結,成為在記憶行為發生之前,就已經具有先驗情感結構的上都構形符號。
毫無疑問,元上都的建立以及兩都巡幸制度實施,為文人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全新的場域。這一場域一方面是作為承續王朝正統的都城象征,如將舊時的“漢式”宮殿熙春閣(位于宋時汴京)遷于上都而建大安閣;另一方面元上都亦保留著標示蒙古民族獨特風貌的景象和活動,如棕毛殿等“失剌斡耳朵”式的蒙古宮帳,以及其中不斷舉辦的詐馬盛宴。對于扈從文人來說,上都的一宮一殿,一草一物不僅帶給他們海宇混一的自豪感和震撼感,也因神秘的異域圖景而產生強烈的獵奇感。新場域的呈現,創新和豐富了書寫都城的意象群落,而一系列上都意象在元代詩歌創作中的不斷使用,也使之成為物象與城市感知相匹配的固定方式和具有建構性及程式化意味的符號,以此突出上都壯麗與陌生,承接詩人震撼感和獵奇感,形成元代詩歌書寫這種獨特主題所使用的較為一致的方式。楊鐮謂之為“同題集詠”,“幾乎全部館閣詩人、有一定影響的文臣,都是‘上京紀行詩’和‘宮詞’的作者”,歌詠上都主題的作品“有‘齊唱’,有‘輪唱’,有‘合唱’”。(22)楊鐮:《元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第649-650頁。李嘉瑜視之為“集體記憶的顯影”,是“位居時代主流的集體聲音和共同想象”,是“創造上京‘地方感’的重要元素”。(23)李嘉瑜:《記憶之城·虛構之城:〈灤京雜詠〉中的上京空間書寫》,《文與哲》2011年第19期。
然而,當“在場”的實景書寫向“不在場”的記憶書寫轉換時,這種“程式化”意象所具有的穩固的“意義自足性”,便不專注于同題創作和共同想象中的建構意義,而更在于它作為一種符號已經具有的城市構形屬性。換言之,記憶書寫所使用的系列上都意象,更側重于將之視作既定的,表現上都文學形象的“表情符號”,其目的更加直接地指向辨識與喚回上都,提示和喚起記憶的表象及畫面。而這種“喚回式”的書寫所使用的方式首先便是“復制”,宇文所安說,古典文學常常是“從自身復制出自身”,“從往事中尋找根據,拿前人的行為和作品來印證今日的復現”。(24)宇文所安:《追憶》,鄭學勤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1頁。這種復制和復現往往帶有濃郁的經驗性特征,比如對上都宮闕之雄偉壯麗的書寫:
大安閣是廣寒宮,尺五青天八面風。(許有壬《竹枝十首和繼學韻》之十)(25)許有壬:《至正集》(卷二七),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5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40頁。
層甍復閣接青冥,金色浮圖七寶楹。(周伯琦《是年五月扈從上京宮學紀事絕句二十首》之二)(26)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1863頁。
大安樓閣聳云霄,列坐三宮御早朝。(《元宮詞》)(27)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第1頁。
這三句詩對大安閣的書寫是一致的,即突出大安閣之高,可接云霄,是王城的象征。而給人直觀的印象是,許有壬、周伯琦筆下的大安閣描寫是在極力地“加工”。許詩首先與廣寒宮進行類比,讓人產生聯想,進而又補充“尺五青天”“八面風”的具體感知,周詩則以七寶佛塔之高來具體比對這座宮殿,通過這種類比和加工使得大安閣與表現上都宮闕的雄麗形成固定的匹配關系。這可以算作元代文人對大安閣形象描述的“集體聲音”,正如羅大巳所言,上都景致“中臺馬公祖常、奎章虞公集、翰林柳公貫,時能以雄辭妙筆寫其一二”(羅大巳《灤京雜詠跋》)(28)楊允孚:《灤京雜詠》,第1頁。,館閣文臣的文學書寫早已將這些景致變成了人們所熟悉的文學意象。那么,屬于記憶書寫的《元宮詞》對大安閣的描述便是對這種“集體聲音”的呼應,復制這種已然凝聚了固定“意識”的、成熟的上都意象,直接完成大安閣形象的構形,這里的大安閣已經具有了一定的形象性,通過“大安樓閣”與“聳云霄”的快捷描述,進而以“帶過”的方式轉入對下一個場景——宮內早朝的描寫。在《灤京雜詠》《元宮詞》中,無論是上都地標性的宮苑建筑,還是獨特的宴會和異域物產,抑或是由上都地域性的特征而引發的感官體驗,如“相國門前柳未花”(《灤京雜詠》)、“獨木涼亭賜宴時”(《元宮詞》)(29)楊允孚:《灤京雜詠》,第4頁。目的多是在提示場景,喚回其真實可感的形象。
如此,較之于通過類比、聯想等方式進行意象建構的書寫,“喚回式”的記憶書寫則更多采用白描手法,將上都意象作為一種實指意義的描述性意象,如:
紫菊花開香滿衣,地椒生處乳羊肥。氈房納實茶添火,有女褰裳拾糞歸。(《灤京雜詠》)(30)楊允孚:《灤京雜詠》,第8頁。
侍從皮帽總姑麻,罟罟高冠勝六珈。進得女真千戶妹,十三嬌小喚茶茶。(《元宮詞》)(31)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第33頁。
這兩首詩給人的感覺似乎有蒙太奇式的剪輯效果,意象紛來踏至地疊合在一起,自在地呈現。紫菊、地椒、乳羊、氈房、茶、火、衣裳、牛糞;皮帽、姑麻、罟罟冠、六珈(發簪玉飾)、茶茶(女子)等以名詞組合的方式形成描述性意象的并呈和跳躍,從而具有繪畫效果,由視覺透視情境,構成兩幅靜態的、清晰的畫面。白描的使用,意在指物造形的精細,用寫實的筆觸逼真地再現場景,使得記憶的文本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忠實”的摹寫,如同寫真集一樣,用圖相指示上都的具體形象。確如羅大巳所說,《灤京雜詠》的效果“使人誦之,雖不出井里,恍然不自知其道齊魯、歷燕趙,以出于陰山之陰,蹛林之北,身履而目擊。”(羅大巳《灤京雜詠跋》)(32)楊允孚:《灤京雜詠》,第1頁。上都形象的喚回,是回憶給人最美好的期許,但是,喚回的記憶果如我們的期待嗎?
二、情感距離與記憶文本重構
或許,每一位對回憶抱有天真期許的人,最終多會得到不容樂觀的回應。因為回憶總是與真實存在一定距離。這種距離的產生首先來自于時間,“回憶永遠是向被回憶的東西靠近,時間在兩者之間橫有鴻溝,總有東西忘掉,總有東西記不完整。回憶永遠是從屬的,后起的”(33)宇文所安:《追憶》,第2頁。。況且《灤京雜詠》《元宮詞》中的回憶行為發生時,中間不僅橫跨著普遍意義上的時間之流,更有改朝換代的歷史洪流激蕩起的劇烈波濤。同時,對于回憶者來說,這種距離也來自于空間印記的磨滅,他們所回憶的上都,是一座被戰火焚毀,永遠回不去的城,“度先生(楊允孚)往來,正當有元君臣恬嬉之日,是以不轉瞬間,海內分裂,而灤京不守,遂為煨燼”(34)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第722頁。。時空將回憶者阻隔在記憶的彼岸,讓回憶變為一種永恒的回望。而更關鍵的距離感,來自于由時空距離而造成的親歷者與書寫者身份的變化與分離,進而所產生的情感距離。
揚·阿斯曼(Jan Assmann)說:“記憶是一種有著身份指向的知識。”(35)阿斯特莉特·埃爾,馮亞琳:《文化記憶理論讀本》,第123頁。身份,在這里,不僅有記憶主體身份的區別,也更表現為書寫者與記憶者的身份差異。元代上都題材的詩歌,其創作主體大多是扈從文臣和館閣詩人,在“在場”的創作活動中,親歷和書寫是即時的,親歷者和書寫者的身份也是合一的。然而正是由于身份的重疊,扈從文臣和館閣詩人的上都書寫不免有“身在此山”的情感隔閡,正如蘇天爵《跋胡編修上京紀行詩后》所言:“朝士以得侍清燕,樂于扈從,殊無依依離別之情。”(36)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八),陳高華、孟繁清點校,中華書局,1997年,第470頁。而《灤京雜詠》雖是通過楊允孚自己的親身經歷,以個人回憶的方式展開的個人書寫,但當他提筆書寫之時,身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羅大巳《灤京雜詠跋》說:“君固已杜門裹足,歸老故山,方日與田夫野叟相爾汝,求以自狎。”(37)楊允孚:《灤京雜詠》,第1頁。又其好友郭鈺《題楊和吉灤京詩集》詩云:“豈知歸去煙塵驚,山中閉門華發生。云氣蓬萊心未已,夢中猶在東華行。”(38)郭鈺:《靜思先生詩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47頁。在元明易代之際,楊允孚歸隱山林,以遺民自居,使他從一位上都生活的體驗者變為離開者,轉而又成為上都的追憶者和緬懷者。這種身份的變化,反而拉近了楊允孚與上都的情感距離。在對往事的回憶中,傾注了他深沉的懷舊情緒,讓人慨然詠嘆,悠然遐思。故而四庫館臣在評價《灤京雜詠》時說:“故宮禾黍之感,則與孟元老之《東京夢華錄》、吳自牧之《夢梁錄》、周密之《武林舊事》同一用意。”(39)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中華書局,1960年,第1458頁。《元宮詞》的情況則更加復雜,它的創作已經完全進入了另一個時代(40)據朱有燉自序,《元宮詞百章》作于永樂四年(1406),此時離上都焚毀已過去將近半個世紀。,更何況書寫者和親歷者(回憶者)是分離的,書寫者的身份是一位新朝王室宗藩,以旁觀者的姿態和代言的方式轉述記憶的內容,其間有一種居間的關系存在。不難想見,在《元宮詞》的創作過程中,存有那些“引誘”和“調解”記憶的因素。這種身份的分離,無疑,又拉開了作者朱有燉與上都的情感距離。
如此看來,記憶也不僅是一種“知性知識”,而更是一種“感情的記憶”(41)徐賁:《人以什么理由來記憶》,吉林出版社集團,2008年,第3頁。。情感距離的存在和差異,讓記憶文本的書寫者在通過“他者”(包括以前的自己)的記憶,一次次召回上都形象的同時,也不斷地進行“自我”的文本重構。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認為,“回憶是在與他人及他們的回憶語言的交流中建構的”,因而記憶的講述不僅是“詳盡的編碼”,也是使經歷變成故事的翻譯。(42)阿斯特莉特·埃爾,馮亞琳:《文化記憶理論讀本》,第149頁。記憶的文本化,使記憶的表述如同故事的講述:當親歷、感受一座城時,這座城是一個樣子;當離開后又去追憶這座城時,這座城又是一個模樣;當把回憶起的這座城講給別人,在別人的腦海中,這座城又成了另外的樣子。“回憶具有根據個人的回憶動機來構建過去的力量,因為它能擺脫我們所繼承的經驗世界的強制干擾”(43)宇文所安:《追憶》,第149頁。。因書寫者現實情境和需求的區別以及書寫者和記憶者的間性力量,不僅推動了記憶內容的重疊,也完成了記憶元素的變化、補充和重新組合,從而重構一個有效的記憶空間。書寫者對記憶的重構,構成《灤京雜詠》《元宮詞》對元上都書寫的第二重結構。而這種重構首先表現在書寫時情感成分的投入情況。
較之于館閣文臣的雅制創作,《灤京雜詠》具有濃郁的感情色彩。它在寫景中充斥著情緒化的表現,如同剛剛啟封的一瓶老酒,強烈的氣息直沖而出,彌漫在整個空間。“挑燈細說前朝事,客子朱顏一夕凋”“離愁萬斛無人管,載得殘詩馬上歸”“強欲澆愁酒一巵,解鞍閑看古祠碑”“急管繁弦別畫樓,一杯還遞一杯愁”“故鄉不是無秋雨,聽過穹廬始愴神”“試將往事記從頭,老鬢征衫總是愁”(44)楊允孚:《灤京雜詠》,第10-11頁。,憶也是愁,說也是愁,飲也是愁,聽也是愁。詩人被感情操控著,有太多的愁苦化不開,也藏不住,只有抒發出來,訴諸于無盡的文字當中。而《元宮詞》則不同,總體來說,在《元宮詞》的書寫中,情感淡化下來,幾近退場。“愁”“苦”“傷”“愴”“怨”等表現情感的字眼在《元宮詞》中幾乎沒有,“凄涼”“寒霜”“冷酒”“惆悵”“稀”等感受性的詞匯也很少出現。即便如“上都四月衣金紗,避暑隨鑾即是家。納缽北來天氣冷,只宜栽種牡丹花。”“月明深院有霜華,開遍階遷紫菊花。涼入繡帷眠不得,起來窗下撥琵琶。”(45)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第7、39頁。等詩句出現了一些具有感受性的詞語,但如果按照感物寄情的傳統詩歌寫作手法,冷的感官體驗以及“深院”“霜華”等物象是最容易觸發情感波動的,然而詩人卻筆調一轉,變成“只宜栽種牡丹花”“起來窗下撥琵琶”的平實書寫,有意地克制住感情的流露和宣泄。由此,情感成分的多寡充分地體現在《灤京雜詠》和《元宮詞》對眼前復現的上都景物的選取和處理方式上。
如果說《元宮詞》斡旋和化解了情感的流勢和力量,讓景物成為一種相對客觀的呈現,《灤京雜詠》對上都物象的處理方式則表現在通過景物“應物斯感”,疏導情感的流向。如:
上都隨駕自西回,女伴遙騎駿馬來。踏遍路傍青野韭,白翎飛上李陵臺。(《元宮詞》)(46)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第57頁。
鸞輿八月政高翔,玉勒雕鞍萬騎忙。天上龍歸才帶雨,城頭夜午又經霜。(《灤京雜詠》)(47)楊允孚:《灤京雜詠》,第7頁。
這兩首詩均是回憶鑾駕由上都返程之事,選取的場景都是返程途中人馬繁忙的景象。《元宮詞》中,路邊的野韭被馬踩踏,驚起白翎鳥的場面與情感毫無牽涉;《灤京雜詠》卻把觀察的視角轉向氣候變化,料想午夜城頭又會有寒霜降臨,由“萬騎忙”的熱鬧場面轉變為寒霜所帶來的孤寂感。回憶總是帶有傾向性,記憶的材料“用一種由有特色的事件構成的形式再現出來”(48)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劉大基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305頁。,將書寫引向詩人想要表達的情感框架內。在楊允孚的筆下,這種情感的“帶入”方法是慣用的書寫技術,如“鸚鵡臨階呼萬歲,白翎深院度清秋”“河上驅車應昌府,月明偏照魯王宮”“卻怪西風渾不顧,一般吹送滿頭霜”“燕舞巧防鴉鶻落,馬嘶驚起駱駝眠”“凍生耳鼻雪堪理,冷入肝腸酒強支”“洛中惆悵路千里,塞上凄涼月半鉤”(49)楊允孚:《灤京雜詠》,第5、7、9、10、11頁。等。也正是這種情感的引導和帶入,使得《灤京雜詠》中的上都在楊允孚的書寫中從一座繁盛的、肅穆的、奇異的城變成了一座有溫度的、溫情的城,上都在楊允孚的書寫中逐漸清晰,如楊鐮所言,楊允孚筆下的上都“是用若干細節填充起來的”,以詩人的情感化解臺閣詩人們“雍容典雅”的隔膜。(50)楊鐮:《元代文學編年史》,第607頁。
雖然,溫情的城更易讓人身置其中,有切深感受,但強烈主觀色彩的融入,讓這座城早已成為一座變形的城。變形,是記憶文本重構的重要方式。于《灤京雜詠》而言,變形的上都主要是通過心靈加工,詩中的上都景物是心靈化的產物和感情的幻象。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上都空間意象的時空化處理上。如“翠樓紫閣盡崔巍,花落花開不用催。最是多情天上月,照人西去又東來。”“東風亦肯到天涯,燕子飛來相國家。若較內園紅芍藥,洛陽輸卻牡丹花。”(51)楊允孚:《灤京雜詠》,第9頁。翠樓、紫閣、相國家本是標示書寫位置的空間存在,但詩人筆下的空間卻轉而用時間來進行標識,在空間的書寫中增加了時間的延續性。翠樓、紫閣存在于花開花落和月的照映間,相國家也存在于東風和燕子的來去時,這種空間意象的時空化表現,超出了視覺形象的客觀性范圍。視覺形象往往是一種既定時間值內的空間印象,如“合香殿外花如錦”(52)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第3頁。,展示的是一種即視感,而時空的加入則帶來一種蒼茫的視覺效果,在空間的時間化中,具體的、細節的空間成為記憶情感的酵母,為被回憶的空間賦予了特別的感受力,它所要強調的是抽掉了空間印記的情感內容,引起對人來人去、人事滄桑的感嘆。
和《灤京雜詠》有別,《元宮詞》中情感的淡化和退場,使得上都在書寫結構中,其形象退居次要位置,而城中或宮中發生的事成為主要的書寫內容。可以這樣認為,《元宮詞》中的上都是作為背景存在的,上都形象從靜態、逼真的繪畫效果中變形,逐漸朦朧、弱化,變為一座“虛化”的城。變形的具體方式是淡化實體,如在上都宮殿、景物等描述性意象完成城市構形之后,補配一些具有暗示性和象征性的意象。“大安樓閣聳云霄”“棕殿巍巍西內中”,在交代場景后,朱有燉的筆觸轉向早朝和御宴,“政是太平無事日,九重深處奏簫韶”“御宴簫鼓奏薰風”(53)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第1頁。,“簫韶”“簫鼓”“薰風”暗示和象征著歌舞繁華、太平無事,大安閣、棕殿中早朝和御宴的場面被虛化為無形的聲音,直沖云霄的樂聲掩蓋了巍峨的層甍復閣和精美的楹柱雕飾,甚至御宴中的人聲鼎沸,宮殿影影綽綽地籠罩于歌舞繁華之中。由此,上都有形變無形,清晰變模糊,其質實性被化解,畫面顯得渾沌而朦朧,成為一種“構成藝術意味的感性抽象物”(54)蘇珊·朗格:《藝術問題》,滕守堯、朱疆源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92頁。。情感距離的長短,造成上都在楊允孚和朱有燉筆下變形為兩座不同面貌的城。那么,在這座被“溫情化”和“虛化”了的上都背后,是無盡的哀婉和感慨,還是深沉的思考與警示?
三、封存“愉悅”與審視“狂歡”
實際上,每一種藝術形式的文本,都在竭盡全力地擴充著自己的表現疆域,試圖突破它潛在的極限,記憶文本也是如此。假如說真實性的還原是人們對記憶的期許,是期待的記憶,那么記憶文本的書寫者又期待著什么?或者說他們想要通過對上都的回憶向人說些什么?從這個角度來說,記憶是記憶文本實現的媒介,它所具有的傳播(介紹過去)和暗示(解碼、提示過去)的功能引發文本書寫者對記憶有效性的關注。記憶的文本永遠不可能是普遍意義上的復制或仿制,也不是簡單意義上的重構或變形,它的歸宿是一種“解釋”,或“具有偏見性的解釋”(55)蘇珊·朗格:《藝術問題》,第91頁。。也就是說,書寫出來的東西很大程度上是書寫者覺得有意味的東西,是書寫者(直接受眾)將自己的價值和判斷強勢融入到記憶主、客體及記憶行為中,源源不斷地輸送給后來的受眾,從而增進思考或反思。但這種脫離原始記憶的文本并不意味著虛假記憶,而是對記憶的理解,或通過記憶所表達的某種立場,屬于認識論范疇。記憶在喚回和變形過程中的解釋,賦予其更加鮮明的、有所指向的意義,由此構成《灤京雜詠》和《元宮詞》關于上都書寫的第三重結構。
歷來對都城的描寫都有其文化地理的意義,所謂“王者必居天下之中”(56)荀況:《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75頁。,空間位置的“地中”在文化上浸染了權威與至高無上的價值觀,從而在一般意義上和宣揚文治聯結起來。正如韓愈所言“秦處西偏,專用武勝”“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衢州徐偃王廟碑》)(57)韓愈:《韓昌黎文集校注》,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60頁。,“地中”與“文德”的結合,形成固定的以都城宣揚文德的書寫傳統。比如元人對上都大安閣的書寫,許有壬“閣中敢進竹枝曲,萬歲千秋文軌同”(58)許有壬:《至正集》(卷二七),第140頁。,胡助“年年清暑大安閣,巡筆山川太史書”(59)胡助:《純白齋類稿》(卷十四),第127頁。。大安閣地處元上都的中心位置,是國家儀式和朝廷典禮舉辦的場所,蕭啟慶《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指出大安閣的功能,包括皇帝即位、冊立皇后、燕饗諸王大臣、接待外國使節等。(60)蕭啟慶:《元代族群文化與科舉》,臺灣聯經文化事業公司,2008年,第30頁。這是一個由中心位置展開的都城書寫方式,和歷代京都賦的書寫模式一致,從中可以體會出統治和政治權力的意味,“國家承平之久,山川草木之間,五色成文,八風不奸。文士含茹光景,故率多雅制……而從臣又多司馬長卿、揚子云之流,其藻思足以鋪寫承平風物之盛”(陳旅《跋上駕紀行詩》)(61)胡助:《純白齋類稿》(附錄卷二),第218頁。。作為臣子和利益群體,親身體驗了上都繁盛的文臣故而也必須“采用頌揚的形式,藉由夸耀代表帝國的宮殿,彰顯皇權的崇高尊貴”(62)李嘉瑜:《宮城與廢墟的對視:元代文學中的大安閣書寫》,《文與哲》2012年第21期。。
《灤京雜詠》和《元宮詞》對上都地景的書寫也圍繞在空間地理所形成的文化意義上展開,朱有燉在詩的起首,指明書寫的起始位置——大安閣,以及在大安閣中臨朝的場景,以大安閣為中心,輻射到棕殿、清寧殿,甚至更遠的李陵臺、龍虎臺等地;楊允孚在進入上都描述時,首先展示的也是作為上都大內正殿的大安閣及其別殿水晶殿,然后是皇城西內的棕毛殿,官河、紅橋等宮城景物。這種書寫次序的安排,接續都城文學傳統,讓《灤京雜詠》《元宮詞》也浸染了某種有關“統治”和“秩序”的色彩。然而,經歷滄桑之變,頌揚的筆致早已衰枯,遺民楊允孚用熱烈的筆調真情回憶和感受這座城的溫度,可以說,上都在楊允孚的筆下是作為情感抒發的材料和載體被書寫,情感延伸了詩人的想象空間,上都的興衰幻滅在個人的失意迷惘中成為具有普遍性的,卻又解不開的理智困惑,情非得已地將所有情感打包封存。與之相反,朱有燉卻用冷靜的筆調將其作為審視和評價歷史的資料,“虛化”無疑延長了記憶的思考線索,讓詩人從容地審視“狂歡”,展開一場關于歷史盛衰的理性反思。
解釋,首先就來自于書寫所面向的對象。對象的不同決定書寫的角度和解釋的方式,讓那些對“作為題材的原型所進行的‘處理’”,成為“創造出一種自身就具有某種意義的形式”(63)蘇珊·朗格:《藝術問題》,第92頁。,從而借以表達某種深層意蘊,增加記憶文本的深度和厚度。倘若元代扈從文臣和館閣詩人對于上都的現場書寫多是寫給同僚詩友看,或直接是應制、應教的作品,進而普遍采用“仰視”的方式,由仰視而頌揚。那么,在很大程度上,《灤京雜詠》作為情感載體,則是寫給自己看,《元宮詞》更多地表現為“遺之后人”(64)朱有燉《元宮詞序》言其詩“亦有史未曾載,外人不得而知者,遺之后人,以廣多聞。”參見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第2頁。的意義。
寫給自己,決定《灤京雜詠》采取一種“進入”上都的方式展開書寫。“大安閣下晚風收,海月團團照上頭。誰道人間三伏節,水晶宮里十分秋。”(65)楊允孚:《灤京雜詠》,第4頁。這里,詩人仿佛又置身于上都,在大安閣下感受溫和的晚風和水晶宮的愜意涼爽,遙望那懸掛在樓閣上空的明月。然而忽經翻覆的繁華,如何才能“進入”?恍恍惚惚的昔日景象,如同團團海月的投影,水月鏡花、層層疊疊般地凝結于夢境:
與客飛觴夜討論,夢回猶自酒微醺。
帝里風光入夢頻,鳳城金闕一般春。(66)楊允孚:《灤京雜詠》,第11、10頁。
夢境增加了詩歌的想象值,使詩人清晰地觸摸往日溫存,清清楚楚地回憶起往昔一切,不厭其煩地羅列鋪陳那些美好的、快樂的瞬間,深怕留下一個記憶的死角。李嘉瑜將之視為“個人私密記憶”,認為“個人記憶的私密性與獨特性”“賦予這座城市獨一無二的性格”,在楊允孚虛構的夢境中,“天子是太平天子,公主是太平公主,關隘是太平弓矢,時間是太平年歲,樂音是太平之聲,上京自是永恒的太平國土”,這種愉悅的記憶是詩人“內心深切的期盼”,期待快樂重新出現,“美好樂園重新被打開”。(67)李嘉瑜:《記憶之城·虛構之城:〈灤京雜詠〉中的上京空間書寫》,《文與哲》2011年第19期。但楊允孚用夢境構筑的美好樂園,難道只是“個人私密記憶”?這個童話世界當真還能被重新打開?
正如前文所述,楊允孚在回憶中溫習一個已經遠去的、遙遠世界的繁華,其中更裹挾著改朝換代的創傷經歷。昔日的溫存和眼前的頹檐敗壁,曾經的繁華和戰亂后的殘破蕭條形成強烈反差。繁華只是一夢,帝都的風光終究要隨著世事變遷而消逝,挑燈細說的前朝之事,與客飛觴討論的人事,都不過是命運的規則。命運的宿定,讓今昔的落差成為一種歷史盛衰的必然,“人被困陷在自然的那種既定的機械運轉中,他們逃脫不了盛衰榮枯這種自然的循環往復的變化”(68)宇文所安:《追憶》,第80頁。,從夢中醒來,又不得不回到空虛的現實,在經歷歲月沖刷后,詩人猛然發現:變化的不只是世事,還有人。“宮監何年百念銷,冠簪驚見髻蕭蕭”(69)楊允孚:《灤京雜詠》,第10頁。,倐乎衰老的容顏、強支的身軀,在用以麻醉自己的酒精中,生發出無盡的感傷。
感傷,是在面對不可避免的衰落時表現出的無能為力感。“一曲琵琶可奈何,昭君青冢恨消磨。可憐滿地黃云起,不似連天芳草多。”(70)楊允孚:《灤京雜詠》,第9頁。無可奈何的感傷埋沒在荒涼的青冢中,消磨著無邊歲月。滿眼的黃云、滿地的荒草,不堪目睹,又造成強烈的幻滅感,以及它所帶來的,對生存意義的懷疑和迷惘:“我憶江南好夢稀,江山于我故多違。離愁萬斛無人管,載得殘詩馬上歸。”“百事關心有許忙,秋風掠削鬢邊涼。曉來為憶西山雨,怕看行人歸故鄉。”(71)楊允孚:《灤京雜詠》,第11、10頁。既然好夢稀少,也無人在乎萬斛的離愁,那么江山景物于我又有什么意義?即便卷攜殘詩歸鄉,卻又不忍直視歸鄉的行人,更何況何處是歸鄉?又安能回得去故鄉?此情此景映射了此身是妄,詩人猶如被命運操縱,分裂出無數自我,迷失了人生的方向。
這一切與其說是個人私密記憶,不如說這就是人們在回顧和面對世事無常、自然循環時能夠找到和體會到的最多的東西,也是楊允孚在寫給自己的記憶文字中想要表現的最具普遍意義的情懷。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回顧歷史時可供關照的情感模式:此生既已迷茫,王朝的盛衰幻滅更如“剪不斷,理還亂”的謎團,“居庸千載興亡事,惟有天中月色知”“天上人間今又昔,灤河珍重水長流”(72)楊允孚:《灤京雜詠》,第11頁。,在人世間的不斷變動中,只有明月、流水是恒定的,困陷其中逃不掉的人,除了發出的最深沉的感慨,又能做什么?除了向灤河道一聲珍重,又能說什么?記憶的書寫在這里就像合上一本舊時的相冊,將一切愉悅封存其中。
當上都再次被打開,其實已不是那個個人筆下的童話樂園。歌舞升平、歡宴不斷的帝國盛世,在朱有燉那里表現的并不是個體的哀樂,他對歷史迷局懸出的問題卻有了清醒的思考。本來,《元宮詞》書寫的目的就是“遺之后人”,它要告訴后人的恐怕不光是宮闈秘事,更在努力地分析著世事衰落的原因。
寫給后人,決定《元宮詞》采用“俯視”上都的書寫方式。詩人總是站在一個居高的位置,俯察著身下的這座城,以及城中那些進進出出的人物和歡鬧的事件。《元宮詞》中也寫“太平”,也寫無處不行的笙歌歡宴,“海晏河清罷虎符,閑觀翰墨足歡愉”“百年四海罷干戈,處處黎民鼓腹歌”(73)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第76、89頁。,歲乏不絕的宴會似乎比楊允孚想象中的還要豪奢,還要頻繁,但不同于楊允孚的激動和熱烈,《元宮詞》的筆調都是冷靜的,盛大的歡聚沒有激起書寫者本人的情緒波動,詩人似乎是在緘默不語地觀看著一場場世間的玩偶戲,戲的主角們沉迷于自己的狂歡中,絲毫不察覺外面發生的一切。
茫然無知,正是《元宮詞》詩歌的張力所在。帝王不斷舉辦御宴,賞賜臣屬;諸王駙馬們舉著葡萄美酒連聲賀壽;妃嬪們沉迷于唱銀錢(賭博);宮女們歡聚在合香殿外賞花;西方舞女、二八嬌娃扭動身軀跳著迷人的天魔舞;女官們操持翰墨,抄寫竹枝詞;權貴子弟們一杯接一杯地暢飲阿剌吉(酒);鹿頂殿中陳列著各式金盒珍饈并演繹著百戲。這些場合,主人公們被“蒙在鼓里”,完全沒有意識到之后戰火來襲。而作為旁觀的詩人卻清醒地知道毀滅即將發生,“在所有的引人入勝的繁華和所有的感官快樂之中,都隱藏著罪惡和危險以及懲罰和厄運的暗流”(74)宇文所安:《追憶》,第69頁。,茫然無知使得詩歌帶有濃郁的悲劇色彩,它呈現在那里,如同讓人欣賞一朵即將凋零的花朵,極力炫出最后一抹艷姿。
毀滅,是狂歡注定要帶來的厄運,只不過汲汲于尋歡作樂的人們不曾察覺,也無意去察覺而已。它通過詩人的審視,以“后人哀之”的方式顯現出來。“瑞氣氤氳萬歲山,碧池一帶水潺潺。殿旁種得青青豆,要識民生稼穡難。”(75)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第21頁。大內丹墀栽種草原青草,即“青青豆”,或“香草”,也作“示儉草”,是元代詩歌常寫的典故,如柯九思《宮詞》“數尺欄桿護香草,丹墀留于子孫看”(76)顧嗣立:《元詩選》(三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183頁。,“示儉草”本是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欲使后世子孫知勤儉之節”(77)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上),中華書局,1959年,第72頁。。然而在詩人看來,“示儉”的青草還在,勤儉的垂訓在此時卻未能奏效。在燈月交光、笙歌燕舞的狂歡中,人們更加無所禁忌,無休止、“不暇自哀”地流連于奢靡生活之中。
既然在詩人眼中祖先之“勸”變成了“哀”,那么教諭還是否要重提?詩人透過對奢靡的審視,思考也隨之展開:
分得不均嗟怨眾,受恩多是本朝人。
偶值太平時節久,政聲常少樂聲多。
三弦彈處分明語,不是歡聲是怨聲。(78)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第114、89、38頁。
第一句詩寫元廷“叆馬”,即賑災物質的分配。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存在分配不勻的情況,造成民怨沸騰。“嗟怨”的產生指向的是人們對既定規則和秩序的無視和逾越。而人們久久沉醉于太平歲月中,無心城外之事。那么,三弦彈處的分明之語——怨聲,也就不僅僅是宮女的哀怨,而有了更加廣泛的意義:是民怨,抑或天怨。詩人在這里極力規勸、儆誡著僭越逾制的后果及其歷史教訓。如此再來回看上都,在朱有燉筆下,他認為這座城與其說是被戰爭而毀,倒不如說它就毀于城中的那些人和事,毀于“政聲常少樂聲多”這樣的人事失序。朱有燉寫給后人的文字,也就在于人們在反思歷史時,那種普遍具有的“后人哀之”能否“鑒之”,是否“復哀后人”的歷史警示和意義。
總之,從元上都記憶到記憶中的上都文學書寫,通過文本語言的符號化建構、提取,記憶功能的增值、轉換,記憶文本書寫者操縱“記憶之筆”,使記憶中的上都形象重現、重組,被表述、被解釋。既構筑一座烏托邦式的上都,也沖去彌漫其上空的迷霧。長流的灤河,記憶著無盡的悲歡,也夾帶著沉重的嘆息和深刻的啟示,翻滾于千載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