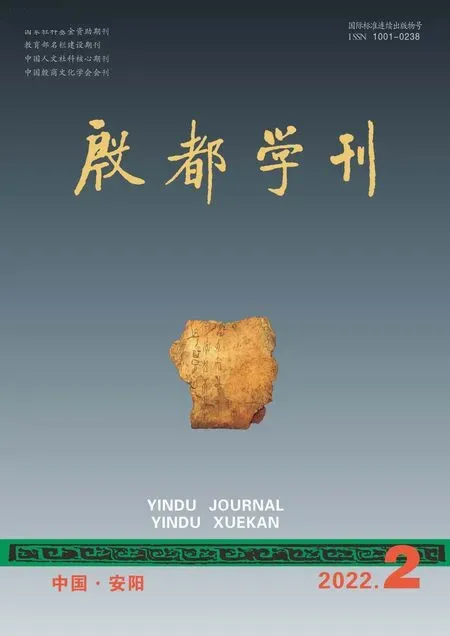周代夢與命祀關系考述
張秋芳
(安陽師范學院 歷史與文博學院, 河南 安陽 455000)
關于夢或者命祀問題,學者曾分別作過諸多研究(1)夢研究方面:從文化學角度展開研究的有劉文英《夢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傅正谷《中國夢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等等。從歷史學角度切入的有胡厚宣《殷人占夢考》,載于《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宋鎮豪《甲骨文中的夢與占夢》,《文物》2006年6期;楊健民《中國夢文化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等等。從心理學角度研究的,古今中外成果繁多,最具代表性的為弗洛伊德《夢的解析》,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還有從民俗學、美學等方面展開討論的,不再一一贅述。命祀方面:命祀問題一般常見于祭祀類相關文章中,如葛志毅《周原甲骨與古代祭禮考辨》,《史學集刊》1989年第4期;孟凡港《周人祭祀殷先王考》,《光明日報》2012年6月15日等。,但對于夢與命祀的關系卻鮮少論及。夢信仰代表思想觀念方面,命祀代表制度方面,當思想與制度發生碰撞時,它們的關系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是由一方服從于另一方,還是并駕齊驅呢?本文擬就此略作探索,以觀周代感性與理性世界之間的力量消長,由此窺探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
命祀,是周天子對諸侯祭祀權的封授和規定,是在宗法制和分封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實際上是周天子利用祭祀活動控制諸侯國的一種重要方式。周天子在封藩建國、封土授民的同時,也授予諸侯祭祀權。如《尚書·康誥》記載周公封康叔于衛時說:“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又說“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孫星衍疏:“享者,《說文》云:‘獻也。’凡封諸侯,必命其封內山川社稷,所謂命祀。”(2)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中華書局,1986年,第371頁。故最后周公道:“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3)(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卷14《尚書正義·康誥》,中華書局,2009年,第436頁。可見,授祭祀權即“命祀”,與封土授民是同時進行的。《國語·周語下》亦云:“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亡王之后也。唯能厘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度于天地而順于時動,和于民神而儀于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韋昭注曰:“受祀,謂封國受命,祀社稷、山川也。”
關于“命祀”的記載,亦見于《左傳》哀公六年:
初,(楚) 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谷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史記·楚世家》也載此事說:“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集解》引服虔曰:“謂所受王命, 祀其國中山川為望。”《周禮》中亦有類似說法,如:《春官·大伯宗》曰:“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大祝》曰:“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于邦國都鄙。”《天官·冢宰》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這說明無論是畿內還是畿外,封國都要接受天子祭祀權的封授。
“命祀”作為一項制度真正被確立下來,是在西周建國之后,也包括“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2013年,第334頁。“祭不越望”等原則。文獻中雖有“三代命祀”之說,但在西周之前是模糊的。正如王國維先生在《殷周制度論》中所言:“自殷以前, 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當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葉稱王。湯未放桀之時,亦已稱王。當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稱王。蓋諸侯之于天子,猶后世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5)王國維:《觀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6頁。他在《古諸侯稱王說》中再次明晰了這一點, 即在天則未嚴之時,眾多方國首領也有稱王的現象(6)王國維:《觀堂集林》,第779頁。。這一觀點已經被學界多數學者所認同。可見在西周之前,君臣之間是沒有清晰界線的,自然“命祀”也不可能嚴格按原則區分了。
關于周代“命祀”的制度,《禮記·祭法》中有明確規定:“諸侯在其地則祭之,王其地則不祭。”《國語·魯語上》云:“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韋昭注云:“賈、唐二君云:‘周公為太宰,太公為太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說明命祀之職由周公、太公擔任。并且為了保證命祀的實施,命祀規定皆載于“神約”。如《周禮·秋官·司約》說:“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此“神約”包括周王所命諸侯祀典(7)(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卷68,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93-94頁。。鄭玄注曰:“神約,謂命祀郊社、群望及所祖宗也。”神約一經制定,便“藏之宗廟,以璽正諸。”(8)黃懷信:《鹖冠子校注·王鈇》卷中,中華書局,2014年,第197頁。這一切都說明周代的“命祀”已經規范化、制度化,而且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
但是,當這一切與傳統宗教思想發生沖突時又會怎樣呢?比如命祀與夢信仰。命祀作為一種實行于周代的規范化祀典制度,它要求諸侯國、都鄙等必須遵從王室之命進行祭祀, 對王室惟命是從,如若背叛,即為不恭,是要受到周天子嚴厲懲罰的。懲罰方式有征伐,如《國語·周語上》說:“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于是乎有刑之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此外,還有刑罰、削地絀爵等處罰方式,如《周禮·春官·大祝》曰:“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鄭玄注曰:“有逆者,則刑罰焉。”《禮記·王制》曰:“山川神祗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
夢信仰是先秦時期人們重要的精神活動,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漢書·藝文志》所言:“眾占非一,而夢為大。”如果死去的人托夢求祭,人們往往親自前往祭掃,不敢懈怠,然后才能心安理得。這種因夢而祀的觀念從商以前一直到春秋都深深地影響著人們的祭祀行為。那么當二者同時出現時又是怎樣的狀況呢?《左傳》僖公三十一年記載的衛成公夢康叔: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余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這里說的“間”,楊伯峻先生注云:“借為干,犯也,違也。”“諸侯之國所當祀者,由周王室命之。衛國之所當祀者,為成王、周公所命,今祀相,在命祀之外者,故云犯成王、周公之命祀也。”(9)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487頁。可見,當夢與命祀制度發生沖突時,衛成公最終選擇了命祀制度。又《左傳》僖公十年記載:
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始登仆, 而告之曰: “夷吾無禮,余將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10)筆者按:這是一則沒有夢字的夢例。但筆者認為所言亦是夢。太子申生在僖公四年的時候已經自縊,現在是僖公十年,狐突怎么能夠遇見太子呢?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在夢里。整個敘述乍一看,似是在講現實發生的事件。因為夢就像一面巨大的鏡子,它不僅囊括現實中的一切,還高于現實。現實中沒有的、見不到的、做不到的,它都能夠實現。夢里的一切可以和現實生活相差無幾,有時當事人都弄不清楚究竟是夢還是現實。《莊子·齊物論》就講過:“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也,覺而后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后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劉文英先生這樣說道:“夢的真實性與虛幻性具于一體。從主觀方面來看,我夢見張、夢見王、夢見山、夢見水,我絕不懷疑這種體驗的真實性……然而從客觀方面來看,張、王遠在異地,山水遠在室外,而我根本足未出戶,并且躺在床上沒有挪動。”(劉文英:《夢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這與狐突遇見太子異曲同工,太子雖然已經去世,但由于是在夢里,所以他們能夠遇見、能夠交流,如同我們真實的世界。
在這里,狐突的勸諫,亦表明“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的祭祀原則被時人所信奉。
以上兩例均說明夢的權威性尚不及制度化的“命祀”。然而有時“命祀”制度以及“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的祭祀原則,也會因為夢而不被遵守。如《國語·晉語八》晉平公夢黃熊之記載: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 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 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在上述記載中,晉平公不但沒有遵守命祀制度及其祭祀原則,而且為了治愈疾病還“遍諭上下神祇”,聽從子產的建議,設董伯為尸,以祀夏郊。按照命祀制度,這一切都是不允許的,晉平公沒有權利祭祀夏郊,更不能遍諭上下神祇。如《禮記·曲禮下》說: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遍。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遍。大夫祭五祀,歲遍。士祭其先。
又《禮記·王制》說:“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荀子·禮論》說:“故王者天太祖,而諸侯不敢壞,士大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祗乎諸侯,道及士大夫。”可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他們在祭祀上是有嚴格等級限制的。那么晉平公是怎么做到既可以僭越天子舉行郊祭,又不被眾人指責的呢?首先,是借助于夢。夢信仰在社會中本來就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所以子產很清楚拿夢說事極易被人們接受,而且夢是天命或祖先命令傳達的中介,會被認為是天意所致。故晉平公生病之際夢黃熊入寢門,子產解釋為鯀之所變化,晉平公患病實為未舉行夏郊所致,建議晉平公祭祀夏郊,并認為這是三代一貫的做法。可是子產明知“天子祀上帝, 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的祭祀規定,為什么還建議晉平公祀夏郊呢?難道僅僅是因為夢?子產給出的理由是“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可見由于周王室的衰落,周天子已經不能再控制諸侯嚴格恪守周禮了。天子所祭祀的神祗,已需要諸侯(霸主)來輔佐。其次,國力所致。晉國當時是諸侯國中的霸主,想必子產在釋夢之前已經想到這點,所以才敢說這樣的話:“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
其實,在整個事件中,夢只是破壞命祀的一個借口,真正的原因在于晉國的強大。從另一個角度看,也體現了理性精神的發展。春秋時期,關于理性的發展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楚人雖重占卜,但并不唯卜是從。春秋時期,楚國大夫斗廉就曾說過“卜以決疑,不疑何卜”③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31頁。 的話,表現出楚人對占卜的理性態度。再比如公元前478年,楚惠王為報復陳國向太師子谷和葉公子高征詢選帥的意見。當二人意見相左時,楚惠王采取了占卜的方法來定奪帥之人選。結果“王卜之,武城尹吉”[注]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709頁。。于是讓武城尹和公孫朝一起攻陳。其實,太師子谷推薦的人雖然有能力,但因為有被俘的經歷,難以服眾;葉公子高推薦的人雖然能夠得到兩位的共同認可,但太師子谷就會很尷尬。所以楚惠王占卜的人選正好調和了二人的意見。這次人選看似是占卜的結果,其實并不代表神的意志,而是楚惠王和朝臣不同意見調和的結果。由此可見,楚人在占卜中,理性精神發揮著主導作用。
以上種種跡象表明,春秋時期神權崇拜的內容越來越淡化。由夢而祀的觀念逐漸由過去的單純行為演變為一種政治手段或者工具。祀與不祀不再聽命于夢,而在于如何釋夢,而釋夢則又由政治需求所決定。所以說,春秋時期夢的作用逐漸減弱,人們只有在想滿足自己的需求時,才會讓它重新站出來,不過是對由夢而祀這種合法信仰的利用而已(11)廖小東、豐鳳:《中國古代國家祭祀的政治功能及其影響》,《求索》2008年第2期。。通過分析夢與命祀的關系可知,春秋時代,周天子地位下降,王室衰微,逐漸喪失了對諸侯祭祀權的控制,命祀制度不斷遭到破壞。同時從另一角度也反映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即理性方面得到了更多的張揚,而非理性事物(譬如占夢活動等)對事態發展的影響日漸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