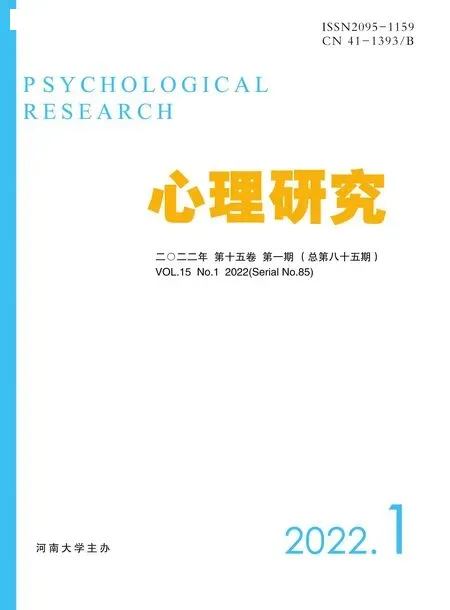“社會認知論”對心理學的理論貢獻
舒躍育 靳佳麗 李嘉明
(西北師范大學心理學院,甘肅省行為與心理健康重點實驗室,蘭州 730070)
1 引言
長久以來,主流心理學一直著重于方法技術的發展,卻忽視了對心理學的本體論預設的關照。 作為一門從哲學和生理學中獨立出來,并力求成為一門科學的學科,“心理學從未擺脫對其他成熟自然科學的依賴,并一直通過‘物性’來定義‘人性’,通過探究物理世界的方法來直接探究人類的生活世界”(舒躍育,石瑩波,袁彥,2019)。心理學本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以研究“物性” 的方法研究“人性”,很難實現心理學自身的學科價值。但是并非所有的心理學家都忽視了“人性”的存在。 以社會認知論①本文提到的“社會認知論”特指班杜拉的社會認知論思想。的創始人班杜拉(Albert Bandura)為例,他強調人性在心理學中的意義,并對人性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可以說,班杜拉的社會認知論體系就建立在他對人性的更為有效的解釋基礎之上。 回顧班杜拉的心理學理論,可以為當代心理學工作者思考如何建立以“人性觀”為核心的學科同一性提供歷史視角。
行為主義最早對人性的認識源于笛卡爾的機械唯物主義中“動物是機器”的主張(葉浩生,楊莉萍,2021,p147) 及洛克的白板說。 在實證主義大背景下,華生認為人的心理、 意識只是一種假設,不能加以證實,所以忽視了人的自由意志和精神屬性,遵循嚴格的決定論,把人看作機器。 可以說,華生認為的心理學是行為的科學,亦是把人看作機器(物)的科學。在華生之后,魏斯、亨特、拉什利、斯金納等行為主義學家沿襲了他的主張,他們反對研究人的意識,主張研究人的行為。 但仍有行為主義學家關注人的主體性在心理學中發揮的作用,如社會認知論的代表人物班杜拉。 與激進的行為主義學家所秉持的機械論的人性觀不同,班杜拉對人有著更豐富的認識。 這一點不僅體現在他基于對人的認識提出的自我效能感、觀察學習、替代強化等社會認知論的核心概念方面,也體現在他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重視方面。 他認為在互聯網時代,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教育、健康、工作、企業等領域皆發揮著重要作用(Bandura,2006)。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班杜拉的人性觀更接近人本身的真實情況。 而心理學要建立學科同一性,首先應該認識到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人,是什么? 班杜拉從人的主體性層面,作出了他的回答。
2 承認自由的人性觀
20 世紀80 年代,班杜拉系統論述了社會認知理論的兩大基本假設: 三元交互決定論和人的能動性或意向性。 社會認知論雖然屬于行為主義學派,但其遠不同于早期行為主義的觀點。 行為主義的創始人華生及早期行為主義的代表人赫爾、 斯金納等人認為心理學應該摒棄“意識、動機”等內容,直接研究人的行為。 但在20 世紀50 年代,行為主義存在的問題日益凸顯并由此引發了科學心理學的又一次危機,被絕大多數早期行為主義心理學家所拋棄的意識、動機、思維等概念重新回到了心理學的研究議題中。 這一時期,認知心理學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開始興起。 班杜拉在行為主義背景下,吸取了認知心理學的觀點,并自發地走向人本主義,形成了以強調個人、 行為、 環境三元交互為基礎的社會認知論。 又因為社會認知論主要圍繞著人的五種能力所展開,所以個人因素在社會認知論中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針對個人因素,班杜拉梳理了心理動力學理論、 特質論、 激進的行為主義的人性觀及因果模型,并對此人性觀和因果模型提出了新的看法。
在人性觀方面,班杜拉認為心理動力學理論忽視了人的復雜性和多變性(班杜拉,2018,p2),特質論主張雖然看到了人的內部因素卻很少關注特質如何生成、激發和指引行為的問題(班杜拉,2018,p6),激進的行為主義雖并不否認內部事件與行為相關聯,但對此毫無興趣。 對此,他提出了三元交互決定論,認為人既不是由內部力量驅動的,也不是被外部刺激自動塑造和控制的,人的機能的實現由行為、 認知和其他人的因素以及環境因素三者作為相互決定因素共同起作用 (班杜拉,2018,p19)。 在這四個理論當中,特質論與心理動力學雖然也強調人的內部因素,但他們認為人的行為是由內部因素決定的,而且這兩種內部因素——特質、 無意識是既定的,我們的行為是特質、無意識等因產生的果。這就是決定論的觀點,我們的一切行為都是被決定了的,并沒有主觀意愿的參與,也就是說,人沒有自由意志。 因果模型正是決定論的一種體現。
在因果模型方面,心理動力學理論持徹底的心理決定論①班杜拉認為心理動力學是徹底的心理決定論,但這種觀點存在爭議,如J.F.里奇拉克(J.F.Rychlak)并不認為心理動力學是決定論。,將行為的原因歸結為無意識的內部決定因素(班杜拉,2018,p3); 特質論強調內部決定因素,認為特質可以預測行為; 激進的行為主義持徹底的環境決定論,認為人的行為是對刺激的反應。 這三種理論都認為人的行為是由某些因素所決定的。 盡管三方交互決定論仍然是一種決定論觀點,但這種決定論是一種溫和的多元決定論,或者說是一種相容論。 班杜拉承認人具有自由意志,并且認為人的自由意志與決定論并不相悖。 對此,他解釋道,“自由是通過運用思想、 運用人所掌握的技能和行為選擇所需要的自我影響的手段來實現的。自我生成的影響與外部影響一樣都對行為起決定作用”(班杜拉,2018,p40)。 事實上,社會普遍接受的觀點,正是人具有自由意志的觀點。 否則,違法犯罪的人就沒有必要受到懲罰,因為他們的犯罪行為并非主動實施。
班杜拉的三元交互決定論中的主體因素體現了人的自由意志,他認為人性是以巨大的潛能為特征的,這種潛能可以通過直接和觀察的經驗,在生物限度內,被塑造成各種形態(班杜拉,2018,p22)。而人的性質是由各種基本能力組成的。 正是由于這些基本能力,人才能夠做出十分復雜的行為。
3 展現人性的五種基本能力
具體來講,班杜拉將人的基本能力分為五種,分別是使用符號的能力、 深謀遠慮的能力、 替代能力、自我調節的能力和自我反思的能力。正是基于對人的五種能力的假設,班杜拉構建了龐大的社會認知論體系。
第一,使用符號的能力。 在進化過程中,人類獲得了一種高級的符號能力,使他們能夠超越其直接環境的社會壓力,并使他們在塑造其環境和生命歷程的能力上變得獨特(Bandura,2008)。正是由于具備這一能力,人們才能夠理解周圍的環境、 構建行動的指南、從認知上解決問題、支持深謀遠慮的行動過程、 通過反省獲得新的知識,并與任意時空之外的人們進行交流(班杜拉,2018,p9)。 符號的使用是人類與動物的區別之一。 在卡西爾看來,人是符號性的動物,符號化的思維和行為是人類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象征,并且人類文化的全部發展都依賴于這些條件,這一點是無可爭辯的 (卡西爾,2016,p46)。 并且,人類開辟了一個跟直接的時間和空間不一樣的符號的時空觀。 人類對時間和空間的感知有一套獨特的機制,比如人類開心和悲傷狀態下對時間快慢的感知不一。 除此之外,這種獨特的符號時空觀也幫助人類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并發展出文明。 對人類而言,一種社會高度的文明,就在于這個社會善于總結并將知識抽象化。 班杜拉的觀察學習正是基于人類的符號活動將知識抽象化的過程。 在觀察學習的第二個階段——保持階段中,符號活動至關重要。 學習者需要將在注意過程中獲取的信息及時通過符號編碼儲存在記憶中,并通過符號的中介轉變為長時記憶。 只有將直接經驗和替代經驗抽象和概括化,才能形成人類所共用的知識體系,并為后代所服務。
第二,深謀遠慮的能力。中國有句古話,叫“謀定而后動,知止而后有得”,即是對人類深謀遠慮能力的鮮明寫照。班杜拉認為“人們不是簡單地對直接的環境進行反應,也不是受過去經驗的驅使。 他們的大多數行為是有目的的,因而是深謀遠慮的”(班杜拉,2018,p20)。 根據Tulving (1985) 的理論,這種能力又被稱作心理時間旅行(mental time travel)。 過去和未來的心理時間旅行對人們當前決策的影響尤為重要(Ozdes,2021)。人們能夠在精神上旅行到一個偶然的過去或未來,而且知道經歷或者將要經歷那個事件的人就是自己,并對當下的選擇產生影響。 在過去的科學傳統中,起因都是關注的重點。 傳統的因果論對心理學的影響可以說是巨大的,我們更多考慮的是過去的經驗給我們的心理行為帶來的影響。然而班杜拉認為“在深謀遠慮中,人們通過制定行動計劃、制定目標、想象行動可能產生的結果來激勵和引導自己。 未來狀態沒有物質存在,所以它不可能是當前行為的原因”(Bandura,2018)。因此,過去的經驗和未來的期待都會影響我們對當前行為的決策,這正是人類特殊的地方,人類可以通過對未來的期待調整當下的行為。 班杜拉將期待分為了兩種,一種是結果預期,另一種是效能預期。 前者是對行為可能帶來的結果的預期,后者是指對自己是否能夠完成某一任務能力的評判。在當前的心理時間旅行的動物模型實證研究中,雖然人類情景記憶和預見的一些重要組成部分與動物相似,如海馬體,但是人類的心理時間旅行仍然有可能依賴于一些獨一無二的人類特征(Suddendorf& Corballis,2010)。 換句話說,深謀遠慮的能力是人類獨有的。
第三,替代能力。 人類的學習并非都要自己親身體驗才能學會,實際上,來自直接經驗的學習現象都可以通過觀察其他人的行為替代地發生(班杜拉,2018,p21)。 如果學生有不想寫作業的想法,卻看見班里被老師發現沒寫作業的學生都受到了懲罰,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不會再實施不寫作業的行為。 替代能力與觀察學習相輔相成,替代能力幫助人類設身處地地感受觀察到的現象與行為,并對自己能否進行類似的活動做出主觀判斷,使人類無需耗費巨大的代價就可以趨利避害,從而更好地生存下去。 但是替代能力也有弊端,如果樹立了錯誤的學習和替代對象,那么將會影響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 如當今某些“網紅”“主播”,這部分群體的確可以促進經濟發展,但如果年輕人都以他們為榜樣,將無益于社會的長遠發展。 在社會認知論中,班杜拉以替代能力為基礎提出了替代強化概念。 仍以上述現象為例,如果上述這些“流量大咖”不斷在這種身份中獲取利益并輸出他們的價值觀,那么以他們為榜樣的年輕人試圖從事“主播”等職業而一夜暴富的信念就會被強化。
第四,自我調節的能力。 通過替代觀察從而進行自我調節闡明了個人是如何形成個人標準并通過是否達到其標準的自我評價來規范其行為的(Bandura,1991a)。 自我調節并非僅僅通過意志控制來實現,它的進行要借助自我觀察、 判斷過程及自我反應三個子功能(班杜拉,2018,p361)。 在進行某一項活動時,人們會觀察自己的行為,當行為與預期目標、 個人標準(往往傾向于道德行為以維護自尊)不符時即改變、調整行為,然后針對調整后的行為做出評價性和實質性的自我反應。 自我調節涉及很多因素的影響,是一項十分復雜的能力。 自我觀察會受到動機、 價值觀、 活動的重要性等因素的影響,判斷過程會受到個人標準、參照性行為、行為的歸因等因素的影響,因此所產生的自我反應也不同。 他們的反應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自我評價取決于他們的行為符合他們所采用的標準的程度(Bandura,1991b)。
第五,自我反思的能力。班杜拉認為“如果有某種特征是只屬于人類的,那就是反思性的自我意識能力。 ……人們不僅通過反思獲得理解,而且他們評價和改變自己的思維。 ……支配人的動因的許多方面的自我認識大部分是這樣的反思性自我評價的產物”(班杜拉,2018,p22)。 由此可以看出,班杜拉非常重視人的自我反思能力,并將其作為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 人的一生都在進行反思,這種反思不僅包括我們對自身行為及結果的評估,也包括與我們在某方面相似的人的行為后果的觀察學習,從而幫助我們認識自己。班杜拉認為“通過元認知自我反思來行使替代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對一個人的效能的判斷。這種核心自信是人類抱負、動機和成就的基礎”(Bandura,1997)。 人們通過對已有經驗的反思作出自已能否勝任一項活動的能力判斷,這就是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高的人更傾向于付諸行動,因為他們相信自己能做到。 但是自我效能感并不能預測一個人是不是真的能夠像所認為的一樣完成任務,在多次任務中,他們會在行動過程中不斷調整自我效能感。 人的一生一直在進行這樣的反思性評價,自我反思能夠幫助我們改變錯誤的觀念,但是也會使錯誤信念產生,比如反芻思維。
當然,這五種能力并不是獨立存在的,無論是觀察學習、 替代強化還是自我效能感,都需要五種能力的有機結合。 而這五種能力,構成了班杜拉人性觀的理論基礎。
4 由“方法中心”到“問題中心”
班杜拉的社會認知論體現出一個好的心理學理論首先會對其本體論問題“人是什么”有較為明確的思考。 心理現象總是以人的活動為載體,因此,對心理現象獨特性的反思,就成為了以人性觀為理論形態的心理學本體論。 對心理學本體論的追問變成了對人性的反思(袁彥,舒躍育,周愛保,2021)。不論是心理動力學、 行為主義還是人本主義,其理論基礎必定脫離不了對人的認識; 無論是哪種取向的心理學研究者,所研究的內容也始終離不開“人性”這個核心問題。但是,長久以來,這一點并未引起主流心理學界的重視,目前心理學仍然處于“以方法為中心”而非“以問題為中心”的階段。
首先,在課程設置方面,心理學本科生必修課必有實驗心理學、心理統計學、心理測量學等方法類課程,然而理論類課程除心理學史及既有理論相關課程的開設外,很少會開設探討心理學元理論及哲學基礎等方面的課程。正如Borsboom 等人(2021)所言:“心理學很少教那些有助于構建理論的技能,比如通過數學手段或計算機模擬進行理論建模。 同樣,關于理論建設本質的哲學工作也很少出現在我們的課程中。”這從側面反映了心理學界對心理學本體論及問題意識的忽視。 如果我們想要提出一個好的研究問題,就離不開對心理學理論的掌握。 作為一名心理學研究者,我們都知道發現問題、 選擇方法、分析數據、解決問題都需要理論的支持。 這并不是心理學界的獨特現象,其實,無論是在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領域還是社會、政治等社會科學領域,都不能忽視基礎理論研究。當前我國遇到的許多“卡脖子” 的技術問題,最核心的,或許在于原創性理論的缺乏。 同樣,縱觀心理學的發展,沒有哪個心理學流派是脫離理論根基單純依靠方法發展起來的,以理論心理學探討的心理學哲學基礎為例:構造主義以經驗主義、 聯想主義和實證主義為哲學基礎,美國機能主義以進化觀和實用主義為哲學基礎,格式塔心理學以康德的先驗論和胡塞爾的現象學及實證主義為哲學基礎,行為主義以機械唯物主義、實證主義、實用主義為哲學基礎,人本主義心理學以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為哲學基礎。 國內心理學界一直“有山頭,無學派”,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忽視了心理學的元理論的發展。
其次,在方法論方面,心理學首先從馬赫那里接受了實證主義,隨后又吸收了胡塞爾的現象學,這兩種方法逐漸發展成為心理學的兩大主體方法論。 目前,以“方法為中心”的邏輯實證主義是國內心理學界的主流方法論。 邏輯實證主義的普遍本質通常被認為對心理學作為一門經驗科學的發展有形成性影響(Brown,1989)。然而歷史上的心理學家,關注方法本身已然超過了研究的內容(Stanovich,2013),這實際上排除了對其他理論及哲學基礎的關注(Yanchar & Hill,2003)。 通常認為,心理學的科學信念是“心理學應該是一門量化的、實驗的科學”。這種做法構成了一種方法論上的自命。 在這種自命中,心理學家們將公認的經驗主義方法視為任何合理研究的唯一合法途徑(Schrag,1983)。 雖然心理學的科學性或者合法性得到了解決,但是這卻也默認了心理學的本體論——物質實體。 按照這一邏輯,任何心理現象要真正存在,就必須接受科學方法的檢驗。 在這一立場下,心理學中無法證明其實體存在的部分,例如人的道德性、 精神性,就會變得毫無意義。 這樣一來,心理學研究所給予的本體論承諾,離社會中真實的人越來越遠,究其根源,在于“方法”與“問題”的倒置。 方法,原本作為學科發展的途徑和手段,現在卻成為了學科發展的標準(舒躍育,2013)。 當研究者過于重視對所謂正統、 主流研究方法的使用時,往往會忽視真正的研究問題,這需要將方法與理論、實踐相結合。以實證主義為方法論基礎的構造主義和行為主義心理學家為例,他們過于依賴工具步驟、 操作的精確性,忽視了心理學的問題、疑難和目的(劉翔平,1991)。
社會認知論建立在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基礎上(Bandura,2018),從“以人性為核心的理論觀”出發,融人的自由意志與決定論為一體,兼納實證主義方法與現象學方法特征,因而才能超越行為主義的局限。 特別是,它所提供的人性論預設,離現實生活世界中的人越來越近,對于理解我們人類自身,提供了更多的啟示。 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國內心理學一直以實證主義心理學為主流取向,并試圖與哲學撇清關系。 無疑,實證主義心理學研究方便研究者操作、 量化與重復,并為心理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不可否認的是,實證主義也因為方法中心、 精確證實和人性的缺失對心理學產生了負面影響 (戴健林,1999)。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方法為問題所服務,心理學研究者應該為以人性觀為基礎的心理學研究選擇或重建方法論。 從這個意義上講,班杜拉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重新審視元理論與具體研究的關系、 方法論與本體論之間關系的契機。
5 心理學的學科同一性
進一步而言,班杜拉的理論貢獻對我們反思心理學重建學科同一性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類比埃里克森對個人同一性的定義①埃里克森在其著作The Childhood and Society 第一版中將同一性定義為個體對于關于自己是誰、在社會中應該占有怎樣的地位、將來準備成為怎樣的人以及怎樣努力成為理想中的人等一系列問題的覺知。,心理學的學科同一性即指心理學是什么、 將來準備發展為怎樣的學科以及怎樣努力成為理想中的學科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 作為一門探究人性的科學,人性與物性的差異構成了心理學獨立于自然科學的理論依據,它蘊含著心理學作為獨立學科的價值之所在,同時也構成了審查及評判學科發展狀況的標準 (舒躍育,2013)。
實現心理學的學科同一性意味著心理學家對心理學的基本問題有一個相當一致和統一的認識。 對完整人性的探究,就是建立心理學學科同一性的基本問題之一。 心理學對自然科學方法論的有力承諾使得心理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同時拒絕了心理學的人文傾向(Green,2015)。但是,由于對自然科學的崇拜,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人”不再是人本身之所是。 當人性中的“物性”被單獨拿出時,人就像是一個“組合人”(Hacking,1986)。在探究這一基本問題的過程中,如果過于強調研究方法是否為主流、統計方法是否高級,無異于削足適履。 這一問題并非通過現有的自然科學方法論就能夠回答,研究方法必須伴隨著問題的發展而發展,圍繞這一基本問題去探究并建構適合的方法論,才能相得益彰。
但并不是說我們就要拋棄自然科學方法,心理學是一門涵蓋范圍非常廣泛的學科。 班杜拉認為,“作為一門核心學科,它(心理學)特別適合促進理解人類的生物心理社會綜合性質,以及他們如何能動地管理和塑造他們周圍的日常世界”(Bandura,2006)。 如果心理學家要研究“人類生物心理社會綜合性質”,僅僅只使用自然科學方法必然會力不從心。 如果把心理學視為一個學科體系……它包括非經驗學科層、經驗學科層和技術學科層(舒躍育,石瑩波,袁彥,2019)。科學心理學僅占了經驗學科層的一部分,并非是心理學的全部。 因此,如果心理學完全按照自然科學的模式生搬硬套,忽略了心理學本身所包含的非經驗學科層等內容,并將適用于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奉為圭臬,將會因噎廢食,最終限制心理學的長遠發展。
而就“人性觀”與“方法論”這兩個問題,班杜拉的理論實踐為我們提供了他的方案。 一方面,班杜拉學術思想的轉變,正是從自然科學的框架中脫離出來,走向心靈主義的過程。 他師從本頓,可以說接受的是正統行為主義思想,但他最后卻自發地走向了人本主義。 發生這一轉變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他對人性有著與傳統行為主義不同的看法。 傳統行為主義把行為主體或學習主體對強化的直接經驗看成是學習的必要條件,這隱含了“人性是而且只能是個體化的存在”,班杜拉認為人不僅是個體化的存在,還是類的存在。 相較于傳統主義者而言,班杜拉對人的類屬特征的這種理解,可以看成他對人類存在方式的新發現(高申春,1999,p24)。基于對“人性”獨特思考,他不斷完善并發展了對心理學做出重要貢獻的社會認知論。 另一方面,他的研究總是以問題為中心。 心理學家對人性的理解也決定了他們科學研究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的應用反過來又幫助他們發現一些支持他們人性觀的證據,從而加強他們對人性所持的觀點 (高申春,1999,pp27-28)。 班杜拉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因而反對傳統行為主義將動物實驗結論推至人類社會。 他以人為被試設計了大量的實驗,在豐富堅實的實驗驗證基礎上提出了社會認知論,他的理論及其示范治療方法體現了當代心理學的機能和實用精神(葉浩生,楊莉萍,2021,p212),但他并不局限于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桎梏。 他總是根據問題選用或創立方法,試圖理解全面的人,強調心理學的綜合性質和重視人的感受等,這些都體現出他的人本主義和現象學色彩。
6 結語
班杜拉是第三代行為主義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著作等身,在心理學為人類做貢獻的路上不斷奮進。 他的社會認知理論是對傳統行為主義批判、繼承、發展的結果。 他以人為本、不為方法所限的理論研究態度在當代心理學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意義。一代偉人永遠離我們而去,但他的學術思想,將一直在心理學歷史長河中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