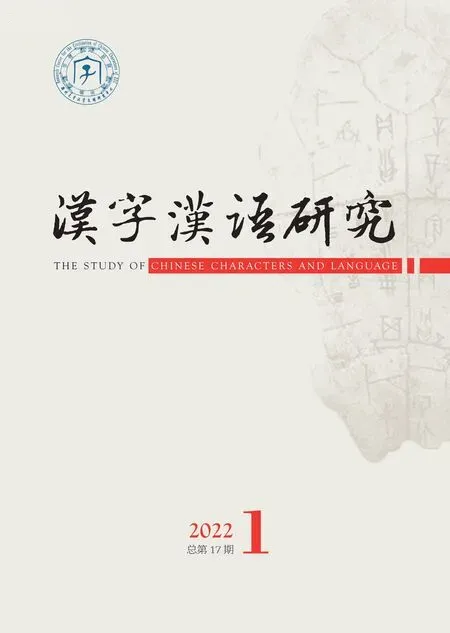讀楚簡五記*
俞紹宏 孫振凱
(鄭州大學漢字文明研究中心)
提 要 從聯綿詞的發展史與學術研究史角度來看,安大簡《關雎》“要翟”讀“腰嬥”具有合理性,傳世本“窈窕”因失去構詞理據而出現了多個轉語書寫形式。楚簡中多見的“褮”用作“勞”或是假借與同義換讀共同作用的結果:“褮”假借為“營”,再同義換讀為“勞”。楚簡中的“丨”可釋為“杖”,在清華簡《五紀》中可讀“戕”或“蕩”。《五紀》中的“上甲”即《春秋》三傳中存在的用“上+天干字”紀日的形式,為處于某月上旬之甲日。《五紀》中存在的若干商代文字或可說明其有著較古老的淵源。
1.安大簡“腰嬥”與傳世本“窈窕”
《詩經·關雎》“窈窕”,安大簡作“要翟”,整理者讀為“腰嬥”,解為細長的腰身(黃德寬、徐在國,2019)。學者多不認同這一考釋意見,最為代表性的反對理由是:“窈窕”是一個宵部的聯綿詞(或作連綿詞,本文統一作聯綿詞),有多種書寫形式,如要紹、妖嬈、要媱、偠紹,《詩經·陳風·月出》中“窈糾”“懮受”“夭紹”和漢代的“要媱”等,馬王堆帛書中引作“茭芍”。它們能構成如下的平行關系:
佻佻 嬥嬥 苕苕
窈窕 要翟 要紹(夭紹)
聯綿詞不應該拆開解釋,“窈窕”的各種詞形,都是姣好之貌。聯綿詞的意義常常比較虛,不能太具象、太坐實。所謂“窈窕”是指女子嫻雅美麗,當然包括面貌、儀態和氣質,將其限制在腰細這一點上就太狹隘了,像《聲類》對“嬥”字的解釋就是如此。《方言》卷二“美狀為窕,美色為艷,美心為窈”,上下兩字分訓,不可信①以上諸說見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安大簡〈詩經〉讀書班討論紀要》,“章黃國學”微信號(zhanghuangguoxue),https://mp.weixin.qq.com/s/DmYWtRngVUTaR5j4T6fqvg。。
杜澤遜(2020)對安大簡此語作過探討,轉述如下:此釋“要翟”為“腰嬥”,義為“細而長的腰身”,乃形訓之法。“要翟”乃聯綿詞,義當從王逸說,為嬌好之貌,其含義初與字形無涉。《毛詩》作“窈窕”。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卷后古佚書《五行》引《詩》作“茭芍”,“茭芍”“窈窕”“要翟”皆一聲之轉,字形無涉,而音近義同,皆嬌好之貌。《毛詩》拘于字形,從“穴”訓“窈窕”為“幽閑”,鄭玄更訓“窈窕淑女”為“幽閑處深宮專貞之善女”,是以“窈窕”為幽深之貌,顯以“洞穴”之義推之。然則馬王堆帛書引《詩》作“茭芍”又當訓為何耶?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陸德明《經典釋文》引)亦以字釋字,未喻其為聯綿詞,不可分而解之也。佻佻、嬥嬥、苕苕、窕窕,皆聯綿詞,形不相涉,音則相近,義則為男子嬌好之貌,《關雎》“窈窕淑女”之“窈窕”為女子嬌好之貌。其皆為嬌好之貌,音皆相近,義正相同。故《說文》云:“嬥,直好貌。”《廣雅》云:“嬥嬥,好也。”然則要翟、茭芍、窈窕、佻佻、嬥嬥、苕苕、窕窕皆聯綿詞,一聲之轉,并音近而義同,皆嬌好之貌也。古書中與“要翟”音近義同之聯綿詞尚有《文選·西京賦》“要紹”、《文選·南都賦》“偠紹”“要紹”。《楚辭·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注:“要眇,好貌。”又云:“眇,一作妙。”洪興祖補曰:“眇,與妙同。”又《楚辭·遠游》:“神要眇以淫放。”洪興祖補曰:“眇與妙同。”要紹、偠紹、要眇、要妙,與“要翟”,亦一聲之轉,為聯綿詞,聲近而義同,義為王逸注“好貌”。《廣韻》“偠”字下云:“偠?,好貌。”其在馬則有“騕褭”,其在女子則為“婹?”,義皆當為好貌,而施之于不同對象,則為男子之好貌、女子之好貌、神馬之好貌,隨文釋義,終不能離其宗也(?、褭、?皆從“鳥”聲,“褭”旁當為“鳥”旁之訛變)。偠?、騕褭、婹?與要翟、窈窕亦皆聯綿詞,其字形變動不居,而音皆近,義皆同,為“好貌”。女子之好,“細腰”或其一端,而不盡在于細腰可知也。“要翟”之為女子好貌,不過為一組聯綿詞各種寫法之一種,正不必求其義于“要”之字形也。以“要”為“‘腰’之初文”,“要翟”讀為“腰嬥”,“要翟”之義為“細而長的腰身”,恐有拘執之嫌。
學者們普遍以為“要翟”“窈窕”是聯綿詞,聯綿詞為雙音節單純詞,不能分開來講。筆者以為,所謂聯綿詞不可分開來解,應當是一個現代觀念。
首先,以為聯綿詞不能分開來講是現代學者對聯綿詞的一大誤解。李運富(1987/2008;1990;1991a;1991b;2008)等文對聯綿詞作出了全面系統的研究,他在考察《廣雅·釋訓》、宋代張有《復古篇·聯綿字》、元代曹本《續復古篇》、明代楊慎《古音駢字》、符定一《聯綿字典》、王國維《聯綿字譜》等文獻基礎上,指出聯綿詞這一概念出自張有《復古篇》,聯綿詞包含雙音節的單純詞與合成詞,也即有部分聯綿詞是可以分開講的。其論證翔實,結論可靠,還古人有關聯綿詞概念之原貌。據沈懷興(2013)考證,聯綿詞為雙音節單純詞這一觀點形成于20世紀20至40年代。
其次,要注意漢語中有哪些是真正不能分開來講的聯綿詞,還要注意詞義不可分開來講不等于講不清詞義來歷。由于詞義歷時發展的鏈條滅失,加之古籍中大量使用假借字,訓詁實踐中常遇到不知其來歷、講不清其詞源的雙音節詞。對于這些詞,學者往往根據上下文語境來推勘其詞義,自然無法講清其理據和詞義來源,因此被視為不能分開來講的、雙音節單純詞性質的聯綿詞,在訓詁史上欠下了一筆筆糊涂賬,而聯綿詞原本應當是可以講清來歷、可以探源的。如據郭瓏(2006:55),對于《詩經》中的“綢繆”一詞,王寧就以為它是由兩個同源詞構成的義合式聯綿詞,“參差”是由單音節的“差”向前再衍生一個不表意的音節“參”而構成的衍音式聯綿詞,“蟋蟀”則是模擬自然聲音(蟋蟀叫聲)而產生的摹聲式聯綿詞。可見“蟋蟀”是可以講清其詞義來歷的,“綢繆”“參差”不僅能夠講清其詞義來歷,而且其結構上是分成兩部分的。
再如“漣漪”一詞,其來源于《詩經·伐檀》“漣猗”,而“猗”是一個句末語氣詞,用法同“兮”,因此“漣猗”本來不是一個詞。“猗”受其前字從“水”影響而類化從“水”,以至于高文達(2001:238)誤將“漣漪”視為不可分開來講的聯綿詞。“漣猗”在安大簡《詩經》簡77中作“可”,整理者讀“漣兮”(可參黃德寬等,2019)。還有“猴猻”“猢猻”,其有多種異寫形式,徐振邦(2013:1034-1035)視之為不可分割的聯綿詞;獅子又稱“狻猊/狻麑”,高文達(2001:382)視“狻猊/狻麑”為聯綿詞。而據董志翹(2020),“猴猻”音轉為“猢猻/胡猻”,又作“胡孫”“活猻”“活孫”“滑猻”等,“猻”為梵語、蒙語、滿語中表示“獸”類的詞尾“-sun”“-suh”的音譯,“猴猻”是一個“小名+大名”的梵漢合璧詞。董志翹(2020)指出“狻猊”可稱“麑”“猊”,推測“狻猊”出自西域,“狻”極有可能源于西域表“獸”義的“-sun”的音譯,“狻猊”是一個“大名+小名”的結構,是一個西域語音譯+漢語的合璧詞。此類詞語還有很多,本文不再一一列舉。因此,我們不應該將所謂聯綿詞不可分開來講視為詞義訓詁中的鐵律,而應積極探索那些看似無法分開來講的所謂聯綿詞的詞義來歷,看看它們能不能分開來講。
回到“窈窕”一詞,其異文較多,安大簡作“要翟”,這一異文出現得最早,且能夠對其詞義作出合理的解釋,筆者認為讀“腰嬥”比讀作滅失了詞義來歷的“窈窕”要好。“要翟/腰嬥”為“窈窕”等異文書寫形式的源頭。推測其一開始應當存在少量的異文書寫形式,這些書寫形式使詞義掙脫了字形的束縛,割裂了詞義與字形的關系,因而人們講不清道不明其詞義來歷,滋生了更多的異文書寫形式,而這些逐漸增多的音近異文書寫形式更加強化了今人所謂“窈窕”是聯綿詞、不能分開來講的片面認識。
補充說明前引《楚辭》中的“要眇”,其在《湘君》中訓為“好貌”固然可講通文意,但在《遠游》中難以講通文意。“要眇”《文選·上林賦》作“杳眇”,或作“杳渺”“窅眇”等,深遠也,深遠貌(黃靈庚,2007),此解才切合《遠游》文意。作“窅渺”或為本字寫法:“窅”有深義,“渺”有遠義。“妖”“要”古音均屬影紐宵部,《湘君》中訓為“好貌”的“要眇”可能讀作“妖妙”,或者“要”讀作見紐宵部的“嬌”“姣”,與“妖”均有美好義。
2.楚簡“褮”字構形
安大簡《侯風·碩鼠》簡82“莫我肯勞”之“勞”,原簡作“”,一般隸定作“”,整理者以為“褮”初文,“”“勞”古通(可參黃德寬、徐在國,2019)。此字形楚簡多見,也見于金文與殷商甲骨文,可隸作“”,釋讀為“勞”是根據金文與楚簡文例推勘出來的。季旭昇(2014:922-923)以為甲骨文中此字從二火、從衣,會燈下綴衣辛勞之意,如《邶風·凱風》“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衣中有小點,或象縫綴之形,后泛指一切辛勞;另一思路是其象水形,則為“澇”。
筆者以為“綴衣之勞”可備一說,但未成定論。
第一,漢字中的象形、指事、會意字往往選擇那些容易與字義發生聯系的圖形、偏旁(構件)來造字,以便于人們依據字形聯想字義,如會意字中的“牧”“莫(暮)”“隻(獲)”“臭”“息”“伐”“弄”“兵”“尖”等。《說文》:“勞,劇也……用力者勞。”若《說文》所說可信的話,“勞”本指用力之勞,而綴衣用現在的話說只是針線活,相對耕種稼穡,做針線活算是輕松的事情,因此燈或火下綴衣難以使人聯想到“勞”。針線活中需要費力的是納鞋底(前幾十年手工納鞋底還很常見),若殷商時期制作鞋子與后世一樣需要納鞋底的話,為什么不用在火下納鞋底來造出“勞”字,這才更符合《說文》對“勞”字的解釋,而選擇要輕松得多的綴衣來造“勞”字?
第二,或以為母親白天工作,夜晚還要熬夜縫綴衣服,可見母親之辛勞。問題是“勞”字所出的甲骨文是中原地區殷商時期的遺物,中原地區自古以來屬于發達的農耕文明區,盡管我們對商代的農業勞動究竟是怎樣的所知甚少,但農業勞動具有季節性是肯定的,農忙季節之外,還有許多農閑時光,為什么不在農閑時節,在白天縫綴衣服,而非得要到晚縫綴呢?就是在農忙季節,也有許多閑暇時光,因為農業勞動的特點是兩頭忙,中間輕松,兩頭是指耕種與收獲階段,中間是指農作物養護階段。耕種結束后,到收獲之前,閑暇時間很多,完全可以在白天縫綴衣服,為什么非得要晚上做呢?
試想,一個母親,縫制衣服白天時間不夠,還要晚上熬夜,一年該要縫制多少件衣服?“”字上從二“火”,若為燈下綴衣,還會點上雙火(不知是火把還是燈。古有照明工具“庭燎”,可參《小雅·庭燎》),成語有“囊螢映雪”,《儒林外史》中的嚴監生臨終時伸出兩根指頭,就是不斷氣,只是因為燈上點了兩根燈草,怕浪費油,挑掉一根燈草后才咽了氣。這些說明,燈在過去是一種奢侈品,能在晚上點上燈也是一種高消費行為,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擔的。既然能點上兩盞燈,說明家境殷實,完全可以請人代勞制衣,何須晚上挑燈自勞?我們雖然難以知曉殷商時期的農業生產勞動情況具體究竟是怎么樣的,但是我國西南一些少數民族以及非洲的一些部落,農業上曾長期處于刀耕火種階段,盡管勞動生產率低下,收入不高,生活窮苦,但是不失閑暇,無須夜間縫綴,可資佐證。
至于將燈下綴衣與“母氏劬勞”聯系起來,恐怕就更是想象之辭了。“勞”有勞心與勞力之別,“母氏劬勞”當指養育子女之心勞。《周頌·載芟》“有嗿其馌,思媚其婦”,《豳風·七月》“同我婦子,馌彼南畝”,說明男女有分工,男人下地干活,婦女送飯。《周南》之《葛覃》“是刈是濩,為為绤”“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頃筐”,《芣苡》“采采芣苡”,《汝墳》“伐其條枚”“伐其條肄”;《召南》之《采蘩》“于以采蘩”,《草蟲》“言采其蕨”“言采其薇”,《采》“于以采”“于以采藻”;《魏風·葛屨》“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豳風·七月》“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以上可見婦女們主要從事采集、砍伐修剪枝條、做針線活、洗滌等勞動。雖然講的是周代的情況,但大致反映了農耕社會的實際狀況。
部分學者將綴衣之勞與牧民生活聯系起來。牧民放牧也有時令性,他們在放牧季將牲口趕往草場之后,也就沒有什么事,白天已經很閑暇了,就更不需要晚上綴衣了。
據黃凌倩(2016:75-76),吳振武曾指出清華簡伍《封許之命》簡6“脅”可以同義換讀為“肋”,再借讀為“勒”。據俞紹宏等(2017)、俞紹宏等(2021),楚簡中假借與同義換讀糾纏在一起的復雜用字現象還有多例,有的甚至還可以用假借與同義換讀后的字形作為聲符、義符造字。如“倉”及“倉”聲字可以借用作表寒冷義的“滄/凔”后,同義換讀為“寒”,再讀作“汗”;“坐”可以同義換讀為“跪”后再借用作“危”,“危”可以同義換讀為“坐”后再借用作“坐”聲字;等等。郭店簡《六德》簡16“”可能是以假借為“營”再同義換讀為“勞”的“”充當聲旁,從“心”,心勞之“勞”本字。《集成》①本文《集成》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2840號“”為“”而聲旁有所省簡。新近刊布的清華簡《五紀》簡90“”、簡121“”,前者整理者疑是“”字省體,“”從陳劍釋“暴”,簡90中讀“標”或“表”,視為從“爻”省聲;后者即“”,整理者讀“衛”(可參黃德寬,2021)。據俞紹宏、張青松(2019),“”所從之“”及相關字見于楚帛書,如上博三《周易》簡22和上博四《交交鳴烏》簡4,其與“衛”讀音關系密切;上博四《昭王與龔之》簡9中的“”從“日”,“”聲,學者或釋“熭”,再同義換讀為暴曬的“暴”,則《五紀》簡90此字或可釋“熭”,同義換讀為“暴”,再讀作“標”或“表”。這些同義換讀與假借摻雜在一起的例子可以為“”釋“褮”而假借為“營”再同義換讀為“勞”提供佐證。
3.清華簡《五紀》“丨”字補釋
“丨”楚簡已經數見。2021年11月27-28日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主辦“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筆者獲悉在清華簡(拾壹)《五紀》中又出現了“丨”字,據說在簡文中為征伐之類意思。
“蕩”有滅失、清除一類意思,如《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蕩”“覆”同為滅除義。《禮記·昏義》:“蕩天下之陽事。”“蕩天下之陰事。”鄭注:“蕩,滌蕩去穢惡也。”孔疏:“‘蕩天下之陽事’者,謂救日之時著素服,蕩除天下之陽事。”則“蕩”為清除義。《墨子·經說上》:“霄盡,蕩也。”孫詒讓《墨子間詁》引畢沅云:“‘霄’與‘消’同。”《經說上》以“霄盡”解“蕩”,則“蕩”有盡義。《楚辭·九章·思美人》:“吾將蕩志而愉樂兮。”“蕩志”之“蕩”舊訓“滌”,“滌”有滌除義,詞義擴大,也就是清除義。
綜上,筆者以為讀“蕩”“戕”均優于讀“撼”。
4.《五紀》中的“上甲”
《五紀》簡36出現“上甲”一詞,整理者說“上甲”即元日,良辰。“上甲”在其后直至簡39簡文中又出現了六次:“上甲有子”“上甲有戌”“上甲有申”“上甲有午”“上甲有辰”“上甲有寅”。筆者以為,簡文中的“上甲”也有可能指一個月上旬的甲日。
傳統干支紀日法存在多種變例。有些學者指出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單獨用天干字或地支字表示日期的例子;青銅器銘文中也有只用一個天干字表示日期的例子,有的還用“孟+天干字”來紀日,如“孟庚”,等等,都是干支紀日法的變例。新蔡簡中有用天干字“癸”“乙”“丁”加“睘”及“睘”聲字組合以紀日的現象,“睘”及“睘”聲字讀為“還”,它們應當是表示處于一個月中旬位置上的“癸”“乙”“丁”日,它們相對于處于上旬的“癸”“乙”“丁”日而言,相當于一個月從上旬的“癸”“乙”“丁”日開始,十天干進行了一個輪回,又回復到了中旬的“癸”“乙”“丁”日,因此寫成“癸嬛”“乙還”“丁睘”之類。用“天干字+還”也是干支紀日的變例。以上干支紀日法變例可參俞紹宏(2015:341-344)。春秋時期的湯鼎(《集成》2766號)銘文“隹正月吉日初庚”中,“初庚”為當月第一個庚日,與“孟庚”之“孟”含義相同。
《五紀》的“上甲”可能是用“上+天干字”來紀日,這一紀日方式也見于傳世文獻。如: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春秋·昭公二十五年》)
郊用正月上辛。(《公羊傳·成公十七年》)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左傳·哀公十三年》)
系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穀梁傳·哀公元年》)
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系牲。(《穀梁傳·哀公元年》)
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穀梁傳·哀公元年》)
以上用“上+干支字”表示每個月上旬日期,“下季+干支字”表示每個月下旬日期。這樣每個月上旬用“上+天干字”紀日,下旬用“下季+天干字”紀日。以上所列文獻中缺中旬干支紀日變例。《穀梁傳·昭公二十五年》:“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是說在上辛與季辛之間還隔著一個中辛。“中辛”見《今本竹書紀年》:“后二年二月仲辛,率群臣東沈璧于洛。”其作“仲辛”。《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類似的文字也見于《呂氏春秋·仲春紀》:“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中(仲)丁”“中(仲)辛”在新蔡簡中就是“丁還之日”“辛還之日”。上引文獻中的“上丁”還見于《禮記·月令》季秋之月:“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若此,則簡文中的“上甲”為傳統干支紀年法的一個變例。“上甲有子”“上甲有戌”“上甲有申”“上甲有午”“上甲有辰”“上甲有寅”分別指處于一個月上旬的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日。
5.《五紀》中若干古老字形在文獻斷代研究中的價值
據黃德寬(2021),《五紀》中存在若干形體古老的字形。如“厷”字,據劉釗(2014:164),商代甲骨文中作“”,為指事字。據董蓮池(2011:328),商代金文同,西周金文中指事符號與主體部分脫離而獨立成圈形。帶有獨立的圈形的字形為戰國楚簡所繼承,如馬承源(2002)《民之父母》簡9“厷”作“”。而《五紀》篇簡94“厷”作“”,顯然是甲骨文與楚簡字形的雜糅,其圈形之外的部分為“厷”字初文,這一初文保留了甲骨文寫法,指事符號與“又”分離。《五紀》簡82中又作“”“”,為“”之訛,所從的“厷”字初文訛作“尤”。
《五紀》中的“身”有兩種字形,一種是楚簡中常見的字形;一種如簡29作“”,簡35作“”,簡109作“”,簡110作“”,顯然保留了劉釗(2014:497)所錄商代甲骨文中作“”“”形的“身”字寫法,尤其與作“”形的“殷”所從的“身”旁近似(古文字正反無別,都是“身”字),董蓮池(2011:1135-1138)、其他楚簡材料未見此類寫法的“身”字。
以上字形表明,《五紀》篇可能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很有可能與殷商時期產生的文獻有聯系,否則不會出現這些商代甲骨金文中常見而在西周文字中不見的字形。《五紀》中偶然見到這些字形,說明該篇帶有這些字形的文字內容可能來源于商代。古書在傳抄過程中,產生年代早的文本往往會留下早期文字痕跡,如黃德寬(2020)《四告》簡1“元”作“”,就是一個保留了早期金文原始象形寫法的字形,整理者說《四告》四篇內容獨立,可以分成四篇,而簡1屬于第一篇告文,為周公告皋陶,簡文“元”字寫法正符合殷商與西周早期金文寫法,與周公所處時代切合,而與西周中期以后上均作橫畫的“元”字寫法明顯不同①趙平安(2020)指出清華簡《四告》中有一些字與甲骨文關系密切,有一些字與西周金文關系密切,這是四篇告辭成文較早的反映,《四告》有明顯層累生成的印記。。
字形在甲骨與青銅器斷代研究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楚簡文獻尤其是古書類文獻斷代研究也應當充分發揮字形的作用。對于出土的楚簡文獻中存在古老字形的,比如存留有殷商字形,而這類字形在西周文字中已經消失并有了其他替代字形,在楚簡中也有了其他替代字形,那么這個文本就可能具有較早淵源。“淵源”包含兩方面含義,就《五紀》而言,一方面,其可能在商代就已經有了雛形,清華本《五紀》是歷經增補修繕而形成的傳抄文本。《書·多士》:“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周滅商,殷商典冊自然會被周人收入囊中。《詩經·商頌·那·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以《那》為首。”《國語·魯語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為首。”《論語·為政》:“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這說明孔子見過夏、商文獻。《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周籍入楚。因此《五紀》源自殷商遺文是有可能的。
另一方面,清華本《五紀》可能成書于商代之后的西周至戰國時期,撰寫者參考了商代遺留下來的文獻。這兩種情況都會在文本中留下商代文字遺跡。
當然,在古書辨偽研究者看來,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大規模出現偽書的第一個階段,當時的文人喜歡托古傳志。因此,該篇成于戰國時期,其作者故意摻雜了若干古老的字形,以顯示該篇是一部“古”書,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這就像《尚書》一樣,敦煌寫本中就有意識地摻雜了許多“古文”字形。不過,摻雜“古文”字形造假應當始于漢代,戰國文人使用這種造假方式的可能性不大。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我們在利用文字對文獻進行斷代研究時要注意,文字文獻斷代與詞語文獻斷代不同。就利用詞語進行文獻斷代研究而言,一方面,有些詞語一開始用假借字記錄,出現得很早,后來才改用本字記錄,但由于披著假借字的外衣而不為研究者所識別,因而被誤斷為晚出詞語,進而將帶有本字記錄的這些詞語的文獻也斷為晚出文獻。而事實上這些本字記錄的詞語很有可能是在后來的傳抄過程中改易的。另一方面,科學地選擇斷代的參照文獻很重要,就楚簡文獻斷代而言,學者或選擇甲骨、金文來作為參照,比如楚簡某篇文獻中出現了某些詞語,而在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中未發現這些詞語,就斷定楚簡文獻產生的歷史不會早于殷商、西周時期(有人甚至根據甲骨文中沒有關于夏朝的記錄就否定夏朝的存在)。這種研究方法并不科學:甲骨文主要是對時事的占卜記錄(已經滅亡多年的夏朝自然很難被甲骨文所記錄),西周金文主要是封賞冊命、歌功頌德的記錄,且數量、篇幅有限,因此甲骨、金文使用的詞匯量本身就很有限,而戰國楚簡許多是真正意義上的古書,其詞匯量自然要比甲骨文、金文豐富,其中存在甲骨、金文中找不到的詞語并不能證明其產生的年代晚。因此,盡管《五紀》中存在著諸多甲骨文、金文中找不到的詞語,我們也不能據之來否定《五紀》可能具有較為古老的淵源。
補記:
潘燈(網名)《清華簡〈五紀〉初讀》(簡帛網簡帛論壇欄目)后有以下貼文:
汗天山(網名)以為原讀“表”之字或當讀為“衛”,簡文“衛躬唯度”,意即通過了解度數來養護自身,簡文下文有身體各部位疾病所在,或當與此句有關(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94&extra=&page=20)。
好好學習(網名)以為《五紀》“丨”可讀為“攘”,“磔攘”成詞古書有之,“攘征”與“攘伐”義近(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94&ex tra=&page=9)。
釋“攘”說值得重視。劉洪濤教授指出“針”從“十”聲,《五紀》此處可讀“殲”。筆者以為,就釋“針”之說而言,讀“殲”要優于讀“撼”,但考察楚簡中該字出現的所有文例,釋“針”不如釋“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