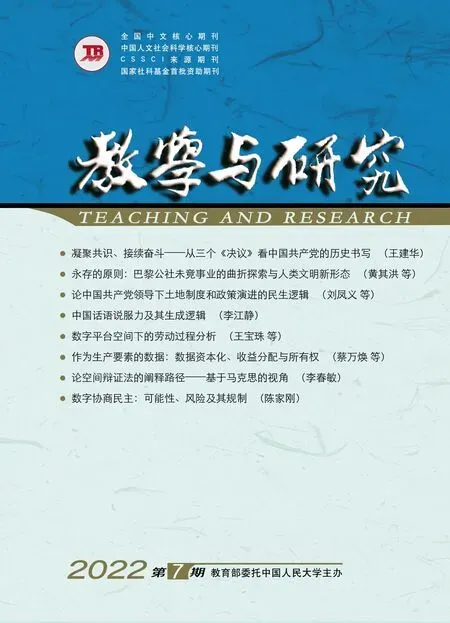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從知行到行動
李基禮
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問題,既關乎思想政治教育理論體系的構(gòu)建,也涉及當代思想政治教育使命的把握。在現(xiàn)有研究中,對何者為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的問題存在不同看法:一是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學范疇體系及基本范疇的邏輯起點,只能是思想與行為這對基本范疇,而不能是其他范疇”。(1)徐志遠:《試論思想政治教育學基本范疇的邏輯結(jié)構(gòu)》,《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二是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的起因或起點范疇是個人與社會。(2)孫文營:《思想政治教育學基本范疇體系劃分的新視角》,《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04年第11期。三是把現(xiàn)實的人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起點。(3)劉瑞平:《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起點》,《光明日報》2006年10月16日。四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起點定位在國家主體或統(tǒng)治階級主體。(4)邵獻平:《思想政治教育中介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4頁。五是認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起點是個人需要和社會需要。(5)趙勇、王金情:《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起點新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年第5期。還有其他一些觀點,不一而足。在這些觀點中,個人與社會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而現(xiàn)實的個人則被視為唯物史觀的邏輯起點(6)舒遠招、鄢夢瑤:《關于馬克思唯物史觀邏輯起點的幾點思考》,《云夢學刊》2018年第4期。,階級統(tǒng)治只能說是思想政治教育產(chǎn)生的社會條件,個人與社會的需求則是大部分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相比之下,思想與行為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的觀點顯得更為合理和具有說服力,它借用馬克思對邏輯起點的科學規(guī)定加以論證(7)上述有些觀點也借用馬克思對邏輯起點的科學規(guī)定加以論證,本文對“思想與行為”觀點的相關批判也適用以此為論證思路的觀點的批判。,在思想政治教育學界也更具代表性。(8)該觀點的提出者徐志遠多次發(fā)文加以重申,最近一次在《論現(xiàn)代思想政治教育學基本范疇的內(nèi)在邏輯聯(lián)系》(《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9年第5期)一文中。該觀點被張耀燦等主編的《思想政治教育學前沿問題》(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43頁)一書所采納。后來邵獻平等修正了自己之前的觀點,也認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起點是現(xiàn)實的人的思想與行為”(邵獻平、何麗君:《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起點》,《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年第5期)。然而,這種觀點不管從馬克思關于邏輯起點的理論還是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對象來看都存在諸多問題。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問題。
一、思想與行為: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的反思
對理論體系邏輯起點最早做出深刻思考的是黑格爾,而科學地解決理論邏輯起點問題的無疑是馬克思。關于這一點已有很多研究,無須贅述。(9)代表性的論文如馮振廣、榮今興:《邏輯起點問題瑣談》,《河南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那么,馬克思對邏輯起點的規(guī)定有哪些呢?已有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的研究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比較全面的,認為馬克思關于邏輯起點的科學規(guī)定包括如下幾方面內(nèi)容:“第一,邏輯起點是一門科學或?qū)W科中最常見、最簡單、最抽象的范疇;第二,邏輯起點應與研究對象相互規(guī)定;第三,邏輯起點是一切矛盾的‘胚芽’,是事物全部發(fā)展的雛形;第四,邏輯起點同時也是歷史的起點。”(10)張耀燦等主編:《思想政治教育學前沿問題》,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頁。然而,從馬克思關于邏輯起點的科學規(guī)定出發(fā),我們難以推斷思想與行為是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
首先,思想與行為不是最簡單、最抽象的范疇。就“最簡單”而言,它首先就不是一個范疇,而是兩個范疇。既然如此,至少從數(shù)量上說就不是最簡單的。不管在黑格爾還是在馬克思那里,作為邏輯起點的范疇都是一個,而不是兩個或一對。因為如果是兩個的話,既存在誰是最簡單的問題,也存在哪個范疇最基礎的問題。就“最抽象”而言,也不能同時把思想和行為都視為最抽象的范疇,相比而言,思想比行為更為抽象,因為進一步分析,一般而言人的行為始終是有思想、有意識的行為。退而言之,即使思想與行為是最抽象的,也不一定就是邏輯起點,因為抽象是相對而言的。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沒有像古典經(jīng)濟學和資產(chǎn)階級庸俗經(jīng)濟學那樣把價值這個更抽象的范疇作為邏輯起點,因為商品是“勞動產(chǎn)品在現(xiàn)代社會所表現(xiàn)的最簡單的社會形式”(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2頁。。也就是說,這里的抽象是相對資本主義社會復雜的生產(chǎn)關系而言的。
其次,從邏輯起點與研究對象的關系來看,也很難說思想與行為是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盡管關于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對象眾說紛紜,但最具代表性、也被大家廣泛認可的是“兩規(guī)律論”,即人們思想政治品德形成、發(fā)展的規(guī)律和對人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規(guī)律。如果以“兩規(guī)律”為研究對象,就不能說明邏輯起點與研究對象是相互規(guī)定的。因為這兩個規(guī)律建立在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對象包含的特殊矛盾化解的基礎上,這一矛盾就是“一定社會發(fā)展的要求同人們實際的思想品德水準之間的矛盾”(12)陳萬柏、張耀燦主編:《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6頁。,而該矛盾所包含的主要不是思想與行為的矛盾,而是社會所要求的與個人實際的思想品德即思想與思想之間的矛盾。況且從社會現(xiàn)實來看,這種知行分離的現(xiàn)象實際上也并非個人的正常態(tài)。關于這一點,下面在闡明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時還會進行詳細分析。
再次,把思想與行為這對范疇作為思想政治教育一切矛盾的‘胚芽’、作為構(gòu)成體系的細胞形式,不管在形式上還是在內(nèi)容上都難以說通。從形式上看,作為胚芽的細胞是一個整體,是一個事物,思想和行為則是兩個東西。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商品孕育著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商品是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的邏輯起點,而不是商品所包含矛盾的兩方面即使用價值和價值是邏輯起點。從內(nèi)容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領域的特殊矛盾是一定社會發(fā)展的要求同人們實際的思想品德之間的矛盾,作為特殊矛盾,它規(guī)定著其他矛盾。正如上面已經(jīng)指出的,這一矛盾實質(zhì)上是社會所要求的思想道德觀念與個人的思想道德觀念之間的矛盾,是思想與思想之間的矛盾,而不是思想與行為之間的矛盾。我們并不否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包含知行矛盾,但它的確不是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
最后,思想與行為也不能說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歷史起點。關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歷史起點問題,存在不同的說法:一是起源于原始社會,以思想的產(chǎn)生為依據(jù);二是起源于階級社會,以政治的產(chǎn)生(即階級統(tǒng)治出現(xiàn))為依據(jù);三是起源于近代資產(chǎn)階級社會,以競爭性意識形態(tài)的產(chǎn)生為依據(jù);四是起源于無產(chǎn)階級的誕生,尤其以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產(chǎn)生為依據(jù)。不管以何者為歷史起點,我們都無法確定思想與行為為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初對象。如果仔細分析,這種把思想和行為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的觀點實際上假設了思想政治教育任務就是實現(xiàn)思想向行為的轉(zhuǎn)化,也就是把思想與行為之間的矛盾作為基本矛盾。由此出發(fā),當我們考察歷史起點時,恰恰應當去考察思想與行為分裂的歷史起點,然而在上述幾種觀點中都無法找到這樣一個起點。
總之,從馬克思對邏輯起點的基本規(guī)定出發(fā),我們難以把思想與行為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不過這種依據(jù)馬克思邏輯起點的科學規(guī)定闡明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的論證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思路,同時以思想和行為為邏輯起點的觀點也為我們反思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提供一個起點,即如何理解思想與行為的關系,并由此為我們尋找真正的邏輯起點提供啟發(fā)。
二、行動: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的確立
把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確定為思想與行為這對范疇,可能源自未經(jīng)反思的兩個前提:一是從教育學角度出發(fā),自然地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解推動教育對象思想品德從思想向行為轉(zhuǎn)變,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內(nèi)化外化過程,但這種理解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它偏離了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領域的特殊矛盾。二是更深層次的、未經(jīng)反思的前提,即知行分離的二元論,然而這種觀點恰恰是基于抽象的概念分析,而不是從現(xiàn)實的個人出發(fā)的。從現(xiàn)實的個人來看,知與行分離只可能有如下幾種情形。
一是無“知”之行,即沒有意識或意義的行為。雖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說某一行為毫無意義,但這一說法是對人的行為的一種價值判斷,而不是指行為本身沒有意識,真正要說沒有意識的行為,只能說是夢游這類行為或日常生活中無意識的機械動作。
二是無“行”之知,即沒有行為意向的意識。我們通常所說的白日夢似乎可以歸于此類,其實也不盡然,說一個人做白日夢并不是說它沒有行為意向,而是說這種想法不切實際,如果真要說是沒有行為意向的意識,古希臘的哲學沉思可以算入其中。
三是知行不一,即知行不一致意義上的知行分離。對此,我們可以分為主觀與客觀上的知行不一致。主觀上的知行不一致可以分為兩種情形:一是認知上的問題,體現(xiàn)為因思想意識、認知能力問題而沒有達到預期目標,然而這并不是知行分離問題。就個體而言,知與行是統(tǒng)一的,只是由這種“知”指導的“行”沒有達到某種客觀后果。二是自我控制能力問題,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知”不能完全決定“行”,還需要情感和意志力的支撐,這種知行矛盾可歸結(jié)為心理、意志問題,屬于心理調(diào)適和精神治療的范圍。還有人可能認為這種概括并不完全,還存在說與做不一致的問題。對這種現(xiàn)象,其實并不能說是知行不一致,這里的說并不是其真實的想法,說本身可以視為一種策略性行為,這種行為實際上與行為者的真實想法是一致的。客觀上的知行不一致是因為客觀的社會因素導致知與行無法一致,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身不由己,即知無法行。這種知行矛盾并不是個體的知行分離意義上的知行矛盾,實際上是社會所要求的、強制性的行為規(guī)范與個體意志之間的沖突,也就是社會要求個體必須按照這種行為規(guī)范(即社會的行)來行動,而個人則拒絕按照這樣的行為規(guī)范來行動。簡單地說,就是由個人的知所指引并實現(xiàn)出來的行為與社會的行為規(guī)范之間的沖突,而不是個人自身的知行分離和不一致。
縱觀上述,從知行關系的分析發(fā)現(xiàn),知行分離和不一致并不是人的存在常態(tài),絕大多數(shù)人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的行為是受思想意識指引的,有著特定意圖的。這種受思想意識指引、有著特定意圖的行為在社會學中稱為行動。那么,為什么會產(chǎn)生知行分離二元論的看法呢?其實這是人們應用思維對人的行動進行抽象的結(jié)果。通過抽象,我們把行動的主觀部分稱之為思想或意識,把客觀部分稱之為行為;或者說從行動中抽象出主觀的思想意識和客觀的可觀察的行為,由此構(gòu)成了思想與行為、知與行的分離和二元對立。這就像馬克思從商品中抽象出使用價值和價值一樣。
既然知行分離的二元論對絕大多數(shù)人在絕對多數(shù)情況下并不具有現(xiàn)實性,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觀點,即思想與行為是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就更加難以站得住腳。那么,什么才能成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呢?其實,盡管思想與行為、知與行不能作為邏輯起點,但這一觀點已經(jīng)包含了真理的要素,即作為兩者之統(tǒng)一的現(xiàn)實基礎的“行動”則可以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對此,我們可以應用馬克思關于邏輯起點的科學規(guī)定來加以檢驗。不過,在此之前需要進一步精確馬克思主義理論關于邏輯起點的基本規(guī)定。
列寧在論述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的邏輯起點時是這樣說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資產(chǎn)階級社會(商品社會)里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平凡、碰到過億萬次的關系:商品交換。這一分析從這個最簡單的現(xiàn)象中(從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這個‘細胞’中)揭示出現(xiàn)代社會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敘述向我們表明這些矛盾和這個社會——在這個社會的各個部分的總和中、從這個社會的開始到終結(jié)——的發(fā)展(既是生長又是運動)。”(13)《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0頁。這一論述表明,商品作為最常見、最簡單和最抽象的規(guī)定源自資本主義社會結(jié)構(gòu)及運動的現(xiàn)實邏輯(現(xiàn)實的并不是歷史的),而不是一個純邏輯或先驗問題。商品之所以被作為最常見、最簡單的范疇,源自資本主義社會生產(chǎn)表現(xiàn)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商品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而商品之所以被作為最抽象的范疇,這是因為它已經(jīng)潛在地包含了后面的一切矛盾尤其是基本矛盾,而這一切矛盾恰恰構(gòu)成了馬克思研究《資本論》的對象,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chǎn)關系。因此,最常見、最簡單、最抽象實際上是對邏輯起點特征的規(guī)定,而“細胞”則是對邏輯起點的形象說法,研究對象所包含的一切矛盾尤其是特殊矛盾才是對邏輯起點的實質(zhì)規(guī)定。于是,我們要把握邏輯起點,可以根據(jù)上述特征來初步辨別何者為邏輯起點,但是否構(gòu)成邏輯起點的根據(jù)在于是否包含一切矛盾尤其是研究對象所包含的特殊矛盾。
從特征上看,行動可以說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最簡單、最常見的現(xiàn)象。在現(xiàn)實社會中,思想政治教育所研究的對象是現(xiàn)實中的個體,而每個個體的現(xiàn)實存在就展現(xiàn)為一個個具體的行動,在社會生活中行動是最簡單和最常見的現(xiàn)象。如果這還只是初步斷定行動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的話,那么,其最終根據(jù)在于行動已經(jīng)潛在地包含了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對象的特殊矛盾及其展開形式。因為現(xiàn)實的行動既是個體的也是社會的,行動是每個個體的自主行動,然而作為現(xiàn)實個人的行動始終處于社會關系中,是與他人相關的,因而也是社會的行動。行動的這種雙重屬性,構(gòu)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對象所包含的特殊矛盾的萌芽。另外,行動是知與行的矛盾統(tǒng)一體,也構(gòu)成思想政治教育這一重要矛盾的萌芽。因此,我們才說行動是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行動內(nèi)部所包含的、處于潛在狀態(tài)的矛盾才發(fā)展出來,生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現(xiàn)實運動過程。
三、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的展開
行動是一個包含個體性和社會性雙重因素的統(tǒng)一體,行動的這種雙重性與人的存在方式相互規(guī)定。人的存在首先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不僅如馬克思所指出,人的本質(zhì)是由社會性所規(guī)定的,“在其現(xiàn)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頁。,而且它也是人得以產(chǎn)生的前提,人必須生活在共同體中才得以可能生存下去。同時,行動也是個體的人的存在得以展開的方式,個體正是在行動中實現(xiàn)自我。就行動所包含的個體性和社會性兩個方面而言,社會性構(gòu)成它的根本規(guī)定,因為每個人都生活在共同體中,個體的行動既關乎共同體的其他成員,也需要與其他成員協(xié)調(diào)一致。然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不是兩種行動,而是行動的兩個方面,它們統(tǒng)一于行動這個統(tǒng)一體之中。
行動就其本來目的而言,是為了確保個體的人的生存。然而,個體的人本身無法獨立自存,從誕生之日就依賴于特定的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個體性的行動構(gòu)成人之存在的目的,而共同體構(gòu)成人之存在的手段。從共同體的角度來看,個體的行動必須符合共同體的行動,也就是行動必須一致,否則以共同體形式存在的類之存在將難以維系。為此,行動中對立統(tǒng)一的兩個方面就出現(xiàn)了分離,社會性的行動作為個體一致性的行動,即共同體所要求的行動,開始從行動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事物,這就是社會規(guī)范的產(chǎn)生。最初,社會性的行動表現(xiàn)為偶然性的一致行動。后來,在社會生活反復試驗或經(jīng)歷中,以往臨時性的協(xié)調(diào)一致的行動就被固定下來,成為個體在特定社會條件下行動必須遵從的標準和規(guī)范。于是,統(tǒng)一于行動內(nèi)部的兩個因素或兩個方面就分化為獨立的、相互對立的事物,即個體行動與社會規(guī)范。
社會規(guī)范的產(chǎn)生原本只是為了保障人的生存需要,人的行動與人的生存保持著直接的聯(lián)系,最初作為臨時性的、不斷變動的協(xié)調(diào)一致的社會性行動只是作為保障人的生存的手段而發(fā)生作用。然而,隨著社會規(guī)范獨立出來后,個體行動首先面對社會規(guī)范,社會規(guī)范成為個體行動的準則。于是,社會規(guī)范逐漸演變?yōu)槟康模袆优c人的生存或存在之間的直接關系就被中介了。
現(xiàn)在的問題是,內(nèi)在于行動的個體性與社會性兩個因素外化為現(xiàn)實的個體行動與社會規(guī)范兩個事物后,新的問題即個體行動與社會規(guī)范一致性、個體行動是否符合社會規(guī)范的問題就產(chǎn)生了。那么,如何確保前者符合后者呢?需要某種力量來維系。社會規(guī)范的最初維系主要是通過原始宗教的形式完成的。作為宗教禁忌的社會規(guī)范通過宗教的神秘力量和禁忌修復(對違反禁忌的懲罰)得到維系。這種維系社會規(guī)范的力量開始以混合體形式出現(xiàn),表現(xiàn)為個體對社會規(guī)范的敬畏,敬與畏并沒有分開并得到意識。之所以如此,社會個體的知與行還沒有區(qū)分,或者說社會還沒有意識到知與行是不同的事物,這就涉及行動的二重分化,即知與行的分化。
個體性與社會性是行動作為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包含的兩個因素,而知與行則是從行動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做出的區(qū)分,也是行動包含的兩個因素,當然最初是潛在地包含這兩者的。在行動內(nèi)部的原初狀態(tài)下,知是行動的意識,行是行動的表征,知與行統(tǒng)一行動之中。這種統(tǒng)一并不是我們習以為常所理解的似乎先有知與行,然后才是兩者的統(tǒng)一。恰恰如前面所闡明的,個體性與社會性是行動的兩個方面一樣,他們都是行動內(nèi)部的兩個要素或兩個方面,統(tǒng)一于行動這個統(tǒng)一體中。其實,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知行二分的觀念是歷史的產(chǎn)物,在原始宗教中或人類行動最初意識中,知是行的一部分,更準確地說知行是不分的。知被視為能夠引起現(xiàn)實世界變化的因素,如在古代社會中某種念頭、咒語或夢被認為能夠直接作用于現(xiàn)實世界。只有人類文明發(fā)展到一定高度之后,才意識到知行是不同的事物,才出現(xiàn)了知行的分化。知行分化的后果就是思想與行為的產(chǎn)生,思想體現(xiàn)為獨特的觀念及其體系,而行為則表現(xiàn)為物理過程。于是,行動正當與否的問題轉(zhuǎn)移到思想上。由此,服從社會規(guī)范的力量也就發(fā)生了分離。
在知行分化的基礎上,個體對社會規(guī)范的敬畏被分開并被意識到。這種分離導致的后果就是服從社會規(guī)范可以源自兩種力量:一是由“敬”演化而來的對社會規(guī)范的認同力量,二是由“畏”演化而來的強迫服從社會規(guī)范的懲治力量。后者逐漸分化為逼迫個體服從的各種軟的(如社會輿論產(chǎn)生的心理壓力)、硬的(如國家暴力)強制力量,而前者需要創(chuàng)造整體性的解釋模式即思想理論體系,從而為社會規(guī)范提供觀念支撐。這種被創(chuàng)制的思想理論體系要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的認同力量,就需要一個教化過程,這個教化過程就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初形態(tài)。
然而,隨著共同體內(nèi)部人的生存狀況的分化,個體行動與社會規(guī)范之間的沖突加劇。于是就會產(chǎn)生兩種后果:一是個體出現(xiàn)行為失范,就是社會個體以反常的行為來破壞社會規(guī)范;二是沖擊支撐社會規(guī)范的解釋體系,出現(xiàn)思想異端,然而最初這種沖擊并不是整體性的,即解釋體系本身還不會被陌生化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盡管我們?nèi)匀豢梢哉J為這種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教育,但對社會內(nèi)部成員而言還達不到這一反思高度。就像中國傳統(tǒng)社會,農(nóng)民起義可能會沖擊現(xiàn)存的社會規(guī)范,但無法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因為整體的觀念系統(tǒng)還沒有受到根本性質(zhì)疑。當然,由于個體行動與社會規(guī)范間沖突的加劇,作為教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進一步強化。
個體行動與社會規(guī)范間的沖突只有轉(zhuǎn)化為觀念體系的沖突時,思想政治教育才在原則高度上達到意識形態(tài)教育的規(guī)定性。具體而言,就是個體行動本身的正當性被另外一種思想體系所支撐,構(gòu)成對現(xiàn)存社會規(guī)范正當性的挑戰(zhàn),彼此的思想體系都被對方視為意識形態(tài)。只有到這個時候,思想政治教育才在現(xiàn)實性上被把握為意識形態(tài)教育。因此,才有人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僅僅追溯到近代資產(chǎn)階級啟蒙運動,“不同的政治集團為了獲得政治權(quán)(利)力展開了激烈的意識形態(tài)競爭”,由此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之地”(15)金林南:《從政治的意識到意識的政治——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政治哲學探析》,《思想理論教育》2010年第19期。。而我們所特指的思想政治教育即無產(chǎn)階級的思想政治教育恰恰在無產(chǎn)階級與資產(chǎn)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中才得以產(chǎn)生。
綜上所述,正是從包含個體性和社會性兩個對立因素的行動出發(fā),思想政治教育的產(chǎn)生及其現(xiàn)實運動才得以完整地揭示,我們也才能完整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復雜的社會歷史運動過程。至此可以說,行動是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
四、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與歷史起點的關系
在闡明行動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之后,與邏輯起點相關的最后一個問題則是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與歷史起點之間的關系問題。因為在馬克思關于邏輯起點的論斷中還有一個基本觀點,即邏輯與歷史的一致。不過在闡明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與歷史起點關系的問題前,有必要簡要澄清一下馬克思關于邏輯與歷史一致的命題。
已有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研究把邏輯起點與歷史起點一致作為確定邏輯起點的依據(jù),其實這種理解與馬克思本人的看法存在差距。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邏輯起點的揭示并不是歷史分析的產(chǎn)物,而是理論抽象的結(jié)果,或者說不是一種線性的因果分析,而是共時性的結(jié)構(gòu)分析。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明確地指出:“把經(jīng)濟范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后次序來排列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xiàn)代資產(chǎn)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系決定的,這種關系同表現(xiàn)出來的它們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fā)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問題不在于各種經(jīng)濟關系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們在‘觀念上’(蒲魯東)(在關于歷史運動的一個模糊的表象中)的順序。而在于它們在現(xiàn)代資產(chǎn)階級社會內(nèi)部的結(jié)構(gòu)。”(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8頁。因此,在構(gòu)建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時,我們并不需要與歷史起點一致來擔保。
當然,馬克思本人也沒有否定兩者在總體上有大致對應的關系。就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與歷史起點的關系而言,其實我們在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時初步發(fā)現(xiàn),邏輯起點與歷史起點存在一致性,而且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的展開與思想政治教育的歷史發(fā)展在總體上大致相對應。
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的行動,其最簡單、最抽象的規(guī)定是個體性與社會性的統(tǒng)一。由于它的抽象性而適用于一切社會,一切社會中的行動既是個體性的又是社會性的,具有這種二重性的行動是人的存在方式。盡管這種一般性的行動是我們從現(xiàn)代社會及其思想政治教育中抽象出來的簡單規(guī)定性,但它也表現(xiàn)為歷史的發(fā)端。在人類歷史的早期,行動本身所包含的個體性與社會性之間的矛盾尚處于潛伏狀態(tài)。盡管行動始終是個體的行動,然而這種行動的個體性還只徒有其形式,在現(xiàn)實性上個體的行動只是共同體行動(即現(xiàn)實的社會性行動)的組成部分。反過來,共同體行動也沒有外化為固定的社會規(guī)范,只有在共同體日趨成熟和穩(wěn)定時,行動的這一因素才真正外化出來了,也就是被社會學所關注的宗教禁忌。由此可以說,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與歷史起點是基本一致的。
關于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的展開與思想政治教育的歷史發(fā)展之間的關系,其實上面在論述前者的時候,為了輔助理解也穿插了一些歷史的展開過程。下面我們就完整地梳理出兩者大致的對應過程。起初,行動的社會性因素外化為社會規(guī)范(即宗教禁忌),與之對立的個體行動都必須服從社會規(guī)范,然而隨著個體意識的發(fā)展,社會規(guī)范的正當性問題被提出,這一問題伴隨著階級社會的產(chǎn)生而產(chǎn)生。但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由于精神生產(chǎn)權(quán)始終掌握在統(tǒng)治階級手中,被統(tǒng)治階級只能從統(tǒng)治階級生產(chǎn)的思想體系中為各自的行動辯護。因此,此時的思想政治教育還是一種教化,其目的就是個體行動必須服從精神上的社會規(guī)范,或者說個體在精神上也服從或認同社會規(guī)范,個體行動還沒有在精神上分化或獨立出來。只有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對立階級達到了一種階級自覺,產(chǎn)生了對立的意識形態(tài),個體性行動與社會性行動的對立達到了一種思想或精神高度,由此才產(chǎn)生了具有意識形態(tài)斗爭原則高度的思想政治教育。綜上,從整體上來看,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的展開與思想政治教育的歷史發(fā)展基本一致。當然,邏輯起點的展開并非先驗的,其實是在歷史研究或經(jīng)驗研究中提煉出來的,這就賦予了邏輯展開以現(xiàn)實性。
最后還需注意的是,這種邏輯起點的展開從根本上說是對現(xiàn)代思想政治教育進行抽象分析的結(jié)果,遵從的是馬克思所說的“科學上的正確方法”,即“抽象的規(guī)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xiàn)”(17)。同時,我們只有站在現(xiàn)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現(xiàn)實高度,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歷史發(fā)展,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29頁。。
總之,行動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符合馬克思關于邏輯起點與歷史起點一致的基本論斷,但要意識到這一論斷并不構(gòu)成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確立的必要條件。
五、結(jié)語: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把行動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并非僅為我們提供一個新論斷,它對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就理論意義而言,它有利于進一步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主次矛盾、基本規(guī)律及其關系問題。在上文我們多次提到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的特殊矛盾是一定社會發(fā)展的要求同人們實際的思想品德水準之間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實際上是兼具個體性和社會性雙重屬性的行動的邏輯和歷史運動的產(chǎn)物,由此我們才能指證行動是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以此為出發(fā)點,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特殊矛盾運行過程的正確揭示,就能夠幫助我們準確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規(guī)律,從而不至于出現(xiàn)紛繁雜多的思想政治教育規(guī)律說。當然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但邏輯起點的確定為我們提供了前提和基礎。另外,邏輯起點的準確定位也能為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zhì)、結(jié)構(gòu)、功能等提供依據(jù)。總之,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的確定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對象、邏輯結(jié)構(gòu)和學科體系。
就實踐價值而言,它有利于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攻方向,明確當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和擔當。以往把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理解為知行這對范疇,就會引導我們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務放在知行轉(zhuǎn)化上,把主要精力放在單個教育對象上,這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思想政治教育學特殊矛盾的解決。而當我們確定行動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時,盡管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特殊矛盾的兩方面依然是個體性與社會性之間的矛盾,但通過對行動的邏輯與歷史運動的揭示,我們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社會行動的沖突聚焦在意識形態(tài)的沖突和斗爭上。盡管這種斗爭不像現(xiàn)實的政治權(quán)力斗爭那樣直接,但由于現(xiàn)代社會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往往建立在認同基礎上,這就凸顯了這種斗爭的極端重要性。由此我們才能深刻地理解馬克思所說的這句話的現(xiàn)實意義,即“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zhì)力量只能用物質(zhì)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jīng)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zhì)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頁。這就讓我們更加明確,思想政治教育的當代使命就是占領意識形態(tài)的制高點,加強理論說服力,在意識形態(tài)斗爭中取得勝利,最終增強理論自信。
以行動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盡管具有上述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也得到較為嚴格的論證,但仍然存在某些質(zhì)疑和挑戰(zhàn)。其中,最具挑戰(zhàn)性的看法是行動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不具有唯一性,行動可能是其他學科尤其是社會學的邏輯起點。這一看法其實包含兩個問題:一是關于唯一性問題,如果我們能夠合理地論證行動是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邏輯起點,而且從行動出發(fā),能夠更好地化解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理論問題,構(gòu)建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理論體系,對現(xiàn)實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更好的解釋力,那么即使不具有唯一性,也不能否定這種觀點的合理性。就如馬克思把商品確定為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的邏輯起點,但也沒有證明商品作為該邏輯起點的唯一性一樣。二是是否為社會學的邏輯起點問題,根據(jù)已有社會學研究,社會學邏輯起點的代表性觀點有關系行為論(20)張傳武:《論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與邏輯起點》,《理論學刊》1991年第5期。、現(xiàn)代性論(21)文軍:《邏輯起點與核心主題:現(xiàn)代性議題與社會學理論的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和市民社會論(22)王浩斌、王飛南:《市民社會:現(xiàn)代社會學的邏輯起點》,《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還沒有發(fā)現(xiàn)把行動作為邏輯起點的觀點,即使今后有,正如唯一性問題所指出的,并不構(gòu)成對我們觀點的挑戰(zhàn)。當然,我們提出行動是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的觀點只是對該問題尤其是對知行論的深化,隨著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的不斷創(chuàng)新,思想政治教育學邏輯起點可能會得到新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