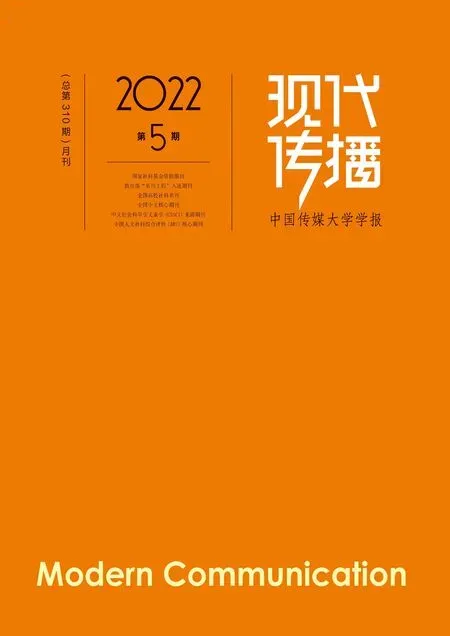新世紀中國藝術電影書寫:記憶空間、空間副本與身份追認*
—周 星 吳曉鐘—
何以探究新世紀電影?研究者有不同角度,但更為新鮮的切入卻需要理論的多樣性。而空間命題到底如何介入研究并且打開更為開闊的視野?這的確需要有貼切對象和超越對象的勇氣。近年在對于中國電影學派的經驗總結之中①,力求以整個中國電影的發展的優秀典型作品為案例,提煉出中國電影學派的理論依據。我們不能不時常比較世界電影并以世界電影理論來進行深入探討。中國電影常態研究,更多重視其與時代變化中意識形態和社會人心之間的關聯。于是難免以電影的商業化和市場化,以及大眾娛樂需要作為成熟與否的標志。但藝術電影在此時應該承擔更重要的責任。在當前時代背景下,無論是在新主流電影的創作,還是在商業類型電影的創作中,抑或是在藝術電影的創作中,電影與記憶的關系皆愈顯密切。電影不斷摹寫人們的記憶的同時,也不斷鍛造著人們的記憶,電影深刻地改變了記憶方式與記憶內容。新世紀中國藝術電影便往往以記憶作為核心的要素,普遍以“記憶空間”書寫空間變遷中的個人記憶、歷史細節與文化記憶來描摹創作,以一種個體記憶實踐著集體歷史的重寫,憑吊集體記憶并追認其身份認同。這便引發了本研究試圖進一步探究的問題思考:新世紀中國藝術電影書寫中的記憶生成機制為何?其“記憶空間”構建的空間敘事邏輯為何?其記憶書寫的精神文化內核又是如何?于是,本文論及的“記憶空間”自然是試圖作為切入口,即視空間為記憶的要素、附著物、庇護所、歷史文本與隱喻載體,空間參透了記憶的意識與無意識的心理過程。對“記憶空間”的選擇、裁剪和建構,潛藏著創作者的記憶、情感和評論。中國電影在21世紀開啟了市場化路途,但新世紀藝術電影中的“記憶空間”影像卻具有格外值得注意的要素,從中可以結合電影研究與文化研究的方法,以綜合運用“文化記憶”“第三記憶”“記憶之場”“空間敘事”等文化理論、記憶理論、空間理論、電影理論,進行現象的歸納及文本的分析考察。經過20年的新世紀變遷,中國電影具有了更為寬闊的表現天地,值得拓展思路來思考新世紀藝術電影中的文化記憶、空間副本與身份追認,這有新的認識價值。首先,探討“記憶空間”如何喚醒觀眾的文化記憶,如何將個人記憶提升至文化記憶,并與當前社會文化產生情感聯結與對話關系,有利于建構新的文化體系。其次,空間副本是“記憶空間”的依樣重塑,一種相對于正本的復制、備份,其可復制性使記憶得以大批量復制、激活、延續與強化,有利于形成記憶的文化認同。再者,身份追認則強調歷史身份的重新確認,依憑文化記憶與空間副本的生成,獲得過往身份的自洽追認,重新認識自我與社會的關系。這些關鍵性的思考將有利于我們總結“記憶空間”的記憶生成機制、空間敘事邏輯和精神文化內核。
一、文化記憶:內容、個體記憶與記憶的社會框架
(一)記憶理論:從集體記憶至文化記憶
探討中國電影的記憶,尤其是藝術電影中的記憶問題是基于“記憶”愈發成為文化研究的熱門概念,圍繞“記憶”的理論話語不斷地擴張,從心理學、生理學轉向人文學、文化學等。1925年,法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記憶研究奠基人之一的莫里斯·哈布瓦(Maurice Halbw?achs)首倡“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理論——“集體記憶是一個特定社會群體之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②。特指某種為社會群體所共享、延續與構建的記憶,服務于社會當前的情境與需要,存在于社會的各個群體之中。作為一種新的記憶研究范式,該理論以“記憶的社會框架”(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概念將個體記憶提升至集體層面,認為社會框架提供共同的價值認同,價值的生成依照這一框架,可以令個體記憶通向集體,從而開辟出新的理論視野,令“記憶”成為共享的文化力量。
“文化記憶”同樣作為一種開放的理論,日益發展為一門顯學,其跨學科價值更是不斷得到挖掘。20世紀90年代,揚·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理論承襲了哈布瓦赫的記憶理論,特別是針對其“記憶的社會框架”理論有著延伸性的發展,強調并闡發了記憶的文化之維。他指出“文化記憶”是針對一個社會/時代至關重要的信息,構成社會/時代的集體記憶,而與之相關的人憑借不同的文化形式重溫這些記憶,以確認和強化自身的身份認同。對于中國電影而言,文化記憶似乎并不缺乏,但以往的研究卻缺乏對其深入探討。新世紀藝術電影中的“記憶空間”敘事,普遍從個體記憶的視角出發,結合記憶的社會框架,以文化記憶為回憶內容——聚焦如計劃生育、下崗潮、國企改革、改革開放記憶、流行記憶、社會運動記憶、苦難記憶等重大事件中的集體記憶——生成銀幕上的文化記憶,保存與傳遞那些對集體的構成與延續至關重要的記憶內容,為文化記憶的存續注入新的生命力。比如我們從獲得柏林電影節兩項銀熊獎的王小帥導演的《地久天長》(2019)來看,其文化記憶所賦予的這種似乎陳舊的題材,卻給予了動人心魄的表現沖擊力。而電影在隨后的計劃經濟生育制度取消之后,更提前為將來的歷史記憶和歷史表達留下了一個濃彩重墨的文化存留。
“記憶空間”中的回憶形象總是依托于具體的空間與時間。揚·阿斯曼認為每種文化均會形成一種“凝聚性結構”(Konnektive Struk?tur)——“它起到的是一種連接和聯系的作用,這種作用表現在兩個層面上:社會層面和時間層面。”③在社會層面構造起一個“象征意義體系”——一種共同經驗、期待和行為的聯系空間;在時間層面則將昨天跟今天連接起來。基于此,“記憶空間”也是文化記憶的一種“凝聚性結構”,既構成社會的聯系空間,亦實現時間上的連續性,讓個體歸屬于“我們”。電影理論大師安德烈·巴贊(Andre Bazin)將電影的發明視為人類的“木乃伊情結”(Mummy Complex),以實現人類記憶的時間存續。揚·阿斯曼則指出,對于哈布瓦赫意義上的“集體記憶”而言,“四十年意味著一個時代的門檻,換句話說,活生生的記憶面臨消失的危險,原有的文化記憶形式受到了挑戰”④。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s)進一步指出:“記憶是在三個構成要素的互動中得到形構的,它們分別是‘載體’(Car?rier)、‘環境’(Environment)與‘支撐物’(Sup?port)。”⑤對于文化記憶而言,載體依賴于能夠代代相傳的文化客體、符號、媒介等;環境是憑借這些記憶符號創造自己身份的群體;支撐物是主動使用這些符號和參與這些符號的個體。于是我們說,“記憶空間”是文化記憶的一種符號載體,且足以保障記憶的存續;持有身份認同的觀眾群體是其環境,有一定的時代門檻;而創作者則是其支撐物,憑借三者之間的互動來形構與保留文化記憶。
(二)個體記憶之名下的文化記憶書寫
阿萊達·阿斯曼堅稱:“因為歷史的超重,文化記憶失去了它的兩個核心功能,即強度和身份認同,或者叫推動力和塑造性的自我畫像(Formatives Selbstbild)。”⑥個體記憶的文化重要性愈發提升,它不但是構建自我畫像的起始,也是集體記憶的前提。生動的個體記憶將生命歷程的框架同身份認同緊密聯系起來,為理解歷史提供新的資源。于是,個體記憶之名下的文化記憶書寫,也成為藝術電影書寫記憶的一種有效策略。藝術電影追求的往往是被社會記憶所遺忘的那個部分,或曰部分記憶的“殘片”。常以重構的方式突破商業類型電影對歷史再現的壟斷,試圖把心理習慣與意識灌輸、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聯系起來,從而引導觀眾從新的角度反思記憶,讓個體記憶與集體歷史相互補充、協商與融合。
中國電影的新世紀藝術電影,往往將個體命運或家庭命運的敘事貫穿至時代大潮的歷史軌跡中,以此憑吊集體記憶并追認其群體身份認同。私人化的回憶視點將故事的敘述心理化,而非一味局限在歷史事件上,更容易引發情感的共鳴與回憶的代入,普遍顯示出歷史表達的克制與記憶書寫的真切。這些影片基于自身經驗的微觀世界,把歷史內化為個人的情感記憶,并在深度的人性探討中迸發情感的力度,從而令個體記憶與文化記憶產生關聯。典型的例子莫過于王小帥導演的三部影片,它們共同回憶改革開放初期的縣城記憶,以其獨特的個體記憶實踐著集體歷史的重寫。《青紅》(2005)以自傳式的視角追憶20世紀的80年代初期,復原時代文化的典型場景。影片中的父親一心想離開貴州,女兒青紅卻與本地人戀愛,由此產生的父女矛盾、空間矛盾注定了悲劇性的結局。一如瑪麗安·赫希(Marianne Hirsch)的觀點:“后記憶”(Postmemory)是一種集體創傷經歷者的后代記憶,“創傷后遺癥在兩代之間傳遞和共鳴”⑦。青紅的命運成為“后記憶”代際傳遞下的悲劇。《我11》(2012)則以一個“白襯衫”事件來結構故事,以符號化的空間意象構建少年王憨的青春物語與廠區記憶。少年個體化的視點成為歷史的旁觀者,他帶著成長的代價向傷痛的記憶轉身告別,隱喻了特定年代下的集體青春。《地久天長》更捕捉了前后三十年的今昔歷程,通過兩個家庭之間難以排遣的心靈創傷,折射幾十年的集體心靈史。影片既還原了歷史氛圍下的鮮活記憶和個人遭際,也書寫了計劃生育、國企改革等轉型期的文化記憶,從作者化的個體記憶轉向更為廣泛的公民傳記。此外,顧長衛導演的兩部影片同樣講述改革開放前后的社會轉變,《孔雀》(2003)、《立春》(2008)均以同一時期的縣城為時空背景,對準個體的日常記憶,還原當年的人文風貌、物質條件、自然景觀等記憶空間,生成熟悉的歷史意象、歷史場面,并以悲憫的敘事基調完成從個人記憶到集體記憶、文化記憶的升華,捕獲觀眾的情感認同。
(三)記憶生成機制:記憶的社會框架
正如哈布瓦赫所述,記憶是與集體、社會及環境緊密相關的現象,“人們通常正是在社會之中才獲得了他們的記憶的”⑧。“記憶的社會框架”決定了記憶的回憶方式——依賴社會的互動與確認,并與社會的主導思想、文化規范密切相關。阿萊達·阿斯曼在哈布瓦赫的理論基礎上提出,個體記憶總是包容在范圍更廣的家庭記憶、社群記憶、社會記憶、政治記憶乃至文化記憶當中,從內容到語境都總是集體的。例如,《海上傳奇》(2010)以多位個體的口述記憶來側寫近代史,賈樟柯導演就此闡釋道:“群體記憶、國家敘事、時代傳奇與小民悲歡交織,貫穿公共和私人的生存領域。”⑨的確,文化記憶是個體記憶的升華與歸總,回憶的過程總是受到選擇性策略的控制。換言之,個體記憶的價值是在“記憶的社會框架”中得到解釋,而框架的改變也將導致某些記憶的遺忘。例如,《歸來》(2014)、《芳華》(2017)均采取對歷史背景的淡化處理,以個體記憶中的愛情敘事來沉淀宏大歷史下的個體之維。影片共同指向了一段被主人公所遺忘的歷史,勾連起復雜的社會文化語境,主人公也都經歷同一時期的創傷經驗,而記憶的損失也構成一種隱喻。
文化記憶的內容是理念的復合體,是一個時代/社會所不可或缺的知識價值體系,它需要適當的綜合文化環境,也總是以“不在場的在場”存在于人們內心中,構成一種“有價值的記憶”。恰如地理學家愛德華·蘇賈(Edward W.Soja)所稱:“空間的組織不是一種‘容器’,就是一種外部的反映,即社會動力和社會意識的一面鏡子。”⑩例如,《我們倆》(2005)中作為北京城市文化意象之一的四合院,充當著地域文化、身份認同與文化記憶的符號,承載著人們對溫暖社會聯系、穩定人際關系的懷舊與向往。《長恨歌》(2005)則審視20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的上海浮沉,回憶上海小姐與弄堂等空間之間的緊密聯系,以城市速寫的方式描摹老上海的生活記憶,以有意而為之的鏡像建構出摩登上海的文化記憶。因此,文化記憶不是個體記憶的簡單疊加,其建構總是取決于集體的需求與現實的期待,總是由相關之人根據當前的需要對記憶賦予新的意義,從而在不斷地自我審視中保持其生動性,促成一種集體認同的文化體系。例如,《七月與安生》(2016)的小說于2002年出版,曾帶給讀者以“純愛至上”的文化記憶。影片則將故事改編成“女性成長”,揭示其對于時代文化和審美認同的捕捉與闡釋,呈現為一種文化記憶的回收與改寫。總之,記憶的生產與再生產總是伴隨著記憶的選擇判斷與修改重建,將其納入社會框架中評估與闡釋,使記憶重獲真實感、鮮活感,從而讓記憶成為當下的思想資源,串聯起觀眾與記憶的新關聯。
二、空間副本:形式、地方記憶與場所記憶
這里提出“空間副本”是基于文化記憶論說而推出的延續性概念,空間副本是“第三記憶”的典型存在形式。何以如此?法國哲學家、現象學創始人胡塞爾(Husserl)曾提出意識的兩種記憶形式——“第一記憶”(感覺)與“第二記憶”(回想)。2012年,法國技術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此基礎上提出“第三記憶”理論,并認為電影本質上就是一種“記憶工業”,“第三持留指的是在記憶術機制中,對記憶的持留的物質性記錄”。第三持留又稱第三記憶,“所有記錄,無論其形式如何,都屬于這一類型的記憶。胡塞爾本人將這一類型的記憶稱之為圖像的意識”。我們認為,“空間副本”是“第三記憶”的典型存在形式。如若說,“記憶空間”的正本儲存于人們的腦中,那么“空間副本”則是“記憶空間”的依樣重塑,一種相對于正本的復制、備份,而成為“記憶空間”的外化形式。“空間副本”按照意識的方式將記憶物化下來,而成為可供消費的意識商品,觀眾得以在其中消耗關于記憶的欲望。斯蒂格勒精當地概括道:“第三持留,即技術的痕跡,是技術的痕跡使‘此在’(Dasein)得以進入那個既成的過去時刻。”電影作為一種持留的代具,為意識流提供空間性的直覺,“作為對流動中的自身的記憶,意識流轉瞬即逝,因而必須以外界載體、記憶的代具為支撐”。概言之,“空間副本”將記憶“客觀地”持留住,捕捉下的時空連續體將保存為觀眾的客觀記憶,從而令記憶擺脫主觀性的束縛。
揚·阿斯曼聲稱:“回憶形象需要一個特定的空間使其被物質化,需要一個特定的時間使其被現時化,所以回憶形象在空間和時間上總是具體的。”無獨有偶,斯蒂格勒秉持類似的觀點:“任何一種第三持留都總是既具有空間性,又具有時間性——它既是‘時間的空間化’,又是‘空間的時間化’,也即一種延遲差異。”“空間副本”的時空構建亦是具體的:在空間層面上,古希臘羅馬的記憶術的核心就在于“視覺聯想”,“空間副本”作為連接記憶的“視覺聯想”、橋梁與物質支撐,令回憶更為形象生動,激活觀眾相關聯的空間記憶,生成“記憶空間”的想象與認同;在時間層面上,又作為銘刻時間的媒介,將記憶拉回某一時間點,凝固某一階段的記憶形態,并重建一個記憶事件,以便促進歷史與當下的對話。經由“空間副本”的時空構建,記憶得以被保存、復制、共享、延續、強化、置換、確證乃至于懷疑,而不再是個人獨有的私人秘密。觀眾投入“空間副本”并忘卻自我,與電影中的“記憶空間”相結合,既滿足了記憶的欲望,也將獲得更多的啟發。在新世紀藝術電影的創作中,地方記憶與場所記憶是兩類典型的“空間副本”的呈現形態。
(一)地方記憶:第三記憶的經驗空間
雅各·德里達(Jacques Derrida)認為電影是對記憶的記錄及播放;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認為記憶是一種現實化的“時間—影像”;斯蒂格勒則認為電影是一種可以被儲存、篩選與刪節的“第三記憶”——不斷調節人對記憶的感覺與回想。“空間焦慮”最初指人們在陌生環境中尋找路徑的焦慮感,現在它更多地被用于指人們因離開熟悉的環境而對自身錯位的恐慌感,一種空間錯位后的身份缺失的恐懼。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 Tuan)在其構建起人文地理學科的《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一書中表明:“當我們感到對空間完全熟悉時,它就變成了地方。”這意味著,“第三記憶”所反復提供的經驗空間也將影響人們的“地方記憶”。正因為“第三記憶”的空間建構、記憶建構的特性,使得藝術電影創作者的地方身份、私人記憶及特定地方文化的吁求,都構成必然要考慮在內的因素。許多“作者導演”的“記憶空間”更是充盈著主體的文化意識與美學追求,例如成長于貴州的王小帥、山西的賈樟柯、陜西的顧長衛、上海的婁燁、遼寧的張猛、貴州的畢贛……這些創作者將自身的經驗與地方歷史氣息相結合,得出空間形象的記憶文本與文化想象,而對“空間副本”的選擇、裁剪等,皆潛藏著創作者的觀點、情感,也與創作者的籍貫、成長經歷與身份認同等息息相關。
也許舉出來自貴州凱里的本地導演畢贛的《路邊野餐》(2016)可以更好看到其典型表現。影片中一連串的長鏡頭顯露他對于經驗空間的鐘情與熟稔,多次演繹出“記憶空間”與詩意象的交織捕捉。確如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之言:“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談一談自己的小路、岔路、路邊長椅;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做一張地圖,把失去的鄉野標示出來。梭羅(Thoreau)說過,他把自己的田野地圖刻在他的靈魂里。”畢贛也將記憶中的凱里地圖刻錄在“空間副本”中,為觀眾建立起凱里的地方記憶。《蘇州河》(2000)則描繪出城市漫游者別樣的精神地理,搖晃的長鏡頭,自然光下的跟拍,攝錄下上海之不安與曖昧的一面。“漫游其實就是進入城市內部結構、窺探城市秘密和體感城市官能的過程。”婁燁在他的故里尋找記憶中的精神家園,那些瞬間的感知浮現,把上海從常規經驗中抽離出來,生成圍繞著蘇州河及其周邊環境的獨特的經驗空間。
段義孚十分強調地方的切身經驗,認為心理、生理的經驗構成情感記憶的基礎,“永久情感的種子已然被植入。微不足道的事件總有一天能夠建構起一種強烈的地方感”。足見他更為重視從“空間感”到“地方感”的提升,以及容易被淡忘的空間經驗的價值。的確,創作者對于某一空間的美好記憶,對于曾經投入大量精力與感情的地方,總是留存著最真切的經驗與記憶,而對于“地方記憶”的失去,便也總是伴隨著失落悵惘。空間感知來自于持續的經驗積累,地方認同則代表一種精神性的依戀,被人們視為生命組成的一部分。例如,《山河故人》(2015)憑借黃河、文峰塔、關公等符號隱喻下的故鄉記憶,映照人物的命運、時間的流逝與文化的遷移。影片通過一段愛情糾葛揭開轉型時期的創傷記憶,通過電影畫幅的變化與經驗空間的變遷來表征地方記憶的巨變,觀照回不去的精神故鄉,安撫失憶的心靈。又如《岡仁波齊》(2017)中的文化拓撲學的空間認知方式,也強調逾越物理本身的經驗記憶之維,生成有形與無形的文化產物。“地貌并不僅僅是沉積留下的痕跡,還是一種歷史文本,一種只有通過身臨其境、親歷他鄉和艱苦跋涉的朝圣之旅才能閱讀的歷史。”
在同質化、碎片化的城市空間中,人們難以獲取對空間的總體性把握,產生主體與空間的斷裂感。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于1988年指出:“認知圖繪(Cognitive map?ping)的概念正好可以用來說明個體對于城市空間的直接感知與個體把城市作為一個缺席的總體性加以想象性的感知之間的辯證關系。”保羅·羅德威(Paul Rodaway)則在《感官地理》(Sensuous Geographies:Body,Sense and Place)一書中把“認知圖繪”引申為人們認知空間的一種方式,“認知圖繪”強調街道、建筑、名勝古跡等地標的重要性,重視認知者的歷史和地理知識,屬于理性的認知。《十七歲的單車》(2001)甫一開場,快遞公司的經理要求員工們記下北京所有的胡同、商業街區等名字,公司的墻面上貼著的正是北京地圖。在摩天大樓、四合院、胡同、馬路等并置的都市空間中,少年的自行車穿行其中,繪制出北京記憶的“認知圖繪”。“個體首先要了解的是其所處的位置關系,其中包括標志物,這實際上起到了一種心理錨固點的作用。”一如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述:“大城市是人類至今創造得最好的記憶器官。”城市空間創造市民共同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環境,因而具有記憶的象征符號功能,有什么樣的城市記憶,便有什么樣的城市空間影像與之對應。譬如,《過春天》(2018)中流動性的公共空間直接參與敘事,構成香港城市記憶的器官,使時間在流動的空間中得到呈現。
(二)場所記憶:被喚醒的記憶之場
20世紀80年代中葉,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在其主編的《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中建立了“記憶之場”(Lieux de Mémoire)理論——由“場所”(Lieux)與“記憶”(Mémoire)組成,作為建構歷史敘事的兩個要素。他解釋道:“之所以有記憶之場,是因為已經不存在記憶的環境。”他從“場所”一詞的三個層次上說,“記憶之場是實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場所……構成這三個層次的是記憶和歷史的作用,二者交互影響,彼此決定著對方”。因此,他將記憶之場視為“另一種歷史”。“記憶場所存在的根本理由是讓時間停滯,是暫時停止遺忘,是讓事物的狀態固定下來。”“‘記憶之場’這一概念完全產生自失落感,因而被打上了懷念逝去之物的印記,它自動地被用來指稱記憶的存儲工具、回憶中的避難地和特殊群體的身份象征。”這種記憶裝置的目的在于喚醒與恢復那些漸漸平庸的場所。同樣,“空間副本”的記憶建構也依托特定的空間場所,場所不僅支撐著記憶,亦反作用于記憶。揚·阿斯曼稱之為“被喚醒的空間”(Belebter Raum)——“它們是回憶的空間框架,即使當它們或者說尤其是當它們不在場時,便會被當作‘故鄉’在回憶里扎根”。因此,場所記憶作為被喚醒的“記憶之場”,具備了類似“公共紀念碑”的記憶功能。
場所的“特異性”是指某一特定的場所,與根植于此的社會實踐、文化、歷史之間的關系的產物。新世紀藝術電影往往針對特異性的場所,進行帶有視覺隱喻的敘事發掘,用以書寫記憶、鄉愁、歸屬感與歷史。典型如,關注工人群體在工業場所中的文化記憶,追憶廠區車間內的鋼鐵時代。《少年巴比倫》(2017)以廠區空間為敘事空間,布設舊時代的象征符號,還原糖精廠車間及工人勞作的文化記憶。廠區化身為文化記憶的物質支撐與生動形象的回憶場所。《鋼的琴》(2011)同樣將故事設置在國企改革下的東北廠區,廠房成為表演的場所,記憶的情緒與動機影響著記憶的通達,被壓抑的人與事物再度上演著感性的記憶場景。正如德國歷史學家萊因哈特·科澤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提出的“感性回憶”(Emotional Memory)概念,這種記憶由感官知覺來塑造,儲存在人的身體里,每當需要時便自行浮現。愛德華·蘇賈意義上的“情感地理”(Affective Geographies)則強調各因素的文化建構及主體的情感介入,“情感地理是對體現于空間性的諸種社會關系的具體化,將空間闡釋為一種‘具體的抽象’”。《我們倆》中,作為老北京傳統建筑的四合院,如今已成為“奢侈”的家屋空間。影片中的四合院是一個由家長里短、鍋碗瓢盆所組成的小型社區,故事以一個院落中的相互幫助、相互影響,喚醒傳統生活方式的場所記憶與情感地理。如果說,人們的生命歷史可以經由意象來建立,那么影片中的四合院作為回憶的藏身之所,正是把壓縮的時間寄存于自身,并成為一種人格的延伸,從而引導觀眾回憶自己所待過的某間特別的屋子。
戴維·哈維(David Harvey)在闡述“空間調控”理論時,發現城市的人造環境在保存與破壞之間存在著互相的緊張影響,他稱之為“地理景觀無休止的塑造與再塑造”。此間,“廢墟變成了一道記憶的風景,在這片風景之中,與這些地點相聯系的歷史在觀察者那里被鮮活地回憶起來”。拆遷則是對場所記憶的抹除,“唯有在空間中才得以發現。潛意識深居其中。回憶無所遷動,它們空間化得越好,就越穩固。把時間中的一份回憶加以場所定位”。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更直言:“活著就是留下痕跡。”《三峽好人》(2006)在詩城奉節行將被淹沒之前攝制,記錄下真實的拆遷影像,以“空間副本”的方式給予見證、備份與記憶。反復出鏡的廢墟場所,恰以改寫的空間折射出時間的巨變,隱喻變遷中的社會風貌。《二十四城記》(2008)則將鏡頭對準從沈陽遷移至成都的420軍工廠——歷經1958年至2008年的半個世紀的歷史變遷,影片于工廠再搬遷之前,通過口述史的方式把即將退隱的工人精神和場所記憶留下。長鏡頭凝視下的廠房,以感傷填充了這將要完成意識形態交接的懸置場所,再度記錄下成長中的中國的歷史碎片。《郊區的鳥》(2018)同樣記錄下郊區的廢墟場所,喚醒城市變遷中幾近湮沒而難以復現的一份童年記憶。《風中有朵雨做的云》(2016)聚焦“城中村”這樣一個獨特場所,構筑荒誕的心靈景觀。場所記憶帶給人們的情緒色彩于此彰顯,迫使觀眾反思個體與時代、個體與城市的復雜關系。
三、身份追認:意義、共享的記憶與身份認同
關于身份的探討并不少,無論中外都是一種文化研究的落腳點。但新世紀藝術電影尤其值得關注。“身份”(Identity)是個體之于社會的自我意識與主體經驗,構成個體對其所屬社會群體組織的認知,以了悟個體與時代社會的相互關系,找到自身在某一群體中的歸屬感。記憶的文化內核指向個體的身份焦慮、價值迷失與身份追認。“記憶制造意義,意義鞏固記憶。意義始終是一個構建的東西,一個事后補充的意思。”“追認”即對記憶的追回與指認,獲得過往身份的自洽認同。“記憶空間”追認空間主體在流動時間中的價值,并訴諸于身份認同。旨在激活個體的身份記憶,回望那些值得記取的共享的記憶,從而化解精神危機,重新認識自我與社會的關系,并主動地接受集體記憶、文化記憶的重構。可以說,身份認同就是文化記憶之“動力結構”中的核心要素。
“記憶空間”的意義指向身份追認,并將此連接至當下。身份追認也意味著記憶的改造,我們經由共同的追憶來重新定義我們自己。“被回憶的過去永遠摻雜著對身份認同的設計,對當下的闡釋,以及對有效性的訴求。”新世紀藝術電影主動參與現代化轉型的文化探討,在當代的文化語境中激活人們共享的文化記憶,緩解轉型期的文化陣痛,重塑從個體至集體的身份認同。例如,《站臺》(2000)里,文工團的流浪藝人作為寥落的縣城青年,向往外面的世界,流浪演出是其逃脫現實局限的辦法。“崔明亮們”的文化身份仿佛是過渡性的存在,他們渴望從站臺出發,尋覓詩意的彼岸。面對轉型期縣城經驗中的空間焦慮,站臺空間成為他們通往“現代性”的身份寓言,站臺意象也將為一代觀眾所保留。又如,《地久天長》通過講述“記憶空間”下的兩家人的命運起伏,訴說無常悲劇的前因后果,喚起歷史命運下那些常人的甘苦記憶與善意和解,重獲記憶的撫慰,鑄就地久天長的心靈史詩。德國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認為社會意義上的空間本質是心靈空間,正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填充了空間并賦予以意義。影片正是借由一代人的記憶空間重建與心靈空間書寫,表達了人性救贖下的文化反思。最終樸素的相互和解更是時代心靈的顯現,人們得以尋回人生的向度。
“歷史是一個社會對過去的記憶,而記憶的作用取決于這個社會在何種情況下發現自我。”文化記憶不會自動地傳遞下去,只有立足于“記憶的社會框架”,讓藝術電影的記憶話語匯入更廣泛的公共領域,與觀眾展開文化協商、話語融匯與情感聯結,才能在身份認同的構建中發揮起作用。例如,《一秒鐘》(2020)將身份認同與“影院觀影”的文化記憶相融合,以張九聲承擔文化記憶的主體,并通過他帶著個體情感的追憶,呼喚出觀眾所共享的集體記憶。“記憶術借助的是想象出的空間,而回憶文化是在自然空間中加入符號,甚至可以說整個自然場景都可以成為文化記憶的媒介。”影片及時呼應“后疫情”下影院觀影的“文化危機”,讓“影院空間”再度成為人們情感共鳴與文化共享的“記憶空間”,激活觀眾記憶中的影院文化認同與電影情懷,重思人與電影的關系。也正因為當下的介入,才使這段封存的觀影記憶脫離原有語境,重新成為共享的記憶。
關于身份追認,哈布瓦赫如是說:“只要我們把自己置于特定的群體,接受這個群體的旨趣,優先考慮它的利益,或者采取它的思考方式和反思傾向,那么,我們就會把自己的記憶匯入這個群體的記憶。”《八月》(2016)便是通過少年的追憶來向父輩的記憶致敬,從長輩們的奮斗經歷中繼承記憶,獲取群體的身份認同,最終內化為自身記憶的組成。影片以少年的目光把握20世紀90年代的文化氛圍,敘事的心理結構還原了當年的時空氛圍與個體細節,比如黑白的影像構建起記憶的色彩,固定機位的搖鏡頭還原少年的孩童感知。“深謀遠慮制造了回憶空間,這些空間作為褶皺、空洞和疊層與事件的洪流相對抗,并且為推遲、反響、重復、重新連接和更新創造可能性。”張大磊導演并未強化電影制片廠這樣的特殊空間,而是構建起國營企業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樣的時代背景,著意書寫更具普遍性的工人階級的文化記憶,主動介入到歷史敘述的構建中,訴說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同構關系,從而實現了文化記憶的代際傳承。
四、結語
不必忌憚于我們建立在反思中國電影學派研究中的歷史經驗,去借鑒西方電影相關的文化理論來看待中國新世紀電影的一些藝術表達,恰恰是為了更好地來看清隨著中國融入世界,中國電影和世界電影之間更密切的關系,以及創作者更融合于普泛性的電影創作語言、文化思維的藝術精神表現。上述闡釋的文化研究的必要,不妨祭出斯蒂格勒的箴言:“第三持留是意識的代具。沒有這一代具,就不會有思想,不會有記憶的留存,不會有對未曾經歷的過去的記憶,不會有文化。”至此我們得以發現“記憶工業”在記憶維度、政治維度、文化維度上的可能與啟發,電影作為“第三記憶”正是通過記憶的“修訂”實踐著歷史的“重寫”,印證著記憶書寫的內在機制。然而記憶永遠變動不居,“文化記憶內部的動力機制,使它并不排斥變革和磋商”。誠如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之名句:“重要的是講述話語的時代”。“記憶空間”也必將在不斷地建構與重構中提升曾經的內容、形式與意義。“記憶不僅重構著過去,而且組織著當下和未來的經驗。”人們去往“記憶空間”的意向創造了歷史時間,也將鑄就未來的目標。
注釋:
① 可參考周星撰述:《建構中國電影學派:傳播視域中的概念探究與其適應性》,《現代傳播》,2017年第11期;《中國電影學派歷史梳理、命名概念與發展認知》,《藝術百家》,2018年第5期;《建構中國電影學派》,《中國電影批評年鑒2017》,中國電影出版社2018年版;《中國電影學派建設視野中的改革開放40年抒情傳統嬗變》,《藝苑》,2019年第1期;《中國電影學派體系的確立及其發展路徑——新中國電影70年宏觀透視》,《影博影響》,2019年第5期;《中國電影學派視域下“沉郁頓挫”的影像抒情審美》,《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5月21日。
⑤ [德]阿萊達·阿斯曼:《個體記憶、社會記憶、集體記憶與文化記憶》,陶東風編譯,《文化研究》(第42輯),2020年第3期,第54頁。
⑦ Marianne Hirsch.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Poetics Today,vol.29,no.1,2008.p.106.
⑨ 賈樟柯:《賈樟柯電影手記2008-2016》,萬佳歡編,臺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