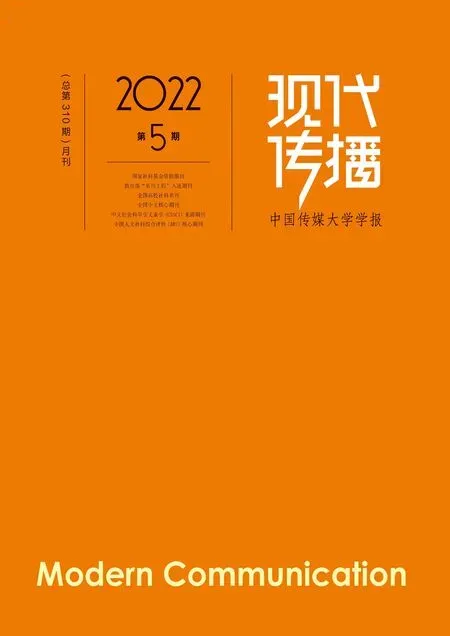短視頻展演的數字審美與情感邏輯*
——基于“非常規數據庫”的視角
—戰 迪—
“數據庫”(database)概念最早源于計算機領域,被定義為數據的結構化集合。由于研究人員以樹狀、網狀、關系和對象等不同方式來組織數據,數據庫自誕生之日起就以結構化而非整合化的形式來滿足對信息資料存取、檢索的需要。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迭代升級,傳統的靜態數據庫形式日益變化,人們對數據庫的理解觀念也不斷獲得更新。時代躍遷至數字媒體語境,“現實—媒體—數據—數據庫”這一既往局限于專業領域內的信息整理方式在技術賦權的加持下被重新定義。人們一般將數據與算法的關系理解為“被動—主動”的二元對立模式,然而,在短視頻資源野蠻生長的近年,我們清晰感受到這一新興數據庫形式正以某種非常規的形態呈現在世人面前。碎片化后的數字視聽地圖似乎遠比傳統影像地圖鋪展得更為寬廣,“長尾效應”催生的新媒體文化景觀已然超越了其原始文本的意義時空。不斷被索引、拼貼、合成的數據庫資源在高速刷新的數字平臺中被形塑為迥然有別的文化樣貌,構成了可以敘述的數據庫和情感豐饒的數據庫兩種交叉融合的技術文明。前者表征著當下的信息數據在看似無序的項目中以組合和聚合的方式創造敘事性因果邏輯;后者則意味著普羅大眾將操作友好的視頻編輯軟件作為通用的圖像生成器,批量化生產故事,建構私有化的情感經驗。因而,我們可以將當下的短視頻生產平臺命名為“非常規數據庫”(unconventional database)。
2016年9月以“音樂創作類短視頻社交軟件”為自我定位的“抖音”App自上線以來,就引發了學界關注的目光。隨著短視頻產業的火爆,越來越多的學者試圖探究其背后的成因。目前較為一致的觀點是:除了移動通訊速率提升、資費下降等客觀條件外,短視頻還激活了用戶自我呈現、表達的潛在欲望;填補了用戶碎片化時間和即時閱聽的心理需求;更為重要的是,短視頻因其模仿、復制的“迷因”(meme)特質形成了類似基因、病毒傳染的復制、傳播、變異規律,這一“數字迷因”(digital meme)令用戶欲罷不能。顯然,短視頻產品是后現代工業體系的產物。一般認為,后現代主義的顯在影響是促成了空間化(spatialization)而非時間化的文明。因而漠視時間、歷史扁平化、拒絕宏大敘述成為了這一文化的通識性標簽。而在眾多短視頻產品中,我們吊詭地發現,曾經被大眾文化擠壓在相當逼仄的展演地帶的美聲、民族歌唱和器樂演奏等嚴肅藝術形式以生活美學的形態重新復活在廣闊的短視頻時空中。廖昌永、郁鈞劍、王麗達、于海洋等老中青歌唱家的聲樂表演,郎朗、于紅梅、陳軍等演奏家的器樂表演收獲了較傳統媒體中更為廣泛而持久的關注,其點贊、轉發、評論量激增,眾多百萬粉絲的個人賬號集體性催生了短視頻用戶的“數據庫情結”。我們需要追問的是,緣何涇渭分明的各類藝術形式可以同時在短視頻平臺中獲得青睞?其表現形態與傳統媒體有何區別聯系?這些藝術展演又是以怎樣的生產機制促成用戶接受情感的凝聚呢?本文希圖結合人文社會學科“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背景下的相關理論和數字技術可供性(digital affordances)理論給予回應和闡發。
一、重復性、交互性與流動性——數字審美的公共性
在短視頻生態中,嚴肅藝術與通俗藝術雜糅并濟的現象不僅是此類數字信息推廣環節的“長尾效應”和傳播特性的“數字迷因”使然,更可以被視為線上線下數字糾纏(digital entan?gle)所帶來的公共審美事件。與其說作為數字文化物質載體的短視頻是一種物理媒介,毋寧說其心理媒介的特征更為明顯。藝術史學家莎琳德·克勞斯(Rosalind Krauss)就分析道:“視頻的真實媒介是一種心理狀況,是一種從外部對象——他者中撤回注意力,并轉而投注于自我的過程。”①作為一個“通用的圖像生成器”②,短視頻可以靈活、便捷地編輯視聽文本,并將其以彼此相似卻迥異的形態傳輸在數字平臺中獲得交互式體驗,從而激發用戶的心理參與熱情,搭建起全新的公共審美時空。例如從橫屏到豎屏的構圖之變,就頃刻間完成了敘事場景到肖像場景的觀念轉換,這在相當程度上改造了傳受雙方的認知關系。如果說在Web 1.0時代,社會網絡中“人—電腦—人”交往模式的本質仍舊是“人—人”的關系,那么在Web 2.0時代的今天,“個人—個人”的關系已經徹底蛻變為“情感人—情感人”的關系。③曾經居廟堂之高的嚴肅藝術下沉到數據文化廣場,文化名人在短視頻平臺中與普羅大眾展開傾情對話。顯然,短視頻社交平臺在傳播格局上直接促成了數字媒體環境下文化傳播的“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蛻變。
相較于傳統媒體,以短視頻為代表的數字媒體文化之“新”,顯然是技術生態革命的產物。數字技術憑借其信息生產可供性(produc?tion affordances)、社交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s)和移動可供性(mobile affordances)的賦能調和了“公共”和“藝術”之間的矛盾和悖論,使得古典主義、現代主義藝術形式走進了當代藝術和后現代藝術的生產語境,并產生了某種結構化變異,回歸于生活美學的新路。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將技術歸納為四種類型:生產技術使我們能生產、轉換或操縱事物;符號系統技術使我們能夠運用符號、意義、象征物,或者意指活動;權力技術決定個體的行為,并使他們屈從于某種特定的目的或支配,使主體客體化;自我技術則使個體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幫助,進行一系列對自身身體及靈魂、思想、行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達成自我的轉變,以求獲得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④可以想見,短視頻生產中的交互式傳播方式大大激活了當代人藉由自我技術的完善所構建的視聽意象生產和消費行為,為公共審美的形成注入了強大的操控能量。那么,短視頻平臺這一“非常規數據庫”具體是如何打通傳統與現代、精英與大眾的審美區隔,為各類型藝術的展演搭建起數字平臺的呢?我們不妨從重復性、交互性和流動性三方面著眼加以辨析。
第一,數字網絡的算法推薦在迎合用戶既有興趣的基礎上,總是嘗試推薦新穎的視聽內容,一旦新的視聽內容被用戶接納,那么相關信息就會接踵而至,變換方式重復強化,令用戶的文化視域得以拓展,閱聽趣味和情感“破繭重生”。例如2021年春節聯歡晚會中廣受歡迎的歌曲《燈火里的中國》經張也、周深演繹后,在短視頻平臺中被廣泛傳播,相關效仿、改編的作品紛紛涌現,以至于原始文本中的旋律“魔性”地縈繞在用戶的數字終端,讓人欲罷不能。與簡單、刻板的重復不同,這種重復是視聽改造后的重復,無論是橫屏到豎屏的剪裁,還是演唱者到教學者、翻唱者的轉變,用戶總是在一種“熟悉的陌生感”中反復賞鑒、互動,最終在心理層面構成了一種習慣性認知框架,催生出情感認同(emotional identity)。每一段藝術展演的短視頻內容都是場景化改造后的具體形式和內容,為竭力達成對用戶的勸服效果,諸多作品以或奇觀化或生活化的心理意象來激活圖像認知的情感反應(emotional response),進而實現用戶視聽思維的情感轉移(the transfer of emotion)。可以說,短視頻重復性生產和建構的視聽意象“不僅意味著對情感本身的具體化表達,而且被賦予了額外的勸服權重(persuasive weight)”⑤。從這個意義上講,短視頻對文藝文本的策略性重復依托某種情感意象承擔起用戶視覺和聽覺的組織者角色,協助用戶確立起認知、感受和行動相一致的自我意識。
第二,交互性作為數字視聽媒體有別于傳統媒體的重要信息傳播特征,賦予了用戶參與式生產的可能。看似隨意的評論、點贊、轉發背后,卻潛藏著用戶與表演者之間微妙的互動關系。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就認為,交流與互動可以消除語義之霧,幫助人們從自我設定的堡壘中突圍,有效揭示他者的特性,并協調彼此之間的行動。⑥在大眾文化的長久浸淫下,當下很多人認為自己已經難以和嚴肅藝術形成心靈對話的默契。但在短視頻平臺中,人們偶發性地被唯美的嚴肅音樂片段震撼和感染,在獵奇性心理的催促下,不斷滑動的指尖稍作停留,短暫地欣賞,并在評論區發表留言,同視頻作者和其他用戶展開探討,這無形中激發了他們沖破藝術類型藩籬的沖動,從自發到自覺,積極參與到相關短視頻的情感賞鑒中來。“抖音”平臺中二胡演奏家高韶青2016年在加拿大總督就職典禮上二胡演奏《戰馬奔騰》的視頻震撼人心,時至今日該影像仍然在短視頻平臺廣為傳播,獲贊超百萬。而青年民歌演唱家于海洋在琴房教導業余學員的短視頻同樣贏得超高人氣。視頻評論區中,學員的資質遭到不少網友的炮轟,于海洋則親自置頂回復網友:“孩子剛剛變完聲,年紀還小,需要更多的鼓勵,請各位留言得饒人處且饒人。”簡短的一席話不僅瞬間化解了尷尬,更彰顯了青年藝術家宅心仁厚的品格。于海洋贏得網友集體性情感支持的同時,也在無形中完成了其與網友情感、態度、行動的協調一致。事實上,在短視頻藝術展演的交互實踐中,其凸顯了社會化互動中的日常性表演特質,打通了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其“擬劇理論”中所提出的前后臺之分,從而重建了表演者的“人設”。作為情感共鳴、社會信任、社會資本的基礎,短視頻中表演者的“人設”是自我與他者基于展演情境和網絡情境“合塑”的結果。短視頻空間的虛擬性賦予了表演活動以更為豐富的手段和技法,也為表演者的“自我呈現”“印象管理”提供了有效渠道。可以想見,交互性展演中的情感認同之所以具有優先性特點,就在于其“作為一種直接的自我意識,超越于理論認知和實踐行動中主客、物我、身心的二元區分和對立”⑦,最大程度上營造出傳受雙方的深度關聯。
第三,短視頻媒體是以液化而非固化的傳播形態呈現在公眾視野中的。任意敲擊、滑動的指尖在海量視聽文本中輕松行使著選取、關注、刪除、鏈接的權力。如果說傳統影視的本質是以物質形式記錄和存儲的可視化數據,那么以短視頻為代表的數字媒體則不再被簡單理解為數據處理的分析機,它更像是19世紀的雅卡爾提花機,儼然成為了泛媒環境中的數據合成者乃至操控者,勾勒出一幅幅流動的現代性圖景。帶有節點化、鏈接化色彩的短視頻盡管易于斷裂、易于取消,其“游戲規則的生命不會超過游戲進行的時間,有時甚至還短于游戲進行的時間”⑧,但這種流動性卻賦予了用戶個體選擇與轉換文化趣味、身份、組織的靈活性與便捷性。流動的視聽信息促成了“脫嵌”(disembed?ing)的實現,文化主體可以從固有的時空條件和認知慣性的套嵌關聯中解脫,尋求新的歸屬可能。此時,深邃、典雅,且情感豐盈的嚴肅藝術被人們寄予了“臨時避難所”式的期待,成為了超然于社會現實的數字“烏托邦”。人們不必仰望,亦無須凝視,只需略一凝神,就可能收獲瞬間的情感提純、凈化,以及精神庇護。此時,人們已經忽略了自己在現實世界中的身份、等級和存在狀態,下意識地被嚴肅藝術喚醒了自立、自主的選擇意識,主動感受內心深處的自我意識,并建構起相應的情感認同心理。
二、藝術檔案的結構化與反結構化實踐——日常情感的激活
棲身于“非常規數據庫”的短視頻應用程序中的藝術展演并非以雷同于傳統媒體的表現形式出場。用戶發布的視頻內容多體現為生活美學的多元樣貌。具體來說,系列作品中既有舞臺展演的再編輯,也包括藝術家臺前幕后的彩排花絮、教學片段、社交活動、生活趣聞,以及利用應用程序自設的特效、合拍等內容,因而形構為生活美學的數字路標。所謂生活美學,并非歐美文藝學理論中所指稱的“日常生活審美化”和“日常生活美學”,而是介于“日常性”與“非日常性”之間的一種美學新構。正如該美學理論的倡導者劉悅笛所言:“生活美學既認定美與日常生活的連續性,又認為美具有非日常生活的另一面。”⑨
生活美學的興起是對全球化、數字化浪潮最新動向的直接回應。當下媒介化社會中新穎的審美要素琳瑯滿目、層出不窮,廣泛蔓延在社會文化生活的每一處角落。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藝術家們試圖突破審美類型和等級的桎梏,致力于打破藝術與非藝術的邊界。因而曾經作為古典主義美學基本內在法則的“審美非功利性”和“藝術自律論”遭到激烈的挑戰和解構。大膽走出“文化神圣化”藩籬的藝術家們對其個體的文化身份、展演場景和表達方式都進行了重估與重認,刷新了因循已久的觀念系統。特別是在數字媒體語境下,創作者有意以實用的生活審美取代非功利性審美,以“有目的的無目的論”取代“無目的的合目的論”,以“日常生活經驗的連續體”取代“審美經驗的孤立主義”。⑩上述觀念反映在短視頻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創作者在PUGC技術理念的帶動下,游走于生活、藝術、產業的交接地帶,尋求創作突圍。頻繁現身于“抖音”數據庫中的著名歌唱家廖昌永不僅以碎片化形態展示其宏大的演唱片段,還上傳了青年求學時代恩師周小燕先生對他輔導、點評的歷史記憶影像。此外,廖昌永同女兒在吉他伴奏下合唱的場景、同大學生互動教學的畫面、同年輕藝術家彩排交流的影像以充滿感性色彩的展演形態捕獲了眾多視頻用戶的注意力資源。類似的系列短視頻創作不僅與儒家文化“禮樂相濟”的精神傳統相得益彰,更包孕著“以美啟真”“以美儲善”的開放性審美情感邏輯。
如果僅僅從碎片化、快節奏、流動性的生活情感與嚴謹、整飭的藝術展演相結合的視角來揣摩短視頻生產中“生活美學”的品格尚顯得簡單而機械,那么,將短視頻藝術展演視為一個信息存儲豐富的數據檔案庫,進而考察其內外部的結構化與反結構化運作機理,似乎對該問題的解析更具闡釋效能。
對人類文化作用機制中結構化與反結構化的探索在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世俗時代》一書中有著詳實的闡述。從宗教時代到世俗時代,結構與反結構的張力始終存在。結構化代表著來自社會觀念系統中的秩序與規訓,反結構化則表征著來自人們內心深處反秩序與反規訓的潛意識沖動。媒介化社會中,如果說傳統媒體中的“儀式傳播”(rites communication)是結構化的,那么短視頻社交媒體中的娛樂化、狂歡化內容則是反結構化的。人們對反結構化內容的需求本質上是公共空間世俗化的結果。正如泰勒所提出的“氣孔”(安全閥)理論,“社會需要這樣的臨時許可,允許因日常生活的壓抑而積累的‘氣’釋放掉,為的是煥然一新地回到標準的規則”。維克多·特納(Victor Witter Turn?er)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社會思想文化的平衡是動態發展的,嚴格意義上的平衡本不存在。人們需要秩序來維持安全與穩定,但基本的欲望也必須得到宣泄與釋放。社群結構化的秩序需要定期追溯其反結構之根,反結構力量的失落反而會令社會文化中緊繃的發條斷裂。宗教社會延續至今的狂歡節具有時機性和多層次性特點,恰恰是反結構話語價值的絕佳例證。
現代社會是一種高度秩序化、結構化的運行系統,體制的、法律的、道德的、倫理的法則框架保證著社會發展的有序運轉。家庭與工作、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涇渭分明。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常常感到單調、乏味甚至窒息。此時人們對時間的把握格外嚴謹,閑暇時間被切割為一個個碎片。正是在這樣的心理時空中,美國學者克萊·舍基(Clay Shirky)提出了“認知盈余”的概念,他把全世界所有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時間看作是一個集合體,也就是一種“認知盈余”。“我們可以把自由時間當作一種普遍的社會資產,用于大型的共同創造的項目,而不是一組僅供個人消磨的一連串時間。”可以說,短視頻中風靡的類型化的藝術展演正是認知盈余的“觸發器”,藝術家及其擁躉憑借著共通的情感資源和興趣愛好將儀式化色彩熾烈的嚴肅展演解構、重構為帶有生活美學氣象的數字藝術檔案,在傳播、分享的過程中竭力調和著用戶的“認知儲備”,甚至在不經意間發掘出用戶既往不曾意識到的盈余趣味,進而開發他們并不自知的審美潛能。在這其中,短視頻制作、發布、分享中的開放性、對等性、共享性特質發揮著巨大的能動作用,人機耦合的藝術體驗既滿足了當代人在后現代文明慣性中的認知框架,也在不斷探索著不同類型藝術形式在數字媒體時空中的“續航”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于通俗、流行藝術,嚴肅藝術的短視頻推廣需要相當程度的用戶黏性和社群共同體的應援。因而,社群規模、共享成本、共同趣味的凝聚就成為了創作者們急需面對的創作議題。某種意義上講,粉絲共同體所營造的網絡社會資本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短視頻藝術展演中粉絲共同體的情感認同及其催生的自豪感激勵著創作者不斷發揮想象力、創造力,將藝術家IP形象極力放大、拓展。在近年來的創作經驗中我們可以發現,藝術家精深造詣的結構化力量與其日常生活中宣泄、狂歡、戲謔意味相結合的反結構化力量共同作用于粉絲共同體,激活了他們的日常情感,迎合并型塑他們的欣賞品味。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網絡社會資本的粉絲共同體,他們個體間結構化連接的緊密程度、彼此間關系的強弱程度、相近或相通的知識背景、話語習慣、表達方式,都對短視頻產品傳播效果的實現具有現實意義。此外,藝術家本人的聲譽、信用、魅力等也最終決定著其受關注度能否可持續推進。正如彭蘭教授所言:“平臺如果能在機制上促進個人社會資本的獲得與積累,那么,個體參與共同體建設的積極性也會提高。”
三、世俗時間、更高時間、起源時間——情感公眾的主體性建構
不難發現,短視頻平臺中的藝術展演除極特殊情況下以直播形式進行同步性實時互動外,大多數時候是在傳授雙方時空分離的異步狀態下完成敘事的。就此而言,短視頻生產對敘述時間的把握與傳統媒體中的非直播時間異常相似。所不同的是,傳統視聽媒體的藝術生產始終局限于權威化的封閉性生產時空,呈現給公眾帶有“完成時”特征的藝術作品,而數字媒體的參與式生產則使得藝術展演演化為開放式、進行時的文化交流狀態。藝術賞鑒者因而可以在內容尊享和環境私密的雙重擔保下突破物理時間限制而在虛擬時間中任意穿梭,恣意放縱個人化的情感和直覺。
關于時間命題的拷問始終是文藝哲學的重要思考對象。除我們慣常理解的物理時間、心理時間和蒙太奇時間外,時間的先驗性和感知性早已被知識界反復探討。康德(Immanuel Kant)就將時間作為現象學的基本圖示來看待。湯普森(Garrett Thomson)進而總結認為:“時間是感性的先天形式,它既是先天的,又是可感知的。”尤其需要關注的是,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深挖的世俗時間、更高時間和起源時間對短視頻生產中情感公眾主體性建構的思考具有更為顯著的啟發意義。這里的“世俗時間”(secular time)與本雅明(Benjamin)所言的均質的(homogeneous)、空洞的現代性時間(empty time)相仿,它是日常性的,周而復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更高時間”(higher time)是匯聚和凝固在歷史記憶中永恒不變的時間段落,之所以“更高”,因為它是“真正實在的、完滿的存在(being),是在時間之外,永不改變”;與前兩種時間概念不同,“起源時間”(time of origins)并不是哲學家和神學家的通用術語,而歸屬于民間大眾傳統。起源時間“與日常時間中的當前時刻復雜地聯系在一起,這是因為它可以經常性地通過禮儀而抵達,而其力量也一再被化用于某些特權時刻”。
不難想見,短視頻藝術展演中的時間構造來源于均質、空洞的“日常時間”,卻被創作者重新提煉打磨。那些承載著厚重歷史記憶和文化記憶的影像數據無疑是“更高時間”的索引和注腳,而采集、編輯于宏大敘事場景中的豎屏視頻更可以被我們視為短視頻平臺中對儀式化“起源時間”的社交媒體改造。當然,人們潛意識中對“起源時間”的重新構想和把握并不局限于嚴肅的影像素材,也廣泛涉獵和攜取帶有狂歡、戲謔、惡搞意味的綜藝素材。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某種獨特的社會想象,平臺設計者有意研發出“合拍”應用程序,通過該程序,普通藝術愛好者也可以在形式上與偶像無限接近,以“同框”形態合作完成一件藝術作品,并將該作品發布在個人的短視頻空間,與其他用戶分享。事實上,這一操作方式在最大程度上實現了對粉絲的情感動員,在時間認知觀念上促成了步調一致的同步性,使粉絲個人在心理層面追溯、重訪,甚至抵達“更高時間”,在實踐層面積極融入“起源時間”的建設。
很明顯的是,數字媒體技術的發展令我們對時間的理解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換。文藝等級制的分野伴隨著人們對時間觀念的深化而改變。每一個時間片段都可能是獨特而富有意義的。現在的拼貼、混仿、狂歡、惡搞在稍縱即逝后也會自然而然地回歸秩序化的時間軌道。我們無法改變線性化世俗時間的靜水流深、秩序井然,但我們卻儼然擁有了短暫躋身于專屬的私人定制的個性化時間的能力感。從這個意義上講,曾經的個人化情感派生于現實生活中環環相扣的社會秩序,而當下的情感則是數字化時間中個人意志的激活與張揚。此時,笛卡爾時代的身心二元論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現實基礎,而因身體與身體、身體與物質、身體與環境、身體與媒介的觸碰和感知所引發的情感體驗被無限放大,情感公眾的主體性被搭建成型。
從非常規數據庫的視角出發,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短視頻數據庫的操縱者和剪輯師,他們不僅可以創建一個特定的時間序列進行自主敘事,也可以大膽棄用令自己興味索然的數據庫資源,“一個一個地將許多層看似同時發生的循環動作呈現出來,將大量獨立卻共存的時間展現出來”。此時的用戶不僅是在編制時間,更是在重新洗牌。藝術展演的短視頻創作者往往通過沖突框架(conflict frame)、情感故事框架(human interest frame)來強化傳播文本的可感性,規劃著用戶關于文藝作品賞鑒的公共議題的情感維度。而用戶卻并不被動,他們在“接觸—選擇—遺忘—重復”的時間認知鏈條中與創作者展開意義協商的爭霸賽。
無可否認的是,短視頻中的藝術展演仍舊是一種流動的“開源代碼”和既有藝術形式的宣推產品,我們無法將其視為一種嶄新的藝術類型,更難于準確預判其未來走向,因而任何一種盲目樂觀的態度都是短視、武斷的。真正需要創作者深度探索的理應是從情感勞動到情感演繹的藝術蛻變。
注釋:
① Krauss,R.Video:The Aesthetics of Narcissism.In J.Hanhardt(Ed.),Video Culture.Rochester:Visual Studies Workshop.1987.p.184.
② Frank Dietrich,Visual Intelligence:The First Decadeof Computer Art(1965-1975).IEEE Computer Graphics and Applications.vol.19,no.2,1985.p.39.
③ 童星、羅軍:《網絡社會及其對經典社會學理論的挑戰》,《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第99頁。
④ [法]米歇爾·福柯:《自我技術:福柯文選Ⅲ》,汪民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3-54頁。
⑤ Hill,C.A.The Psychology of Rhetorical Images.In C.A.Hill&M.Helmers(Eds.),Defining Visual Rhetorics,New York: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4.pp.25-40.
⑥ [美]約翰·彼得斯:《對空言說:傳播的觀念史》,鄧建國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頁。
⑦ 聞駿:《情感與意識:施萊爾馬赫教義哲學思想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51頁。
⑧ [英]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頁。
⑨⑩ 劉悅笛:《審美即生活》,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12、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