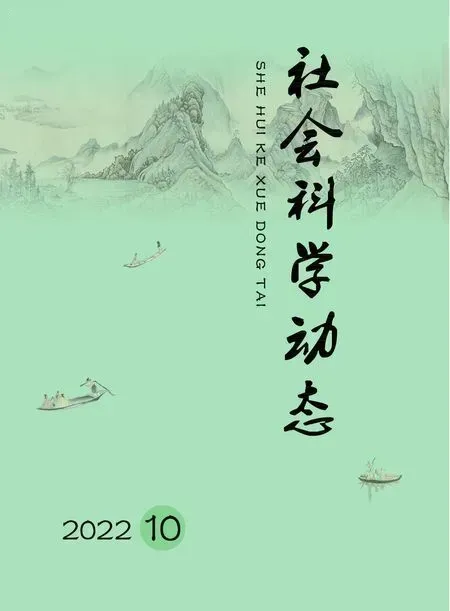文化人類學視角的“還原”與再創造
——陳欣《借鑒與傳承——聞一多的文化闡釋批評研究》解讀
胡 敏
聞一多先生離世已80 余年,國內有關聞一多的研究,雖可稱汗牛充棟,但更多地集中在聞一多作為詩人和民主斗士的一面,而對于聞一多學術文化遺產的研究方面相對較少。原因為何?許祖華教授在《借鑒與傳承——聞一多的文化闡釋批評研究》 (以下簡稱《聞一多的文化闡釋批評研究》) 一書的序言中指出:“研究者本人不僅需要具備中國古代典籍的知識,而且需要相應的理論與方法作為研究展開的支撐……更何況,即使具備了這兩個方面的條件,還存在著一個理論、方法與對象契合的問題需要解決。” 可以說,陳欣博士的這本新著,正是知其難為而故意“為之”,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幾易其稿而成,為聞一多研究開辟了新的領域,擴展了新的視野。
聞一多 (1899—1946),原名聞驊,號友三,生于湖北浠水。聞一多一生興趣廣泛、研究內容豐富而多變:早年放棄美術而致力于新詩,是新月派代表詩人和學者,出版過新詩集《紅燭》 《死水》;系統研究過新詩格律化理論,出版過《律詩底研究》 《詩的格律》;中年又放下新詩專心于古籍,成就更為斐然,從《唐詩》 到《詩經》 《楚辭》,均有扎實的研究成果。聞一多舉凡傳記、札記、史料、年表,均有涉獵,既廣且專,尤其是治學態度之嚴謹,令人佩服。更難能可貴的是,聞一多的治學視角,在民國時期甚至用當今的眼光看來都是相當前衛的,其風格多變而大膽。他撰寫的《詩經性欲觀》,在當時的文壇不啻投下一顆思想的原子彈,這使得其典籍觀理應成為學界研究的重要目標。《聞一多的文化闡釋批評研究》就是在這種理念指導下催生的。
該著的核心內容有三:
(一) 探討聞一多文化闡釋批評方法的特點——“還原”。作者認為,聞一多對古典文學的闡釋是跨文化基礎上的闡釋,是一種綜合性的學科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涉及田野考察、考古工作、語義鉤沉、古籍破譯等多角度、跨學科視角,是一種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化闡釋批評方法。該書從聞一多的訓詁闡釋方法入手進行研究,指出聞一多在其學術研究中,始終堅持從文字的訓詁和考據入手,解釋古代典籍的字面意思;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揭示詩歌的象征意義,從更深的文化層面上闡釋詩歌的內涵,力求還原古代初民的真實生活和思想意識狀況。其中,訓詁和考據并非最終目的,僅是手段;闡釋詩歌字句的象征意蘊和審美意象,揭示《詩經》豐富的社會內涵和當時鮮活而生動的生活狀態,才是批評的真正目的。其本質正是文化闡釋批評。遺憾的是,當時因城市生活和戰亂的影響,聞一多沒有條件進行充分的田野調查。但這些并不影響他作為文化闡釋批評研究的先行者。
(二) 探討聞一多的學術思路和研究方法——跨學科、多角度。聞一多在《詩經》 《楚辭》、原始巫術、圖騰崇拜和中國神話等研究領域的開創性貢獻毋庸置疑。對其研究加以總結,探討其依據深厚的國學功底,借鑒西方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取得現代學術成果的經驗,顯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在這一方面,作者顯示了系統的文化人類學知識。由于作者熟悉聞一多的古代文化研究全貌,且具備良好的文字學、古典文獻學的功底,所論各節皆能落到實處,時見精當評述,彰顯了其開闊的學術眼光和樸素的治學態度。例如,作者將聞一多對古代典籍中象征意象的揭示進行歸納總結,認為聞一多《說魚》的大量論證,是揭示了“魚”的隱語和象征意蘊,說明情欲的饑渴和飲食的饑渴的相同之處,還原了古代人類粗獷豪放的民風和對于“性”的真實態度。作者強調,古代人類“萬物有靈”的“以己度物”視角,是聞一多對訓詁學的創造性運用,是中國文學研究前所未有的、至今仍少人使用的研究方法。作者從文化闡釋批評的角度進行的上述研究,進一步證實了聞一多學術研究的深刻性和正確性。凡此種種的論述,不乏真知灼見。該書通過對《詩經》 《楚辭》 的訓詁闡釋,發現其中大量隱喻性的象征意象,由此進入聞一多所還原的古代社會生活中,探尋聞一多是如何揭示古代人類的象征性思維方式、原始巫術心理和原始圖騰心理,還原詩經時代的性欲觀為“自由放任”,從而揭示出古代人類對于生殖、生產的重視和渴望,其生殖崇拜的真相以及蓬勃的生命力量。
(三) 探討聞一多學術研究的審美批評特點——“詩性”。聞一多在進行文學審美批評活動時,最大的特點就是詩性批評,這也是中國文學批評的重要傳統。詩性批評是一種通過對事物形象性、情感性的熔鑄,以象征、比喻的言說方式,表達批評家對文本的內心感受和體驗的主觀印象。詩性批評的核心是體驗性、感悟性、主觀性,表達的模糊性、多義性;通過這種批評方式,令文化籠罩了文學,文學穿透了文化。作者在最后一章提出“聞一多的詩性批評”命題,試圖把聞一多的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歸結到“詩性批評”的范疇中去,從而使論述具有更強的整體感,并使全書具備了一種開放的意義空間。
《聞一多的文化闡釋批評研究》一書在學術上的貢獻主要在于:
其一,對聞一多的學術研究深入發掘和思考,探討其所以能獲得新見的原因,助力聞一多研究向多方面、多角度發展,拓寬了聞一多研究的學術視野。
20 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包括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建設。過去,研究者的重點一般放在創作上,以作家作品、時代為中心展開研究;相對較為忽視對文學批評觀念與方法論的研究,也缺乏對文學理論的總結和創新性分析。而該著實際上,該書立足于維柯“還原”、即“追本溯源”的文化人類學研究視角,將聞一多的文化闡釋批評貫穿于聞一多的學術研究中,尤其是對《詩經》《楚辭》和中國神話傳說的文化還原,實現了對聞一多學術研究的再研究、深入發掘和思考。
其二,作者運用開闊的跨學科、多角度的理論視野,從文化闡釋批評的獨特角度切入,探討聞一多現代學術研究的經驗,為此領域的當今研究提供理論與方法的借鑒。
作者將聞一多的典籍研究思想予以了較為準確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其“創造性地運用了文化闡釋批評方法”,“大量運用神話學、民俗學、民族學、考古學、美學以及心理學等方面的綜合知識來透視中國古代文學現象,將《詩經》、《楚辭》、神話傳說等納入研究視野,尋找潛藏于、凝聚在文學作品中的蛛絲馬跡,力圖還原那個時代的世界觀、人生觀、宗教信仰和民俗”,“把清代樸學的實證方法和西方人類文化學、社會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加以結合,形成了其獨特的文化闡釋批評方法”。
聞一多的典籍研究著述既富、類別亦廣。對聞一多研究方法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同樣具有獨特、寬廣的跨學科綜合性視野。這對于青年學者來說是不易的。作者以“文化闡釋批評”的視角,從研究中國古代典籍最根本的“訓詁學”進入聞一多研究思想的核心陣地,繼而從原始思維、原始巫術、原始圖騰崇拜、神話研究、生命觀五個大類進行剖析,探尋聞一多研究古代典籍的方法,揭示出古代人類思維方式的三大特點——象征性、情感性、想象性,盡可能“還原”古代人類的生活情境,最后以“詩性批評”進行歸納總結,從中提煉和梳理出聞一多文學審美批評活動的詩性特點。
其三,探討聞一多是如何還原古代人類的思維習慣、心理趨向,其研究方法對現代學術研究具有啟迪和開創性的作用,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更為博大的視野,以及多元化、多層次、多角度的研究方法。
文學是認知世界、表達個人態度、情感、思維存在的方式,文學表達的內容涉及全部的文化現象。不同民族文化決定不同民族的文學形態。通過文學,可以看到這個民族的文化特征。從文學史上看,聞一多是中國現代文學誕生以來,以及中國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第一個用文化的視野與訓詁學視角,兼及從民俗、風俗的角度研究古代典籍的典范。不僅揭示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或被遮蔽的“概念”“意識”“意義”,還原了某些生活現狀,從某種程度給我們揭示了一個相對真實的《詩經》 《楚辭》的“文化生態”原貌。
文化闡釋批評是跨學科的批評,這種研究方法具備多角度視野,能打通古今、打通相關學科知識,更接近于事物的本真。作者認為,聞一多的學術研究方法強調回到古代人類的生活現場,在古代典籍、史料、田野調查中還原古代人類的思維方式和生存狀態,這種研究立場無疑會對后代學者的學術研究有所啟迪。如當代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就是以考古調查發掘為獲取相關資料的主要手段,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采取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只有當我們更加了解自己,了解中華文明的本源,了解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人文底蘊,才能更好地實現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該著將聞一多的文化闡釋批評貫穿到對聞一多的學術研究中,尤其是對《詩經》 《楚辭》和中國神話傳說的文化還原,實現了對聞一多學術研究的再研究,其研究方法對現代學術研究具有啟迪和開創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