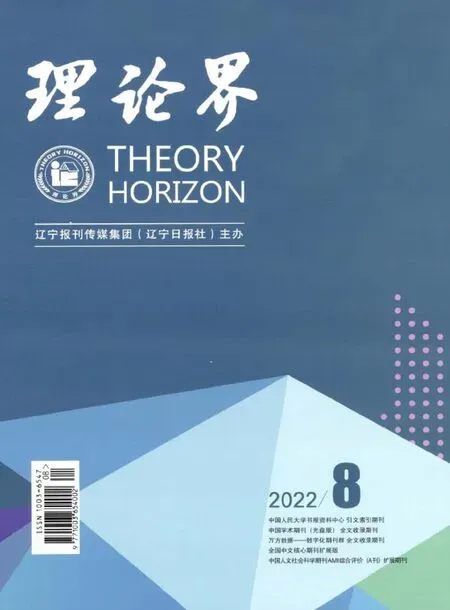論周敦頤“太極”和“誠”關系的二重性及其邏輯展開
袁傳志
一、差異與統一——“太極”與“誠”關系總論
《太極圖說》與《通書》是周敦頤哲學思想的核心文本。在《太極圖說》中,周敦頤構建了一個由“太極”動、靜而生陰陽,然后生五行、萬物的宇宙生成世界。在《通書》中,周敦頤又集中闡釋了“誠”所具有的本體意義。對“太極”和“誠”兩個概念的考察,是研究周敦頤哲學思想不可繞過的問題。然而,就“太極”與“誠”的關系和區別而言,二者之間具有復雜性。如楊國榮所言:“在周敦頤那里,存在的考察與宇宙論難分難解地糾纏在一起。”〔1〕對周敦頤存在論和宇宙論的考察主要圍繞“太極”和“誠”兩個概念展開,這一復雜性在于:一方面,作為宇宙生成本原的“太極”,同時內涵萬物本體的意義;另一方面,就周敦頤的本體論建構而言,“太極”與“誠”均具有本體的意義。圍繞這一問題,文章嘗試對“太極”與“誠”的關系進行梳理,分析其中的復雜性,并闡明這兩個概念關系的不同維度。
在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和《通書》兩部主要文本中,“太極”與“誠”并未同時出現在同一個章節中,但邏輯上,二者的關系密不可分,且有所區分。既往的許多學者在詮釋周敦頤時,較少能夠注意到這點,如陳郁夫在《周敦頤》〔2〕中將“太極”和“誠”分列兩章,并未注意到二者之間的聯系與區別,傾向于將“太極”和“誠”作為兩個獨立的概念進行分別研究,忽略了對二者一致性和差異性的考察。諸多學者意識到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系問題,如梁紹輝認為:“‘無極’是周敦頤宇宙生成的基本思想,他的《太極圖說》以‘無極’立意。‘誠’是他道德、修養的基本思想,整部《通書》以‘誠’立意。”〔3〕并認為“萬物在資元氣以生的同時具有了‘誠’的屬性”。〔4〕在此梁紹輝以“無極”而非“太極”為宇宙論核心,就周敦頤的思想而言,無論以“太極”還是以“無極”為宇宙起點,本原起點的存在毋庸置疑,唯一本原的存在是肯定的。(文章懸置二者差異,認為“無極”和“太極”等同,“無極”即“太極”)因此,梁紹輝認為“誠”作為一種屬性生成于萬物的元氣資生過程中,在某種程度上注意到了“誠”的生成過程,但是梁紹輝只認為“無極(太極)”為本原,而忽略了“無極(太極)”所具有的本體意義,未能全面論述“太極”和“誠”之間的關系。
楊柱才從“太極”和“誠”的統一性維度詮釋二者的關系,并以“太極—誠”的形式來概括周敦頤的本體論思想,他認為:“就客觀世界和意義世界的一體連貫而言,誠和太極是同質、同體并同用的”。〔5〕楊立華贊同此種觀點并認為:“誠和太極在實體這個層面上是完全一致的……不僅在體上一致,用上也完全一致”。〔6〕楊柱才“太極—誠”的表述無疑注意到了“太極”和“誠”之間的一致性,即“太極”和“誠”都具有本體意義,都可以作為世界的本體而呈現。然而,結合周敦頤的文本,可以看出“太極”和“誠”之間具有一致性的同時,亦存在重要的區分,二者雖然都具有本體意義,但是指向不同的維度。因此,“太極”和“誠”之間不僅具有一致性維度,而且具有差異性維度,這兩層維度是本文要分析解決的重點問題。
鄭熊意識到了周敦頤從“無極(太極)”到“誠”存在本體論維度上的思想轉變,并對這一轉變進行了分析。但是他卻將“無極(太極)”和“誠”之間的關系割裂開來,認為:“無極”是周敦頤早期思想中不成熟的理論,故而存在混亂,而“誠”本體是周敦頤拋棄了“無極”本體另外建構的。〔7〕這一觀點有待商榷,周敦頤的“太極”和“誠”之間的確具有差異性,但并不割裂,二者應當建立在如楊柱才所言統一性的基礎上,再進行區分。因此,無論是絕對的統一還是割裂的差異,都無法準確把握“太極”和“誠”之間的關系,就二者的統一性和差異性而言,文章認為:一方面,就“太極”和“誠”的聯系來看,這兩個概念共同具有本體論的維度;從生成論的角度來看,“誠”生成于宇宙論意義的“太極”。另一方面,就二者的區分來看,“太極”之本體意義指向“萬物”之本然世界的本體,“誠”之本體意義指向“萬事”之意義世界的價值本體。這兩層維度分別代表了“天人合一”的兩種不同思路,亦是周敦頤哲學作為理學開山承上啟下的重要理論依據,以下詳述之。
二、本原與本體之辨與“太極”的二層維度
對“太極”和“誠”的關系進行探究,需要對這兩個概念分別進行分析,由此可梳理概念內部的不同維度,有助于對二者的關系展開論述。本節對“太極”的概念進行梳理。對于“太極”的分析,需要對“本原”與“本體”兩個概念進行探討,這是“太極”內涵的兩層維度。通俗而言,宇宙的“本原”與宇宙生成論的觀點相涉,宇宙的生成是由“本原”這一質料演化而成,“太極”動、靜而生陰陽萬物直接展現了“太極”作為生成本原的特征。萬物之“本體”與本體論的觀點相涉,“本體”是宇宙萬物的本質、原動力,朱熹哲學中的“理”便具有此種含義。具體來講,“本原”與“本體”兩個概念有著更深層次的內涵。首先,對于“本體”而言,在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間,在中國哲學的不同文本之間,“本體”均具有不同的含義。從中西比較哲學的角度看,西方哲學的本體論即ontology,指向對存在、系動詞being的考察。而中國哲學的本體論與西方哲學的ontology相比,一方面具有相似之處:“ontology曾被譯為‘本體論’”。〔8〕另一方面中國哲學的本體論亦具有獨特內涵。諸多學者對中國哲學本體論的獨特性進行了考察,有助于對“本原”和“本體”內涵的理解。
方朝暉從中國哲學的角度出發將對“本體”的考察區分為“體用義本體、宗教義本體、哲學義本體”三種模式。“體用義本體”即建立在中國傳統哲學體用論基礎上,與“用”相對的“體”,指向事物本來的樣子,固有存在。“宗教義本體”即中國古代宇宙論意義上的宇宙本原和萬物本體,強調對本體概念的預設和頓悟。“哲學義本體”即西方哲學追求理性分析和邏輯思辨的ontology。〔9〕可以看出,作為周敦頤“太極圖說”核心概念的“太極”指向第二種“宗教義本體”的維度,即“太極”作為宇宙論意義上的宇宙本原和萬物本體而呈現。而宇宙本原和萬物本體則指向兩種建構世界之本的方式。二者之間雖然具有“強調對本體概念的預設和頓悟”的共同特征,但是亦存在明顯的區分。
對于“本原”的考察,可放在對“宇宙本原”和“萬物本體”這兩種探究世界本質不同方式的區分中進行。丁為祥從“宇宙本體論”和“本體宇宙論”兩個角度進行了梳理,有助于理清作為“本原”的太極和作為“本體”的太極之間的區別。一方面,丁為祥認為:“沿著宇宙論進路所形成的本體,所以稱之為宇宙本體論……其所言說的本體就是宇宙論規模——所謂整個宇宙萬物的始基性本體。”〔10〕作為宇宙本原的“太極”具有這種意義,作為宇宙生成的質料,“太極”動、靜而生陰、陽,陽變陰合生“水火木金土”之五行,進而生成萬物,由此構建了一套“太極—陰陽—五行—萬物”〔11〕的宇宙生成圖式,在這一過程中,“太極”本原作為宇宙生成的基本質料而呈現。所謂宇宙本體論的本體,實質上便是這種質料性的本原。
另一方面,“所謂本體宇宙論,從形成思路而言,則是指首先確立本體,并在本體之觀照、統攝下所形成的宇宙論。”〔12〕從這一角度看,周敦頤思想中“太極”亦具有此種本體性,作為萬物的本體,“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13〕五行統一于陰陽,陰陽統一于太極,太極的形態是無形無狀。就“太極”作為最終的統一性而言,萬物的本質是“太極”,萬物因“太極”而生生不息變化無窮。如果說從五行到太極中間還需要跨越陰陽二氣,那么“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為萬;萬一各正,大小有定。”〔14〕五殊即具有特殊性的五行,這一特殊性即指向以五行為代表的萬物,二實即實際存在,或者說具有實在性的陰陽二氣,“二本則一”之“一”即“太極”。此處周敦頤以“一”和“萬”的關系來闡明“太極”與“萬物”的關系。“是萬為一”即萬物以太極為一,以太極為本體,萬物統一于太極,太極寓于萬物之中。這種“一”和“萬”的關系即典型的本體論命題。因此,可以看出,周敦頤的“太極”思想是如丁為祥所謂“宇宙本體論”和“本體宇宙論”兩套宇宙構建范式的混合。對于“太極”而言,它同時具有宇宙論的本原存在和本體論的本體存在二層意義,“太極”不僅是萬物得以生成的本原,而且“太極”蘊含于萬物之中,是萬物得以挺立的本質。此兩層維度代表了儒家哲學兩種探討世界本質的不同進路,這兩層維度的發展變化亦彰顯了儒家學者在思想發展中認識世界的視域轉化,周敦頤“太極”的概念同時具有此二層維度,一方面體現了其哲學的復雜性,另一方面體現了儒家轉型期思想變革的不徹底性。
從思想史發展的角度看,周敦頤思想中太極本體和本原的復雜與混亂值得同情。如徐洪興認為:“宋代之前,宇宙生成論在中國本土哲學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而宇宙本體論卻無多大探究。是周敦頤首先在北宋理學家中嘗試從本體論維度思考宇宙的本源問題。”〔15〕作為理學的開山人物,周敦頤在繼承漢儒以來的宇宙本體論的基礎上嘗試本體宇宙論的開拓,展現了其開創性,亦呈現不徹底性。此外,周敦頤在“太極”之宇宙本原和萬物本體之外,又另以“誠”為本體,這雖然推動了本體論建構的完善,但是一般而言,無論是作為物質質料的本原還是作為本質規定的本體,終極的存在只有一種。而作為本體的“誠”的加入則增加了周敦頤本體論建構的復雜性。
三、“誠”的二層維度與“太極”“誠”的關聯
“太極”作為宇宙生成的本原,展開了從太極到萬物包括人的宇宙生成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太極”展現了其本體性。從天人合一的視域看,“太極”“萬物”“人的形神”“人極”等之間展開了其天人合一的互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從太極本原到萬物生生再到人之形神再到萬事之出,此種天人合一的模式是從天到人的自上而下的合一模式。而天人合一的模式顯然不止這一層,還有著從人到天的自下而上的維度。自上而下的維度是以太極為核心,生成陰陽、五行、萬物的過程。而自下而上的維度體現于人主動成己與成物,在萬事中不斷地五性感動、區分善惡、成為圣人并以“中正仁義”的原則“立人極”的過程,這一過程展現為人對天道的把握過程。通過這一過程,人成為圣人而達到與太極同等的高度,即所謂“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16〕這也是周敦頤所構建的宇宙世界中,自下而上“原始反終”的天人合一過程。在從人到萬事生成的過程中,周敦頤強調“人極”而非“太極”,“太極”在人與萬事展開過程中的作用似乎并未直接彰顯。同時,“太極”作為宇宙本原,具有先驗的本然屬性,從邏輯上無法直接為人的經驗性的道德和價值世界的展開提供本體依據。
因此,在“太極”之外,周敦頤在《通書》中又將“誠”確立為人的道德價值本體。這一確立與《太極圖說》“圣人主靜而立人極”的觀點密切相關。周敦頤多次提及誠與圣之間的關系,認為:“誠者,圣人之本。”〔17〕“圣,誠而已矣。”〔18〕“誠、神、幾,曰圣人。”〔19〕這說明誠為圣人之本,圣即是誠,圣與誠具有一致性的特征。因此,圣人立人極,即是誠者立人極,“誠”即是人極的狀態、品質。由此,《通書》之誠與《太極圖說》之圣人、人極乃至萬事、形神之間的關系便得以打通。鄭熊指出,周敦頤的“誠”觀念走的是“人→天的倫理道德天道化路線”,〔20〕即明確了此種確立“誠”的道德價值本體、并從人反推至天(太極)的過程。但是,鄭熊認為周敦頤思想成熟以后“拋棄了早期的‘無極’本體,重新建構了一個新本體‘誠’”。〔21〕這一觀點有待商榷。實質上,這一“誠”本體的開創與“太極”本體并不沖突,而且具有一定的關聯。“太極”與“誠”的關系在于:一方面,從生成論的角度來看,“誠”源自“太極”本原所生成的世界;另一方面,從本體論的角度看,“誠”在“人事”的生成和發展中確認了自身的本體性,這一本體性與“太極”本體既互相區分,又互相補充。以下詳述之。
“誠”最初作為誠實、誠信的美德而呈現,是儒家思想中與仁、信、忠等并列的美德條目之一,如:“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禮記·祭統》)《大學》將“誠意”作為八條目之一進行論述,此八條目是進德之道路,其中的每一條也可視為人的美德條目。“誠”作為本體性的哲學概念呈現始于子思,在《中庸》中,“誠”上升為本體論意義上的天道與人道的根本原則。即:“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禮記·中庸》)天道即誠道,而人道是對誠道的貫徹和執行,具有立人極地位的圣人是對誠道的從容踐行者。這從本體上確立了誠道作為天理之本然與人道之當然的特征。《中庸》和《易傳》對儒家的本體論、宇宙論思想有集中闡發,對此,溫海明認為“要在生生不息的意義上,理解宇宙和人之間本體性的關聯。……人參于天地間,要理解天地生生不息之大本大源,就必須面對《易傳》和《中庸》”,〔22〕即指出了二者之間的重要關系。因此,在《通書》中,周敦頤綜合《周易》和《中庸》的思想,以《周易》文本闡釋《中庸》之“誠”,將“誠”放在“太極”的宇宙生成論框架之下進行分析,集中闡述了“誠”的本體意義。
“誠”與“太極”關聯的第一層維度在于:“誠”生成于作為宇宙本原的“太極”。“誠”是以“太極”為核心的宇宙生成過程中的重要內容之一,“誠”作為道德(五常)與價值(百行)的本體,并不是先天的存在,而是有其生成的過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23〕從生成論的意義上講,作為“萬物資始”的“乾元”,與“太極”所具有的本原意義相同,即宇宙萬物生成的本原。“乾元”與“太極”,僅是概念使用上的不同,所具有的內涵一致。“乾元”作為“誠”的本源,即“太極”作為“誠”的本原,因此,“誠”本身的生成亦沒有脫離“太極”所生成和展開的宇宙世界。可以看出,同一概念具有不同含義(太極),同一內涵(本原)使用不同概念(乾元和太極)表達,亦是造成周敦頤哲學建構復雜性的原因之一。
相對于“乾元”即“太極”,“乾道變化”即“太極”動、靜而最終生成萬物的過程,即“太極”的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相對于“乾元”所具有的始基、本原意義,“乾道”則意味著“太極”所具有的具體的規定性、變化性。萬物在“太極”的生成變化中不斷尋求和確立自身的位置和意義,“誠”亦如此。“誠”呈現為道德與價值的基本原則和基本依據,即“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24〕“誠”作為仁、義、禮、智、信之五常的根本,作為人類日常行為的基本原則,成為與人相涉的道德、價值的本體,這一確立過程既基于“誠”自身所具有的“純粹至善”的品質,同時亦基于人在道德實踐過程中的選擇。即人們發現,“五常百行非誠,非也”。〔25〕人的倫理和日常行為的展開需要“誠”的指導。因此,“誠”一方面源自“太極”之本原,不離“太極”本原所生成的宇宙世界;另一方面又在生成的過程中確認了自身“純粹至善”的道德與價值本體的地位。這是“誠”與“太極”關聯的第二層維度。
四、“太極”“誠”的差異性與周敦頤的創見
“太極”因作為萬物生成的本原與本質性規定而具有本體意義,“誠”作為“五常百行”等道德與價值的基本原則也具有本體意義。如此在周敦頤的哲學體系中便存在兩個本體,此種“雙本體”的存在增加了對周敦頤存在論考察的復雜性。通過梳理周敦頤的文本和思想,可以看出,作為本體的“太極”和“誠”本體具有不同的側重點,可以作出區分。
深入梳理《太極圖說》和《通書》的文本可得,周敦頤文本中與“太極”相關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太極圖說》中,他在《通書·動靜》章中提及“太極”,即:“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26〕無論是動靜之辨,還是四時、五行、萬物,其論述的內容仍然是基于對《太極圖說》的闡發,并無范疇上的擴充。而對“誠”的論述則集中于《通書》的前幾章節,主要是《誠上》《誠下》《圣》《誠幾德》。《通書》其他章節亦有所涉及,而在《太極圖說》中沒有出現有關“誠”的論述。因此,基于文本的呈現看,“太極”是《太極圖說》的核心,而“誠”是《通書》的核心,這是二者文本依據上的不同。但同時,如朱熹所言:“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于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27〕《通書》發太極之蘊展現了《太極圖說》與《通書》之間存在密切關聯,因此,對于“太極”和“誠”的考察,雖然二者各有側重和區分,但是又不能對二者進行絕對分離的理解。
進一步深入梳理文本思想,可以看出,在《太極圖說》中,同時具有本原和本體意義的“太極”主要指向萬物的生成和對萬物的規定,即“物”的維度:“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28〕《通書》中亦多處提及對“萬物”的論述,如“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29〕“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30〕“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31〕從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萬物的生生與變化無窮基于“二氣五行”的化生,而“二氣五行”的終極依據在于“太極”,這體現了“太極”作為萬物之動力和本質所具有的本體意義。周敦頤對萬物的描述始終放在太極、二氣、五行的生成環節中展開,“太極”宇宙生成的最終環節在于生成萬物,萬物的生生展現了“太極”生成世界的變化無窮。因此,“太極”作為“萬物”的本原和本體,清晰地呈現在周敦頤的哲學建構中。從生成的過程講,四時的運行,萬物的生生先于人的生成而存在,人尚未參與其中,此“萬物”具有先驗性和本然性特征。在這一維度上,“萬物”是尚未與人相涉的“本然世界”的基本內容,“太極”呈現為本然世界的“萬物”本體。
在周敦頤描繪了本然世界之“萬物”的生成過程之后,“人”亦進入生成的視野。應當承認,“人”的生成先是基于“物”或者“生物”的自然維度的“形”,是作為自然物之一種而生成,即“形既生矣”。〔32〕“形既生”體現了人作為萬物之一的既成性和本然性,人只有獲得“神”之后,“事”的維度才得以展開,即“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33〕“神發知”意味著人超越了本然之“形”的局限而具有了精神意識和自覺性,從而善惡相分、萬事生出。“誠”的地位亦在“萬事”的發展變化中確立,即:“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34〕五常百行可視為萬事的更為具體的形態。“誠”之本體確立后進而上升到對“萬事”的基本規定,即:“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35〕正如溫海明認為:“‘誠’作為‘言’之‘成’,其本體意義上心意的創造性和新穎性能夠與天意相貫通,心意在領會萬物生生不息、創生不已的同時,不僅僅讓心意保持每時每刻都是新的,而且與天心的意味保持一致,沒有這種對于天意的領會,宇宙本體論意義上的‘誠’就無從談起。”〔36〕“誠”作為“萬事”的本體,一方面是“誠”在大化流行中自身的挺立,另一方面亦是由人在萬事的展開中所確定,“誠”即“萬事”之本體,本質規定。因此,周敦頤說“誠則無事”。〔37〕所謂“誠則無事”,如朱熹注曰:“誠則眾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38〕朱熹以“理”解“誠”,認為從本體的角度看,依照“誠”的原則所行事,就可以不待思勉籌幄而將事完成。只要以“誠”行事,則“無事”,即無“非誠之事”。這意味著“誠”對“事”所具有的規定和本原性意義。
如果說“萬物”指向太極所生成的,外在于人的本然世界的變化維度,那么“萬事”則是內在于人,由人之“神”即精神和思想所主導,由人自身所獨立生成的意義維度。在周敦頤的哲學中,人之“形”即人的形體是萬物的一種,而人之“神”即人的精神才是內在于人的“靈”即獨特之處。因此,周敦頤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39〕楊國榮指出事為“人之所作”,〔40〕在此,周敦頤將人的形生神發落實于“萬事”,展現了人與事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事”因人的存在而形成,而“誠”又作為“萬事”的本體而呈現,由此“誠”作為價值本體,既規定著人之所做之事,亦規定著事的主體即人。
因此,可以看出,“太極”為“萬物”之本體,“誠”為“萬事”之本體,二者分別指向世界的兩層維度,即先于人存在的本然維度和與人密切相關的道德價值的意義維度,在這兩層不同的維度之中,“太極”和“誠”承擔著不同的本體意義和作用。這是二者最為重要的區別。然而,由于“誠”生成于“太極”之宇宙世界,與人相關的“萬事”與外在的“萬物”息息相關。同時,人之“萬事”的世界亦展開于“萬物”的變化無窮之中,“事”與“物”呈現密不可分的特征。因此,“太極”亦可被納入內在于人的“萬事”視野進行考察,但是如前所述二者之間的區別是清晰的,這種密不可分的特征是導致周敦頤存在論和宇宙論復雜性的原因之一。
總的來看,在周敦頤的哲學建構中,“太極”和“誠”的關系呈現一致性和差異性兩層維度。一方面,“太極”自身具有“本原”和“本體”兩層維度,“誠”本身亦具有從“太極”本原中生成和自身挺立為本體兩層維度;另一方面,“太極”和“誠”的區別主要集中在“本體”維度,“太極”主要作為本然世界的“萬物”本體而呈現,而“誠”主要作為與人相關的意義世界的“萬事”本體而呈現。在這多層維度中,作為“本原”的太極是周敦頤對傳統儒家宇宙論的繼承,作為“萬物”本體的“太極”和人的道德價值“萬事”本體的“誠”,是周敦頤對傳統儒家本體論的開拓。從邏輯上看,這一開拓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從傳統的宇宙論中開拓出來。周敦頤之后,儒家的世界建構模式則逐步從宇宙論的構建模式轉向了本體論的構建模式,且日臻成熟,這是確立周敦頤為“理學開山”的重要理論依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