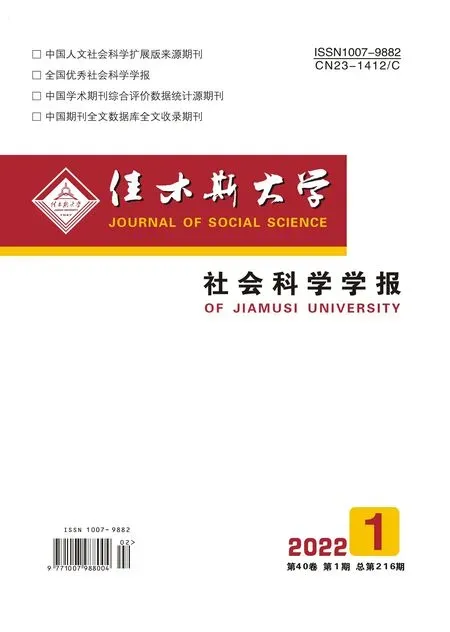古代文章“法古”思潮下的創變取向*
王明強
(南京中醫藥大學 中醫國學研究所,江蘇 南京 210023)
如何師法是古代文論師法論的核心問題。古代文論家常常談及具體的師法方法,與韓愈同時代的李方叔曾記載當時“摹畫”古文之法:“嘗見先生長者欲為文時,先取古人者,再三讀之,直須境熟,然后沉思格體,看其當如何措置,卻將欲作之文,暗里鋪摹經畫了,方敢下筆。踏古人蹤跡,以取句法。既做成,連日改之。十分改就,見得別無瑕疵,再將古人者又讀數過,看與所作合與不合?若不相懸遠,不致乖背,方寫凈本,出示他人。”[1]諸如此類的具體師法之法對初學文者不無裨益,卻并非古代師法論真正精蘊所在。古代文章一稟宗經法古之宗旨,為文復古的理論與實踐構成古代文章發展主流。但,在法古旗幟背后,是歷代文章家致力于文法創新與變化的不懈努力與實踐。《禮記·大學》載湯之《盤銘》云:“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2]《周易》云:“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道。”[3]313-314“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3]319“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3]324中國文化本身蘊涵著生生不息的創新通變基因,基于這種文化基因的中國古代文章和文章學呈現出不斷推陳出新的勃勃生機。
一、從“陳言之務去”到“點鐵成金”:唐宋時期文辭創新理論的歷史進路
劉勰《文心雕龍·通變》云:“文律運周,日新其業。”[4]199韓柳在推起復古文潮的同時,亦賦予師法以創新內涵。韓愈提出師法古圣賢的同時,以“勇往無不敢”[5](《送無本師歸范陽》)的精神提出要“自樹立,不因循”,其在《答劉正夫書》中云:“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甚至寧愿為當時人所怪,也要開創一條求“新”求“異”的創作之路,“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后世之傳也”。韓愈的求新求異具體指向文辭,在他看來道是自古而然不容變異的,但文辭卻可以日日新,為此,在師法上他明確提出“師其意不師其辭”[6]。“不師其辭”就要求創作時“惟陳言之務去”,摒棄當時社會上習用的陳詞濫調,以求鮮人耳目。當然,韓愈“務去陳言”并非刻意求奇,而是建立在較為深厚的學養之上,只有“氣盛言宜”,才能達到“務去陳言”。對此,清人黃宗羲有較為精辟的論述,其《論文管見》云:“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剝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以璞為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則必如《曹成玉碑》,乃謂之去陳言。豈文從字順者,為昌黎之所不能去乎?”[7]韓愈古文在繼承先秦兩漢文優秀傳統的基礎上,推陳出新,自鑄偉詞,具有很大的創造性。明代主張“文必秦漢”的何景明說“古文之法亡于韓”,即從另一側面揭示韓愈古文變古的實質。因此,韓愈師法古文,實則自創古文之法。柳宗元更是提出“何所師法”“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8]890(《復杜溫夫書》)。
韓柳之后,自我創法意識為其后學繼承。韓愈門下沈亞之《送韓靜略序》以草木之秋萎春盛為喻,鼓勵作者以經史百家之書為肥料和水分,在充分吸取的基礎上獨創發展,自致高敞:
或者以文為客語曰:“古人有言:‘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乃客之所尚也,恢漫乎奇態,紬紐己思,以自織剪,違曩者之成轍,豈君子因循之道歟?”客應曰:“草木之病煩也,使秋以治之,繼孱萌于窮枿之余,搔風披露,相望愁泫,陽津下潛。雖佳懿之彩,猶且抑隱,惟恐失類于慘禪煙黃之色耳,安暇自任其所長耶?即春以治之,擢氣于其根,升津百體之上,暢之風露,而繡英作,誇紅奮綺,緗縹紺紫,錯若裝畫,揚華流香,靄蕩乎天地之端,各極其至,使肆勇曜如是,寧可以一狀拘之?人有植木堂下,欲其益茂,伐他干以加之枝上,名之樹資。過者雖愚,猶知其欺也。且裁經綴史,補之如疣,是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其柯萌之鋒,由是而銳也。夫經史百家之學,于心灌沃而已。余以為構室于室下,葺之故材,其上下不能逾其覆,拘于所限故也。創之隟空之地,訪堅修之良,然后工之于人,何高不可者?祭酒導其涯于前,而后流蒙波,稍稍自澤。……”[9]
韓愈另一高足李翱則提出“創意造言,皆不相師”之說,其《答朱載言書》云:
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于腹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谷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10]
唐代古文家的創新言論主要拘于文辭,這種文辭上的創新也一直為后世文章家所強調,如呂留良云:“文最忌熟,熟則必俗。……今人為文,唯恐一字一句不熟到十分,萬手雷同,如一父之子,尚得謂之文乎?”[11]3345(《呂晚邨先生論文匯鈔》)劉大櫆《論文偶記》強調“文貴去陳言”[12]。文辭創新能自鑄偉辭最佳,然其流弊往往步入艱深奧澀、怪怪奇奇一途。這種情況在劉勰那里已予以詬病,其《文心雕龍·定勢》云:“厭讀舊式,故穿鑿取新。……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補不常,則新色耳。”[4]202昌黎為矯駢文庸俗陳腐之陋,便不免過正之弊,但其學養深厚,尚能做到“氣盛言宜”,大多數文章在語言上是比較平易的,但其后學末流往往流于“怪怪奇奇”。元代王若虛曾對此有較為公允的評論,其《文辨》云:“文貴不襲陳言,亦其大體耳,何至字字求異如翱之說?且天下安得許新語邪?甚矣,唐人之好奇而尚辭也。”[13]到宋代王禹稱有感于韓愈后學偏于古奧難懂,強調應發揚經籍及韓愈散文中明白曉暢的傳統,其在《答張扶書》中明確指出古文要寫得通達易曉:“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為之也。……既不得已而為之,又欲乎句之難道耶?又欲乎義之難曉耶?”[14]與此相應,宋代力倡為文明白曉暢的言論蜂起。《呂氏童蒙訓》云:“為文必學《春秋》,然后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為深隱不可學,蓋不知《春秋》者也。且圣人之言,曷嘗務為奇險,求后世之不可曉?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15]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序》云:“抑韓子之為文,雖以力去陳言為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為貴。”[16]都是對文辭創新偏弊的糾正。至黃庭堅則提出較為綜合的文字創新理論。對用字襲古與獨創的矛盾,黃庭堅指出“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萎靡,其病至今猶在。”主張在襲古的基礎上創新,提出“點鐵成金”說,認為“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17]475(《答洪駒父書》)。與唐代古文家極強的開拓創新意識不同,黃庭堅此論更為穩健、符合實際,指出要在融化前人陳言的基礎上再鑄偉詞,實現了師法與創新的辯證結合。對于“點鐵成金”之法,清人黃本驥《讀文筆得》中有形象化地解讀:“作文之法,襲取前人字句以為己有,與作賊無異。然賊最須善作,必較原本更為佳妙,雖失主認贓亦難辨別,方為能手。若活剝生吞,到案即破,則為笨賊矣。”[18]但理論如此,實際運用卻難。用字有所本,卻又不能直用其語,在行文時須重加鑄造,必有異稟絕識,融會古今文字于胸中,而灑然自出一機軸方可。因此,文辭創新似易實難,且唐宋古文家開拓創新的言論雖多在文辭,但他們最主要貢獻卻在篇章之法。羅萬藻在《韓臨之制藝序》中曾指出唐宋古文對篇章布置之法的開拓創新云:“文字之規矩繩墨,自唐宋而下,所謂抑揚開闔起伏呼照之法,晉漢以上,絕無所聞,而韓柳歐蘇諸大家設之,遂以為家。出入有度,而神氣自流,故自上古之文至此別為一界。”[19]這種篇章布置之法到明代唐宋派那里得到大力推闡,對文章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從取法秦漢到師法唐宋:明清時期篇章行文之法求變的邏輯理路
明清時期,文法理論由文辭創新轉入篇章行文之法的求變。唐宋古文家對取法秦漢僅是泛泛而論,明代秦漢派則對如何師法展開深入探討和論爭,這以發生在同為前七子代表人物的李夢陽和何景明之間的爭議為典型。何景明關注的文法是為文構思之法,在《與李空同論詩書》中即云:“仆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20]576但其文法求變的思想非常明顯,持“舍筏以登岸”之論[21]卷六十二(李夢陽《駁何氏論文書》),“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仿形跡”[20]575(《與李空同論詩書》),認為“法”只是象“筏”一樣的為文工具而已,文成則可舍法,根本就不必守之不易。甚至主張“欲博大義,不守章句,而于古人之文,務得其宏偉之觀、超曠之趣。至其矩法,則閉戶造車,出門合轍,不煩登途比試矣”[20]6(《述歸賦序》)。為文“閉門造車”即可,甚至有師心自任的趨向。正因此,李夢陽抨擊他“信口落筆”,并將復古派之衰歸罪于他的此種論調:
當是時,篤行之士翕然臻向,弘治之間,古學遂興。而一二輕俊,恃其才辯,假舍筏登岸之說,扇破前美。稍稍聞見,便橫肆譏評,高下古今。謂文章家必自開一戶牖,自筑一堂室;謂法古者為蹈襲,式往者為影子,信口落筆者為泯其比擬之跡。而后進之士,悅其易從,憚其難趨,乃即附唱答響,風成俗變,莫可止遏,而古之學廢矣。[21]卷六十二(《答周子書》)
與何景明不同,李夢陽則主張“文必有法式”[21]卷六十二(《答周子書》),要“尺寸古法”[21]卷六十二(《駁何氏論文書》)。李夢陽與何景明之爭看似屬于守法與變法的沖突,實則不然,李夢陽所關注的文法較之何景明立意甚高。李夢陽之“法”指向文章創作基本規律,“古之工,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為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仆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筑一堂,開一戶,措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方圓而遺之可矣,何有于法?何有于規矩?”甚至指向文的本質性規定,“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諧音度。如方圓之于規矩,古人之用之,非自作之,實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實物之自則也”。李夢陽曾以字為喻形象化地說明他所說的“法”與何景明之“法”的不同,“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21]卷六十二(《駁何氏論文書》)。李探討的是字所以為字的內在規定之法,而何探討的是字形成不同體勢之法。從內在規定性之法出發,李主張“尺寸古法”,即主張為文要尊奉最根本之法則。但一旦論及具體為文,卻并不主張墨守成規,而是反對“守而未化”,反對“蹊徑”[21]卷五十二(《徐迪功集序》),主張“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熔而不自知”[21]卷六十二(《駁何氏論文書》)。對此,他論述說“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倕之圓,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21]卷六十二(《駁何氏論文書》),同樣的規矩方圓,可制作出不同形狀的木頭,制作方法是靈活多變的。因此,與何景明僅從形文之法求變相比,李夢陽的法式求變論眼界極為寬廣,理論頗為完善。
但,究竟何為文之“應諸心而本諸法”的“物之自則”,如何又能“尺尺寸寸”之?李夢陽曾以“格”來指代他所謂的“物之自則”,“夫文自有格,不祖其格,終不足以知文。今人有左氏、遷乎,而足下以左氏、遷律人邪?……足下謂遷不同左氏,左氏不同古經,亦其象耳,仆不敢謂然”[21]卷六十二(《答吳謹書》)。對司馬遷、左氏、古經文之間的不同,李夢陽認為僅是其“象”不同罷了,而究其“格”應該是相同的。但以“格”來論述文之“物之自則”,僅是換了一個概念而已,而“格”同樣是難以說清的一個概念。不論是何景明還是李夢陽,雖對秦漢文章藝術構成的內在規律有所關注,但并沒有展開深入探討和總結,尤其是李夢陽主張法式秦漢文章之“格”,希望在整體氣質上向秦漢文章靠攏。整體上的肖古、合“格”,理上易論,具體實踐往往難以企及,結果往往只能在文字上肖古,李夢陽其文就已經被譏為“故作聱牙,以艱深文其淺易”[22]1497。到后七子的李攀龍則直言:“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摭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于古之作者而已。”[23](《李于鱗先生傳》)被譏為“所作一字一句,摹擬古人,驟然讀之,斑駁陸離,如見秦漢間人”[22]1507(殷士儋《李攀龍墓志》)。正是切痛于秦漢派此種流弊,唐宋派轉而師法偏重篇章布置之法的唐宋古文。篇章布置之法與文辭不同,文辭與作者積累密切相關,而篇章布置卻與作家構思密切相關。基于積累之上的文辭創新不易,且往往流于怪奇,而基于構思之上的篇章布置卻可以“出入有度,而神氣自流”,達“神明之變化”。唐順之提出“法者,神明之變化”理論,直接把“變化”的屬性賦予“法”,“文不能無法。……圣人以神明而達之于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窺神明之奧。其窺之也,有偏有全,有大有小,有駁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24]卷十(《文編序》)。
唐宋派師法唐宋古文,探討總結為文之法,亦有牽強附會之處,雖也遭致后人詬病,但多為指導初學和應付科考之需,其理論精髓并非主張泥于古法,而是強調創作實踐中的文法神變。這一理論精髓被清代文學家所承續,“清初三大家”之一的汪婉即主張“學于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25](《答陳靄公書(二)》)。對于文法神明變化的強調,有清一代與唐宋派相較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王夫之就認為唐宋派立矩定法、模規唐宋,總結文法有余而創新變化不足,甚至將唐宋派所總結的為文之法稱為“死法”“魔法”,“鉤鎖之法,守溪開其端,尚未盡露痕跡,至荊川而以為秘密藏。茅鹿門所批點八大家,全恃此以為法,正與皎然《詩式》同一陋耳。本非異體,何用環紐?搖頭掉尾,生氣既已索然,并將圣賢大義微言,拘牽割裂,止求傀儡之線牽曳得動,不知用此何為?”[26]205“陋人以鉤鎖呼應法論文,因而以鉤鎖呼應法解書,豈古先圣賢亦從茅鹿門受八大家衣缽邪?”[26]221(《夕堂永日緒論外編》)魏際瑞則提出學習古人之法即要能入又要能出,“不入于法則散亂無紀,不出于法則拘迂而無以盡文章之變”[11]3596,甚至認為“規矩”與“變化”在終極意義上同為一體,“由規矩者,熟于規矩,能生變化。不由規矩者,巧力精到,亦生變化,變化相生,自合規矩”[11]3600(《伯子論文》)。其弟魏禧為其文集作跋,特地指出云:“他人俱從規矩生神明,吾兄是從神明生規矩也。”[27]魏禧則認為“變者,法之至者也。此文之法也”[28]428(《陸懸圃文敘》)。與寧都三魏交往頗密的陳玉璂與三魏持相同論調,“人知無法之為病,不知有法之為病。惟能不囿于法,始可自成為我之法”[29]卷九(《與張黃岳論文書》),并曾以弈棋為例闡述無法更勝于有法:
文不可以無法,然徒規摹于古人,尺寸不失,第可為古人之法,而我無與。惟不見所以用法之故,若絕不類古人,而古人之法具在,特不可執一古人以名。嘗見善弈之家,按譜布算,攻守進退盡得其法,未嘗不足取勝;而更有人焉,于散漫不經意之處,落落布子,前吾所依,后無所據,茫然不知其意指所在,已而回環轉應,其所以制敵之妙,實在于此。然后知善用法者,能用法于無法之先,非按譜者可幾其萬一也。[29]卷二(《魏伯子文集序》)
其云:“吾輩生古人之后,當為古人子孫,不可為古人奴婢。蓋為子孫,則有得于古人真血脈;為奴婢,則依傍古人作活耳。”[11]3612(《日錄論文》)根基于古代“通變”哲學基因上的師法論最終指向不是師其辭、襲其文,而是既承六經之旨、先古之意,又能“自出機杼”“成一家之言”,古代文章家不斷尋求達致文法創變之途徑。作家為文,是為法所縛,還是法為己用,是主客間的一場較量。作家取得勝利的關鍵是提升主體性,以己之力勝法之力。對此,明清文章家分別大體給出兩種法門。明代唐宋派與陽明心學相結合,提出“本色”論,唐順之云:
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師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來,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為文章,其于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復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24]卷七(《答茅鹿門知縣(二)》)
本色論從“心源”上尋求文法來源,在破除死法的同時也隱藏著背棄古法的危險,因為“心”必指向自由無拘束之“真”,以致后來發展至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藐棄一切文法的理論,使文章步入逸蕩一途。與心學盛行、崇真尚我的明代不同,崇尚醇雅和學術的清代則多以識量破死法。王夫之云:“若果足為法,烏容破之?非法之法,則破之不盡,終不得法。詩之有皎然、虞伯生,經義之有茅鹿門、湯賓尹、袁了凡,皆畫地成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死法之立,總緣識量狹小。如演雜劇,在方丈臺上,故有花樣步位,稍移一步則錯亂。若馳騁康莊,取途千里,而用此步法,雖至愚者不為也。”[26]68-69魏際瑞云:“文章首貴識,次貴議論,然有識則議論自生,有議論則詞章不能自己。”[11]3595(《伯子論文》)魏禧認為文法已盡于古,只有提高識見,才能破死法,“文章之變,于今已盡,無能離古人而自創一格者。獨識力卓越,庶足與古人相增益。是故言不關于世道,識不越于庸眾,則雖有奇文,可以無作”[28]265(《答蔡生書》)。劉熙載《文概》則云:“文以識為主。認題立意,非識之高卓精審,無以中要。才、學、識三長,識為尤重,豈獨作史然耶?”[30]作者貴識,在清代可謂共識,文章領域如此,詩學領域亦然,葉燮提出作者創作才、膽、識、力四要素,“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31]16。但四者之中,“識”又是首要的、決定性的,“大約才、膽、識、力四者,交相為濟,茍一有所歉,則不可登作者之壇。四者無緩急,而要載先之以識。使無識,則三者俱無所托。……惟有識,則能知所從、知所奮、知所決,而后才與膽力皆確然有以自信。舉世非之,舉世譽之,而不為其所搖。安有隨人之是非以為是非者哉!”[31]29與本色論潛在師心自任的危險不同,識量論本質是以我融法。因為識量與法度是兩面一體的,徒有識量,而無法度以見之,亦不得顯。只有法度,而無識量,文亦缺乏生氣。魏禧將兩者的關系以本領與家數論之:
今天下家殊人異,爭名文章,然辨之不過二說:曰本領,曰家數而已。有本領者,如巨宦大賈,家多金銀,時出其所有,以買田宅,營園圃,市珍奇玩好,無所不可。有家數者,如王、謝子弟,容止言談,自然大雅。有本領無家數,理識雖自卓絕,不合古人法度,不能曲折變化以盡其意。如富人作屋,梓材丹雘,物物貴美,而結構鄙俗,觀者神氣索然。有家數無本領,望之居然《史》《漢》大家,進求之,則有古人而無我。如俳優登場,啼笑之妙,可以感動旁人,而與其身悲喜,了不相涉。然是二者,又以本領為最貴。[28]352(《答毛馳黃》)
本領即稟異識卓見,家數即富古文之法,為文二者皆不可或缺,而要以“我”來融會古法,古法變成我法。魏禮比魏禧所見更高一疇,其云:“述作而無我,我何為而作哉?人之貌不同,以各有其我;人之詩文競出不窮,以其有我也。是故以古人之氣格識法而成其我,徒我不成;猶必具五官百骸神血須眉發爪而成人,人人皆同而皆不同,各我其我也。……然喪我者吾,吾者何耶?蓋所謂法者。古人之法,亦我之法,會古以忘我,我足以忘乎古。”[32](《阮疇生文集序》)魏禮此論超拔于“我”“古”相融,而達致“古”“我”兩忘,“古”“我”兩忘方能真正步入為文的自由自適之境。
以“我”融法,僅提高主體識量是不夠的,還要對古法做到“熟”與“化”。 蘇軾曾教導黃庭堅作文之法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17]470-471朱熹亦教導弟子云:“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脈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33]3301葉元塏《睿吾樓文話》引《潛丘札記》載歸有光逸事一則云:“偶拈得一帙,得曾子固《書魏征傳后》文,挾冊朗讀至五十余遍,聽者皆厭倦欲臥,而熙甫沉吟詠嘆猶有余味。”[11]5452“熟”并非機械的熟練,而是要做到以我化法,以我融法。《睿吾樓文話》載《西軒客談》云:“前輩說作詩文,記事雖多,只恐不化。余意亦然。謂如人之善飲食者,肴蔌、脯 、酒茗、果物,雖是食盡,須得其化,則清者謂脂膏,人只見肥美而已。若是不化,少間吐出,物物俱載。為文亦然,化則說出來,都融作自家底,不然,記得雖多,說出來,未免是替別人說話了也。故昌黎讀盡古今書,殊無一言一句彷佛于人,此所以古今善文一人而已。”[11]5422-5423張謙宜云:“凡讀文,當低心伏氣,誦畢再細細玩味,務令眼光透出冊子里,精神溢出字句外,久之熨貼,漸能熔化,不知不覺,手筆移入隊中,從此自成局面。若獐慌失措,只講皮毛,強吞活剝,只似戲子穿行頭,干你甚事!”[11]3939(《絸齋論文》)師法而不能“化”,我與法還是分離的,只能做到用法,而無法達到法之自由神變。明代王世貞正是有感于自己“記聞既雜,下筆之際,自然于筆端攪擾,趨斥為難。若模擬一篇,則易于驅斥,又覺局促,痕跡宛然,非斫輪手”,才決定“目今而后,擬以純灰三斛,細滌其腸,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兩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詠之,令其漸漬汪洋”,并期望達到“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縱意暢,神與境合”[34]964(《藝苑卮言》)的創作境界。師法不能“化”,創作出的文章就不是真正自我的創造,而會有古人的影子。明代王鏊曾云:“為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為孟也;歐學韓,不覺其為韓也。若拘拘規效,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35]對于文法化與不化的差別,清代魏禧以人身之香氣加以形象化地說明,“平時不論何人何文,只將他好處沉酣,遍歷諸家,博采諸篇,刻意體認。及臨文時,不可著一古人一名文在胸,則觸手與古法會,而自無某人某篇之跡。蓋模擬者,如人好香,遍身便配香囊;沉酣而不模擬者,如人日夕住香肆中,衣帶間無一毫香物,卻通身香氣迎人也”[11]3610(《日錄論文》)。
師法達致化“境”,絕非易事。《管子·七法》論“化”云:“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36]“化”是一個持之以恒、鍥而不舍、反復實踐、循序漸進的過程。朱熹論“化”云:“變是自陰而陽,自靜而動;化是自陽而陰,自動而靜,漸漸化將去,不見其跡。”[33]1877“化”又是一個由動入靜,歸于無痕的過程。對于這一過程,文論家比以釀酒,宋代張镃《仕學規范》引張子韶云:“書猶麴糵,學者猶秫稻,秫稻必得麴糵,則酒醴可成。不然,雖有秫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文雄深者,有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是數者,雜然列于胸中而咀嚼之,猶以麴糵和秫稻也。醖醸既久,則凡發于文章,形于議論,必自然秀絕過人矣。故經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觀也。”[37]以我化法正如釀酒,法融通于無形,具體為文之時我即法、法即我,對于此種創作境界,柳宗元云:“快意累累,意盡便止。”蘇軾云:“止乎所當止,行乎所當行。”王世貞云:“分途策馭,默受指揮,臺閣山林,絕跡大漠,豈不快哉!”[34]964(《藝苑卮言》)此種自由揮灑、快意暢達境界的形成正是由于我與法之間的融通無礙,可以說是為文境界的極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