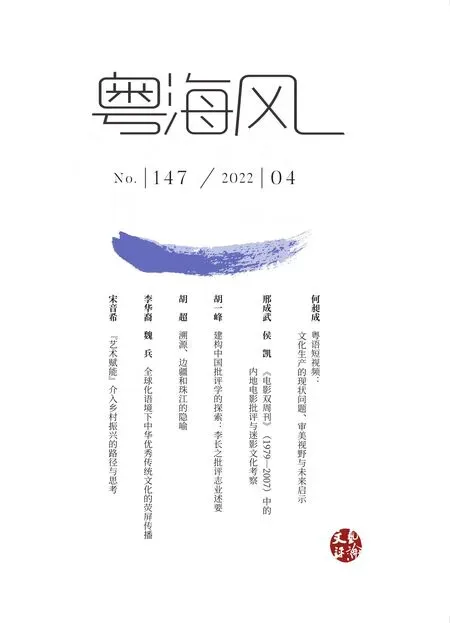建構(gòu)中國批評(píng)學(xué)的探索:李長之批評(píng)志業(yè)述要
文/胡一峰
李長之是我國現(xiàn)代著名文藝評(píng)論家,也是各種“現(xiàn)代中國文學(xué)史”中的“常客”。司馬長風(fēng)在《中國新文學(xué)史》(1976年)中就把李長之列為20世紀(jì)30年代中國的“五大批評(píng)家”之一。[1]近來,筆者研讀多卷本《李長之文集》,兼及相關(guān)研究成果,深感李長之對(duì)于我國文藝批評(píng)事業(yè)之價(jià)值,仍未得到充分估定。尤其是在文藝批評(píng)廣受關(guān)注的當(dāng)下,重讀李長之的批評(píng)文字,理解其批評(píng)思想,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李長之的批評(píng)志業(yè)博大精深,若一言以蔽之,莫如“建構(gòu)中國批評(píng)學(xué)”七字。
一、為中國文藝批評(píng)建一個(gè)“體系”
“批評(píng)學(xué)”所要回答的是批評(píng)所涉及的理論問題。用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的眼光,對(duì)于中國文藝批評(píng)歷史進(jìn)行梳理,在20世紀(jì)20年代也已開始,但是,從理論上系統(tǒng)地論述批評(píng)的相關(guān)理論問題,并嘗試建構(gòu)一種體系,使之成為專門的學(xué)問,這一工作直至今日也不能說已經(jīng)完成。縱覽李長之的論著可以發(fā)現(xiàn),他幾乎思考了一個(gè)批評(píng)家面臨的所有理論問題,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可見,雖然他沒有明確提出“批評(píng)學(xué)”的概念,但他構(gòu)建批評(píng)體系的自覺及其努力,事實(shí)上為中國“批評(píng)學(xué)”的建構(gòu)奠定了基礎(chǔ)。在不同的時(shí)期寫的文章中,他都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過體系的問題。在《偉大的批評(píng)家和文學(xué)批評(píng)史》中,他說“偉大的批評(píng)家卻是無不自圓其說,他的根據(jù)是整套的”[2]。在發(fā)表于1935年的《批評(píng)家所憑借的是哪一點(diǎn)》中又說,“批評(píng)家是主觀的。他有他的觀念世界,他在其中而無所矛盾,這就是所謂體系。他看要從整個(gè)的看,他應(yīng)付要就整個(gè)的應(yīng)付,他援引也是出發(fā)自他的整個(gè)思想而援引。零零星星不是批評(píng)家;批評(píng)家當(dāng)然對(duì)事物有印象,然而倘若這些印象沒有聯(lián)系,不配是批評(píng)家。”這就從特殊走向普遍,必須超越個(gè)體的經(jīng)驗(yàn),運(yùn)用理性的武器。[3]而在《現(xiàn)代美國的文藝批評(píng)》中,他指出,美國由于哲學(xué)和歷史的淺薄,缺乏自己的文藝批評(píng)。“中國有與美國相同處,就是同樣地現(xiàn)在拿不出代表本國的成為獨(dú)立面目的體系的文藝批評(píng)來”[4],而這是文藝批評(píng)的根本問題。他感慨中國的文藝批評(píng)史“荒蕪”“破碎”,“縱然披沙揀金,金子太少了!”數(shù)來數(shù)去,我們的純粹藝術(shù)批評(píng)家,不過是劉勰,鐘嶸,張彥遠(yuǎn)。此外,不是瑣碎,就是頭巾氣,就是油腔滑調(diào),找一個(gè)清清爽爽、生氣勃勃而嚴(yán)肅的批評(píng)家,了不可得。[5]直到1946年底,李長之歷數(shù)五四以來中國新文藝批評(píng)的進(jìn)程和成果之后,仍提出“體系的批評(píng)原理,還有待建造”[6]。
通讀李長之的著述的人,想必會(huì)發(fā)現(xiàn)他的《中國畫論體系及其批評(píng)》是極為獨(dú)特的一部。雖然,李長之的寫作涉獵面極為廣泛,如他的朋友所規(guī)勸的“攤子鋪得太大”,但總的來看,文學(xué)占了絕大部分,論及美術(shù)的極少,除了此文,大概只有《唐代的偉大批評(píng)家張彥遠(yuǎn)與中國繪畫》《呂斯百先生的畫室》《陳之佛教授的花卉畫》《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籌備期一屆美展參觀記》等幾篇。因此,這本書稱得上其寫作編年中一次奇峰突起。從寫作時(shí)間來看,此書原為李長之在清華大學(xué)上鄧以蟄“中國美學(xué)史”課程的作業(yè),原寫于1936年12月,1942年12月重改,彼時(shí)李長之已在中央大學(xué)任教。如果把這篇文章放在李長之建構(gòu)中國批評(píng)學(xué)體系的理論背景下來看,還會(huì)發(fā)現(xiàn)此文實(shí)為李長之系統(tǒng)梳理中國文化特別是批評(píng)理論資源,建構(gòu)批評(píng)體系的一次試水。在全文的“導(dǎo)言”中,他開宗明義地提出,“國人對(duì)于中國畫論和中國畫,在過去從歷史的——實(shí)用的觀點(diǎn)去整理者多,從體系的——哲學(xué)的觀點(diǎn)去整理者則少。現(xiàn)在此作即從后者出發(fā),作一個(gè)初步的嘗試”,“我們可以在好像沒有頭緒的畫論中,找出一個(gè)體系來,并且因而可以看出中國畫在藝術(shù)上之究竟的意義和價(jià)值來”。[7]他還說:“通常那種可以意會(huì),不可以言傳的態(tài)度,我是不贊成的,因?yàn)椋^不可以言傳,是本沒有可傳的呢?還是沒有能力去傳?本沒有可傳,就不必傳;沒有能力去傳,那就須鍛煉出傳的能力。對(duì)于中國舊東西,我不贊成用原來的名詞,囫圇吞棗的辦法。我認(rèn)為,凡是不能用語言表達(dá)的,就是根本沒弄明白,凡是不能用現(xiàn)代語言表達(dá)的,就是沒能運(yùn)用現(xiàn)代人的眼光去弄明白。中國的佛學(xué),畫,文章,……我都希望其早能用現(xiàn)代人的語言明明白白說出來。”[8]時(shí)隔幾十年后,知乎網(wǎng)友“陳飛飛”這樣評(píng)價(jià)此書:“關(guān)于中國繪畫的論述,已經(jīng)汗牛充棟,可對(duì)于外行來說,李長之先生的《中國畫論體系及其批評(píng)》應(yīng)該是脈絡(luò)最清晰的。”“這本書嘗試從三個(gè)方面總結(jié)中國繪畫的特點(diǎn):主觀——?jiǎng)?chuàng)作者人格、對(duì)象——?jiǎng)?chuàng)作題材、用具——?jiǎng)?chuàng)作手段,和互聯(lián)網(wǎng)常見的who-what-how思維模型不謀而合。”[9]
應(yīng)該說,李長之的目的實(shí)現(xiàn)了。我想,李長之并非神仙,斷無預(yù)知今日互聯(lián)網(wǎng)崛起之能力,更不可能早在幾十年前就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模型”。《中國畫論體系及其批評(píng)》之所以超越時(shí)空還能收獲網(wǎng)友點(diǎn)贊,應(yīng)歸功于中國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現(xiàn)代轉(zhuǎn)化的客觀需求,也從一個(gè)微觀個(gè)案說明,雖然李長之并未完成他理想中的“批評(píng)體系”的建構(gòu),但他的基本思路和學(xué)術(shù)路徑是有價(jià)值的。
那么,按照李長之的設(shè)想,該如何建造“體系”呢?他認(rèn)為,文藝批評(píng)所關(guān)涉的問題包括四個(gè)方面:第一,看一個(gè)作品說的是什么?而此處的“什么”不是指作品的內(nèi)容,而是指作者在作品中表達(dá)的中心思想。第二,看一個(gè)作家表現(xiàn)是否成功。第三,看一個(gè)作者該不該說,這涉及創(chuàng)作倫理的問題。第四,看一個(gè)作者為何表現(xiàn)這樣而不表現(xiàn)那樣。這是社會(huì)學(xué)、心理學(xué)、人類學(xué)的問題,“完全的批評(píng),則必須這四方面的問題同時(shí)解答”,唯此,才能建立健全的批評(píng)體系。具體而言,李長之列出了8個(gè)方面54個(gè)問題。這8個(gè)方面分別是:關(guān)系形上問題者、關(guān)于美的問題者、關(guān)于文藝作品本身者、關(guān)于作家者、關(guān)于作家與其作品之關(guān)系者、關(guān)于產(chǎn)生作品之事項(xiàng)者、關(guān)于批評(píng)自身之問題者、關(guān)于文藝教育者[10]。
這些問題組合起來,其實(shí)是文藝批評(píng)學(xué)的一份“論綱”,遺憾的是,李長之來不及按照這一論綱,完成文藝批評(píng)體系之建構(gòu),但他一生所作百萬字著述,實(shí)則已就上述問題作了論述和闡發(fā)。1933年,李長之發(fā)表《我對(duì)于文藝批評(píng)的要求和主張》,1942年結(jié)集為《批評(píng)精神》一書時(shí),他將此文作為自己認(rèn)定的“第一篇批評(píng)理論文字”,并說“其中大部分意見,現(xiàn)在也還沒有變更”。[11]可見此文集中體現(xiàn)了李長之的批評(píng)觀。此外,他還寫過《論偉大的批評(píng)家和文學(xué)批評(píng)史》《批評(píng)家為什么要批評(píng)》《文藝批評(píng)家要求什么》《論文藝作品之技巧原理》《文藝批評(píng)方法上的一個(gè)癥結(jié)》《批評(píng)家所憑借的是哪一點(diǎn)》《產(chǎn)生批評(píng)文學(xué)的條件》《文藝批評(píng)在今天》《為專業(yè)的批評(píng)家呼吁》《釋文藝批評(píng)》《雜談批評(píng)》等一系列文章,從這些著述勾勒出李長之想要建構(gòu)的“批評(píng)體系”或批評(píng)學(xué)的基本樣貌,可以發(fā)現(xiàn)兩塊極為重要基石,一為“批評(píng)精神”的倡導(dǎo),一為“批評(píng)文學(xué)”的建設(shè)。
二、文藝批評(píng)的關(guān)鍵在于批評(píng)精神
李長之說過,“我覺得文藝批評(píng)最要緊的是在‘批評(píng)精神’。”[12]在他看來,能稱之為批評(píng)家的,不在于專精于某各藝術(shù)門類,而在具有批評(píng)精神。可以說,如不理解李長之所說的“批評(píng)精神”,無法讀懂李長之的批評(píng)思想。回顧近代文藝史,寫過“文學(xué)批評(píng)史”或“文藝批評(píng)史”者多矣,但如李長之這樣對(duì)“批評(píng)”本體進(jìn)行深入分析者卻不多。在《釋文藝批評(píng)》中,他對(duì)“批評(píng)”做了詞源學(xué)的考證,認(rèn)為批評(píng)二字連用始于明朝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總序》,……文藝批評(píng)四字連用則是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以后才出現(xiàn)的。英文的Criticism,德文的Kritik,這兩個(gè)字都源于希臘文Krinein,是分別、決定的意思。可見,“批評(píng)的原意是判斷和決定,后來專指指出文學(xué)或藝術(shù)的優(yōu)缺點(diǎn)”。[13]比起李長之的時(shí)代,現(xiàn)代數(shù)據(jù)檢索技術(shù),讓我們得以更方便地遍索古籍。可以發(fā)現(xiàn),明清時(shí)期對(duì)“批評(píng)”的應(yīng)用已經(jīng)較為常見。比如,明代李贄的《寄答留都書》中說,“前與楊太史書亦有批評(píng),倘一一寄去,乃足見兄與彼相處之厚也。”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中說:“俺小店乃坊間首領(lǐng),只得聘請(qǐng)幾家名手,另選新篇。今日正在里邊刪改批評(píng),待俺早些貼起封面來。”與“批評(píng)”含義相仿的概念“評(píng)論”的使用則更早。比如,《后漢書·黨錮傳》中說:“君為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píng)論朝廷。”范曄的《獄中與諸甥侄書》中說,“既造《后漢》,轉(zhuǎn)得統(tǒng)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píng)論,殆少可意者。”元雜劇《殺狗勸夫》中的“哥哥你自忖量,你自評(píng)論,您直恁般愛富嫌貧。”在這些例句中,“評(píng)論”或“批評(píng)”顯然都具有評(píng)判、議論的含義。不過,李長之此文的用意在于為“批評(píng)”爭一個(gè)獨(dú)立“身份”,其方法論意義和篳路藍(lán)縷之功,超越于具體的詞源考證之上。李長之意義上的“批評(píng)精神”,包括三個(gè)要點(diǎn):
其一,正義感。李長之認(rèn)為,正義感是批評(píng)家最重要的性格。“什么是批評(píng)精神呢?就是正義感;就是對(duì)是非不能模糊,不能放過的判斷力和追根究底性;就是對(duì)美好的事物,有一種深入的了解要求并欲其普遍與人人的宣揚(yáng)熱誠;反之,對(duì)于邪惡,卻又不能容忍,必須用萬鈞之力擊毀之;他的表現(xiàn),是坦白,是直爽,是剛健,是篤實(shí),是勇猛,是決斷,是簡明,是豐富的生命力;他自己是有進(jìn)無退地戰(zhàn)斗著,也領(lǐng)導(dǎo)人有進(jìn)無退地戰(zhàn)斗著。”[14]他前無古人地把孟子認(rèn)定為“中國第一個(gè)批評(píng)家”,也正是看重其正義感。
其二,獨(dú)立與理性。李長之認(rèn)為,“批評(píng)是從理性來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的批評(píng)家,大都無所顧忌,無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15]“一部文學(xué)批評(píng)史是一部代表人類理性的自覺的,而為理性的自由抗戰(zhàn)、奮斗的歷史。只有在這種意義上,批評(píng)是武器,換言之,就是人類理性的尊嚴(yán)之自衛(wèi)”。[16]因此,他贊揚(yáng)劉知幾“獲罪于時(shí),固其宜也”的態(tài)度,感慨德國的萊辛賣稿為生因批評(píng)之故不能維持生活的境遇。從這些前賢那里,進(jìn)一步印證批評(píng)精神“是反奴性的,是為理性爭自由的”,奉命而作、聽命而為就不是批評(píng)了。“凡是屈服于權(quán)威,屈服于時(shí)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虛榮和金錢),屈服于輿論,屈服于傳說,屈服于多數(shù),屈服于偏見成見(不論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創(chuàng)造),這都是奴性,這都是反批評(píng)的。”[17]千篇一律的文章,應(yīng)景的文章,都有違于批評(píng)精神。“專為書店作出版消息式的書評(píng),這是小伙計(jì);專為朋友捧捧場面,或者為不同派的作家檢定一下意識(shí),以證明別人之沒落,這是叭兒狗;為讀者獻(xiàn)一殷勤,專作作全書的章次和標(biāo)題,或者專抄本文,這是錄事;怕得罪作者,而專在抑揚(yáng)上作功夫,弄得啼笑皆非,這是舊劇里令人作嘔的小旦;有的倒不客氣了,這個(gè)字也錯(cuò),那個(gè)字也錯(cuò),然而這卻是止于有了勘誤表的用處的校對(duì)。——這些不唯不是偉大的批評(píng)家,甚而連渺小的批評(píng)家也不是。”[18]正因?yàn)槿绱耍u(píng)家必然是有觀點(diǎn)的。如果只從事于思想體系的建構(gòu),那只是思想家,若從事文學(xué)的研究,則只是文學(xué)理論家;或者只為尋求事實(shí)而作考據(jù)訂正的工作,比如語言學(xué)家、傳統(tǒng)的小學(xué)家,都不能算作批評(píng)家,因?yàn)樗麄儧]有進(jìn)入價(jià)值層面,缺乏鮮明的真假善惡美丑的態(tài)度。[19]
其三,追求真善美。李長之曾自我設(shè)問“文藝批評(píng)家要求什么”,然后回答說:“一個(gè)字的答案:要求‘真’。”“詳細(xì)些,就是對(duì)于作品求一個(gè)真面目和真價(jià)值”。[20]在《魯迅批判》的初版序中,李長之說他寫作此書的用意很簡單,“只在盡力之所能,寫出我一點(diǎn)自信的負(fù)責(zé)的觀察,像科學(xué)上的研究似的,報(bào)告一個(gè)求真的結(jié)果而已,我信這是批評(píng)者的唯一的態(tài)度”。[21]為了求真,批評(píng)家必須保持忠實(shí)的態(tài)度。“礙了面子,說話是不能忠實(shí)的;互相標(biāo)榜,說話是不能忠實(shí)的;受了命令,說話是不能忠實(shí)的;別有目的,如想登廣告,想出風(fēng)頭,想拉攏,想敲竹杠,是不能忠實(shí)的。這些都有害于批評(píng)。”就求真這一點(diǎn)而言,文藝批評(píng)家與自然科學(xué)家有共同之處,都是追求事物的真相,他檢驗(yàn)一個(gè)作品的成分像一位化學(xué)家,研究作家的各方面環(huán)境,又如一個(gè)生物學(xué)家。但是,與自然科學(xué)家不同的是,文藝批評(píng)家不但要真相,還要“真價(jià)”,也就是對(duì)作品進(jìn)行價(jià)值判斷。[22]因此,批評(píng)兼具科學(xué)性與藝術(shù)性。從求真的一面而言,批評(píng)必須堅(jiān)持科學(xué)精神,客觀地材料為導(dǎo)引,而達(dá)到結(jié)論;從批評(píng)家的感情投入而言,又與科學(xué)家不同,“卻有一種像作家在創(chuàng)作時(shí)所需的天才似的,他在批評(píng)時(shí)有一種特別銳利的才能,極其靈敏,而極其透到,他能馬上看出一個(gè)作家所持有的作風(fēng)的所在,也就是要貫穿于這個(gè)作家整個(gè)作品的一致性的,并且他之得之,與其說是一種理智的領(lǐng)悟,毋寧說是一種情感的會(huì)心。”[23]這是批評(píng)的藝術(shù)性。
三、“批評(píng)文學(xué)”的獨(dú)立價(jià)值
李長之十分強(qiáng)調(diào)批評(píng)的獨(dú)立性,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批評(píng)文學(xué)”的概念。“就文學(xué)范圍之內(nèi)而談批評(píng),批評(píng)是一門專門之學(xué),它需要各種輔助的知識(shí),它有它特有的課題。如果不承認(rèn)這種學(xué)術(shù)性,以為‘入門’、‘談話’的知識(shí)已足,再時(shí)時(shí)刻刻拿文學(xué)以外的標(biāo)語口號(hào)來作為尺度硬填硬量的話,文學(xué)批評(píng)也不會(huì)產(chǎn)生。”[24]遺憾的是,李長之沒有對(duì)“批評(píng)文學(xué)”這一極富創(chuàng)造力的概念進(jìn)一步展開。這或許是因?yàn)樵诋?dāng)年的李長之看來,“就過去和現(xiàn)在看,中國很不容易有批評(píng)文學(xué)的產(chǎn)生”,批評(píng)要說真話、要分析、要反奴性,而這些產(chǎn)生批評(píng)文學(xué)的條件,還沒有具備。“一旦這些條件具備了,當(dāng)然批評(píng)文學(xué)的產(chǎn)生就容易了。但這只可希望于將來。”[25]在李長之所營構(gòu)之語境下的“批評(píng)文學(xué)”顯然不同于“文學(xué)批評(píng)”。“文學(xué)批評(píng)”指的是對(duì)文學(xué)的批評(píng),與“文學(xué)批評(píng)”相并列的是戲劇批評(píng)、電影批評(píng)等概念,而“批評(píng)文學(xué)”卻是文學(xué)內(nèi)部的一個(gè)具有相對(duì)獨(dú)立性的領(lǐng)域,與之相并列的乃是小說、散文、劇本等概念,是對(duì)作為文本的批評(píng)的類別總稱。文學(xué)批評(píng)史研究者指出,李長之提出的“批評(píng)文學(xué)”概念,不僅是一種概念的變化,更是一種批評(píng)觀的變化。[26]
那么,批評(píng)文學(xué)包含哪些要素呢?對(duì)此,李長之也有過比較充分的論述。在他看來,批評(píng)包括兩方面內(nèi)容或兩個(gè)步驟,第一步是理解,第二步是褒貶。從理解的角度而言,作為批評(píng)者,只了解作品表層的內(nèi)容是不夠的。譬如《紅樓夢》,只看見男男女女的故事,不能算理解了作品,因?yàn)樯形凑莆兆髡叩摹氨疽狻薄!耙驗(yàn)樵谀撤N意味上說,任何人都是哲學(xué)家:這由于任何人對(duì)于人生都有他的觀感和解答,以及自己一致的人生態(tài)度故。尤其在一個(gè)作家,他特別有人生的體驗(yàn),他特別有所感觸,他特別又有所追求,當(dāng)然更有此種傾向。什么是最支配他的生活的呢?什么是在他思想的活動(dòng)上最根本的作為出發(fā)點(diǎn)呢?簡化了又簡化,必至于有最后的一點(diǎn)余剩、非常結(jié)晶的東西,這就是作家的中心觀念,批評(píng)家的寶貴的鑰匙。”[27]李長之所說的批評(píng)家要理解的“內(nèi)容”指的是“表現(xiàn)在作品里的作者之人格的本質(zhì)”,比如“自由”之于歌德,“雖九死其猶未悔”之于屈原,“任真無所先”之于陶潛,便是內(nèi)容。[28]掌握了這一點(diǎn),才算是把握了作者的本意。這就需要三個(gè)條件:哲學(xué)家的頭腦、跳入作者的世界、知道作者的社會(huì)環(huán)境。所謂哲學(xué)家的頭腦,并不是說批評(píng)家要有多么豐富的哲學(xué)或哲學(xué)史知識(shí),而是說體系化地表達(dá)蘊(yùn)藏于作品中的作者思想觀念。“在一個(gè)作家,未必能把自己的思想統(tǒng)一,或能夠統(tǒng)一而自己并不曾意識(shí)時(shí),這既更需要有哲學(xué)頭腦的批評(píng)家來幫作者完成。即使是偉大如歌德,在這一點(diǎn)上,恐怕也是要感謝后來的大批評(píng)家的。”[29]由此可見,李長之所謂“批評(píng)”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代作者立言的意味,因此,他提出要掌握作者的“中心觀念”,將其作為“批評(píng)家的寶貴鑰匙”,進(jìn)而理解作者的思想體系。不過,李長之的意思并不是要將批評(píng)對(duì)象作為闡發(fā)或佐證批評(píng)家觀念的“材料”,因而他緊接著提出批評(píng)家需“跳入作者的世界”,在作批評(píng)時(shí)“不但把自己的個(gè)人偏見、偏好除去,就是他當(dāng)時(shí)的一般人的偏見、偏好,他也要滌除凈盡。他用作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聽,和作者的悲歡同其悲歡,因?yàn)椴皇侨绱耍覀儠?huì)即使有了鑰匙也無所用之。”他現(xiàn)身說法道,“我是喜歡濃烈的情緒和極端的思想的,我最憧憬的,是理性的自由,假設(shè)我只在我這世界里,我是沒法了解陶淵明、李商隱的。然而我能了解陶淵明、李商隱者,就只在我能跳入他們的世界故。”[30]了解了作者“說的是什么”之后,還需明了其“為什么這樣說”,這就要了解作者的社會(huì)環(huán)境。批評(píng)家必須清楚作家的一切,非如此,不能從作者個(gè)體擴(kuò)展到對(duì)一個(gè)時(shí)代整體創(chuàng)作情況的理解,也無法找到作品的時(shí)代基礎(chǔ)。實(shí)際上,李長之評(píng)論某個(gè)作家時(shí),一直強(qiáng)調(diào)要通讀該作家的所有作品。“我已經(jīng)養(yǎng)成一種習(xí)慣了,對(duì)于一個(gè)人的作品倘若沒有遇到機(jī)會(huì)整個(gè)的去看的時(shí)候,我是寧愿不作片斷的瀏覽的。這理由很簡單,就是我怕看不全一個(gè)人的作品,容易得到一種不正確的印象,而這不正確的印象久而久之,會(huì)成了偏見,便反而妨礙虛心。”[31]如果我們換用現(xiàn)代的學(xué)術(shù)語言來說,李長之所說的“理解”的三個(gè)條件,前兩個(gè)屬于“內(nèi)部批評(píng)”,后一個(gè)屬于“外部批評(píng)”。而這個(gè)問題正是長期居于文藝批評(píng)理論大廈核心位置的論題。
在理解的基礎(chǔ)上,方可論褒貶。僅有理解而無褒貶,不算真正的批評(píng)。而褒貶又分內(nèi)容與技巧兩個(gè)方面。李長之認(rèn)為,對(duì)作品內(nèi)容的分析,應(yīng)和“道義”相聯(lián)系,認(rèn)為文藝可以和道義絕緣、可以書寫不含道義的內(nèi)容的觀點(diǎn)是錯(cuò)誤的。用道義批評(píng)文藝,有時(shí)可能會(huì)錯(cuò)妄,但這不代表道義不能作為批評(píng)文藝的標(biāo)準(zhǔn),而是因?yàn)槟承┡u(píng)家所持的“道義”并非真的道義,譬如“忠君”,本不是道義,如果用它來評(píng)價(jià)文藝,就會(huì)出現(xiàn)問題,而且道義具有時(shí)代性,如果用過去的道義去限定文藝的未來,自然會(huì)發(fā)生錯(cuò)誤。[32]
而且,批評(píng)家對(duì)于內(nèi)容的批評(píng),不在于指出內(nèi)容本身的優(yōu)劣,“我們更要切實(shí)地指出,如果那優(yōu)長是在現(xiàn)生活里所常見的,我們當(dāng)如何的發(fā)揮,否則當(dāng)如何的企求;假如那缺陷是潛伏于現(xiàn)生活的根柢里的,我們也要如何地挑剔出來,加以糾正,否則也當(dāng)如何的防杜。對(duì)于內(nèi)容的檢討,必如此,才盡了批評(píng)的職責(zé)。”[33]當(dāng)然,李長之更重視的,還是作品的技巧。這是其職業(yè)批評(píng)家身份的體現(xiàn),也是其作為批評(píng)家不同于一般的作品閱讀者之根本所在。他認(rèn)為,“在創(chuàng)作一篇文藝作品時(shí),技巧的重要,毋寧說是有過于內(nèi)容。其所以為藝術(shù)者,不在內(nèi)容,而在技巧。因?yàn)榧记墒俏乃囍畡e于一般別的非文藝品的唯一的特色之故。文藝品不成了法律,不成了廣告,不成了傳單,其故在此。現(xiàn)在的人,一般的是輕視技巧的,往往顧惜了內(nèi)容,對(duì)技巧有所寬容,這無疑的是否定了文藝——即使對(duì)內(nèi)容的論斷不妄。”[34]在技巧方面,批評(píng)家先應(yīng)明白“一般的最高的技巧”,也就是藝術(shù)技巧的理想狀態(tài),這令批評(píng)家獲得考量現(xiàn)有作品技巧的標(biāo)準(zhǔn)。李長之以高度濃縮的語言指出,藝術(shù)技巧的一般要求是“力”和“美”,而“力”也是屬于“美”的。換言之,美的標(biāo)準(zhǔn)是技巧的最高標(biāo)準(zhǔn)。按照這一標(biāo)準(zhǔn),方可評(píng)價(jià)“作家所特有的技巧”,而要完成這一點(diǎn),也必須“跳入作者的世界”,假想自己有些思想和情緒需要表達(dá)出來,以此印證作品對(duì)于情感的表達(dá)成功與否,以此來體驗(yàn)作者創(chuàng)作時(shí)的甘苦。對(duì)文藝作品技巧的重視,可謂李長之文藝批評(píng)的一大特色。“技巧”和“形式”都與內(nèi)容相對(duì)而言,李長之認(rèn)為,在這個(gè)意義上,二者的意思是相同的。只是“形式”更具有定型和抽象化的意思。[35]他認(rèn)為,當(dāng)我們?nèi)橥度雽?duì)藝術(shù)品的欣賞時(shí),往往只專注于形式,而忘卻了材料或內(nèi)容。他所說的“形式”,也就是藝術(shù)家的表現(xiàn)手法和技巧。“形式就是內(nèi)容經(jīng)過藝術(shù)的觀照而具體化了的,形式不但表現(xiàn)當(dāng)下作家所要表現(xiàn)的內(nèi)容,而且透露那作家的整個(gè)精神”,“當(dāng)你欣賞那藝術(shù)品時(shí),你對(duì)于內(nèi)容的要求,已由形式上被你直覺的銳感所深深感印了,……你已懾服于美的形式之下,……那內(nèi)容在形式里已好好地傳給你了。”[36]“技巧”包括三個(gè)方面,一是風(fēng)格,二是手法,三是結(jié)構(gòu)。他以造房子為喻,風(fēng)格是如何排列磚瓦的問題,手法是選擇哪一樣的磚或瓦的問題,結(jié)構(gòu)則是房子的間架設(shè)計(jì)問題,“內(nèi)容”則是建筑師要表現(xiàn)的概念。而如以人體為喻,風(fēng)格仿佛一個(gè)人舉止,手法如皮膚肌肉,結(jié)構(gòu)卻好比骨骼,“這三者合成,給人一個(gè)總的印象,便相當(dāng)于所謂技巧。只有那個(gè)人的真精神,為這舉止、皮膚肌肉、骨骼所表現(xiàn)的,才是我所謂‘內(nèi)容’。”[37]
余 論
李長之說過,“批評(píng)”不是空的理論也不是一種知識(shí),而是一種實(shí)踐,“批評(píng)也決非只是說明某一種作品就完了,卻是更要求改良,能夠發(fā)生實(shí)際作用。過去有人說:‘哲學(xué)不只說明世界,而且在變革世界’。現(xiàn)在我們可以套這句話說,‘藝術(shù)不只在說明人生,而且在變革人生’;‘批評(píng)不只在說明藝術(shù),而且在變革藝術(shù)’!”[38]他曾指出一系列貌似批評(píng)的現(xiàn)象,但并非批評(píng)。這段話雖然很長,但極有針對(duì)性,縱然八十余年后之今日讀之,依然凜然有生氣:
有許多人好像是批評(píng)家的,而其實(shí)不是的,例如:第一,只作一種體系的思想,而與人無涉的,他只受別人的批評(píng),而不批評(píng)別人,他只重在他自己的創(chuàng)獲,而不重在別人的褒貶,這便只是純粹的思想家,而不是批評(píng)家,倘若他從事的是文學(xué)的研究,則只是文學(xué)的理論家,也不是文藝批評(píng)家。第二,只為一問題而探求著,而不必關(guān)聯(lián)于整個(gè)的作為前提的批評(píng)的根據(jù)的,他得的是事實(shí),他所為的只是供再有別人作更進(jìn)一步的解釋的,這便是專門家的學(xué)者,而不是批評(píng)家,倘若在文學(xué)的范圍以內(nèi),這便是考據(jù)、訂正的工作(如外國的語言學(xué)家,如中國的小學(xué)家),而不是文藝批評(píng)家的批評(píng)工作,所以止于如此的,也不是文藝批評(píng)家。第三,只為一時(shí)代的文藝思潮的反映(如中國從前人在八股時(shí)代之講古文義法,如中國現(xiàn)在之要求非寫實(shí)不可的文藝)而著書立說的,這也不是批評(píng)家,雖然批評(píng)家也會(huì)染有時(shí)代的色彩。批評(píng)家之所以為批評(píng)家,乃是另外還在他的獨(dú)特的、不茍同的、不盲從的真知和灼見。第四,從創(chuàng)作家的觀點(diǎn),能夠撇卻主觀的愛好,而道出其他作家的得失的(如李白,杜甫之偶然而論詩是),這也只是證明這位創(chuàng)作家的批評(píng)有時(shí)可靠了,這是耍賴的辦法,因?yàn)樘热粽嬷竿麆?chuàng)作者批評(píng)的時(shí)候,那自以為高于批評(píng)家的創(chuàng)作家卻又會(huì)說“這不是我的事”了。批評(píng)家有批評(píng)家主要的精神,所以這四種都不能稱為批評(píng)家。[39]
值得注意的是,李長之眼中的“批評(píng)”,其意義和價(jià)值是超越于文藝之外的,關(guān)系到對(duì)整個(gè)文化乃至全社會(huì)的建設(shè)。因此,他特別強(qiáng)調(diào)對(duì)批評(píng)家尤其是青年批評(píng)家的培養(yǎng)。1934年他在《青年批評(píng)家的培養(yǎng)》一文中認(rèn)為,大眾的力量正在覺醒和提高,中國將進(jìn)入一個(gè)建設(shè)的時(shí)代,而“大建設(shè)以前,是需要批評(píng)的。大建設(shè)的逼近,是令人越感到批評(píng)的迫切的。”[40]1957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時(shí)形成熱潮,而中共八大關(guān)于第二個(gè)五年計(jì)劃的建議中,也專門提到了開展文藝批評(píng)。這讓李長之再次燃起了對(duì)批評(píng)的熱愛,他大聲疾呼要重視批評(píng):“批評(píng)本來重要,現(xiàn)在更重要,將來還要重要。在這‘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shí)候,批評(píng)也更改活躍起來了。”他又以一貫的充滿情感和熱望的語氣提出,這是批評(píng)家“千載難逢的機(jī)會(huì)”,“大家都瞪著眼在期待創(chuàng)作,同時(shí)也瞪著眼在期待批評(píng)”。為此,他還專門列出了培養(yǎng)專業(yè)的批評(píng)家的“方案”。李長之的培養(yǎng)方案提出,要善于發(fā)現(xiàn)在批評(píng)方面有興趣有才能的人,為他提供系統(tǒng)學(xué)習(xí)專業(yè)知識(shí)和接觸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體驗(yàn)生活的機(jī)會(huì)。同時(shí),鼓勵(lì)批評(píng)者自由創(chuàng)造,引導(dǎo)其走專業(yè)化的道路。他還提出刊物應(yīng)有經(jīng)常的固定的批評(píng)家,文藝團(tuán)體則應(yīng)做好批評(píng)家培養(yǎng)的組織工作,等等。[41]這些意見,即便放到今天來看,依然具有很強(qiáng)的針對(duì)性。當(dāng)然,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李長之的“方案”的結(jié)局只是“紙上談兵”。““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后,李長之復(fù)出。有人曾表示愿意重印《魯迅批判》,但有一個(gè)條件,把書名改為“魯迅分析”,李長之拒絕了。[42]這個(gè)歷史細(xì)節(jié)耐人玩味。《魯迅批判》是李長之的成名作,也給他帶來了不少磨難。而之所以引發(fā)磨難,很大程度并非是其內(nèi)容,而是書名中的“批判”二字。對(duì)于彼時(shí)的李長之而言,重印此書無疑有助于再次開啟學(xué)術(shù)和批評(píng)生涯,我想這也是李長之內(nèi)心渴望的,但他不悔少作的姿態(tài),讓我們看到他獨(dú)立、自尊的人格,而這正是他所孜孜以求的批評(píng)精神,也是他希望建構(gòu)的中國批評(píng)學(xué)最閃亮的內(nèi)核。
注釋:
[1]司馬長風(fēng):《中國新文學(xué)史》(中卷),臺(tái)北:昭明出版社,1976年,第248頁。其他四位分別是周作人、朱光潛、朱自清和劉西渭。
[2]《李長之文集》第三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頁。
[3]同[2],第441頁。
[4][5]同[2],第43頁。
[6]同[2],第522頁。
[7]同[2],第239頁。
[8]同[2],第240頁。
[9]陳飛飛:《我讀〈中國畫論體系及其批評(píng)〉》—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1274060
[10]篇幅所限,問題的具體內(nèi)容此處不贅述。可參考《李長之文集》第三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7頁。
[11]同[2],第151頁。
[12]同[2],第3頁。
[13]同[2],第317頁。
[14]同[2],第200頁。
[15][17]同[2],第155頁。
[16][18][39]同[2],第24-25頁。
[19][20][21]同[2],第25頁。
[22]《李長之文集》第二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頁。
[23]同[2],第442頁。
[24]同[2],第321-322頁。
[25]同[2],第153頁。
[26]周海波:《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史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6頁。
[27]《李長之文集》第一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頁。
[28][32]同[27],第53頁。
[29][30]同[2],第13頁。
[31]同[22],第333頁。
[34][35]同[2],第17頁。
[33]同[2],第53頁。
[36]《李長之文集》第七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3頁。
[37]同[2],第54頁。
[38]同[2],第528頁。
[40]《李長之文集》第八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78頁。
[41]同[2],第556-557頁。
[42]于天池:《憶長之老師》,《李長之文集》第一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