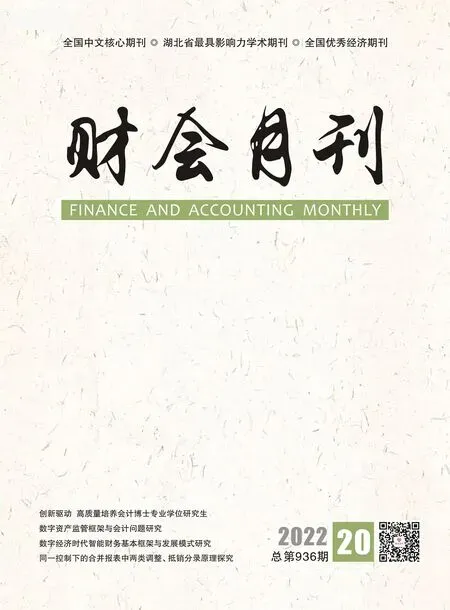淺析事項法下的會計信息呈現
王明威,郭 棟
隨著“大智移云物區”等數字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和現代商業模式的不斷變革,傳統會計信息系統受到了越來越明顯的沖擊。在實務界許多行業的頭部企業已開始進行財務的數字化轉型,而學術界也對業財融合、區塊鏈以及財務共享等對于會計信息系統的影響進行了較多的討論[1],這些變化使得信息生產者提供信息的能力得到了質的提升。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會計應當如何對信息進行記錄和反映?一些學者認為“事項法”比傳統的“價值法①”會計更能滿足“網絡時代”下信息使用者對于會計信息的需求[3,4]。然而,現有研究中對于事項法下應當記錄哪些信息、應該如何展現會計信息甚至是對事項法本身的含義這一基本問題均缺少相關的論述,本文試圖從估值(決策有用)這一會計目標的角度對上述問題展開分析。
一、事項法的內涵
在分析事項法下會計信息應當如何記錄和呈現之前,首先必須要明確“事項法”本身的含義。“事項法”一詞最早由Sorter[2]正式提出,他認為傳統的財務會計實質上是一種價值法會計,在價值法會計中,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已知并且非常充分地得到了確定,因此會計學者可以推導出信息使用者進行決策時所需的最優輸入值②,信息提供者以此為指導提供相應的輸入值。對應地,Sorter[2]提出了事項法會計,并指出事項法下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同樣是已知的③,但是由于信息使用者類型豐富,按價值法下僅出具同樣的一份匯總報表不能滿足不同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因此需要使用事項法提供細顆粒度、低結構化的數據,采用多種計量屬性混合使用、貨幣計量和非貨幣計量混合使用的計量方式,對價值信息和非價值信息進行全面的披露,使得信息使用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對原始數據進行匯總、計價和評價④。同時,Sorter 認為事項法與價值法的根本區別在于,會計報告中何種程度的整合與評價是合適的,以及由誰來進行整合與評價⑤。他認為:價值法下最終呈現的是從會計人員的角度進行評價并高度整合后的信息,而這種高度整合使得財務報告損失了大量信息;事項法下則是通過提供細顆粒度的信息,讓信息使用者自行進行評價和整合,以滿足其自身的信息需求。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事項法下也可以提供會計人員整合后的信息,但需要保證信息使用者對未整合的原始數據的可獲得性。
從Sorter 的相關論述可以看出,他實際上并未指出價值法與事項法的本質差異以及需要事項法會計的原因,而是在說明事項法最終的列報和披露與傳統的價值法下的會計有何區別,他認為最重要的區別在于是否提供細顆粒度的信息。雖然Sorter 也提到了事項法下假設信息使用者本身的信息需求存在差異,但由于同時假設了已知各類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因此其提到的傳統價值法會計只要能做到提供細顆粒度信息,同樣能夠滿足不同類型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因此也就不需要再區分所謂的“價值法”以及“事項法”。并且根據Sorter關于事項法和價值法根本區別的看法,只要傳統會計通過不斷擴充財務報告內容最終能讓信息使用者獲取未整合的原始數據,“價值法”與“事項法”就不存在本質區別。因此,盡管Sorter 開創性地提出了“事項法”這一思想,但事實上他提出的“事項法”只是一種提供更多、更細顆粒度輸入值的“價值法”,兩者之間并不存在本質上的區別。
在Sorter 提出“事項法”的思想后,有學者對事項法的含義以及事項法下一些術語的概念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完善[5-7],提出了如何構建事項法下的會計信息系統[6,8,9],并通過實驗探究事項法與價值法下信息使用者使用會計信息的情況是否存在顯著差異[10],而更多的研究則是在強調事項法的相對優越性,對事項法本身涉及的理論問題并沒有進行深入探討[11-13]。盡管存在著一定數量的以事項法為主題的研究,但鮮有研究涉及事項法與價值法的根本區別,總體上觀點仍舊限于Sorter[2]所論述的內容。少數提及事項法本身的會計理論的文章主要將事項法的前提假設由完全了解信息使用者需求放寬至不完全了解信息使用者的需求[6],甚至完全不了解信息使用者的需求[13]。此外,放寬假設后的事項法認為,即使不完全了解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事項法會計的最終目標依然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信息[6,10]。雖然Lieberma 等[6]和Benbasat等[10]指出事項法下并不了解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但在事項法提供哪些信息的論述中卻又與Sorter[2]的描述基本類似,即提供有關經濟事項的各種信息,讓信息使用者自己根據決策模型的需要選擇適用的信息⑥以滿足自身需求。然而潛在的問題是,判斷經濟事項是否相關這一過程本身就需要了解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因此Lieberma 等[6]和Benbasat 等[10]提到的事項法的記錄和列報本身與其假設是矛盾的。
雖然Lieberma等[6]和Benbasat等[10]的后續論述與其假設存在矛盾,但其提出的事項法下不完全甚至完全不了解信息使用者需求這一前提假設卻是十分必要的。根據Sorter[2]的表述,不同信息使用者的決策模型以及所需的輸入值存在差異⑦,此時再假定完全了解各類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可能是一個過于嚴格的假設,反而會影響后續分析以及實際應用。本文認為,盡管現實中信息使用者的類型以及對信息的需求可能會有較大差異,但其中存在一些信息需求類似于常識或公開信息是信息提供者或準則制定者所知曉的,例如在進行估值時信息使用者更關注與公司的未來現金流以及成長機會相關的信息,因此本文認為不完全了解信息使用者需求這一前提假設可能更符合現實情況,相對更為合理,后續的分析也應建立在這一假設的基礎之上。同時,本文假設這部分已知的信息需求與價值法或事項法下最終對外提供的信息存在交集,并且已知信息需求與價值法下提供的信息的交集是已知信息需求與事項法下提供的信息的交集的子集⑧。
更為重要的是,本文認為,不完全了解信息使用者需求這一假設從根本上將事項法與傳統的價值法區分開來。由于這一條假設的存在,事項法和價值法后續會計信息的記錄以及列報呈現出了本質上的差異。在傳統的價值法下,由于準則制定者或信息提供者已知信息使用者的決策模型以及信息需求,根據會計目標即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信息提供者只需要收集這些信息,最終將這部分內容報告即可。因此,價值法之下是由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決定財務會計收集哪些信息以及如何進行最終的列報和披露。根據價值法對使用者信息需求的假設,當價值法下的財務報告提供細顆粒度的信息時,說明信息提供者或者準則制定者已經明確知道了這樣的信息具有決策有用性(至少對大多數信息使用者而言)。然而在事項法下,由于不完全了解信息使用者的需求,而事項法會計的目標依然是提供對使用者而言決策有用的信息,信息提供者就無法只依賴于已知的信息使用者需求來決定最終提供哪些信息,因此信息提供者應當從自身提供信息的能力出發,盡可能地收集信息,并通過恰當的方式進行最終呈現,使得信息使用者可以自由整合信息以實現提供決策有用信息這一目標。因此,事項法下被會計記錄的內容是由信息提供者的信息提供能力所決定的。如果在事項法下信息提供者相對于以往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那么這種情況主要反映的是信息提供者本身提供信息的能力提升,其額外提供的這些信息并不必然具有決策有用性。同時,Sorter[2]所提出的“事項法與價值法的根本區別在于會計報告中何種程度的整合與評價是合適的,以及由誰來進行整合與評價”,本質上是本文所提出的兩種會計方法下對于信息使用者信息需求了解程度不同所導致的。
總之,由于事項法假設信息提供者不完全了解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而其目標又與價值法相同,即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這就使得事項法下被會計記錄的信息內容只能取決于信息提供者的信息提供能力,而非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二、事項法下會計信息的記錄
事項法下對會計信息的記錄是對“事項”的第一次反映,也是會計信息最終得以呈現的前提和必要條件。如何記錄會計信息這個問題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事項法下應當記錄哪些事項,其二則是從哪些角度來記錄這些事項。前者實際上是事項法中“事項⑨”一詞的定義問題,而后者實際上是選取事項的哪些特征進行記錄的問題。盡管前人文獻中對于這一問題也有所討論,但在討論過程中忽視了事項法下信息提供者不完全了解信息使用者信息需求這一前提假設,因此本文將根據這一假設對上述兩個問題逐一進行討論。
(一)對“事項”定義的再探討
關于“事項”的含義,Sorter[2]在首次闡述事項會計理論時,把“事項”稱為“經濟事項”,是“可能在各種決策模型中有用的相關經濟事項”。但其并未對“經濟事項”展開進一步的論述,同時由于本文假設信息提供者只能了解信息使用者的部分需求,因此信息提供者只能對已知的信息需求范圍內的信息判斷其相關性,而對于已知信息需求范圍之外的信息并不能判定其相關性。同時Sorter 將“可能相關”作為判定標準,本文認為“可能”一詞又使得“事項”所能包含的內容可以無限延伸,而發生的各類事項都有可能會影響企業價值,所以這些事項都可能與估值相關。可見,Sorter 并未對事項做出明確的界定。Johnson[5]把事項稱為“一項行動、發生的事情或一個意外事件”,并且必須能夠觀察驗證事項的特定屬性,同時還提到事項應當既可以反映公司過去的經營成果又能預測未來經營狀況。盡管某一事項是否可以反映公司過去的經營成果是事項的客觀屬性之一,但判斷某一事項是否能反映經營成果則需要信息使用者來完成,就不可避免地會加入主觀因素。而事項法下由于不完全了解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因此只能由信息提供者代替使用者進行這樣的主觀判斷。盡管事項法并不拒絕會計人員的主觀判斷和整合,但同時被要求可以提供未經加工的原始數據,因此按照事項法的思想以及Johnson[5]對事項的定義,公司的各類事項都應當被會計人員記錄下來并對外披露。
此外,McCarthy[8]在設計會計信息系統時將會計信息要素分為經濟資源(R)、經濟事項(E)和參與者(A),并將經濟事項定義為“反映由生產、交換、消費和分配而導致稀缺財富(經濟資源)變化的一類現象”,但其并未說明企業的哪些事項不屬于這樣定義的經濟事項,甚至企業所有事項都可能屬于這樣的經濟事項。嵇建功[7]認為價值狀態之間的變化構成經濟事項,經濟事項是不可再分的,是事項法下最小單位的會計信息,經濟事項也被稱為基本事項。他還指出,企業最日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屬于作業事項,作業事項經過提取、組合并在這一過程中保持客觀性后形成經濟事項。然而他對價值狀態以及作業事項的概念并沒有進行明確的闡述,就難以判斷作業事項與經濟事項的區別,事實上依然沒有解決事項法下事項的概念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發布的修訂版《國際會計準則概念框架》認為,財務報告提供的信息應當包括報告主體經濟資源方面的信息、對報告主體要求權方面的信息以及改變上述資源和要求權的交易、其他事項及情況的結果方面的信息⑩。盡管按照Sorter[2]的邏輯推理,《國際會計準則概念框架》屬于價值法而非事項法,但價值法和事項法在會計目標上是一致的,并且前人對于事項法下“事項”一詞的定義也著重于反映公司經濟資源或價值的變化,因此本文借鑒《國際會計準則概念框架》的思想,將事項法中的事項定義為“報告主體的經濟資源和對應的要求權以及經濟資源和要求權的變動?”。
(二)如何對事項進行記錄
在初步明確了事項(事項法下的會計對象)的含義之后,下一個問題則是應當從哪些方面對事項進行記錄和反映(相當于確認和計量)。Sorter[2]只提到了應當提供有用的相關事項的信息。Johnson[5]對Sorter 的論述進行了完善并認為事項“可以用無限多數目中的一個或多個性質、屬性或特征來描述”,同時指出“應當排除所有出于當前目的被認為是無關緊要的屬性,例如銷售商品時的大氣溫度和濕度,銷售員和買方的性別、年齡、種族、宗教、新陳代謝、心理狀態和交易中花費的時間”,此外他還認為事項的貨幣特征以及預測屬性應當是最重要的特征。但是本文認為,除了在不完全了解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這一假設下無法判斷哪些屬性無關緊要,Johnson對于貨幣特征的強調實際上與Sorter提出的事項法下貨幣計量和非貨幣計量混合使用直接相矛盾,在這種強調貨幣特征的情況下,事項法會計最終記錄下來的信息自然也是以貨幣計量信息為主,在最終呈現時可能與價值法下的會計信息并沒有明顯差異。嵇建功[7]認為,在最初記錄事項時最重要的信息是事項的歷史價值信息,并認為這類交易信息以三種形式存在:一是一般等價物即貨幣本身,或以貨幣作為交易對象;二是交易價格及其給付;三是交易時間信息,因時間價值理念而成為價值信息,而他在論述這類信息為何重要時依然認為提供這樣的信息能夠最大化信息使用者的效用,同樣暗含了完全了解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假設。
由此可見,以往文獻中的觀點依然包含了對信息相關性的考慮,即這些觀點均建立在完全了解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基礎之上,這與本文分析的前提——信息提供者不完全了解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相矛盾。在本文的假設下,盡管部分信息需求已知,但已知信息需求外的事項如何從信息使用者的角度出發進行記錄實際上不得而知?,并且事實上在選擇描述事項的哪些方面時只要從信息使用者的角度考慮就假設已經知道了其信息需求。本文認為,在信息使用者需求不完全已知的情況?下,只能從信息提供者一方來定義需要進行描述的屬性。事項法下財務會計的目標依然是為信息使用者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信息,但由于并不能完全了解其信息需求,因此如果不考慮提供和處理信息的成本的情況,為了實現事項法下的會計目標,信息提供者應當在記錄時就盡可能將自己能夠記錄下的屬性記錄下來?。
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能夠”也有兩種含義:一種是在不考慮對外提供信息的財務會計活動時,企業本身就會因生產經營需要而進行收集的屬性或信息;另一種則是企業有能力或不知道自身有能力收集屬性或信息,但不考慮對外提供信息的財務會計活動時不會進行記錄的屬性或信息。出于可行性以及盡可能不影響企業其他生產經營活動的考慮,本文定義的被事項法會計記錄下來的屬性或信息應當是“不考慮對外提供信息時,企業自身就會收集的信息”。
三、事項法下會計信息的整合與呈現
傳統會計下的信息列報與披露本質上依舊是對經濟活動“反映的反映”,與此相對應,本文前面討論了事項法會計中事項的概念和從哪些維度屬性來記錄這些事項,這些內容屬于從事項到信息生成的第一個環節,即對事項的“第一次反映”,而信息的生成到最終呈現可能還要經歷“第二次反映”的整合過程,即信息列報和披露的問題。在事項會計的框架之下,本文暫且不考慮信息是否最終會以若干張報表的形式輸出,而關注的是:傳統會計下對經濟活動的“第二次反映”是否也存在于事項法會計之下?如果這種“第二次反映”存在,那么事項法會計中會計信息是以何種形式呈現的?
(一)會計信息整合的必要性
事實上,對于事項法會計之下是否存在“第二次反映”這一問題,已有研究并未就此達成一致結論,一方面很多研究沒有直接回應這一問題,另一方面部分學者否認“第二次反映”的存在[14]。本文認為對這一問題的回應,需要從Sorter[2]對事項法的提出以及事項法的本意中來尋找答案。
Sorter 認為,事項法會計與傳統會計的區別在于“會計報告中何種程度的整合與評價是合適的,以及由誰來進行整合與評價?”。盡管本文并不認為對信息的整合程度是事項法會計與傳統會計的本質區別,但Sorter 的論述至少佐證了信息整合程度的差異是區別事項法會計與傳統會計的一個重要特征。關于信息的整合水平,Sorter認為“考慮到當前的水平,較少而不是較多的整合是恰當的,使用者而非會計人員,必須對其預測一致的數據及效用函數進行匯總、指定權數和計值”。可以看到的是,Sorter 承認對信息的匯總聚合是區分事項法會計與傳統會計的主要區別,他認為傳統會計對信息的匯總聚合是過度的并因此導致了價值的損失。以損益表為例,損益表中的每一個項目至少都經歷了基本事項產生和將這些事項分配到特定期間的過程,而這種分配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信息的真實性。
Sorter 的判斷不無道理。此外,Johnson[5]認為“對于觀測到的結果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數學運算都具有經濟意義”。具體而言,很多信息(數據)的相加(減)其實是不具有意義的,照此邏輯進一步推廣,至少現行的資產負債表之中的很多數字其實并沒有經濟意義?。因此,Sorter和其他學者之所以對信息的整合有所顧慮,一方面是很多整合本身只產生了沒有經濟意義的結果,另一方面整合的過程確實也或多或少地伴隨著信息價值的損失。
然而,Sorter 并不否認對會計信息進行匯總聚合的必要性,正如他認為的,“會計人員的建議權數和評價值得傳達,但要確保使用者也能一直獲得可用的非加權的原始數據”[2]。盡管他強調匯總聚合應該由信息使用者來進行,但他仍然認為會計人員匯總聚合的方法和邏輯是有價值的,只是會計人員匯總聚合的結果應當具有可還原性,即信息使用者應該始終可以接觸到背后的原始數據,可以做出自己的匯總聚合。最后,需要明確的是,Sorter 所倡導的事項法會計強調的是對信息進行“更少”的匯總聚合,并未明確提及禁止信息的匯總聚合。總體上,以上這些分析至少說明了事項法會計在產生之初并沒有反對信息的匯總聚合。
當然,這些只能代表Sorter 作為一個提出事項會計理論的學者在寫作時的想法,而且對事項法會計的描述并不完善,很大程度上體現出來的只是一種理念,并不具有很強的實際可操作性。因此,如果進一步探討事項法會計之下是否應該對信息進行整合,還應該跳出Sorter的觀點。
回到提出事項法會計的本意,雖然事項法的理念在很多人看來是“既然無法知道所有人的信息需求,那么會計作為信息的提供者就不應該考慮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但是按照這樣的理解,不妨繼續思考:為什么在傳統會計理論之下仍有進行會計改革的要求,由之前的“考慮使用者的信息需求、為信息使用者提供決策模型輸入值”轉變為“不考慮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提供與信息使用者決策可能相關的信息”?不難發現,這樣的轉變本質上仍是對“如何使會計信息更好地服務于信息使用者決策”問題的優化方案,提出這樣的想法本身恰恰表明信息提供者對信息使用者的態度并非“不管不顧”。本文認為,事項法的本意其實是“如何更好地考慮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只是它的理念是以一種相對冷漠的方式傳遞對信息使用者的關懷。既然如此,在對經濟活動的第二次呈現上,依舊無法繞開信息使用者的問題,或者說信息使用者對信息的接收效果是事項法會計關注的重要議題,而這是由事項法會計的本意和初心所決定的。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盡管有許多實例證明了信息的過度整合會造成對信息價值的損害[2],但需要注意的是,信息的過度顆粒化也會造成對信息價值的損害。所謂信息價值,指的是信息影響使用者決策行為的能力,而企業經濟活動中的很多事件及其屬性總是以關聯的形式出現的,這些聯系使得信息使用者可以完整和具象地理解經濟活動的實質和真實面貌,一味地追求信息呈現的極致顆粒化、強行割裂某些信息之間的關聯其實是沒有必要的,還可能會阻礙信息使用者對信息的接收和消化,或者分散其注意力,增加其決策的難度。另外,也有一系列研究通過實驗分析了信息整合水平對信息使用者決策行為的影響,Benbasat 等[10]發現,認知風格的差異(分析與啟發式)對決策者所需的信息匯總水平具有顯著影響。總體而言,信息的顆粒度并非越細越好,所提供信息的詳細程度應該取決于問題的類型和決策者的決策水平[16]。因此,就輔助信息使用者做出決策而言,細顆粒度信息并不必然優于高度整合的信息。此外,根據前文的假設,事項法下只是不完全了解而非完全不了解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因此對屬于已知需求部分中的信息,可能在何種程度上進行整合更能滿足信息使用者需求也是已知的,出于更好地滿足信息使用者需求這一目標,事項法在最終對外呈現會計信息時也并不會一味地追求細顆粒度信息。
最后,從事項法會計的具體應用來講,事項法會計的實現最終必然要借助于具有強大計算能力和信息存儲能力的會計信息系統,而信息的匯總聚合對于信息系統的設計非常重要[17],因為其與信息的報告布局和用戶界面設計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也進一步說明了事項法會計之下的信息呈現即便從應用層面進行考慮,也不應該是完全零散和碎片化的。
因此,無論是從Sorter 對事項法會計的提出還是從事項法“更好地考慮到使用者的信息需求”的本意及其實際應用來看,即便是在事項法會計的框架之下,“第二次反映”依舊具有絕對的存在合理性,這與傳統會計并沒有區別。進一步而言,事項法會計與傳統會計在信息的整合問題上確實有差別,但這并不是二者的本質區別,事項法會計之下的信息也應該是整合和結構化之后的信息,其與傳統會計在信息的整合程度和整合方式上存在一定的不同之處,但這本質上是由對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假設所決定的。
(二)會計信息整合的方向
在明確了事項法之下對會計信息進行整合的必要性之后,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對事項法之下的會計信息進行整合,即對事項的“第二次反映”是如何實現的?需要明確的是,現有文獻中很少提及如何對事項信息進行呈現?,因此本文僅僅從理論上嘗試進行一些方向性的探索,對事項法會計信息系統設計中技術細節的分析并不在本文的討論范疇之內。
首先,Sorter[2]提出的“整合”仍是一個十分寬泛和模糊的概念,本文認為其只是提出了減小會計信息顆粒度的要求或建議,而具體顆粒化到什么層面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這也直接導致后續研究在是否需要匯總聚合以及在什么層面上進行匯總聚合的問題上產生了巨大的分歧。在一系列討論之中,Johnson[5]的回應尤為重要,他提出了對會計信息進行整合的不同層次,為后續的分析探索奠定了基礎。
Johnson[5]認為,一般意義上的“整合”主要指的是加法的數學運算,需要注意的是,他這里所說的加法實際上也涵蓋了減法、乘法和除法這些數學運算。從整合的結果來看,信息的最終形式并不會透露其生成的詳細過程。這是Johnson 理解的“整合”的一般性特點,進一步地,他將整合劃分為三個互斥的不同層次,分別為加總(aggregation)、結合(combination)和組合(composition)。在其分析框架下,加總指的是對同類事情同一特征的相加,它可以是時間維度上的相加,例如將單個公司的銷售相加以獲得一段時間內的總銷售,也可以是截面維度上的相加,例如將多個公司的資產相加以獲得特定日期的行業總資產;結合指的是對不同類事情的同一特征的相加,它可以是時間維度上的相加,例如一個公司進行廣告宣傳所發生的費用和它在后續期間所發生的銷售額進行相加(減),也可以是截面維度上的相加,例如將同一期間的現金收入與現金支出合并之后得到凈現金流;組合指的是對不同類事情的不同特征進行相加,與前兩種層次相比,信息組合的形式是高度復雜的,它甚至不需要像傳統的資產負債表或者利潤表那樣試圖得到一些確定的金額或者數字,組合可以包括對不同類事情的貨幣量金額和實物量的匯總聚合。
通過上述含義不難發現,這三個層次下的信息整合程度是不斷上升的,這也暗示著信息損失的不斷增加以及對底層信息進行還原的難度不斷提高。尤其是就信息損失而言,即便是最低層次的整合——對同一類事情同一個特征的加總,也會導致一定程度的信息損失,本質上信息損失的發生在信息整合的過程之中是無法完全避免的。然而信息整合程度的上升也伴隨著其他的一些特征:一方面是信息冗余的減少,這種減少可以緩解不相關信息對使用者注意力資源的占用,節省信息處理時間,提高信息處理效率;另一方面是信息結構和層次的愈加分明,因為對信息進行整合的過程也伴隨著信息的分類,而對事物的分類是知識結構化的一個重要前提,可以顯著地改善信息接受者的學習效果,而且對于需要自主整合信息的使用者而言,其事前需要明確有哪些類型的事情以及每一類信息有怎樣的特征,信息的分類為使用者掌握其面臨的信息的全貌提供了必要條件。因此,對事項的“第二次反映”即信息的整合,其最優方向本質上體現為“信息損失的增加”和“信息冗余的減少與信息結構的更加分明”之間的權衡。而考慮到信息損失的必然性和對信息進行結構化整合的必要性,本文認為在最低層次上對信息進行整合是比較合適的,即對同一類事情的同一個特征進行整合匯總?。
最后,正如本文之前所提到的,即便是最低層次的整合也會導致一定程度的信息損失,而損失的這一部分信息可能在有些情況下對決策者而言是至關重要的。Sorter[2]曾經提到“要確保使用者也能一直獲得可用的非加權的原始數據”,與此對應,Havelka 等[17]在對信息系統的討論中也認為“信息系統還應該為用戶提供足夠的靈活性,以便允許用戶通過特定的聚合方式訪問用戶所需的盡可能多的詳細信息”。基于以上考慮,本文認為,除了對信息進行必要性的整合,設計交互式的信息系統也是非常必要的,借助這種信息系統,信息使用者可以實現對低顆粒度信息的還原,而且信息使用者還可以進行必要的信息檢索,以支持其構建適合自己決策模型的整合數據。這也應該成為事項法會計之下信息呈現的一個重要方面。
(三)現有場景下事項法會計理念的應用
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無疑為事項法會計提供了更為便捷的應用場景。以物聯網技術的應用為例,物聯網通過各種信息傳感設備將所有物品與互聯網進行連接,建立起可以實現物體信息智能化交換、定位的一體化網絡,對傳統會計信息系統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實際上,物聯網技術促進了信息和實物的直接關聯,一方面極大地提升了信息的真實性,使得所有會計信息的記錄“有據可循”,另一方面有助于實現信息的實時化處理,較大程度地控制了由人工錄入所導致的干擾因素,提升了數據信息的客觀性。總體而言,物聯網技術為事項法會計之下的“第一次反映”提供了可靠高效的輔助工具,也已成為越來越多的企業在數字經濟浪潮之下的選擇。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如此,在會計信息的“第二次反映”中,對信息的適度整合仍舊是必不可少的。以聯發紡織(SZ002394)為例,該公司所建立的會計信息系統較為完整地體現了業財融合的理念。通過將會計信息系統與物聯網技術相結合,幫助企業實現了信息獲取與收集的自動化和智能化,促進了“信息流、資金流和物資流”的“三流合一”,既節約了成本,也緩解了人為因素所導致的不良影響。企業將發貨、銷售、訂單處理、資金管理與綜合查詢等業務活動直接與會計信息系統對接,提升了各個環節的工作效率和財務的智能化水平。在銷售系統中,不同交易所涉及的金額與票據仍需要財務部門匯總,在此基礎上公司在會計信息系統中嵌入了綜合查詢模塊,為企業和客戶提供各種具體信息的查詢。概括而言,銷售核算模塊強化了信息的統籌與匯總功能,而信息使用者則可以根據自身需要采用“多條件多組合”的方式進行匯總。
事實上,聯發紡織所建立的融合了物聯網技術的會計信息系統較好地體現了本文所論述的事項法會計理論,以物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為信息生產者的信息提供能力帶來了質的飛躍,直接提升了“第一次反映”中信息的實時性、真實性與可靠性。然而,會計信息并非僅僅停留于此層面,不同交易所生成的會計信息仍需要進行必要的匯總整合,而綜合查詢模塊的嵌入事實上也反映了交互式系統的理念,為具有不同信息需求的信息使用者按照各自偏好進行信息整合提供了實現空間。正如陳虎等[18]所提出的,實現財務數據質量的全面提升與構筑良好的數據生態,需要企業理清各方對財務數據的需求,在此基礎上整理財務數據資產目錄。因此,對數據的匯總整合是必不可少的。當然,技術前進的步伐并不會停止,無論是聯發紡織的會計信息系統亦或是“大智移云物區”都只是這個時代的特定縮影,事項法會計的變革仍未到達終點,但此刻其展現出的方向是符合本文預期的。
四、事項法下的會計準則
在前文對事項法下會計應當記錄哪些內容以及最終如何對外呈現信息的分析基礎上,在這一部分中,本文進一步討論事項法下是否需要會計準則、如果需要則事項法下的會計準則應當包含哪些內容以及與傳統價值法的會計準則有何區別。
根據前文分析,事項法下“第一次反映”的內容(會計記錄)完全取決于信息提供者的信息提供能力;而在“第二次反映”(對外呈現)中,雖然可能需要對信息進行整合,但由于交互式信息系統設計使得信息使用者可以自由構建和使用所需的決策模型以及輸入值,因此每一個信息使用者通過自行設置得到的同一家公司的相關會計信息可能存在顯著差異,相當于很大程度上由信息使用者自身來決定最終呈現哪些信息。因此根據前文論述,這一完整的流程似乎并不需要制定會計準則,只需要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之間的互動即可實現。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本文已經假設信息提供者不完全了解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因此會計信息的記錄和提供只能從提供者的角度出發。與價值法從使用者的需求出發規范信息提供者記錄和對外呈現的信息相比,這會產生新的問題,即信息提供者對于某些概念和術語的定義與信息使用者的理解可能存在差異,甚至不同的信息提供者之間對于同一概念和術語的定義(若不加以規范)也可能會存在差異?,然而由各信息提供者分別說明其所使用的定義可能需要較高成本,并且對于同時跟蹤多家公司的信息使用者而言,其面臨的信息處理成本也是不可忽視的。由此,本文認為,需要事項法下的會計準則對相關術語的名稱以及定義進行規范,使得信息提供者之間以及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間對于同一概念達成一致,進而才能夠有效地利用事項法下呈現的會計信息進行后續的決策。
因此,事項法下依然需要會計準則,其主要內容應當是說明事項法下涉及的各個術語和概念以及其具體定義,與傳統價值法下的會計準則相比,事項法下的會計準則更應當像是“字典”,以供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查閱相關術語及概念定義。
五、總結
隨著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和現代商業模式的不斷變革,事項法會計受到了理論界和實務界越來越多的重視。事項法的概念最早由Sorter在1969年提出,但此時其對事項法中事項的概念以及信息的整合程度的論述并不清晰,從某種意義上講,Sorter[2]只是提出了減小會計信息顆粒度的要求或建議,而這引起了后續眾多學者的討論。本文從會計信息形成到最終呈現所經歷的兩個階段切入,討論了事項會計對事項的兩次反映,最終簡要分析了事項法下會計準則的內容與作用。本文認為與傳統會計一致,事項法之下的會計信息也要經歷記錄(第一次反映)與最終呈現(第二次反映)兩個階段,只是在兩次反映的方式上與傳統會計存在著一些細節上的區別,而事項法下的會計準則應當是對兩次反映中涉及的術語及其定義加以規范和統一。
從會計信息的“第一次反映”來看,雖然Sorter最初提出事項法這一設想時并沒有假設信息使用者的需求(部分)未知,但本文認為這是事項法與價值法的本質區別所在。在這一假設之下,會計記錄(第一次反映)的內容無法由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來決定,而只能由信息提供者一方來決定,因此在這一假設下,事項法下的會計信息內容最終取決于信息提供者提供信息的能力。
關于信息的整合與呈現,盡管有很多文獻和研究認為事項法之下會計信息的最終呈現形式應該是非結構化的,即在完成對事項信息的記錄之后,所謂的“第二次反映”是沒有存在的必要的,但本文認為這樣的觀點有失偏頗。首先,從Sorter 提出事項法會計時的論述來看,他雖然認為信息整合程度是事項法會計與傳統會計的一個主要區別,但并沒有完全否定對會計信息進行整合的必要性;其次,事項法提出的本意是更好地考慮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這也決定了事項法之下的會計信息呈現最終無法回避使用者對信息的接收問題,而追求極致顆粒化的信息既破壞了信息之間的內在聯系,也降低了信息使用者的認知效率;最后,就事項法會計的現實應用和會計信息系統的設計而言,對會計信息進行整合與匯總也是必要的。另外,關于如何呈現事項法之下的會計信息,本文也提出了一些方向性的建議。本文認為,在最低層次上對信息進行整合是比較合適的,即對同一類事情的同一個特征進行整合匯總,而考慮到最低層次的整合所造成的信息損失,交互式會計信息系統的設計也是非常必要的,借助這種信息系統,信息使用者可以實現對低顆粒度信息的還原,以及在自主檢索信息的基礎上構建適合自己決策模型的整合數據。
在上述兩次反映的過程中,信息也從信息提供者轉移到了信息使用者處,然而由于信息提供者并不完全了解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兩者對于同一術語或概念的定義也很有可能存在差異,因此本文認為事項法下的會計準則應當起到規范定義的作用,使得各方對于同一術語或概念的定義實現一致,進而降低信息使用者加工和處理信息的成本。
另外,本文的分析結果也體現了對事項法會計與傳統會計的比較,雖然有很多觀點認為二者的差別只在于信息的顆粒度,但是本文的分析否定了這樣的看法。本文認為,信息的整合并不只是出現于傳統會計中,在事項法會計之下也需要對信息進行結構化和整合,雖然整合的程度可能存在一定差別,但這種差別是可以被無限縮小的。而且,事項法會計與傳統會計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對經濟活動進行記錄時選取的維度和屬性,而這種區別本質上依然是因為對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假設不同所造成的。
【注 釋】
①“價值法”的概念最早是由Sorter[2]提出的,其主要指向傳統會計。為了方便討論,本文將傳統會計和價值法會計視為等同的概念,不再單獨分析“價值法”名稱設置的合理性問題。
②盡管也有可能是準則制定者或學者根據自身經驗以及對投資者調查的結果來猜測哪些輸入值或信息更為有用,但這種方法實質上依然是從信息使用者本身的角度來考慮提供哪些信息。
③原文為:The criticism must be met that the "events" approach relies just as heavily upon knowledge of users' models as does the "value" approach. ......Decisions as to what events are relevant(surely not all events can be recorded)must be made and can only be made with users' needs in mind. Thus, the users' needs must still be known。
④原文為:...... less rather than more aggregation is appropriate and the user, rather than the accountant, must aggregation, assign weights and values to the data consistent with his forecasts and utility functions。
⑤原文為:......the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lies in what level of aggregation and valuation is appropriate in accounting reports and who is to be the aggregator and evaluator。
⑥由于本文只分析估值這一會計目標,因此即使不同信息使用者對于事項法下最終呈現結果有不同的理解甚至無法達成一致意見,也完全不影響其自身的估值決策。
⑦僅通過向所有信息使用者提供相同的財務報表不能滿足其信息需求。
⑧之所以做出這一假設,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事項法下提供的信息應當多于甚至包含價值法下提供的信息,因此事項法下提供的信息與已知信息需求的交集應當更大。
⑨相當于事項法下的會計對象。
⑩原文為:Financial reports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porting entity's economic resources,claims against the reporting entity and the effects of transactions and other events and conditions that change those resources and claims。
?本文認為事項法與價值法的會計對象可以是相同的,但是在具體的會計要素以及之后的確認計量方面兩者應當存在明顯差異。價值法下是從使用者需求出發來定義會計要素并進一步決定如何進行確認計量和列報,而事項法下應當是從信息提供者提供信息的能力出發定義對應的事項法下的會計要素以及之后的確認和計量。出于篇幅和時間限制,本文不對事項法下的會計要素設置進行討論。
?由于只了解信息使用者的部分需求,信息提供者只能確定某一事項的某一屬性是否屬于已知需求部分,不能判斷不屬于已知需求部分的事項或者事項的某些屬性是否與信息使用者決策相關。
?本文的分析中不考慮涉及商業機密或者企業不愿意披露相關信息的情況。
?盡管這部分描述完全從信息提供者而非信息使用者出發,但并不意味著事項法忽視了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恰恰相反,本文的論述正是考慮了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后的結果。在信息提供者不完全了解使用者信息需求的前提下,為了滿足信息使用者可能的多樣化的甚至是信息提供者未知的需求,信息提供者只能通過盡可能多的提供信息來實現;如果忽視信息使用者的需求,那么信息提供者只需要根據已知的信息需求提供相關會計信息即可。
?原文為:As has been indicated, the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lies in what level of aggregation and valuation is appropriate in accounting reports and who is to be the aggregator and evaluator。
?這里最常為人所詬病的就是所有者權益的計算,現行會計準則對所有者權益的定義大多為“企業的資產在扣除負債之后的剩余利益”,首先,會計準則中的資產與負債屬于完全不同的范疇,兩者之間并不存在交集,因而所謂的扣除是沒有任何意義的[15]。另外,即便以資產的價值減去負債的價值,最終得到的結果所代表的經濟意義也不甚明確,無論是對于實現清償權還是股份交易都沒有太大的相關性。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暫且不討論事項法會計之下的信息系統如何設計的問題。
?目前,較多學者均反對在事項法會計之下信息提供者對事項信息進行匯總聚合,并認為事項法之下信息的最后呈現是非結構化的,因此對如何整合信息的討論是非常不充分的。
?Johnson[5]提到的信息整合方式并沒有跳出對信息進行數學運算的范疇,但本文認為事項法之下的會計信息并非都可以進行數學運算,如描述事物性質的文字信息。本文這里提到的整合是廣義上的整合,其針對的對象既包括可運算的信息,也包括不可運算的信息,前者的整合指的是進行某些數學運算,而后者的整合是將符合條件的信息在分類之后儲存在同一模塊中。
?在傳統的價值法下,提供的一切信息及其含義由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決定,自然避免了不同信息提供者之間概念定義的差異,同時由于這些概念的定義本身由使用者信息需求決定,因此也就不存在信息使用者和信息提供者對于同一概念會出現不同定義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