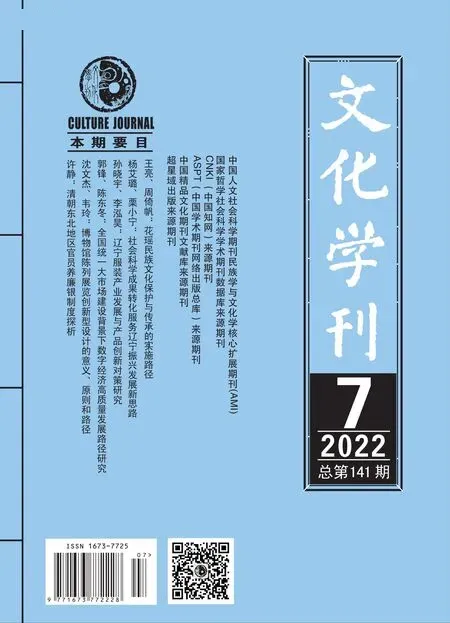翻譯傳播的時代要義
——從《建黨百年中國翻譯傳播研究》說開去
田會輕
王建華教授編著的《建黨百年中國翻譯傳播研究》,既回顧和總結了過往,又規劃與展望了未來,研究視野縱橫捭闔,引證材料豐富翔實,以獨特的認知框架繪制了一幅中國翻譯傳播的全景圖。在百年的發展歷程中,翻譯傳播契合黨的宗旨與使命,彰顯著深厚的家國情懷,體現出高度的責任擔當,匯集成積極的變革力量,促進了社會進步、國家昌盛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才是翻譯傳播的時代要義。
一、促進翻譯傳播的融合
《建黨百年中國翻譯傳播研究》一書開宗明義,將翻譯與傳播加以融合,直接援用“翻譯傳播”的概念進行論述:“總結中國翻譯傳播對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發展的貢獻會對未來中國社會主義強國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和指導價值”[1]“引言”1。此處既指明了本項研究的價值和意義,也揭示出作者對“翻譯傳播”這一概念的認可與肯定。翻譯與傳播的關系,曾在學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將兩者融合起來,其合理性愈益獲得認同。畢竟,翻譯就是傳播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不同文化間的跨語際傳播也不可能離開翻譯。在全球化時代,翻譯與傳播逐漸融為一體,翻譯已然成為跨文化的傳播行為,而傳播也往往借助翻譯才能達到目的。有了傳播學的視野,翻譯將不再是搬字過紙的語言轉換,而將更加注重傳播的媒介和接受的效果,既要考慮接受的環境,又要考慮接受的質量。正鑒于此,翻譯與傳播的結合,翻譯與傳播的融匯,將能結合兩者的長處,在當下的跨語際實踐中形成明顯的優勢。
從本質上說,在不同文化間的跨語際交流中,翻譯就是一種傳播行為,而傳播也是一種翻譯實踐。如果說翻譯是手段,傳播是行為,那么將兩者融匯起來的翻譯傳播將是一個綜合性的系統,這一系統,不僅解決了語際間的溝通和交流問題,更將這種交流引向寬廣的社會領域,以文化的標準加以衡量和確認,以文明的尺度進行比較和鑒別。借助傳播學的視域,吸納傳播學的范式,并在整個社會文化的參照系中重塑翻譯的面貌,就是要將翻譯與傳播結合起來,就是要確立翻譯傳播的學理性,而這種學理性于當下尤為重要。只有在翻譯與傳播相互融合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更好地揭示人類交流活動的內在邏輯,才能更好地闡釋人類溝通領域的復雜現象。可以說,翻譯傳播,將翻譯學、傳播學和社會學相結合,從而賦能翻譯傳播,使其疊加優勢越發鮮明,在新時代必然大有用武之地。“翻譯傳播效果的產生機制就是翻譯傳播的內部要素與外部因素發生影響并相互作用的方式,翻譯傳播效果的產生是內外動因共同作用的結果”[2]。這從王建華的編著中得到了清晰的呈現,該著深諳個中三味,始終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諸多要素出發來確定翻譯的位置與功能,而這正是翻譯傳播的要義,也是翻譯傳播立足新時代、展示新作為的契機,翻譯傳播必將站上更為寬闊的平臺,迎來更為宏大的空間。
立足新時代,翻譯傳播的時代要義內涵更充實、外延更豐富,其所承擔的歷史使命更偉大,所面臨的任務也更艱巨。職是之故,翻譯傳播更須沉潛自身,通過學科反思,凝練自身特色,明確發展方向,集中攻堅克難,在新時代有新作為,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為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更加扎實的業績。
二、回顧翻譯傳播的歷史擔當
縱觀人文社科的各門學問,在推動民族復興、助力國家富強和服務社會進步方面能夠產生如此重要影響的,翻譯傳播不說無出其右,也堪稱居功至偉。《建黨百年中國翻譯傳播研究》一書,分別對建黨前后、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時期、習近平新時代的翻譯傳播情況進行了研究。該著指出:“近代的翻譯傳播活動不僅開啟民智,推動科技進步,促進社會變革,帶來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同時它也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走向偉大復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8。及至建黨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3]。這四項偉大成就,同樣有翻譯傳播人的奉獻,翻譯傳播始終站在時代前沿、引領思想風潮、傳播進步理念、激勵科技發展,促進文化繁榮,推動社會進步,為國家的富強提供智力支持,為民族的繁榮提供思想啟迪,一言以蔽之,翻譯傳播擔負起了自身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職責,充分秉持了翻譯傳播的時代要義。
回望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在積弱積貧的困境里,在備受欺凌的屈辱中,一代代仁人志士苦苦求索救國之道,“汲汲孕育青春中國之再生”[4],曾困惑于器不如人和技不如人,曾恍惚于制度的落后和文化的保守,革新求變屢屢難如人愿,救國方案頻頻無功而返。終于,我們的革命先驅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大地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自此,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歷經艱苦卓絕的革命生涯,新中國屹立在世界東方;我們經過篳路藍縷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社會主義事業有了穩固的根基;我們銳意進取、改革開放,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變革。
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無數革命先烈值得緬懷,無數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令人崇敬,多種學科專業也齊頭并進,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重要力量,翻譯傳播便在其中。翻譯傳播,幫助先賢“開眼看世界”,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引進西方的思想理念;翻譯傳播,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送來了社會主義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事業中,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翻譯傳播更是交流與合作的橋梁,是社會發展與進步的關鍵。翻譯傳播,讓馬克思主義傳布中華大地,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出累累果實,讓中國有了共產黨,讓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各個歷史進程的豐功偉績。翻譯傳播的時代擔當,也將彪炳史冊,成為一座學術史和民族發展史上的豐碑。
三、展望翻譯傳播的新時代前景
《建黨百年中國翻譯傳播研究》指出,邁入新時代的歷史方位,“翻譯傳播什么?如何進行傳播?如此進行的翻譯傳播對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都有什么貢獻?”[1]302要解答這些問題,翻譯傳播必須進行全方位的調整,將自身納入黨和國家的涉外戰略中,以提升黨和國家對外傳播能力為宗旨,全方位地服從和服務于黨和國家的對外傳播大局。
(一)翻譯傳播要積極應對新形勢和新挑戰
展望新時代,我們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我們要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我們要推進“一帶一路”高質量高水平發展;我們要促進人文交流,強化文明互鑒;我們要構建中國特色學術話語、學科話語和話語體系;我們要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要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國家形象。這都是對翻譯傳播工作提出的新期許和新要求,也是翻譯傳播把握新機遇、直面新挑戰、完成新使命的戰略契機。如今,我們的國家已經強起來,正在接近民族復興的光明前景,翻譯傳播更要結合實際、奮發有為,勇于進取、履職盡責,著力于紓解新時代跨文化交際和流通中的現實問題。我們的綜合國力顯著提高,我們的國際地位日益重要,但我們的國際話語權卻相對較弱,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外部輿論環境還亟需改進,我們時不時還會陷于經濟爭端和貿易摩擦,還會遭遇某些核心技術領域的“卡脖子”現象。面對此種情形,我們更須凝聚起磅礴的力量,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而加強國家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更是重中之重,其間翻譯傳播自然責無旁貸。
(二)翻譯傳播要著力打造標識性中國話語和完備的中國敘事體系
展望新時代,我們尤需打造標識性中國話語,尤需打造完備的中國敘事體系,尤需構建完善的大外宣格局,而這正是翻譯傳播的努力方向。我們需要一系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需要既能有效闡釋中國經驗,又能贏得國外理解、接受和認同的中國敘事話語體系,顯著提升我們的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和國際輿論引導力。隨著翻譯學、敘事學和傳播理論研究的新進展,學界對標識性概念愈發重視,對敘事理論體系愈發倚重,“干得好不如說得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客觀現實。這就昭示我們,面對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日漸增多的國際社會,如何將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講述好,如何將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形象敘述好,如何將中國特色、中國經驗、中國智慧表達好,實在是迫在眉睫的重大課題。我們既要精選內容,走“內容為王”的正路,又得設計具體、鮮活、生動的翻譯傳播方式,更要采取富有感染力和溝通性的翻譯傳播途徑。有時據理力爭的論辯交鋒很有必要,有時排山倒海的力量感必不可少,有時春風化雨的溫情更能觸動人心,有時真實感人的小故事更有說服力。翻譯傳播,向來以傳播媒介以及接受環境為重,這為翻譯傳播提升受眾效果提供了保障,也為我們努力打造新時代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翻譯傳播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展望新時代,翻譯必須著眼于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必須著力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今世界,種種問題仍然不斷帶來困擾,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陰魂不散,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還不平衡,資源掠奪和資本壓榨仍然存在,環境破壞和生態危機未能杜絕,經濟制裁和地區沖突時有發生,全球治理赤字異常凸顯。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的成功實踐和文明成果,能夠為世界共享自己的智慧和經驗,提出解決人類共同面臨問題的方案,有效促進全球治理向著更加均衡和健康的方向發展。而要實現這一目標,翻譯傳播當是應有的題中之義。不爭的事實是,我國現在面臨著嚴峻的國際態勢,某些強權國家大搞身份操演和政治操弄,搭建小圈子、結成新幫派,對我國進行圍堵和打壓。對此,我們尤須增強對外傳播能力,全面闡述我國的發展觀、文明觀、安全觀、人權觀、生態觀以及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觀,以真正的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引導塑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建設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翻譯傳播要切實提高自身能力,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要深化交流、擴大合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爭取和創造更好的國際環境。
(四)翻譯傳播要切實增強針對性、策略性和藝術性
展望新時代,翻譯傳播任重道遠,翻譯傳播必須加強自身建設,增強實際工作的針對性、策略性和藝術性。《建黨百年中國翻譯傳播研究》列舉了人文交流的眾多實例,對跨文化傳播交流的重要性多有強調:“我們要將翻譯傳播實踐置于多元文化語境下加以考察,既要警惕文化中心主義對本民族文化的沖擊,也須擺脫文化中心主義的偏見,保持開放的心態接納世界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積極促進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與共同繁榮”[1]238。如果說近代以后的翻譯傳播,曾一度以“譯世界”為特征,更多地將國外的資源引介到中國,促進了中國的進步與發展,那么,現在和今后我們將更多地“譯中國”,將中國的發展經驗和文明成果推介給世界,促進世界各國的發展與繁榮。這一歷史性轉變,綜合地體現了我們翻譯傳播工作的現實針對性。在我國近年來的傳播實踐中,借助網絡和新媒體,拓寬宣介和傳播的平臺渠道,對重大問題及時有效發聲,更是當下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途徑。舉辦豐富多彩的活動,開展生動多樣的交流,促進民心相通和交流合作,會逐步形成我們自身的翻譯傳播優勢。在國際傳播實踐中,我們尤須反觀自身,尤須講究傳播策略,尤須注重翻譯藝術。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要采用貼近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不同群體受眾的精準傳播方式,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區域化表達、分眾化表達,增強國際傳播的親和力和實效性”[5]。只有更加注重策略和藝術,我們的翻譯傳播才會更有時效和實效,我們的翻譯傳播才能更好助力新時代宏偉目標的實現。這就從更大層面對翻譯傳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貴的是,《建黨百年中國翻譯傳播研究》為新時代的翻譯傳播研究積累了文獻學基礎,提示了方法論路徑,開啟了學科化道路,設定了精準的目標,并喻示了光明的前景。
四、結語
無論是近代的苦苦求索,還是建黨前后的孜孜矻矻,抑或建國后的勤勉有為,包括改革開放時期的銳意進取,翻譯傳播始終站在歷史潮頭,秉持時代要義,紓解時代之困,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績。其實,也正是翻譯傳播的時代要義,決定了它的價值與活力。如今,處身新時代,翻譯傳播的前景將更廣闊,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中,我們有理由相信,翻譯傳播必將再次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