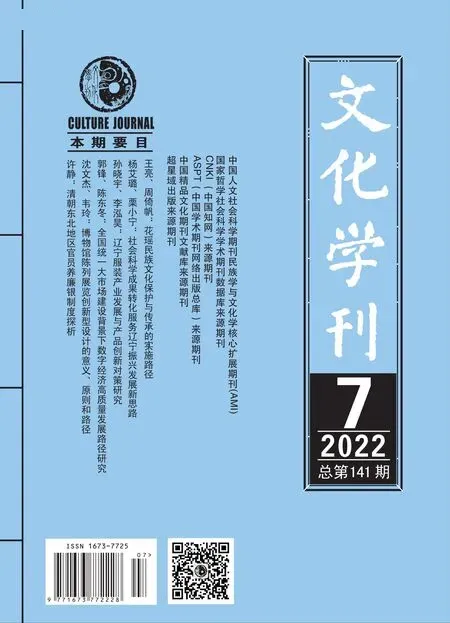通假字與同源字的交叉關(guān)系及其成因分析
殷 亮
一、引言
同源字與通假字是通過不同方式而產(chǎn)生的兩種不同的文字現(xiàn)象,學(xué)術(shù)界對于兩者關(guān)系的態(tài)度分為兩種。一是認(rèn)為二者毫無聯(lián)系不能混為一談,另一種則認(rèn)為二者存在交叉關(guān)系。張覺(1988)指出假借字和同源字完全是兩個不同性質(zhì)的問題。張嚴(yán)均(2019)認(rèn)為有一些字組既是本字和通假字的關(guān)系、又是同源關(guān)系,有交叉關(guān)系的一組字有義素層面的聯(lián)系。牟玉華(2004)肯定了通假字與同源字的交叉關(guān)系的存在同時指出交叉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在很大程度上是音節(jié)表義的結(jié)果。目前,兩種爭論依然存在,所以繼續(xù)研究二者關(guān)系極為重要。本文分析了前人的觀點,依據(jù)相關(guān)釋例論證了同源字與通假字的交叉關(guān)系,同時分析了這種交叉關(guān)系生成的原因。
二、通假字和同源字的關(guān)系
(一)同源字與通假字的判定
王力在《同源字論》當(dāng)中表述道:“凡音義皆近,音近義同,或義近音同的字叫作同源字。”[1]同源字的確定條件是音義皆近,并且由同一個詞根分化。殷寄明在《語源學(xué)概論》中提出“語源相同的文字,兩個或者更多的文字記錄了同一語源,這些文字則為同源字”[2]陸宗達(dá)、王寧認(rèn)為“記錄同源派生詞的字群叫同源字,同源字是同源詞的書寫形式。”[3]從以上幾家對“同源字”的界定來看,音近義通、具有同一語源是判定同源字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
“通假”是古書當(dāng)中出現(xiàn)的一種字形臨時借用現(xiàn)象。一個漢字可以記錄一個或者幾個詞,一般來說是確定的。但出于種種原因,古人在寫文章的時候,放棄本字不用,臨時借用一個音同或者音近的字去代替本字,這種現(xiàn)象就可以被稱作“通假”[4]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指出:“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這是許慎對造字法中的假借下的定義,而廣義的假借還包括本有其字的假借。這也就是王力在《古代漢語》中指出的本有其字的假借即為“通假”。
(二)同源字與通假字的交叉關(guān)系
有關(guān)同源字與通假字是否對立這一問題,學(xué)者們曾展開過深入探討,但目前學(xué)界還存在一定爭論,有無關(guān)和有關(guān)兩種說法。王力明確指出:“通假字不是同源字,因為它們不是同義詞,或意義相近的詞。”[5]楊合鳴指出通假字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即通假字與本字在意義上毫不相干;通假字與本字在聲音上相同或相近;通假字與本字同時并存[6]。蔣紹愚先生卻指出同源字和通假字并不是完全對立的。
廣義的假借不僅僅是指本無其字的假借,還包括本有其字的假借即通假。章炳麟《文始》云:“若本有其字以聲近通用者,是乃借聲,非六書之假借。”假借字與本字之間只存在語音上的相似,并不存在意義關(guān)聯(lián),這是傳統(tǒng)的看法。然而裘錫圭在其《文字學(xué)概要》中提出:“有意挑選意義相關(guān)的字作為假借字的情況也是存在的。”[7]事實上我們見過的許多假借字都與本字存在意義上的關(guān)聯(lián)。例如《漢語大字典》認(rèn)為“逸”與“佚”是假借關(guān)系,事實上存在同源關(guān)系;楊志賢(2011)考察了戰(zhàn)國簡牘文獻(xiàn)中通假字并發(fā)現(xiàn)其中客觀存在大量的同源通假字。
實際上“通假字”和“同源字”是兩種不同層面上的概念,通假字屬于一種用字活動,是不用本字而用同音字代替的書寫習(xí)慣,同源字是同源詞的書寫形式,實質(zhì)上是詞匯的孳乳現(xiàn)象[8]。雖然這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但因其都涉及了同音關(guān)系,所以從整體來看兩者之間存在交叉并存的可能,不能截然對立。很多著作認(rèn)為通假字和本字之間只有音近、音同的關(guān)系,不存在絲毫意義上的聯(lián)系。但事實上,我們見到的許多用例,其本字與通假字之間是存在意義關(guān)聯(lián)的。比如《史記·項羽本紀(jì)》中的“要項伯”,在這個語言環(huán)境中“要”與“邀”構(gòu)成了一對通假字。《說文解字》中解釋“要,身中也”本為腰之初文,又可以引申出“中道邀約”之義,這就使“要”與“邀”在意義上有了聯(lián)系。
意義相通的情況存在于同源字與通假字之間,就使得通假字與同源字之間產(chǎn)生了交叉。例如:“艾與刈”“說與脫”“辨與辯”“備與賠”“闕與缺”這幾組字當(dāng)中被通假字和通假字之間存在意義相近的關(guān)系,又為同源字,可稱為同源通假字。
三、同源通假字釋例
《古今通假會典》《常用古今通假字字典》《同源字典》中收錄了大量存在同源關(guān)系的通假字,這是論證同源通假關(guān)系的重要支撐。根據(jù)先秦古音以及古代的訓(xùn)詁包括互訓(xùn)、同訓(xùn)、通訓(xùn)、聲訓(xùn)等方式,可以判斷通假字與被通假字之間是否存在同源關(guān)系。
(一)“艾”與“刈”同源通假
艾和刈上古同屬疑紐月部,同音通假。艾的本義是草名,即艾蒿,供針灸用。《中華大字典》訓(xùn)為“灸草”。通刈。收獲,收割;引申為殺害,捨生。《集韻·廢韻》:“乂、刈、艾,《說文》:‘芟草也’。或從刀或從草。”艾和刈都有“芟草”這一語源意義。《禮記·祭統(tǒng)》:“草艾則墨”,鄭玄注:“草艾,謂艾取草也。”《國語·吳語》:“而又刈亡之”。注:“艾草則刈”綜上可以認(rèn)定艾與刈有同源通假關(guān)系。
(二)“闕”與“缺”同源通假
據(jù)宋陳彭年《廣韻》“闕:去月切”,“缺:傾雪切”兩者音近。《古今字通假字典》“闕”和“缺”上古同屬溪紐月部,同音通假。王力在《晉靈公不君》一文中對“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的注解可知“闕”通“缺”表過失之義。《論語·衛(wèi)靈公》:“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闕文,即缺文,缺漏的文字)《水經(jīng)注·江水》:“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闕通缺,作空缺講。王力《同源字典》器缺為“缺”,門缺為“闕”,兩者同源。“缺”小篆作 ,其形符為“缶”“缶”為瓦器,《說文》:“缺。器破也。”《玉篇》:“缺,虧也,破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下》:“缺王道之儀”《列子·湯問》:“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闕”小篆作,顯而易見其形符是門戶的形。《說文》:“闕,門觀也。”綜上二者具有音同義近同源通假關(guān)系。
(三)“辨”與“辯”同源通假
辨和辯上古同屬并紐元部,同音通假。辨的本義是分別,辨別。《說文》“辨,判分也。”如《戰(zhàn)國策·趙策》:“鄂侯爭之急,辨之急。”王安石《答司馬議諫書》:“故略上報,不復(fù)一一自辨”這兩個例句中“辨”皆通“辯”。《小爾雅·廣言》:“辨,別也。”《易·系辭下》:“辨是與非”虞注:“辨,別也。”《國語·齊語》:“辯其功苦。”注:“辯,別也。”《呂氏春秋·聽言》:“其有辯乎?”注:“辯,別也。”由此辨與辯同音同訓(xùn),同源通假。
(四)“說”與“脫”同源通假
《周易·蒙卦》“用說栓桔”高亨注:“說讀為脫,用說猶以脫。”《左傳·定公八年》:“陽虎說甲如公堂。”陸德明注“說”為“他話反”,即讀為“脫”。《詩·召南·甘棠》:“召伯所說。”《釋文》:“說又作脫。”可見《周易》《詩經(jīng)》《左傳》中的“說”字均已用于“捝”“脫”之義。《說文解字》言部:說,釋也。從言從兌,一曰談?wù)f。《說文》:“脫,消肉臞也”,從肉兌聲。徒活切。《漢語大詞典》記載脫有十八個義項,其中表赦免;解除;開脫這一意義時存在借“說”表“脫”的現(xiàn)象。例如:今本《詩·大雅·瞻卬》作“汝反說之”高亨注:“說,通脫、開脫”。 說與脫有同一聲符“兌”之字多有“解脫”“開解”義,如《說文》:“挽,解挽也。從手,兌聲。”說,脫的詞源意義為“掙脫”“解開”,是同源通假關(guān)系。
(五)“指”與“旨”同源通假
指和旨同音通假,上古同屬章紐脂部,指的本義是手指。《說文》:“指,手指也。通旨,意圖、意思。旨是會意字,甲骨文從匕,從口,《說文·旨部》:“旨,美也。”《淮南子·主術(shù)》:“發(fā)號以明旨。”《文子·精誠》旨作指。《史記·太史公自序》:“不通禮儀之旨。”《漢書·司馬遷傳》旨作指。
《呂氏春秋》“故布衣行此指於國。”注:“指,才酋志也。”指又作“旨”,《管子·侈靡》:“承從天之指。”注:“指,意 也。”手之所指也就是意之所指。因此二者都具有焦點,意圖指向的意義。綜上二者同源通假。
四、同源通假關(guān)系產(chǎn)生的原因
(一)漢字的音義結(jié)合規(guī)律
有同源關(guān)系的通假字在所有通假字當(dāng)中的比例高達(dá)68%[9]。通假字與被通假字之間存在同源關(guān)系是由于選取了音同、音近的字來表示本字。上古的同音字和同源字之間有很大的相關(guān)性,同音字在意義上有一定程度的聯(lián)系,具有相同的表意功能。因此,同音字當(dāng)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同源字。
語言產(chǎn)生之初,除了純粹的摹聲詞之外,大量的同音節(jié)詞的詞義存在一定的聯(lián)系。《荀子·正名》:“名固無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于約,則謂之不宜。”說明音義結(jié)合規(guī)律是具有約定俗成性的。然而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大量同音字出現(xiàn),舊詞引申到距離本義較遠(yuǎn)之后,在一定條件下脫離原詞而獨立,有的音雖無變但已成他詞。這種情況下音義結(jié)合就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
(二)漢字的語音表義功能
漢字形聲字的聲符不僅是表示讀音的符號,更重要的是它與語意有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而且大多數(shù)聲符相同的形聲字都有共同的語源義。眾多學(xué)者利用漢字的這種功能來探求字源。漢代劉熙的《釋名》即是以探源為目的著作,當(dāng)時的學(xué)者還沒有系統(tǒng)探源的觀念,只是就某一事物探求其來源,但能夠根據(jù)聲訓(xùn)的方法揭示同源詞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是很大的進(jìn)步了。王念孫的《廣雅疏證》,通過因聲求義的方式聯(lián)系同源詞,以聲音為紐帶研究字與字之間的關(guān)系。因聲求義注意于通假,音同音近的標(biāo)準(zhǔn)來界定通假字。類聚群分、同條共貫的主張突出表現(xiàn)在同源詞的研究上,為同源詞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王圣美的“右文說”從形音義出發(fā),以聲音為紐帶來考察同音通假字。
“右文說”在學(xué)術(shù)界產(chǎn)生有廣泛的影響,王圣美認(rèn)為形聲字的聲符可以表示語義,這種觀點也進(jìn)一步證明了語音有表義功能。如此,語音的表義功能進(jìn)一步證明了通假字和本字意義很可能相關(guān)。例如有一些形聲字的意義由兩個義素共同構(gòu)成:一部分是聲符所表示的核心義;另一部分是義符所表示的類別義。如瑕、霞、蝦、騢,“叚”為聲符標(biāo)志的是這組同源詞的核心義紅色;玉、雨、馬、蟲分別表示它們的類屬義。如果假借聲符相同的字來表示本字,也會造成同源通假現(xiàn)象。
(三)漢字在孳乳階段的混用
漢字孳乳初期是極不穩(wěn)定而又漫長的時期,分化字成為一個獨立的新詞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孳乳現(xiàn)象產(chǎn)生之后,孳乳字既表示派生義又有原詞義,也就是說,這一時期孳乳字和源字是混用的,正是由于這一點,一些學(xué)者就將同音假借字與同源通用字混為一談。陸宗達(dá)與王寧在《訓(xùn)詁方法論》中提出“同源通用”的概念,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同源通用”涵蓋了“同源通假”。由此,一些字從漢字孳乳分化的角度來看是同源字,而在使用過程中又被看作通假字。
(四)人們的心理作用
同源字與通假字交叉關(guān)系的產(chǎn)生也受到了人們心理作用的影響。即人們總是希望找到一個語音相近,意義又能盡量靠攏的字來替代本字。在為事物命名時,人們總是通過聯(lián)想尋找與舊事物的相似性特征,并不自覺地用舊有的讀音來表示新的概念的讀音,一定的語音和一定的意義就出現(xiàn)了某種聯(lián)系,在這一方面來說,音節(jié)就有了某種程度的表義功能。正是由于音節(jié)的這種表義功能,上古語音相同相近的詞很大一部分是同源詞。正因如此,古文獻(xiàn)當(dāng)中的通假字中存在同源關(guān)系的字占了很高的比例。
五、結(jié)語
同源關(guān)系與通假關(guān)系是否可以共時并存是學(xué)者們爭論已久的問題,本文認(rèn)為同源關(guān)系和通假關(guān)系可以交叉存在,并舉例分析了“艾與刈”“說與脫”“辨與辯”“闕與缺”“指與旨”的同源通假關(guān)系。同源字與通假字是不同層面的概念,同源字之間側(cè)重語義聯(lián)系,而通假字之間更注重語音關(guān)系,當(dāng)通假字之間存在一個相同或相關(guān)的意義貫通時可以稱本字和借字之間為同源通假關(guān)系。將通假字與同源字嚴(yán)格對立區(qū)分,認(rèn)為同源字絕不是通假字顯然不夠科學(xué),也不符合語言的事實。就其實質(zhì)而言,通假字和同源字本質(zhì)上并不是一個層面上的概念,二者的交叉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明確把握二者各自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就不會出現(xiàn)概念混亂情況。對于同源通假關(guān)系產(chǎn)生的原因,本文認(rèn)為有以下四種可能:音義結(jié)合的規(guī)律;漢字的語音表義功能;漢字在孳乳階段的混用;人們的心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