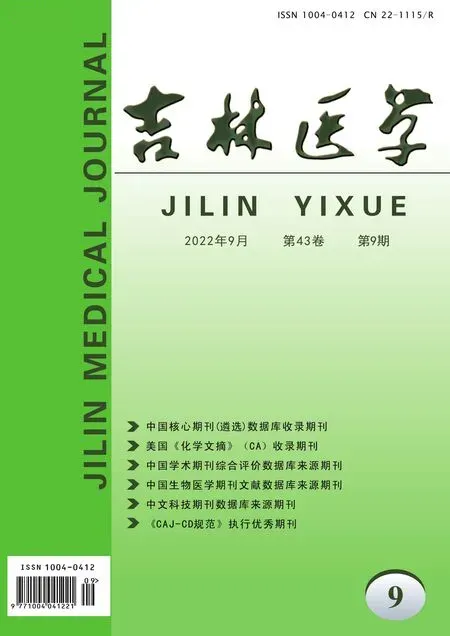生前預囑問卷調查與尊嚴死亡研究
——生命末期管理模式探索
袁 月,王靈強
(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勤保障部隊第九六四醫院,吉林 長春 130000)
生前預囑是指人們在健康或者意識清楚時,先行考慮在瀕臨死亡或處于不可逆轉的昏迷狀態下,誰來替自己做哪些方式的醫療決定,從而簽署的相應文件[1]。通過生前預囑給予患者更多醫療自主權,對生命盡頭的治療方式進行自主選擇,最大限度減少患者承受的病痛煎熬和“過度的”創傷性治療,讓患者自然又有尊嚴地走完生命旅程,不僅有利于減少患者在臨終前的焦慮不安,對醫患糾紛的減少、消失和營造良好的就醫環境也起到一定推動作用[2]。生前預囑為老齡化社會下老年人生命末期健康管理模式提供新方向。我國第一個生前預囑協會于2013年6月在北京成立,通過“選擇與尊嚴”公益網站[3],為人們提供自愿填寫生前預囑的平臺,截至目前已有注冊會員5萬多人,逐漸引發了一系列生前預囑話題的討論,探討其實行的有效性。生前預囑在我國仍是較新概念,且在現有社會經濟和法律規定下仍存在使用困惑[4],為進一步探究人們對生前預囑相關問題的真實看法,本文對此進行問卷調查。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課題組制作了包含22道問題的《生前預囑問卷調查》,從“對死亡的看法”“臨終的計劃”“對不可治愈的傷病生命末期的醫療選擇”“醫療自主權”和“生前預囑的認知態度”等五個方面進行提問。同時,問卷也分別對填寫者的性別、年齡、婚配情況、居住地、受教育程度、職業、醫療付費方式和宗教信仰等8個方面進行提問,以進行進一步數據統計。本研究經過本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同意。
1.2方法:此次問卷共成功收集1 063份有效問卷。其中,男430名,女633名;填寫者年齡主要集中在21~60歲,其中41~60歲共659名,占61.99%;從婚配情況看,已婚人士947名,未婚人士116名。共有來自21個省、4個直轄市、4個自治區和1個特別行政區的人填寫問卷,輻射面廣,其中,參與程度最高的是福建省和吉林省。從教育程度看,問卷填寫者涵蓋了自高中及以下至博士的所有教育階段。問卷填寫者涉及行業廣泛,人數比例較高的五大職業分別為公務員、企業職員、醫務人員、教師和自由職業者。從醫療付費方式看,選擇醫保的有751名,選擇公費醫療226名,自費86名。從宗教信仰看,737名無宗教信仰,224名有佛教信仰,102名有基督教信仰。個人特征在一些選擇中具有趨向性。
2 結果
2.1對“死亡”的看法:生前預囑的最基本前提在于,能正確地面對“死亡”這個概念。問卷問題“您是否愿意在需要時與人談論死亡?”的選擇結果顯示,有88.05%選擇“在需要時與人談論死亡”。受訪者普遍對“死亡”話題的包容度高,根據個人特征分析發現以下幾個特點:
年齡與談論死亡的意愿呈反比,自20~80歲以上5個年齡段愿意談論死亡的比例分別為100.00%,88.36%,89.23%,77.03%,75.00%;受教育程度與談論死亡的意愿呈正比,本科及以上的受訪者愿意談論死亡的比例均在85.00%以上,大專、高中及以下學歷的意愿程度均低于82.00%;醫務人員談論死亡的意愿未高于其他職業,在五大職業中,其他四個職業的選擇均高于86.73%,而醫務人員只有84.51%。一些個人特征未有較明顯的選擇區別。
2.2對臨終的計劃:生前預囑實質上是對自己的臨終安排作提前計劃,問卷共設計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您是否思考過自己的臨終?是否通過任何方式安排過自己的臨終?”問卷結果顯示,有 93人(8.75%)選擇了“思考過,安排過”,有605人(56.91%)選擇了“思考過,未安排過”,有365人(34.34%)選擇了“未思考過”。第二個問題,“生命最后一程您希望在哪里告別?”有55.13%的人選擇了“家里”。第三個問題“您希望親人朋友實現您最后什么愿望?”,有405人(38.10%)選擇了“我希望盡可能有親朋好友陪伴”,553人(52.02%)選擇了“我希望告別儀式從簡”,有879人(82.69%)選擇了“我希望我的親朋好友在我去世后能盡快恢復正常生活”。整體上看,目前整體上對臨終安排的重視程度不高。
根據個人特征分析發現以下幾個特點:從性別看,女性思考臨終的比例高于男性,男性思考并做出臨終計劃的比例高于女性,男性未思考過臨終計劃的比例也高于女性;從年齡看,隨著年齡的增長,對于臨終思考和臨終安排的人數比例都逐漸增加;從受教育程度看,思考過臨終但并未安排的人數比例隨著學歷的增高逐漸降低,未思考過臨終的人數比例則逐漸增加;從職業看,工作穩定程度越高,對臨終的安排越少,但思考臨終的比例越高;婚配情況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對選擇未有較大影響。
2.3對不可治愈的傷病生命末期的醫療選擇:共設計了三個問題,主體分別假設為“我”“我的親人”和“一個人”“在處于不可治愈傷病生命末期時,是否應該選擇使用生命維持療法來維持無質量、無尊嚴的生命?”,選擇的比例分別為90.59%,56.63%和82.97%,在主體為親人時,對生命維持療法的依賴程度明顯高于其他兩項選擇。
從性別看,女性選擇不使用生命維持療法的比例更高,尤其以“我的親人”為主體時男女比例差距最大;從年齡看,年齡層越高越降低對生命維持療法的依賴性,尤其在為“我的親人”選擇時比例差距最明顯;從婚配情況看,未婚者與年齡低者重合率高,因此選擇生命維持療法的人多;從職業看,各種職業在三個問題的選擇上比例相似,但醫務人員在“我的親人”為主體時,選擇不使用生命維持療法的人數遠高于其他職業。有趣的是,以“我的親人”為主體時,“不會”選擇使用生命維持療法的碩士人數為108人(52.43%),博士人數為65人(67.01%),比例差距最大。
2.4對醫療自主權的看法:共設計三個問題。問題“您認為,在不可治愈的傷病生命末期,相比延長生命,更應最大限度尊重、符合并實現本人意愿,盡量有尊嚴地告別人生嗎?”,近96.00%的選擇為“是”。第二個問題“您認為當一個人意識清楚時,誰應該成為臨終要不要生命維持療法的決定者? ”,有超過92.00%的選擇為“自己”。第三個問題假設處于不可治愈傷病生命末期時,有533人(50.14%)選擇了“我不要疼痛”,有519人(48.82%)選擇了“我不要任何形式的痛苦,如嘔吐、痙攣、抽搐、恐懼等”,有65.00%以上的人選擇不增加痛苦的治療,包括各種生命維持療法,只有71人(6.68%)選擇了“我寧愿忍受痛苦,也堅持使用生命維持療法延續生命”。
從性別看,女性選擇“自己”、男性選擇“醫生”為決定者的比例更高。女性選擇生命末期“不增加痛苦的療法”的比例也普遍高于男性;從年齡看,年齡的增加與選擇“自己”為決定者的比例呈反比,對“醫生”的依賴程度逐漸增加,另外,年齡在61~80歲間選擇“我寧愿忍受痛苦,也堅持使用生命維持療法延續生命”的比例高于其他組別;從受教育程度看,大專組選擇“自己”的比例最低,選擇“親屬和家人”的比例最高,而博士組別在選擇形式時,對“我不要疼痛”等形式的選擇都低于其他組別;從職業上看,醫務人員選擇放棄心肺復蘇等維持療法的比例高達76.00%;從醫療付費方式看,所有選擇“醫生”作為決定者的人均來自公費醫療和醫保組別。
數據結果顯示,絕大多數人都傾向于選擇有尊嚴地告別人生,且大部分人對臨終有較強的自我決定意識,有較強的醫療自主權,在面對生命末期的具體醫療手段時,選擇非疼痛的治療手段的人數比例基本都超過半數。
2.5對生前預囑的認知態度:共設計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您是否了解生前預囑”中“是”的比例只占34.81%。第二個問題“您認為推行”生前預囑“是生命末期患者尊嚴死亡的重要途徑嗎?”,有89.65%選擇了“是”。第三個問題有88.90%選擇了“愿意填寫生前預囑”。第四個問題則對生前預囑的建議作多項選擇,有67.73%的選擇關注了生前預囑的法律效力,有51.74%的選擇傾向于“在民間大力試行推廣,待條件成熟時再上升到法律層面”,有71.87%的選擇認為要“保證生前預囑文件的公信力和有效性”。
從性別看,男性更了解生前預囑概念,相較于其公信力和有效性,也更關注生前預囑的法律效力;從年齡看,年齡越大對生前預囑的了解程度越高,但填寫生前預囑的意愿反而降低了;從受教育程度看,填寫生前預囑的意愿也隨受教育程度提高而提高,更關注生前預囑的法律效力和公信力;從職業看,醫務人員和公益組織對生前預囑概念的了解程度高于其他職業,但也只有45.00%左右。醫務人員更關注生前預囑的公信力和有效性,公務員則更關注其法律效力;從醫療付費方式看,自費組對生前預囑的作用認知和填寫意愿都低于其他組別;另外,有宗教信仰者對填寫生前預囑的意愿也低于無宗教信仰者。
生前預囑的認知程度僅有三成,且更多集中在相關從業群體。雖然它作為生命末期患者尊嚴死亡的意義獲得了普遍認可,也有較高的填寫意愿,但其法律效力和社會公信力仍有提升的空間。
3 討論
3.1加強死亡教育:《最好的告別》書中提到,醫患雙方都要學習的任務是,在人的必死性方面謀求共識,并以生命尊嚴和保持有意義生活作為生存追求[5]。死亡教育的目的就是幫助人們正確面對死亡,樹立科學、健康的死亡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同時,學習和探討死亡心理過程,為處理死亡做好心理準備[6]。最終目的,是落實到每個人對生命的尊重和自主。
人口老齡化為代表的現實問題,也推動著社會開始正視和思考死亡問題[7]。但結果顯示,在年長者和受教育程度偏低者身上,對“死亡”話題的包容性更低,近四成人從未思考過臨終安排,都反映出死亡教育的不足。中國傳統文化對死亡話題諱莫如深,“死亡”話題總與禁忌、倫理相聯系,對年長者影響尤甚,導致他們無法正確面對和處理“死亡”話題。
然而,死亡教育是針對每個生命的基本教育、普遍教育和全民教育[8],開展死亡教育是幫助人們開啟生命價值觀的思考,通過各種方式幫助人們正確認識生老病死是生命的自然規律,珍視自己生命的價值,減輕臨終患者的心理負擔,提高對死亡的認識[9]。這是需要各級政府部門、學術團體、社會組織機構等社會各界的重視和支持的。提高老年人生命末期的生活質量,應將死亡教育應用于生命各階段,在全社會、全民覆蓋,關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幫助他們用更平靜的態度去面對死亡。
3.2加強生前預囑研究體系建設:問卷中對生前預囑概念知曉率只有34.81%,與其他針對不同群體的調查研究結果相似。例如何萍等對社區居民調查發現,對生前預囑概念的知曉率為40%[10],Kang等對患者及家屬的調查結果為38.3%的知曉率[11]。通過張蓉蓉等和王毅欣等對老年人以及晚期腫瘤患者的調查發現,調查對象不僅對生前預囑理念認知水平低,對生前預囑的認同度也相對較低[12-14]。對生前預囑法律地位的探討也需加強。生前預囑的合法性研究具有必要性[15],生前預囑可得合憲性考驗,具有民法基礎,并無法理上障礙[16]。
但目前而言,生前預囑概念的認知程度整體偏低,作為新興概念,其相關理論的研究缺乏連續統一的體系性成果,我國也未作進一步立法要求[17]。包括生前預囑的概念解析,與相似概念的有效區分,適用對象、適用時間、適用環境等內容,也都未有統一可參照的文件標準。患者自主權包括了有放棄或者拒絕接受醫療救治的權利[18]。生前預囑合法性的研究,既保障了患者的自主決策權,也保護醫務人員治療的合法性和權益。
以問卷為例,個人特征所影響的個人選擇就為未來研究提供方向,從而有針對性地加強生前預囑概念的體系研究,為其執行與實施制定行之有效的標準文件,提升其公信力和社會認可度,為其“合法”推廣提供保障平臺和文件參照。
3.3解決生前預囑的倫理問題:生命維持技術主要用于自主呼吸、循環、消化等維持生命的重要器官衰竭的患者[19]。患者對這些技術依賴性強,也需要承擔這些技術使用時對身體產生的傷害,在處于不可治愈傷病生命末期時,這樣的治療方式往往只能維持沒有質量的生命狀態。生前預囑就為患者提供不選擇生命維持技術的醫療自主權。但這種避免臨終無效延長生命的理念是與中國的傳統觀念相互矛盾的。正如問卷中顯示,大部分人仍然無法遵從親人選擇“放棄”生命維持技術的決定。儒家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影響就表現在,當生與死被賦予道德意義時,尤其在患者家庭的決策權實際上高于患者本人的環境下,無論是患者家屬,或者醫生,都將“保持患者生命”置于最高追求,從而忽略了患者自身的意愿、尊嚴或者決定權[20]。中國人講求孝道倫理,面對親人選擇“不救”,則會被定義為“不忠不孝沒有人性”,成為親人的困擾。生前預囑本身具備預設性和提前性,也與傳統文化中的“運勢”“壞兆頭”相關聯,阻礙了人們接觸此概念的積極性[21]。應解決生前預囑所包含的倫理道德問題,加強正面、積極、科學的宣傳方式,通過醫務工作者的臨床渠道加強引導,引入相關機構進行生前預囑工作的推進,與患者及家屬進行討論、訪談和周期性溝通,輔助患者及家屬作出適合的決定。
3.4做好醫學行業人員培訓工作:醫務工作者是生前預囑的見證者和實施者,他們的支持能使生前預囑更加順利地被推廣和普及。目前研究卻發現,醫務人員對生前預囑的概念并不熟悉。許琢等對護士生前預囑的認知率調查發現,雖然對相關概念的認知程度中等偏上,但專業性不高,更多依靠的是自學理解[22]。董晗等對實習醫學生的調查同樣顯示,對生前預囑的認知程度超過了70%,但主要知識來源并非課堂教學,而是報紙期刊的自學過程[23]。針對某高校醫學研究生的研究發現,對生前預囑不了解的比例甚至高達79%[24]。吳夢華等也表示,醫務人員的概念認識水平低也導致了生前預囑實施困境[25]。問卷中義務人員的了解程度甚至不到50%。
應加強醫學教育對生前預囑知識的普及和推廣,將相關內容加入課堂教學和醫學類研究生培養計劃中,推動相關專業對生前預囑概念的掌握。應加強相關系統對生前預囑法規和概念進行有效推廣,通過各種講座、研討會和學術研究,增加醫學行業人員對生前預囑在法律法規制定、規則標準健全、社會推廣和實踐方面的參與程度,加強對生前預囑的宣傳與主題活動開展,增強醫務工作者對生前預囑的討論與交流,并在臨床工作中積極推廣相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