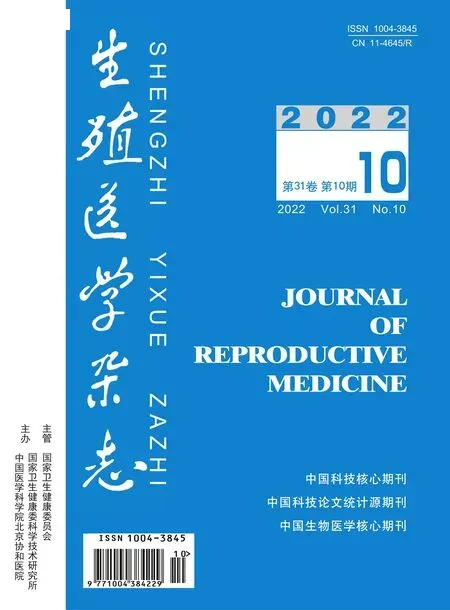上皮-間充質可塑性在胚胎著床過程中的研究進展
黃亞雄,張元珍
(1.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武漢 430000;2.湖北醫藥學院附屬國藥東風總醫院,十堰 442008)
上皮-間充質可塑性(EMP)是上皮細胞和間充質細胞相互過渡轉化的過程,包括間充質-上皮轉化(MET)及上皮-間充質轉化(EMT)兩個過程[1]。MET是指機體在生長發育過程中,部分間充質細胞在各種因素的刺激下,經過多重生物學變化,其間充質細胞的表型和特點逐漸丟失,同時獲得上皮細胞的表型和特點;EMT是指上皮細胞經歷細胞骨架重構后失去細胞極性、黏合連接、細胞橋接,由此獲得間質細胞特征,如遷移和侵襲等能力的生物學過程[1]。盡管EMP過程在胚胎發育和惡性腫瘤中的作用已經被廣泛認可,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EMP在子宮內膜成功蛻膜化、再生/重新上皮化和胚胎植入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本文將對EMP在胚胎著床中不同細胞及組織中的作用和調控機制進行綜述,以期為防治不孕不育及妊娠相關疾病提供更多線索和理論依據。
一、子宮內膜上皮細胞(EEC)中的EMP
胚胎著床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即“植入窗口”(WOI)內發生[2]。在WOI期間,子宮內膜會發生形態學變化,且始終保持一定程度的可塑性,以便能夠適應激素調控的周期性變化,這對胚泡植入至關重要[3]。在此期間,EEC從空泡至核上位置腺體變得更不規則,具有乳頭狀外觀;子宮內膜間質細胞(ESC)發生蛻膜反應,增殖并從成纖維樣細胞分化為上皮樣細胞,形成母體蛻膜;ESC變大,核圓形和核仁數量增加,細胞質中的糖原、脂質滴和分泌顆粒增多,粗面內質網和高爾基體擴張,獲得上皮樣表型[2]。
EMP在子宮內膜維持正常生理功能中的的作用是特別重要的,正如滋養外胚層必須調整其上皮特性與粘附并侵入母體子宮內膜一樣,母體EEC在胚胎WOI期也會發生EMT相關的變化。人類EEC像其他上皮細胞一樣,是有極性的,通常不允許其他細胞粘附,在胚胎WOI期EEC需要改變其極性,以形成一個附著區域。EEC極性的喪失經歷細胞形態和分子組成的變化,這些變化包括微絨毛、細胞表面標志物、細胞連接和細胞骨架分子的變化。在EEC去極化和EMT過程中,細胞與細胞之間連接的主要成分,如緊密連接蛋白和閉合蛋白表達也隨之減少[4]。EEC細胞骨架的改變與腫瘤細胞為侵襲和轉移做準備時發生的改變類似。肌動蛋白網絡是一種動態的細胞結構,它在細胞重塑過程中經歷反復的聚合和分解。在EMT過程中,球狀肌動蛋白單體即G-肌動蛋白,在細胞表面的濃度增加并聚合成絲狀肌動蛋白,成為F-肌動蛋白[5]。肌動蛋白的這種重新分布破壞了皮層肌動蛋白及其調節蛋白的濃度,濃度的改變使得肌動蛋白轉移到腫瘤細胞的邊緣,形成前緣的薄壁樣偽足、絲狀偽足和入侵樣偽足,以賦予其遷移能力[5]。胞飲突也是從細胞頂端表面延伸的富含肌動蛋白的突起,在胚胎著床過程中,分泌中期EEC的胞飲突表達顯著增多。胞飲突可能與腫瘤細胞中入侵樣類似,都可能通過局部作用分子或因子的胞吐作用分別在細胞結構重塑,在胚胎植入過程中發揮作用。還有的研究利用的人EEC的體外植入試驗,以研究胚胎植入過程中的早期事件,如胚胎的初始黏附[6]。用EEC和從IVF循環中回收的胚泡進行的體外共培養研究表明,母體EEC與植入胚胎之間存在相互作用[7]。Simon等[8]研究發現,在體外EEC培養模型中囊胚可上調EEC中子宮容受性標志物整合素β3的表達。此外,有研究發現,母體子宮內膜的信號分子與胚胎著床失敗有關,并可調節EMT過程。Gou等[9]研究發現,胚胎植入期間的子宮內膜中TWIST2在圍著床期表達水平顯著升高,而TWIST2是調控EMT的經典轉錄因子;在妊娠第3天將siRNA-TWIST2注入子宮腔后,N-鈣黏蛋白(N-cadherin)和波形蛋白(Vimentin)的表達在妊娠第5天顯著下調,妊娠第8天植入的胚胎數量顯著減少。以上數據均表明,在胚胎著床過程中TWIST2通過調控EMT影響妊娠結局,腺上皮細胞由EMT介導的細胞形態轉化對胚胎著床至關重要。
微小RNA(miRNA)通過調控轉錄后靶基因的表達在EEC的EMT過程中也發揮著顯著作用。Liang等[10]研究發現,miRNA不僅在細胞內發揮作用,還可以通過多種形式被細胞釋放到細胞外環境中,積極參與調節胚胎發育、子宮內膜功能以及胚胎與母體之間的溝通。miRNA以多種形式影響子宮容受性,其中包括通過EMT/MET轉換的調控[10-11]。研究發現,在小鼠和人類胚胎植入模型的EEC中miR-429、miR-126a-3p和miR-30a-3p在EMP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12]。miR-429在小鼠胚胎植入期間表達下降,上調miR-429可能通過靶向原鈣粘蛋白8來抑制細胞的遷移和侵襲能力從而減少胚胎的植入。相反,miR-126-3p在胚胎植入部位特異性上調,通過調節整合素α11的表達促進細胞遷移和侵襲能力[13]。miR-30a-3p是miR-30a家族中的一員,通過下調miR-30a-3p促進EMT進程進而促使胚胎著床,當miR-30a-3p失調時,EMT相關過程會受到影響,從而改變細胞的遷移和侵襲能力并影響胚胎著床[14]。以上研究表明,miRNA通過在滋養層浸潤階段可能影響EEC中EMT的相關過程,進而在胚胎植入中發揮不同的作用。
二、子宮內膜間質細胞(ESC)中的EMP
子宮內膜經過分化為妊娠做準備的過程稱為蛻膜化。子宮內膜蛻膜化最顯著的變化之一是在ESC中觀察到的形態學改變,其中細長的紡錘狀的子宮內膜間質成纖維細胞轉化為分泌性、類上皮樣的蛻膜細胞[15]。在子宮內膜增生期,基質細胞在排卵前幾乎沒有細胞質并且細胞核呈細長形[16]。排卵幾天后,子宮內膜基質區水腫,ESC細胞質增加。這些改變從末梢螺旋動脈附近的基質細胞開始,隨后在月經周期的分泌階段遍及整個基質[16]。在ESC中積聚糖原和脂質,擴展內質網,并重組細胞骨架肌動蛋白微絲,它們從成纖維細胞狀態過渡到上皮樣細胞[17]。隨著基質細胞的蛻膜化,細胞核變圓并形成更多的核仁,細胞內吞噬體和溶酶體增加,細胞質顯著擴增。蛻膜對于胚胎植入和維持妊娠至關重要。
調控蛻膜基因的核心轉錄因子包括叉頭盒O1(FOXO1)、叉頭盒M1(FOXM1)和同源框基因A10(HOXA10)[18],其中FOXO1和FOXM1都屬于叉頭盒轉錄因子的大家族。已知FOXO1的表達在蛻膜化過程中被誘導,并且是ESC蛻膜化所必需的[19]。FOXO1可以與蛻膜化的人類ESC中的孕激素受體相互作用,以控制細胞增殖和上皮樣分化。
蛻膜化所引起的細胞形態變化與MET過程一致,并且受卵巢激素的調節[20]。Yu等[21]研究發現,人類子宮內膜蛻膜化過程遵循與腫瘤發生相似的MET過程。在增生中期從育齡婦女的子宮內膜活檢組織樣品中分離得到的子宮內膜基質細胞在E2、孕酮(P)和cAMP的作用下表現出可逆的MET過程:當加入E2、P和cAMP后,子宮內膜基質細胞從雙極性、成纖維細胞形態變為典型的上皮樣圓形;當撤回E2、P和cAMP后,子宮內膜基質細胞恢復為細長的成纖維細胞外觀[21]。通過小鼠的體外研究進一步支持蛻膜化過程中MET的發生,體外培養的未蛻膜化的小鼠子宮內膜基質細胞中檢測到間充質來源細胞的標志物波形蛋白表達,而在體外蛻膜誘導的小鼠子宮內膜基質細胞中則檢測到上皮細胞標志物細胞角蛋白表達。Zhang等[22]研究發現,在雌激素和P誘導體外蛻膜化后ESC中角蛋白的表達顯著上調。在體外蛻膜化過程中,子宮內膜基質細胞中可誘導細胞表達角蛋白,表明細胞從基質表型轉變為上皮表型,進一步支持了子宮內膜蛻膜化過程中MET的發生。
Wnt/β-catenin信號通路是蛻膜發生MET的關鍵信號通路。β-catenin充當從細胞質到細胞核的信號轉運蛋白,共同調節某些Wnt靶基因,如WNT4和WNT6。另一方面,WNT4腺病毒介導的過表達促進了人子宮內膜基質細胞的MET體外轉化[23]。Zhang等[24]研究發現,端細胞作為一種新型ESC細胞,可通過激活Wnt/β-catenin信號傳導誘導蛻膜化和MET。蛻膜化和MET可促進子宮內膜的周期性更新和再生,支持胚胎著床并調節滋養細胞的侵襲。蛻膜化不良會導致許多不良妊娠結局,例如著床失敗和反復流產。蛻膜化的子宮內膜基質細胞表現出足夠的運動性和遷移能力,以適應滋養細胞的侵襲。Grewal 等[25]研究發現,人子宮內膜基質細胞中調節細胞遷移,運動性和細胞骨架重組的蛋白(Rho-GTPases RhoA和Rac1)在細胞侵襲和遷移能力中發揮關鍵作用。敲除人子宮內膜基質細胞中Rac1會導致基質細胞運動性降低,從而抑制滋養層細胞侵入子宮內膜基質細胞。
三、滋養外胚層中的EMP
小鼠和人類在胚胎植入前形成的胚泡,其細胞分離成內細胞團(ICM)和周圍的上皮滋養外胚層[26],后者將在整個胚胎植入過程中與EEC相互作用。滋養層細胞具有頂基極性、與相鄰細胞的橫向連接以及與基底膜蛋白的基底接觸,所有這些都是典型的上皮特征。研究發現,EMT過程在胚胎植入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胚胎滋養層細胞通過失去其上皮特性并獲得侵襲能力而進入母體蛻膜[27-28]。在透明帶遷移和脫落之后,滋養外胚層必須在植入并粘附到母體子宮內膜之前為植入做好準備。胚胎的滋養外胚層在植入過程之前經歷了幾次變化,最終產生了侵襲性滋養層巨細胞,植入和早期的血管生成都是由滋養層巨細胞介導,這對形成胎盤必不可少[29]。
值得注意的是,形成的侵襲性滋養層細胞的形態和功能變化與EMT過程完全相同。最初的滋養外胚層通常根據細胞與ICM的接近程度沿同一平面分為兩個區域。極層滋養層位于ICM附近區域,而壁層滋養層覆蓋更遠端的區域[30]。滋養外胚層細胞的頂端區域是胚泡最初與母體腔上皮細胞接觸并粘附的區域。隨后,在粘附和附著過程中,由于整合素αβ異二聚體(例如α5β1)從基底外側區域遷移到頂端結構域。這些整合素通過與輔助信號傳導因子(例如骨橋蛋白)以及母體腔細胞外基質中的因子(例如纖連蛋白)相互作用,介導植入的粘附和侵襲,并與粘附的滋養層細胞的表型和功能變化有關[31]。這些功能變化包括運動能力的增加,細胞間接觸變短,以及E-鈣粘蛋白的下調,這與EMT過程一致[30]。
轉化后的滋養外胚層細胞(侵入性滋養層巨細胞)侵入母體蛻膜并最終形成功能性胎盤[7]。因此,滋養外胚層通過EMT獲得間充質特性的能力是胚胎植入的關鍵。Liu等[32]研究發現,富含半胱氨酸的酸性分泌蛋白-1(SPARCL1)可能抑制ERK1/2途徑中的磷酸化和激活蛋白-1(AP-1)轉錄因子的產生,從而改變了EMT相關分子,如基質金屬蛋白酶2(MMP2)、基質金屬蛋白酶3(MMP3)、N-cadherin、E-鈣黏著蛋白和Vimentin的表達,抑制絨毛外滋養層細胞的遷移和入侵,導致胎盤發育障礙而引起流產。Xu等[33]研究發現,在子宮內膜和絨毛外滋養層細胞中,脂氧素A4可以通過抑制基質金屬蛋白酶9(MMP9)的活性,顯著上調β-連環蛋白的表達,顯著下調波形蛋白、纖維連接蛋白、TWIST、核因子κB(NF-κB)、蛋白激酶B(Akt)和糖原合成酶激酶-3β(Gsk-3β)的表達,抑制EMT并干擾胚胎植入。
此外,miRNA也參與了胚胎著床時滋養外胚層中的EMP。Wnt/β-catenin驅動的信號通路是實現囊胚植入的必要途徑之一。研究發現,Let-7g過表達后,植入后的胚胎滋養外胚層中的EMT過程受到干擾,體內的Wnt/β-catenin信號通路傳遞受損[34]。在胚胎細胞中,Let-7g的過量表達激活了EEC標志物E-cadherin的表達,顯著降低了ESC標志物N-cadherin和β-catenin的表達,阻斷了植入后胚胎發育的EMT過程。Ding等[35]研究表明,miR-27a-3p/USP25軸通過調節EMT過程來抑制滋養細胞的入侵和遷移,從而參與復發性流產(RSA)的致病過程。Liu等[36]研究發現,miR-93通過靶向BCL2L2基因的表達調節滋養層細胞增殖、遷移、侵襲和凋亡。同時,Ding等[37]研究發現,miR-146a-5p和miR-146b-5p過表達抑制了滋養細胞的侵襲和遷移,在滋養層EMT中發揮負調節作用,從而參與RSA的發病機制。
綜上所述,EMP過程在胚胎的植入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調節EMP進程的關鍵靶點以及上下游作用因子變得重要,隨著細胞重塑相關領域的研究越來越多,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調控靶點被發現,并進一步闡明其在胚胎著床中驅動EMP的機制,以促進新的治療策略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