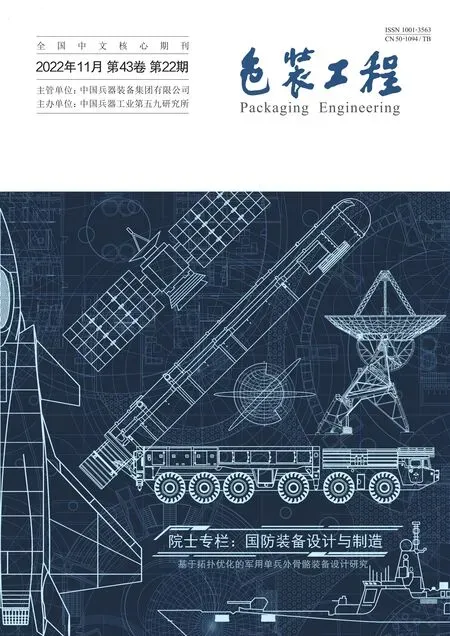文物視角下設計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余隋懷,敖卿,趙丹紅
(西北工業大學 工業設計與人機工效工信部重點實驗室,西安 710072)
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1-2],各代表性文物、典籍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鮮明的獨創性,彰顯著中華文化的偉大。研究各時期文物設計中的文化屬性和技術特點,學習其設計理念與造物思想,并與時俱進地與當下的設計結合,通過繼承、解構和再造,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設計傳承,將有利于實現中華文明的創新性發展。
目前,大部分有設計專業的大專院校采用的是包豪斯時代建立的設計教學體系,這對我國引入設計概念、培養推廣設計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這樣的體系較少涉及中國的設計文化,更談不上對中國自古以來形成的設計價值觀、理念和方法有系統的介紹,造成當下設計類學生對中國的設計歷史與文化知之甚少,設計的文化創意產品大都集中在紋樣的簡單復制、無厘頭般地夸張變形,丑陋不堪,中國優秀文化的精髓基本沒有在設計上體現出來,更何談建立文化自信和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揚。因此,在設計類教學中引入與中國古代優秀設計史相關的內容,就顯得十分必要。
已有一些學者在傳統文化與設計關系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朱上上等[3]提出設計符號學的文物元素再造研究方法,為文化創意產業和文博研究提供參考。張揚[4]深入研究“公道杯”的功能設計和內涵設計為現代設計提供文化支撐。張雯婉[5]深入分析曾侯乙酒器并對其進行再設計,探討產品語義學與文物再設計的適用性。徐丹彤等[6]結合KANO模型和FAST分析法,利用紋飾元素設計旅游文創產品。葉歡等[7]對故宮博物院代表性文物進行紋樣提取,將文創產品運用于現代家具產品設計中。康紅娜等[8]將感性工學與符號推演結合,為博物館文創產品設計提供了新思路。杜杰等[9]分析邊塞詩的藝術和文化特征,運用感知分析和形狀文法,重新演繹邊塞詩文化。丁芳婷等[10]探究典籍《周易》的造物思想與美學思維,實現其思想內核與現代設計融會貫通。張建敏等[11]以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的影響,研究了儒家思想與現代綠色設計的設計理念的內在聯系。鄭麗虹[12]剖析《尚書》以人為本與整體有序的中國古代設計藝術思想。王彬學等[13]研究《考工記》中的智者造物、制器尚象、天時地氣、材美工巧的造物思想,融入現代設計思想以打造中國設計魅力。鄧水蘭[14]則從哲學、價值、節氣、地域等方面研究《考工記》的造物藝術與社會、文化等之間的關系。唐文靜[15]探究道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陰陽有序、知止知足、無為無用等主要觀點,并將其與當代建筑設計相融合。閆如山[16]對比《道德經》中哲學思想和現代設計特征,進一步明確了《道德經》的藝術設計價值。現階段,諸多學者對古代文物的研究更側重于單一文物、典籍或工藝美術作品的分析研究,通過各個歷史時期文物進行設計分析與總結的研究比較少。
中華文化浩如煙海、博大精深,要學習和深入理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通過文物去感知和了解,是比較容易入門的一條途徑。文物是古人設計思想的物化證明,從文物角度看設計,可以提供一種更直觀、更容易理解的方法了解古人的造物動機、思想,了解那個時代的工藝特征及使用效能。選擇陜西歷史博物館中從史前至唐代文物為研究對象,是因為這一時期代表了中華文明從萌芽到成熟的過程;另外一方面是陜西歷史博物館內,唐之后具有設計代表性的文物不是很多,這也是研究的一個局限。
對從史前至唐代每個時代具有代表性文物的設計文化、材料、工藝等多維度分析,盡可能發掘文物的設計完整價值;對各時期文物的對比分析,可以梳理出中國設計歷史發展的脈絡和每個時代的設計文化與技術的烙印。在博物館中,設計者可以尋找靈感與啟發,提升品位,發現文物背后深藏、能激發共鳴的情感,有助于了解我國的文化血脈,了解幾千年來人們解決生活問題的方式,這些至今對我們依然有參考價值。這就是通過文物了解中國古代設計的意義。
1 文化是設計最大的價值目標
對企業來講,銷售產品的最高“境界”是賣價值觀念、賣文化,企業競爭最高的“境界”不是資本競爭、管理競爭,也不是市場競爭,而是文化競爭。100多年前,“包豪斯”創造的設計教育體系奠定了當今設計教育的基礎,其設計價值包含了三個層面:能用——生理層面(滿足功能需求的價值);好用——心理層面(心滿意足的價值);享用——性靈層面(文化價值)。
要達到設計價值的最高層——享用,必須研究消費者的文化需求。而設計中文化價值的研究是呈現多樣性與復雜性的,不同國家與民族都有自身獨特的歷史與文化,并不能概括為一個標準的模式。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設計教育一直受到國外設計界的影響,注重設計表達與思維能力的培養,為改革開放后中國企業的設計與世界接軌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設計教育中,缺失了對自己本民族設計方面的歷史文化系統研究,重“術”而輕“道”,難以形成在世界上具有影響力的,同時又有鮮明中國文化特征的設計教育成果。對中國設計歷史文化的科學系統地梳理,在設計教育中增加有關中國設計歷史文化的通識性課程,將非常有助于中國設計的發展[17-18]。
原研哉說過:“創造力的獲得,并不是一定要站在時代的前端。如果能夠把眼光放得足夠長遠,我們的身后或許也一樣隱藏著創造的源泉。也許未來就在前面,但當我們轉身,一樣會看見悠久的歷史為我們積累了雄厚的資源。只有能夠在這兩者之間從容穿行,才能夠真正具有創造力。”[19]
我們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復古,而是更多地學習前人積累的設計思想和文化,思考如何將這樣的遺產應用于當下或未來,從而實現設計文化的繼承與發揚,這樣才能更好地做到“知來處,明去處”。
2 由文物看創造
不了解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就無法了解中國文化的特色,也就更無從談起具有中國文化特征的設計。文物作為中國歷史的物證,反映了中國歷史各個時期的造物思想與技術,以及設計的源流。柳冠中教授[20]在《事理學方法論》中指出:“設計是人類為了生存在適應和改造自然、創造和借助工具、把‘夢想’變為‘理想’過程的‘實踐’和‘反饋’”。以陜西歷史博物館為主的史前至唐代文物為研究對象,分析從仰韶文化時期、西周時期、戰國和秦朝時期、漢朝時期,以及唐朝時期前人的設計文化的演變,適應和改造自然的“創造”,將有助于了解中國設計歷史的發展脈絡,對設計文化的繼承和創新具有一定的設計參考價值。
2.1 仰韶時期造物的創新與對樸素美的追求
仰韶文化在中國歷史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1],其對龍山文化及二里頭文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孕育時期。從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這一時期設計目的集中在解決生活中的需求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方面,大部分日常器皿的發明都體現在“能用”這一特征上,如三足罐、陶杯、陶甑、陶鬲等;半坡遺址出土、具有意象表達特征的人面魚身紋盆,則反映了這一時期的人對自然、圖騰和生殖的崇拜[22]。這一時期的文物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對自然之美的樸素追求,如尖底瓶、甘肅博物館收藏的馬家窯彩陶渦紋瓶、河南博物館二里頭彩陶等。這一時期是古人解決生存需求的發明創造時期,也是古人從物質追求到精神追求的初步展現時期。
1)從設計能用的價值角度看,文物有陶制的盆、缽、杯、盤、甑(古代的蒸屜)(見圖1a)、半地穴房屋(見圖1b)等。陶甑是偉大的發明,標志著中國式烹飪方式蒸的出現,是節能炊具;半地穴式建筑也是隨著農耕文明出現的,是北方先民的發明,給人類提供可靠的地面庇護之所。這也導致隨后定居部落的形成,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半地穴式建筑內有火塘,有的墻壁被制造成空心的,有助于隔熱保暖。

圖1 仰韶時期功能性文物Fig.1 Functional cultural relics of Yangshao Period
2)從設計得好用角度看,文物有帶把手的陶鬲(見圖2a)、帶蓋子的陶碗(見圖2b)等。把手的發明是為了更方便地拿取陶罐,更重要的意義是解放另一只手;蓋子的發明也許與生產力提升導致食物出現剩余有關。證明古人一直在力圖提升人造器物的使用效能,使其變得更加“好用”。

圖2 仰韶時期易用性文物Fig.2 Usable cultural relics of Yangshao Period
3)從享用的角度看,文物有帶繩紋的三足罐(見圖3a)、帶渦紋裝飾的陶盆(見圖3b)、人面魚身紋陶盆等(見圖3c)。繩紋的裝飾表現出前人對美的追求,標志著裝飾的出現,甲骨文中的“文”就是這樣交叉的繩紋圖案。馬家窯彩陶上的圖案有很多都是與漩渦紋相關,顯然創造者觀察到了這樣的自然之美,用軟性筆與礦物質顏料將這一份感動繪制在陶盆上。圖案里的流水與魚和諧游轉,生生不息,流動不止。正如莊子后來描述的怡然自得的游魚之樂。

圖3 仰韶時期裝飾性文物Fig.3 Decorative cultural relics of Yangshao Period
仰韶時期器物的設計思想是主要滿足生存之需,以及對樸素美的追求,還有一部分是對神靈的敬畏與崇拜[23]。通過對文物的分析,可以發現清晰的設計演變脈絡。如最早的罐狀容器器皿是沒有支撐足的,隨后經過生活實踐和經驗積累,大都統一成了三足支撐結構;盛液體的器皿最早的形態是沒有把手的,隨后演變出現了帶把手的陶器,繼而又出現了帶流口的陶器設計,直到演變成為帶壺嘴的陶器出現(見圖4)。這一時期的文物也可以見證人類需求的變化。由于農耕技術提高,人們不僅能吃飽,還需要吃好,就發明了早期的石磨盤;不僅穿暖了,還需要穿好,就發明了很細的骨針,可以縫制更加細密的麻類織物;隨著生命繁殖基本條件的滿足,就開始出現的裝飾品(骨項鏈和裝飾品)。這也驗證了馬斯洛金字塔的精神需求模式。隨著農耕文明的發展,生活的形態轉為耕種與漁獵,設計的目標就是為了滿足在此條件下的生活需求。制陶技術快速發展,使陶器成為仰韶時期制器的主要種類,誕生了大量的陶制生活用品。仰韶時期的后期,因農耕技術和制器技術的提高,器物的設計出現了更多體現精神追求的藝術設計;制陶技術也從貼塑制陶、泥條盤筑制陶、慢輪修整制陶向快輪制陶技術過渡,陶器的制作也更加精美,龍山文化的蛋殼黑陶就是這一時期快輪制陶的典型代表;骨器制作技術也發展到很高的水平(見圖5a),出現了精致的裝飾品(見圖5b)。

圖4 陶器容器設計的演變Fig.4 Evolution of pottery container design

圖5 仰韶時期骨制品Fig.5 Bone artifacts of Yangshao Period
2.2 殷商與西周設計中的敬畏神靈與師法自然
農耕文明的成熟與發展,使中華文明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導致文字和國家形態的出現。這一時期是從部落國家到城邦國家的過渡時期。文物體現了人對自然與神靈的敬畏,以及對構建社會秩序的思考。青銅制造技術由兩河流域傳入到中原,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青銅器作為祭祀禮器、兵器及生活器皿等而得到廣泛應用,中國步入了青銅時代。
甲骨文的誕生:在3000多年前,出現了迄今為止公認的中國最早文字——甲骨文(見圖6)。最初文字的創造借鑒了自然界中事物的形態,又進行了高度抽象概括,使其具有天然的象形特征[24]。文字設計古樸、優美,具有極高的表達功能和藝術價值。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的見證之一,就是中國的文字。漢字自古至今,從未中斷。

圖6 甲骨文Fig.6 Oracle
院落文化:西周周原的四合院遺址表明,中國在大約3000年前,就有院落的設計[25](見圖7)。中軸對稱,前庭后院,堂居正中,室在兩側,庭院內種植樹木與花草,出現了最早園林設計的雛形。這樣的設計考慮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初步體現了天人合一的設計思想。而中國建筑設計師王澍所設計的垂直宅院便體現出中國建筑文化的繼承和創新(見圖8)。

圖7 西周原四合院遺址復原圖Fig.7 Quadrangle dwellings site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圖8 王澍設計的垂直宅院Fig.8 Vertical house designed by Wang Shu
多功能創新:西周匕匙是具備刀、叉、勺和匕首四合一的多功能創新設計[26],無論是從人的使用與攜帶,還是節能環保的角度來看,都是絕佳的設計之作(見圖9)。

圖9 西周的匕匙Fig.9 Knife spoon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在古代,青銅器也是身份與等級的表達:如鼎與簋陪葬數量的多寡,象征著貴族的地位高低和權力的大小[27](見圖10),器物被更多地賦予了階級等級的色彩。青銅禮器的設計成為這一時期的重要視覺特征,大量的神秘、獰歷紋樣使用,形成了獨特的視覺符號[28](見圖11)。殷商與西周都強調對神靈的敬畏,所以青銅器非常重要的用途是用于祭祀。

圖10 西周的列鼎制度Fig.10 Lieding system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圖11 西周大盂鼎上獸面紋Fig.11 The beast face pattern on the Great Yu Tripod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提出,中國古代以饕餮為代表的青銅器紋飾和造型給人一種神秘的威力和獰厲的美。它是一些變形的、風格化的、幻想的、怪誕的、可怖的動物形象,體現了早期宗法社會統治者的威嚴,力量和意志[29]。
2.3 戰國時期的造物
西周以前青銅器均為渾合厚重的形制,依賴嵌套陶范的鑄造焊接仍是焊接技術的主流[30]。粗糙焊接工藝,無法保證焊后界面的整齊和美觀。隨著細金工藝釬焊的出現,使精細結構的釬焊成為可能,春秋晚期的青銅器出現了紛繁復雜的裝飾結構,工匠們可以構想出更為復雜精巧的青銅器設計。湖北隨縣戰國曾侯乙墓出土青銅尊盤(見圖12)上的鏤空紋飾是由失蠟法鑄成后經釬焊連接的[31]。

圖12 曾侯乙尊盤Fig.12 The bronze zun-pan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Zenghouyi
從春秋至戰國,生產力因鐵器與牛耕技術的應用而得到巨大發展,繼而影響了生產關系的轉變,即由奴隸制轉向封建制[32]。農民有了自由,平民可以通過學習升為士。技術的進步讓生活變得比以前美好,青銅器上的紋樣不再是殷商與西周青銅器上莊嚴獰厲的圖案,取而代之的是描述了人們生活的日常,如采桑、射獵、宴飲與歌舞等,表達了人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意愿。
戰國時期的宴樂漁獵攻戰紋銅壺[33](見圖13)頸部為第1區,上下兩層,左右分為兩組,主要表現采桑、射禮活動。第2區位于壺的上腹部,分為兩組畫面。左面一組為宴享樂舞的場面,表現了載歌載舞的熱鬧場面。右面一組為射獵的場景。第3區為水陸攻戰的場面。一組為陸上攻守城之戰,另一組為二戰船水戰,構成了一幅驚心動魄的戰爭場面。第4區采用了垂葉紋裝飾,給人以敦厚而穩重的感覺。此壺紋飾內涵豐富,形象逼真,再現了古代社會生活的一些場景。它不僅是我國青銅器中的藝術珍品,在美術史上也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圖13 宴樂漁獵攻戰紋銅壺Fig.13 Bronze kettle with banquet music performances,fishing and hunting
秦在發展壯大過程中,采用了法家的治國理念。自秦孝公嬴渠梁起,秦重視變法圖強,廣納賢才,為秦國完成統一大業奠定了基礎。法制精神貫穿于秦國上下,使得秦法“秦法繁于秋荼,而網密于凝脂”。在這樣的思想影響下,秦的造物出現了規整、實用、有效的特征。為了保證器物的效能一致,甚至出現了最初的標準化制造的思想[34]。
秦始皇帝陵出土的4萬枚箭鏃中,只有7枚與其他形制不同;在同型式的箭鏃中,同一鏃和不同鏃主面輪廓的不重疊度誤差分別小于0.15 mm及0.20 mm[35-36]。秦箭頭外形設計為子彈流線型,能有效減少空氣阻力;三棱形設計增加箭頭穿透鎧甲的能力。
秦箭頭是分兩次鑄造的,第一次鑄造鏜(插箭桿的部分)[37]。《考工記》載“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利用現代技術對秦箭鏃檢驗,錫的含量雖不及此,但錫與鉛的加入保證了箭頭的硬度,同時還增加了鏜的柔韌性(見圖14)[38-39]。

圖14 秦兵馬俑出土的箭頭Fig.14 Arrows unearthed from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Horses of the Qin Dynasty
與箭鏃配合使用的發射器具弩機,其各零件尺寸亦基本相同,特別是銷和銷孔的間隙配合有較高精度,零件具有互換性(見圖15)[40]。

圖15 秦兵馬俑出土的具有互換性的弩機零件Fig.15 Crossbow parts unearthed from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Horses of the Qin Dynasty
《考工記》載:“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說明車的制作涉及的工種是最多的,也是最復雜的[41]。秦陵銅車馬是典型設計與制造完美結合的典范之作。工匠們使用了當時最先進的制造工藝,保證了皇家車輛模型的設計實現。秦陵銅車馬制作工藝復雜,結構合理,比例準確,鑄造精致,綜合使用了鑄造、焊接、嵌鑄、鑲嵌及多種多樣的機械連接等工藝技術[42],凝聚著兩千多年前金屬制造工藝方面的輝煌成就,在中國和世界冶金史與金屬工藝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秦代在機械零件的設計中,已綜合應用了力學、材料學、機構學原理,將功能要求、設計可靠性及工藝性等集為一體。
2)在立傘的緊固夾緊裝置中,熟練地應用了相互垂直的楔配合自鎖及曲柄銷鎖緊機構,設計巧妙、結構簡單、制造方便、工作可靠。表明秦代在機構學、工藝學等方面較前有了很大的發展。
3)秦代在機械零件的結合中,已廣泛應用了不同形式的圓柱間隙鉸接配合。圓柱、圓錐及斜面過盈配合,銷釘連接,以及兩種配合相結合的連接形式,表明秦代的機械連接技術也已達到相當高水平(見圖16)[43]。

圖16 秦始皇陵銅車馬Fig.16 The bronze chariots and horses unearthed from the Qin Shihuang Mausoleum
在獎懲嚴明的法律環境下,秦的工匠們必須竭盡所能,按照要求制作最精良的器物。出土文物表明,秦已經有了初級的責任制、標準化制,其目的是保證在不同地點使用器物的效能是一致的[44]。此外,秦國頒布的《田律》規定,在指定的地點和時間內,禁止伐木、打獵、捕魚等,是世界上最早的環境保護法令。這也體現了秦的可持續發展理念。
2.4 以人為本與中西交融
漢代張騫鑿空絲綢之路,西域文化傳入中國,在極大程度上豐富了中國的設計。隨著中國絲綢的輸出西域,西域的琉璃器皿、紋樣、珠寶、香料也進入了中原。由“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香料如檀香、沉香、龍腦、乳香、甲香、雞舌香等在漢代都已成為王公貴族的爐中佳品[45]。道家思想在漢代的盛行和東漢初年佛教傳入中國,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這一時期香文化的發展。西漢早期,熏香文化就已在貴族階層廣泛流行起來[46]。陜西歷史博物館收藏的鎏金銀竹節銅熏爐是漢武帝時期的皇家監制的香爐,集工藝、文化、歷史與人文于一身的國寶精品,漢代的工匠們用九龍與五竹節體現了皇家的九五之尊,以博山造型為爐體,巧妙地將逸散的煙為設計元素,營造了一個云霧繚繞的仙境。體現出中國古代工匠的非凡想象力(見圖17)。

圖17 鎏金銀竹節銅熏爐Fig.17 Bronze bamboo-joint-shaped censer with gilded gold and silver
漢代的雁魚銅燈是以人為本設計的代表器物。可旋轉的兩個燈罩能夠調節燈光照射的方向與強弱;中空的魚腹和雁頭、身、腹部構成了煙道,用于過濾油燈照明時產生的油煙;魚代表著連年有余,表達著古人對富裕生活的追求。大雁是信鳥,是誠信的象征,也是不離不棄、生死不渝愛情的象征[47](見圖18)。

圖18 雁魚銅燈Fig.18 Goose-fish shaped bronze lamp
盛唐時期,是“九天閶闔開工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萬國來朝時代。唐長安城是按照中國傳統規劃思想和建筑風格建設起來的城市(見圖19),城市由外郭城、皇城和宮城、禁苑、坊市組成,面積近84 km2,是世界歷史上面積最大的都城。城內百業興旺、宮殿參差毗鄰(見圖20),最多時人口超過100萬,顯示出古代中國民居建筑規劃設計的高超水平。唐代詩人駱賓王在《帝京篇》里寫道:“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宏偉的城市規劃、整齊的里坊、繁華的東西市,穿行于街道的仕女大膽展示出容妝與華服之美,構成了燦爛的都市景象[48]。這一時期的特征是包容、開放、精美、大氣、時尚,形成了盛世大唐的氣象與風格。

圖19 盛唐長安城Fig.19 Schematic diagrams of Chang'an in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圖20 唐大明宮含元殿Fig.20 Schematic diagrams of Hanyuan Hall in the Daming Palace of the Tang Dynasty
唐朝婦女與其他中國古代時期相比是最開放的,受禮教的羈絆較少。在衣著、感情表達方面都很少受限制。中唐以后的女人可以揚鞭催馬穿行于井市,經常拋頭露面到郊外踏青、聽戲、逛廟會。
彩繪釉陶戴笠帽騎馬女俑形象正是唐代女性自由生活的真實寫照(見圖21)。騎在一匹紅斑點黃馬上的女騎俑眉目清秀、闊眉朱唇、頭戴笠帽,穿著乳白色儒衫外套帶花邊的黃色半袖,下著淡黃色條紋長裙,足登尖頭鞋,勒韁前視,神情悠然,顯示出高貴文雅的氣質[49]。

圖21 彩繪釉陶戴笠帽騎馬女俑Fig.21 Painted glazed pottery Horse-riding Female Figurines
唐代的設計風格深受波斯薩珊、希臘、印度等域外文化的影響,文物反映出設計文化的引入、融合、發展的過程。獸首瑪瑙杯來自西域(見圖22);鴛鴦蓮瓣紋金碗的造型、大部分紋樣和工藝來自波斯薩珊王朝,但也融合了中國人喜歡的鴛鴦圖案(見圖23);羽觴是中國的器物造型,但其上的寶相花紋、闊葉折枝紋、魚籽紋等圖案卻來自西域(見圖24)。由西域傳入的金銀器加工技術包括錘擛、鏨刻、潑珠、花絲、釬焊等,使金銀器的制作更加繁復精美[50]。

圖22 獸首瑪瑙杯Fig.22 Beast-headed Agate Rhyton

圖23 鴛鴦蓮瓣紋金碗Fig.23 Gold bowl with Mandarin duck and lotus petal

圖24 羽觴Fig.24 plume beginning
與圓形對稱構圖的漢鏡不同,唐代的銅鏡無論是形制還是內容上都呈現出開放和包容的特點。形狀包括圓形、菱花形、方形、葵花形等,內容也出現了反映儒、釋、道文化及境外海獸紋、瑞獸紋葡萄鏡等圖案,精彩紛呈(見圖25)。

圖25 金背海獸葡萄紋銅鏡Fig.25 Bronze mirrors with auspicious animals and grapevine
正倉院是日本圣武天皇決定用上等木料建造的一座專門收藏珍貴物品的倉庫,收藏有大量唐代珍貴寶物。唐代工匠制作的“螺鈿紫檀五弦琵琶”(見圖26),不僅在音樂史上有重要意義,制作上也堪稱是精美絕倫的藝術品。我們可以通過這件琵琶一睹盛唐時期的設計及制造水平,精致、華麗,是完全能代表盛唐氣象的珍品。傅蕓子先生在《正倉院考古記》上這樣描述:“紫檀木質,背之全面,有螺鈿之鳥蝶花卉云形及寶相華文,花心葉心間,涂以紅碧粉彩,以金線描之,其上覆以琥珀、玳瑁之屬,于其淺深不同之透明中,顯現彩文之美,極為瑰麗工巧。”[51]

圖26 日本正倉院收藏的唐代琵琶Fig.26 Tang Dynasty Pipa collected in shosoin
縱觀歷史的發展,人類為了生存,在不斷地創造工具、努力實現夢想的進程中從未止步。舊石器時代的人能利用石器和骨器作為工具,設計的特征是原始和拙樸的;新石器時代出現了磨制石器和陶器,農耕文明使人們有了家園意識,設計特征是豐富的器型、精美的裝飾和圖騰,出現了由具象到抽象圖案的過渡;青銅時代極大地提升了生產力,生產關系也發生了變革,出現奴隸制社會。甲骨文是師法自然的設計杰作,文字的象形性有利于降低識字的成本。這一時期的設計特征是大量反映等級的祭祀青銅禮器,設計圖案也多為莊嚴肅穆與獰厲的神秘圖案;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鐵器與牛耕,導致井田制瓦解,封建制的社會誕生。底層百姓獲得了更多的自由,思想也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設計特征表現在出現了很多描述日常生活的圖案。此時青銅器的冶煉技術也達到了巔峰,青銅器加工也更加成熟和精細。秦注重法制,在造物中也體現出“物勒工名”的精神,誕生了“標準化制”與“責任制”的雛形;漢代是真正在政治上實現了民族和國家的概念,用封建體制(三公九卿制)統治了四百多年。鐵器得到廣泛應用,糧食的生產與加工技術日臻成熟。思想上從“黃老之學”過渡到“獨尊儒術”。設計方面開始關注以人為本,以神仙為題材的設計大量出現;唐代繼承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政治開明、思想解放、人才濟濟、疆域遼闊、國防鞏固、民族和睦、開放包容,大唐在當時世界上是無比繁榮昌盛的形象,大唐盛世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中最為輝煌的篇章。盛唐時期的中國,國富民強,通過由國都長安直抵地中海沿岸的陸上絲綢之路,將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傳播四海。在設計方面,完成了中外文化的深度融合,大氣、富麗、璀璨、包容、自信等成為盛唐設計的關鍵詞。
3 格物致知——由器至道
在漫長的中國造物史中,人類也在不斷地總結和提升造物經驗。在春秋戰國時期,就誕生了很多非常著名的設計思想,總結了造物的經驗和規律。從“造物”到“成道”是人類對改變自然的反思和總結。孔子的“盡善盡美”——善與美的統一、“文質彬彬”——形式與內容的統一等構成了中國人的美學思想[52];老子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大象無形”“大巧若拙”“無為”等設計思想反映出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53],至今仍對設計師產生著重要的影響;荀子的以人為本、墨子的兼愛與節用理念是對設計的反思,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54]。《考工記》是中國春秋時期系統記述關于手工業各個工種的設計規范和制造工藝的大全。書中記錄了先秦大量的手工業生產技術、工藝美術資料,以及一系列的生產管理和營建制度,是當時的設計寶典。與之類似,明末科學家宋應星編寫的《天工開物》也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巨著,其全面、系統地記錄了我國古代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技術,在科學史上具有很高的價值。
每個時代都有屬于那個時代的技術特征。技術在變化,而“道”并未過時。設計中的文化繼承不是簡單的圖案復制,而是繼承古人的優秀設計思想——“道”,與時俱進,在現在的技術條件下,設計出符合時代精神的文化產品,滿足人類的需求,創造美好生活。
文化的繼承與創新還要勇于對傳統文化進行重構。銅師傅品牌下推出的孫悟空銅雕(見圖27),開始并未賦予孫悟空太多文化內涵。后來進行了文化重構,賦予孫悟空“千錘百煉、久煉成器、降妖除魔、披荊斬棘、勇往直前、戰無不勝”的新的文化特征,這也正是改革開放以來銳意進取的企業家形象,孫悟空被賦予了新時代的文化特征。孫悟空形象由六小齡童代言,并進入到了主流眾籌平臺,由此帶來了銷量的大增。

圖27 銅師傅的孫悟空銅雕Fig.27 Tong Shifu's Sun Wukong bronze sculpture
4 結語
文物可以折射出所處時代的科技、文化和設計特征等,通過分析不同歷史時期的文物。可以梳理出中國古代設計演變的初步脈絡,了解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的發展對設計帶來的影響。古人對設計與制造經驗的總結,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回顧中國設計的來處,有利于加深對中國設計特色的理解。沒有中國特色,中國的設計就不會走得太遠。
當下的設計教育忽視了對中華設計文化的了解,相當一部分設計師缺失了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很多設計重表達技巧,缺少了文化的靈魂,優秀并具有中華文化的設計難以尋覓。博物館對設計師而言,是巨大的設計寶庫。通過文物了解古人的設計智慧,并用現代的設計語言講述中國的設計故事,釋放古老中國蘊藏的文化能量,才能使中華文明發揚光大。當代設計師的責任之一就是在西方強勢設計審美中,綻放出絢爛的中華文明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