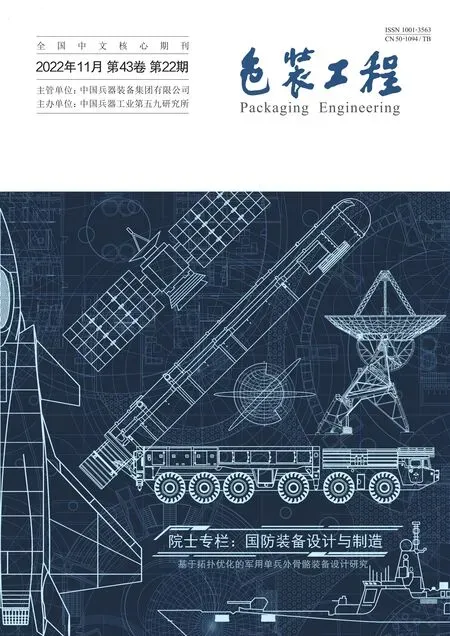基于敘事分析理論的交互裝置設計方法研究
何修傳,楊曉揚
(1.上海電機學院,上海 200284;2.廣州大學,廣州 510006)
近年來,結合交互技術和裝置藝術的交互裝置發展迅速,廣泛應用在各種場景中。交互裝置設計具有跨專業和多元化的復雜性,對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設計思維方法論提出了一定的挑戰,需要用更加開放的視野和態度來進行探討和研究。敘事是人類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一種基本心智模式,把敘事作為設計方法已被證明具有強化溝通和優化體驗等諸多優勢機會。敘事分析是敘事方法論的實踐工具,是敘事的底層邏輯,不僅具有分析故事成分和情節組織等作用,還能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對生活經驗進行故事化構思和表達。基于敘事分析探索交互裝置的設計,意在從設計的故事講述深入到設計的敘事探究,關注設計本體理論性的詮釋,力求為交互裝置設計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1 交互裝置的設計分析
現代狹義上的“裝置”被多數學者認為確立于1917年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基于小便器創作的作品“泉”,是一種強調觀念的藝術產品。裝置作為一種藝術產品形式具有多元闡釋、現成品挪用、空間性、綜合性、觀念性等特點,強調以令人感興趣或令人著迷的方式來吸引和打動人,而不是傳統的審美[1]。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新媒介,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為特征的數字媒介在裝置中的廣泛應用,使很多裝置都具有了交互的特征屬性,逐漸形成了融合交互技術和裝置藝術的一個新物種“交互裝置”。從字面構成上看,交互裝置既可以理解為具有“交互”特征的裝置,是裝置藝術的一種類型;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具有“裝置”特點的交互設計,是一種設計題材。目前,這種整合了媒介、樣式、技術、內容和觀念等內涵的交互裝置,呈現出更多的產品化趨勢,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各種主題的活動和應用場景中,如文化藝術、工程設計、教育廣告、娛樂游戲、數據可視化、情景模擬等領域。
從產品設計的角度看,交互裝置的復雜性特點對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設計思維提出了新的挑戰和新的探索需求。學界對于交互裝置的設計研究比較開闊,涉及技術應用、構成元素和設計體驗等。如高家思等對交互裝置設計研究落腳在軟件技術開發上,該研究集中在幫助兒童搭建和理解各式交互裝置及其控制邏輯的編程系統——LinkBricks,意在通過這種軟件系統創建多樣化的交互行為[2]。李悅[3]則認為一件交互裝置的設計首先需要明確三個基本要素:基礎理念、形式設計、科技支持,然后在此基礎上運用交互設計方法進行創意設計。交互裝置的設計不僅是功能性的體驗,無疑會觸及情感層面的體驗,為此,鐘鳴等[4]基于通感轉化理論研究交互裝置設計方法,指出可以通過用戶感知引導與環境引導推進通感體驗與情感體驗的升級。另外,相關研究還關注到交互裝置設計融入環境景觀、城市廣場、展示空間和文化場所等應用場景的價值、融入場景的方式和呈現出來的體驗特性等。用更加開放、積極的態度去探索和引介新的設計理念與方法,可以被看作是交互裝置設計研究的趨勢機遇。
2 敘事分析作為一種交互裝置的設計方法
2.1 敘事分析
敘事分析是從事敘事學研究的主要工作方式,也是闡釋和評論敘事作品的工具,是敘事方法論的實踐[5]。敘事通常被認為是與“故事”相關的——按照發生順序對相關事件的口頭或書面描述[6];是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基本方法,廣泛存在于我們生活世界的各個方面[7]。20世紀70年代確立了一門專門的“敘事學(Narratology)”,敘事學是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形式主義(Formalism)和60年代法國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在文學分析基礎上形成的,力求通過分析作品的內在結構從而找到規律[8]。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語言學研究理念是敘事分析的基石,他顛覆性地把歷時語言學研究改為共時語言,認為文學作品應該著眼于各部分相互關系的分析,而不是各自的歷史演變。敘事分析就是以索緒爾語言學的結構分析模式來研究對象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之間的關系,力求透過表象獲得對深層結構性的理解[9]。事實上,敘事分析不止于分析,而是一個整體思維過程,包含有經驗的關注、訴說、轉錄、分析和閱讀等五個層面,不僅關注敘事的內容,更會關注敘事方式[10]。最初敘事分析主要集中在文學和語言學的文本分析,后來隨著敘事轉向發展逐漸擴展到更廣闊的文化產品領域,也包括各種主題的設計。轉向后的敘事也逐漸突破囿于作品的話語分析,還積極把分析的思維方式轉變為創作的方法。概括來說敘事分析有三層意思:把研究對象把握為可以進行敘事分析的“敘事文本”;用敘事分析來研究對象;用敘事分析來詮釋和表達對象。敘事分析擴展到設計的重要動因是后現代的設計主張不僅需要關注設計的功能體驗,還需要關注設計的意義體驗。楊祥民[11]指出設計應用敘事是要求設計師在作品中傳達富有寓意的“含義”,增加其附屬價值。從價值層面上看,把敘事方法應用到產品設計中,主要是因為敘事方法能給設計帶來諸多益處。如何人可等[12]指出基于敘事的設計具有注重關聯性、時序性與感染力三個優勢特征;以敘事的形式傳遞產品信息,可以實現產品本身由“物”到“事”,再由“事”到“情”的轉化過程[13];敘事可以通過文本將文化融于產品,讓產品敘述故事,增加產品的文化屬性,可以提升用戶情感體驗[14]。由此可知,設計應用敘事分析的目的不限于分析對象的構成要素和功用性,而在于用敘事的思維邏輯表達對象,強調通過圍繞物的故事與意義開發帶給用戶的情感體驗升華。
2.2 基于敘事分析的交互裝置設計思路
基于敘事分析的交互裝置設計,首先是用敘事理論的觀點去把握對象,這樣一個交互裝置能被概念化為一種敘事題材,繼而可以對其進行敘事化闡釋和創作;其次,參考里蒙—凱南(Shlomith Rimmon–Kenan)對敘事的符號系統分析法,一種敘事題材可以分為故事、文本和敘述行為三個結構層次,來對交互裝置設計進行敘事化分析重構。考慮到交互裝置是動態交互敘事,結合敘事分析中對于文本結構研究的經驗,本文把交互裝置設計進一步整合為交互裝置的主題設計、交互裝置的結構設計與交互裝置的話語設計個要素。在此基礎上繪制基于敘事分析的交互裝置設計思路思維導圖,見圖1。實質上是把索緒爾和結構主義的觀念與敘事學等理論和思維方式應用到交互裝置設計上,把敘事分析作為一種設計方法。具體而言,主題對應的是故事,主要是交互裝置的內涵意義,即敘事者(設計師)通過這個交互裝置想傳達什么樣的內容、理念和信息;結構主要對應的是敘述行為,主要是主題導向的交互行為和過程;話語主要是指交互裝置采用什么樣的表達方式,如媒介、材料和技術應用等。把故事整合為主題的依據是主題之于故事更強調意義,從這個層面上看,交互裝置的敘事分析不是停留在一個故事設計上,而更為關注交互裝置的意義構造,即強調的是作品主張的觀念、價值和目的等;結構則是交互裝置邏輯組織層面,主要包括內容的組織層面,內容與形式、交互動作的連接方式等;話語主要是考查終端的形態等,聚焦在交互裝置實物的符號層面。從敘事分析的思維模式來看,這三要素之間其實是互相轉換和依存的系統。主題需要通過結構和話語來實現;同樣,結構需要以主題為導向,以話語為載體,否則結構就是空洞、抽象的;話語需要以結構作為依據,否則就是無序的混亂,同時需要和主題相聯系和呼應,并強化主題,從而通過敘事的作用整體地表達和呈現。

圖1 基于敘事分析的交互裝置設計思路Fig.1 Design strategy of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 based on narrative analysis
3 基于敘事分析的交互裝置設計案例實踐
節約糧食是一個常態化的話題,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和蔓延,一方面導致連接全球的交通和物流受到嚴重阻礙,另一方面糧食生產也受到疫情嚴重沖擊,從而使節約糧食這個話題的意義更加凸顯出來。以往關于節約糧食的設計主要都是平面海報和視頻為主,用交互裝置來設計這個命題是一種實踐探索。期待通過這個實踐來解讀敘事分析在交互裝置設計中的具體邏輯應用和表達方式,從而對其獲得實證性把握。
3.1 主題設計:意義構建的視角設置
概括而言,主題就是作品的意義[15]。交互裝置的主題設計重點需要分析的是意義從何而來,即意義是怎么進行敘事化構建的。敘事的觀點認為意義構建既不是來源于現實世界的客觀真值復制,也不是來源于主觀世界的憑空虛構臆想,而是在故事的敘述表達中獲得。具體于主題層面的意義構建需要通過視角設置來進行,這里視角的作用不是停留在設置一個故事敘述的立場,而是通過此立場確立敘事表達的內容選擇和價值追求。
視角設置對主題設計的意義構建作用,首先是選題聚焦。顯而易見,節約糧食是一個比較宏大的命題,具體到方案設計上還需要聚焦從而避免空洞。通過相關調研和創意,最終給交互裝置確立了“《稻谷的一生》(后續統稱RICELIFE)”這一主題。這個主題通過視角設置把宏觀的節約糧食大命題聚焦到具體的“稻谷的一生”視點上。稻谷是演繹整個敘事的主角,這樣故事就有了載體和靈魂。通過稻谷這一主角展開敘事,可以使故事有血有肉,有助于主題意義構建得更加具體與更有溫度。同時,通過對《RICELIFE》視角設置的結構分析可以看到,主題強調的是稻谷的“一生”,“一生”是重點,框定了從這個具體的視點來發展和闡釋節約糧食這個命題,確定了后續意義傳達和結構組織的立場。可以看到,視角設置確立了交互裝置意義構建的立場和價值觀,以及具體切入點,在此基礎上展開的故事敘述,就是意義的生產和表現。
其次,通過視角設置的關聯作用給意義構建賦予概念。主題設計中的視角設置還需要強調內容是如何和生活世界相關聯的[16]。視角設置的關聯不是一種機械的對接,而是一種基于概念隱喻的意義構建。《RICELIFE》主題概念受啟發于古代詩人李紳《憫農二首》中“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一句詩詞。李紳的這首詩非常有名,這個主題概念的立意與大家耳熟能詳的詩詞關聯,從而可以使其意義建構具有一定歷史和文化內涵。而且,大部分人每天都在吃稻谷類食物,選擇稻谷的一生作為節約糧食意義構建的視角,也和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這樣的敘事既真實也自然,也容易引起體驗者的認知共鳴。
最后,在選題聚焦和賦予主題概念隱喻的基礎上,視角設置還要引出問題,即發展故事情節,用故事來生產意義。《RICELIFE》這個視角設置最自然引出的問題就是“一生”是怎樣的?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會發展出后續的情節,也能自然地引導觀眾進入故事中。基于敘事的主題意義建構,不是直白的,而是要有情節的,往往呈現為故事中的主角遭遇挑戰,克服各種難題,最終達到目標和完成任務。《RICELIFE》,通過對“稻谷”進行擬人化虛構,對其“一生”從種子到食物需要經歷過的工序進行故事化敘述,表達了每一粒糧食都值得被珍惜,不應該被浪費的主張和理念;讓用戶通過交互裝置的視覺化故事體驗稻谷的生長、運輸與加工等過程,體會糧食的珍貴性,強化節約糧食的意識。見圖2。

圖2 基于敘事分析的主題設計Fig.2 Theme design based on narrative analysis
對《RICELIFE》意義構建的結果評價,首先體現在通過視角設置把命題、敘述者的主觀心智活動和特定的受眾體驗進行聚焦和概念化演繹關聯,從而使主題設計具有可行性的價值;其次,通過視角設置的敘事化意義構建過程實質上是一種可以循證和解釋的設計方法,能有效揭示“主題”這種往往具有神秘感的黑箱式創意,繼而更具操作性地進行主題設計。
3.2 結構設計:內容次序的情節組織
交互裝置確立了敘事主題,還需要進一步通過具體結構來落實主題和發展故事。在敘事分析的世界觀里,人們正是通過敘事結構作為組織日常經驗的模板。這里敘事“結構”不是物理的構造,而是基于情節化的敘事片段序列組合,主要指按照一定的時間或因果關系進行故事片段的組織編排[17]。具體于《RICELIFE》結構設計中,內容次序的情節組織方式主要作用體現在三個方面:交互內容的組織、視覺化的故事板和交互流程圖。
《RICELIFE》交互內容的整體結構采取了以時間為次序的情節組織方式。把交互內容次序設計為“稻谷的生長”“稻谷的收獲”“稻谷的儲運”與“稻谷的食用”4個單元故事,是一種順敘的情節組織方式,通過時間主線來作為推進敘事發展的動力,并形成闡釋稻谷一生的故事。順敘的情節組織方式是一種非常清晰的結構設計,具有明確時間節點和直觀的次序變化,有助于體驗更加輕松且明確。另外,《RICELIFE》敘事結構設計還注重情節組織的有機完整性,四段故事概括了稻谷一生幾個有代表性的片段場景,有序幕也有結尾,形式上具有起承轉合的變化感節奏,符合敘事結構的審美標準。簡言之,基于時間的情節組織方式給《RICELIFE》內容提供了次序安排的邏輯依據,形成的敘事結構不僅具有一定的秩序法則,而且這種結構能被一種以故事性的方式進行感知與解讀,從而有助于體驗者更好理解交互裝置的內容和意義,見圖3。

圖3 《RICELIFE》交互內容組織框架Fig.3 Interactive content organization framework of RICELIFE
故事板則是一種以場景為情節組織方式的內容次序編排,意在把抽象的時間故事轉譯為一種視覺化的空間場景。《RICELIFE》確立了使用順敘為交互內容次序安排的情節組織方式后,還需要更進一步通過故事板分析和組織敘事內容和要素,推敲具體的交互行為和動作。《RICELIFE》選擇了幾個場景進行了故事板的繪制,見圖4。在生長階段繪制了播種和初長的場景,在收獲階段繪制了收獲和篩選等場景,通過故事板使《RICELIFE》結構設計更加充實和豐富。換言之,結構設計不僅可通過情節來組織內容結構的次序,還能通過情節營造一個空間化的故事場景,有助于設計師在場景中更加直觀地探索設計的色彩、視覺化語言的表現風格等問題,繼而來完善和細化設計。
情節具有的整合力與虛構性,有助于把交互流程圖組織成生動的產品使用情景。情節組織具有整合事件、信息的感染力,繼而可以把交互裝置的流程圖從說明操作變成更加生動、有趣的故事敘述,見圖4。《RICELIFE》流程圖不僅是交互流程次序安排的圖示,更是通過敘事的想象力來虛構一個交互流程的使用情景,通過情景來分析交互的合理性和邏輯性。即設計師可以通過使用情景來直觀地檢驗《RICELIFE》結構邏輯是否合理順暢,交互流程的技術、材料和形式設計是否統一和協同等問題。值得指出的是,基于情節組織方式的流程圖次序安排不僅是一種視覺分析工具,還具有一定的認知和改造敘事結構的能動性,有助于設計師用一種可視化的方式表來表征與理解交互流程。

圖4 《RICELIFE》交互流程Fig.4 Interactive flow chart of RICELIFE
3.3 話語設計:視覺符號的生動表征
交互裝置設計有了好的敘事主題和結構,并不意味著就能產生豐富性的體驗效果,需要通過生動表征的視覺符號才能更有效地引導觀眾的特定體驗反應。生動性是敘事話語的典型審美要求,這種要求則可以轉化為基于敘事分析的交互裝置話語設計指導策略。
《RICELIFE》話語生動表征敘事分析,第一體現在交互動作設計的生動性。此交互裝置使用的是一個物理旋轉把手,要求體驗者握住把手持續搖動裝置進行交互體驗,程序上設置是轉動幾圈后故事情節能轉折到下一個場景;這種交互方式容易給體驗者一個非常強烈的參與感,隱喻稻谷從種子到糧食需要持續地辛苦付出,呼應了節約糧食的主題。相較于觸點式的交互語言,這種搖動式的動作語言可以帶來一種持續性的不間斷體驗,基于敘事而言,持續性有助于把體驗者帶入到劇情中,容易產生共振。非間斷物理的互動更容易給體驗者帶來一種控制感,帶給他們引人入勝“移情”認知經驗與感受,獲得更高體驗層級的滿足感和成就感,從而反思珍惜糧食的意義,產生情感共鳴。
配合這種動作語言《RICELIFE》選擇的主要技術開發是基于Arduino主板及編程系統,這是一款具有可擴展的開放硬件及開源軟件平臺,具有易懂、快速上手的特點。物理裝置結構是旋轉傳動齒輪,在齒輪上安裝旋轉阻尼器和紅外感應器,為保證裝置的精度,使用CAD設計并數字化打印。交互的信號處理流程就是用戶轉動齒輪裝置,齒輪裝置上紅外感應器中的信號處理系統將探測到的信號輸送到Arduino控制設備中,Arduino發送信息控制顯示器里的數字內容與用戶進行互動,見圖5—6。

圖5 交互硬件Fig.5 Interactive hardware

圖6 《RICELIFE》系統構成Fig.6 System composition of RICELIFE
第二是數字影像帶來的可能性生動話語體驗。《RICELIFE》選擇基于簡潔明快的二維MG數字動畫為視覺語言,分析這種動畫生動表征敘事,首先體現在通過數字幻象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具有一種虛構的可能性生動體驗。同時,MG數字動畫呈現出來直觀的可見性、“虛幻”的真實性、形式的新穎性使虛擬和真實交織在一起,顯示出從未存在的物體或場景,從而給體驗者帶來一種時空穿越的體驗,營造一種生動的敘事存在感。由于存在感的強弱是影響生動性體驗的重要指標。另外,通過MG數字動畫可以把敘事圖像、文字、視頻、聲音有機地融合起來,本質上是一種多通道的復合體驗。從體驗效果來看,多通道的復合體驗可以使體驗的內容更加立體、生動、有效和集中,從而給體驗者帶來更高效的情感升華,進而產生一種多元代入感體驗樂趣,見圖7。

圖7 《RICELIFE》數字語言Fig.7 Digital language of RICELIFE
一個交互裝置有了好的故事主題和組織結構,不等于就能講好故事,設計的最終呈現很重要。基于《RICELIFE》話語設計敘事分析可以看到,敘事者不僅需要具備豐富的敘事想象力,還需要為最終的話語表現找到合適的視覺表征符號,這需要兼顧設計審美、技術材料和工程預算等因素,考量的是敘事者的復合能力。交互裝置,最終只有借助于生動的話語表征,才能將敘事結構中深層的主題意義、結構組織轉換為一件有血有肉、具有生命力的敘事作品。
4 產品原型體驗測試
產品原型體驗測試通過對《RICELIFE》的使用情況進行交互行為觀察和體驗感受訪談獲得,主要測試目的是驗證設計是否達到預期目標。選擇被試人數20人,在校大學生,年齡段20~24歲。
交互行為觀察測試有兩項指標:指標1交互自明度,指標2操作順暢度。指標1測試設計如下,產品原型組裝好后,要求被試依次體驗這個裝置,在體驗過程中對其操作行為進行觀察。其中交互自明度觀察的內容是:被試能否正確操作此裝置;被試能否順暢完成交互裝置的操作步驟。交互自明度觀察測試主要目的是驗證交互裝置的設計是否具有自明性,即體驗者能否看到這個裝置就能按照設計者意圖來正確體驗產品,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理解敘事意圖和內容。觀察結果:其中11名被試能毫不猶豫地上機操作,另外5名在上機操作之前有10 s左右時間猶豫,3名上機前花了更多時間仔細檢查了裝置,確認交互方式后才開始操作,剩下1名需要尋求幫助。指標2操作順暢度觀察測試主要目的是驗證設計體驗達成度,即系統能否及時響應體驗者的操作,反饋操作現狀和結果,引導體驗交互動作的完成。此項觀察結果顯示10名被試能完整按設計流程完成交互,5名被試中間有過一段時間停頓后完成,3名被試中間需求幫助,2名被試沒完成徑自離開。
體驗感受訪談的測試設計為4個問題:問題1是測試被試對主題理解能否符合設計者的訴求,問題2是測試被試對內容體驗感受評價是乏味還是生動,問題3是測試被試對交互方式操作體驗感受評價是否有趣味,問題4是測試被試體驗完后是否有意愿做出一些節約糧食的行動。問題采用百分制打分,經過訪談和答題數據分析總體均分為79分,見表1。訪談結果顯示被試能基本理解裝置的敘事主題和訴求;用手搖的交互方式比較生動有趣,但是畫面的沉浸感有待加強;搖柄的人機交互不夠順暢;大部分被試有意愿體驗后做出相應的行動。

表1 體驗效果訪談數據統計Tab.1 Statistics of experience effect interview data
產品原型體驗測試顯示設計基本符合要求,但還是有一定的提升空間。在后續的優化完善中,將基于測試的反饋結果對相關問題進行如下修改和完善:操作界面上增加一個提示符號,使體驗者更明確交互的方式;畫面適當加入一些具象化元素,提高畫面感官體驗;搖柄可以增加阻尼器系數,讓體驗者在一個場景完成后有一定的成就獲得感等。
5 構建基于敘事分析的交互裝置設計方法理論框架
結合《RICELIFE》交互裝置案例實踐分析,本文粗略勾勒了一個基于敘事分析的交互裝置設計方法理論框架。見圖8。基于敘事分析的交互裝置設計,首先在需要設計者觀念層上把自己定位成一個敘事者,體驗者就是敘事接受者。交互裝置是設計作品,也是敘事的文本,把設計對象看作敘事文本,意味著策略上把產品設計轉變為故事敘述,繼而在交互裝置設計中可以融入故事的邏輯和經驗,然后通過深思熟慮的敘事分析重新組織和呈現產品設計。

圖8 基于敘事分析的交互裝置設計策略理論框架Fig.8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teractive device design strategy based on narrative analysis
基于敘事分析的設計對象邏輯上可以進行敘事化重組,繼而明確具體的敘事設計要素。文本敘事分析對象的終端呈現是文字符號,重點在于段落和篇章結構系統,抽象的文字本身體驗可以忽略。然而交互裝置終端物質和形式恰好是體驗的界面和對象。所以,重組交互裝置的設計要素,不但要講個好故事,而且要考慮故事如何進行設計表達和實現。需要平衡的是既要避免設計師陷于對技術、材料和藝術形式的迷思而忽略設計所要表達的內涵意義,還要警惕不可實現的虛空故事。
基于敘事分析法設計交互裝置,可以應用敘事的視角、時間、情節等理論經驗作為具體設計語法。如主題設計上通過敘事視角設置更深一層探索交互裝置觀念從何而來,意義如何再現和體驗。情節有助于使交互內容和交互流程有機、整體地組織到一起,構造成一個關聯性的故事體,從而使交互信息的組織、次序更加清晰明確,使體驗者更容易理解交互裝置的意義。敘事的生動性原則可以轉化為交互裝置話語設計的技巧,如使用持續性的交互動作更容易把體驗者帶入到劇情中,更容易創造一種生動的交互語言;其次,數字影像生動性體現在虛構性敘事與多通道的復合體驗更容易激發情緒變化,可以使交互體驗更有代入感。
基于敘事分析的交互裝置設計,設計審美的核心是意義體驗,也可以稱為“好故事”。好故事要求設計關注不限于功能上的實用,而在于意義的建構、表現和傳達。另外,好故事不僅要追求作品富含的意義,而這種意義更需要被體驗者有效解讀。敘事分析關注交互裝置承載意義的語言符號表述和組織,可以為意義體驗提供理性的分析和組織經驗,從而幫助敘事者把想要表達的意義更好地傳達給體驗者,讓體驗者更好地感知和理解敘事者的目的和意圖。
6 結語
敘事分析不僅是分析對象,更是人類的一種認知和解釋意義、為其賦予組織和形式的思維方式,還可以作為一種設計方法來表達和創造對象。敘事分析作為一種交互裝置設計方法的重點在于可以通過敘事給設計賦予內涵意義,避免對技術和材料等的迷思而把設計簡單化為沒有靈魂的形式游戲,并通過意義構建和解釋為交互裝置本身的藝術觀念性和產品功用性融合設計提供一種柔性的手法。換言之,敘事分析不是把文本敘事的原則投射到交互裝置的設計上,而是關注敘事分析作為一種原理性的方法有何作用、作用的機制與方式等。基于敘事分析來探究交互裝置的設計方法,其實是一種選擇,就是選擇用一種人類內在經驗、結構性的語言學思維模式去探討設計的本身,這種探索如果不能勾勒出一種設計思維的學說,至少也提出了一種交互裝置設計的主張,可以有效應對當下交互裝置設計面臨的現實需求。本研究實現了從構思、實踐、測試、評價到理論構建的閉環,具有可操作性的現實指導意義,拓展了交互裝置設計的理論研究,可為面向實踐的設計研究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