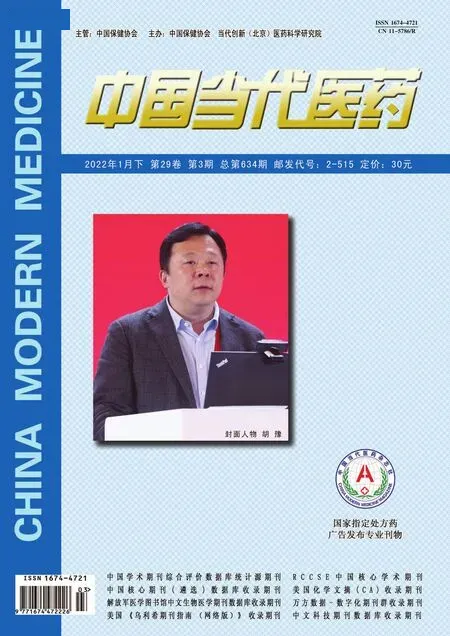“互聯網+護理”上門服務中護士人身安全存在的隱患及對策分析
李金林 趙天珍 劉海燕 韓愛華 肖 廷
1.四川綿陽四0 四醫院 川北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護理部,四川綿陽 621000;2.四川綿陽四0 四醫院 川北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內分泌科,四川綿陽 621000
2018年7月6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教育部等11 個部門聯合印發《關于促進護理服務業改革與發展的指導意見》,從國家層面對護理服務業改革與發展做出頂層設計,要求醫院充分利用互聯網信息技術,推進護理服務業改革創新[1]。2019年2月,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下發《“互聯網+護理服務”試點工作方案》,明確提出“互聯網+護理服務”,鼓勵醫療機構利用本機構的注冊護士,借助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以“線上申請、線下服務”的模式為主,為出院患者、罹患疾病且行動不便的人群提供護理服務、護理指導、健康咨詢等[2]。試點工作方案首先確定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廣東省6 個省市,開展“互聯網+護理服務”的試點工作,并在2020年將試點工作擴展至全國。“互聯網+護理服務”體系滿足了我國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醫療衛生需求,在老齡化時代必將會成為一種剛性需求[3]。但其服務體系尚不健全,存在諸多問題,如護士多點執業未完全開放、政策支持不足、管理機制不完善、護患安全缺乏保障、收費較高等[4-8],這些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互聯網+護理服務”的良性發展。本文擬結合我國“互聯網+護理”上門服務現狀及的實踐經驗分析“互聯網+護理”上門服務中護士人身安全存在的隱患及其解決思路,為“互聯網+護理”上門服務的進一步推行提供參考。
1 “互聯網+護理”上門服務中護士人身安全現狀
1.1 上門服務中護士人身安全風險高于醫院執業
在醫院執業過程中,護士與醫生合作醫治患者,而在“互聯網+護理”上門服務中,護士需要自己單獨操作,在沒有醫生配合的情況下,護士對疾病的治療、護理會受到限制,可能導致疾病的延誤治療。此外,護士在上門服務用藥過程中,一旦遇到藥物安全、過敏等問題,不及時和不妥當的處理均會加大醫療風險。有研究表明,上門服務的護士中,13%經歷過一次不良事件,20%~33%經歷過藥物問題和不良反應,35%的護士和6.4%的助理護士在家庭醫療服務中至少經歷過1 次銳器損傷[9]。另外護士大部分為女性,為患者提供上門服務,可能增加護士的人身安全隱患[10],且目前醫患關系不容樂觀,如果護士的操作未達到患者的預期目標,極易發生糾紛,護士的人身安全將更加得不到保障。
1.2 護士人身安全相關制度不完善
“互聯網+護理”上門服務自開展以來就呈現出巨大的市場需求,但上門服務護士的人身安全配套防范措施未與市場同步。護理服務平臺迅速發展,但至今仍沒有一部專門用于保護上門護士人身意外風險的法律,沒有細化的安全制度與成熟配套的上門服務保險,故無法從法律層面確保上門護士人身安全,這也成為醫院及上門護士的主要顧慮。因此從國家層面立法保障執業安全迫在眉睫,也有研究表明,93.9%的護士希望能從國家層面明確立法,以保障執業安全[11]。
1.3 護士人身安全培訓不到位
護理安全的關鍵就是護理人員的安全意識,提高護士安全風險意識是安全管理的第一步[12]。醫院在臨床中更多強調的是工作,對護士的安全意識不夠重視,從而專門針對安全意識的培訓很少,尤其是防暴培訓。有調查結果顯示,在臨床護理工作中,有93%的護士受到過患者不同程度的暴力侵害,僅有17%的護士對暴力先兆的知識和技能表示了解,未接受和很少接受防暴知識和技能培訓的護士占57%和25%[13]。由此可見護士的人身安全培訓不到位,尤其是在進行上門服務中,護士的單獨執業和女性身份更增加了人身安全風險。
1.4 護士應急處置能力不足
護理應急處置能力是每個護理人員所必需掌握的,是觀察患者病情變化、進行分析判斷、沉著果斷配合搶救和護理的基礎。有研究顯示,69%的護士對突發性事件急救護理有過恐慌心理,不知如何處理,75%的護士對突發性事件急救處理存在思想顧慮[14],更有調查表明,55%的護士希望能接受不良事件發生后的應急培訓,45%的護士希望能得到護理安全相關法規培訓[15]。在上門服務中,護士需要單獨去面對患者,不可預見的病情變化及突發事件對上門服務護士的應急處置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現有的護士應急處置能力水平尚無法滿足。
1.5 平臺建設中缺乏事前預防機制
試點工作方案中要求試點醫療機構或互聯網信息技術平臺應為護士提供手機App 定位追蹤系統,配置護理工作記錄儀,配備一鍵報警裝置,保障護士執業安全和人身安全。然而在現實中,能夠做到的平臺很少,個別平臺在上門服務中全程沒有監控設備和應有的保障,僅通過電話確認安全,一旦服務中發生問題,將得不到有效監管和及時處置,存在巨大的安全隱患。
2 “互聯網+護理”上門服務中保障護士人身安全的對策與思考
2.1 完善“互聯網+護理”法律體系和服務體系
制定完整的“互聯網+護理”法律體系是“互聯網+護理”上門服務保持持續發展的根本條件。用法律來保護雙方,明確上門護士與患者之間的責任、義務、權利,規避潛在風險,同時保護患者的合法權益。相關機構也應針對上門護士頒布相關的法律,將上門服務可能產生的緊急情況進行系統的分類,提供相應的配套保障措施。另外,醫療費用也是目前患者、上門護士及醫療機構關注的重點,是護患沖突的又一導火索,據調查,由醫療費用而產生的醫患沖突占總醫療沖突數量的50%以上[16]。各地區應根據本地實際消費水平,與市場接軌,劃定統一、合理的收費標準,并在平臺上進行價格公示,讓收費變得更加透明。
2.2 嚴格醫療機構管理
醫療機構應加強對上門護士執業資格的準入審核,明確職責,并對其進行培訓與考核,考核合格方能上崗。同時建立服務評價機制,實行動態評估管理,針對不能滿足上門服務需求的護士,及時退出。醫療機構還應對上門護士服務內容進行系統劃分和明確規定,上門護士只對規定內的操作進行處理,超出范圍的建議患者前往醫院進行醫治,以保障患者安全,進而規避自身風險。因患者隱瞞病情或有違法行為而導致上門護士受到傷害時,醫院可將患者拉至醫療黑名單,同時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以保障上門護士執業安全。
2.3 強化上門護士安全培訓及應急處置能力培訓
醫療機構可通過舉辦講座、情景模擬、應急演練、小組交流等形式組織培訓,培養護士的安全意識,提高其應急處置能力。例如上門護士之間可進行溝通交流,對所發生的安全事件進行還原,共同分析、探討,避免相關安全事故再次發生。同時護士應在上門服務時提高警惕,首先核對患者的身份信息,核對之后進行環境和患者評估,如存在安全隱患則應及時向患者說明情況后離開,必要時可以安排同行人員進行協助。在上門服務過程中護士應將手機定位一直開啟,使用平臺提供的攝像頭和報警器,錄像設備在不侵犯患者隱私的情況下使用,為醫患糾紛時提供證據,同時保障自身安全。
2.4 建立上門服務協議管理機制
上門服務中,護士應與在醫院一樣,進行操作前的解釋工作,并取得患者的配合,必要時與患者簽訂服務協議,詳細注明服務的內容、權利與義務等,使患者對于服務的具體信息充分做到知情同意[17]。如患者住院所在的醫院可提供“互聯網+護理”上門服務,可以考慮在出院前和患者進行溝通,并在醫院提前簽署相關協議,方便后續護士上門服務。
2.5 遠程會診助力護理上門服務
遠程會診突破了時間、空間、人力的限制,可隨時隨地進行交流,凸顯了“互聯網+”的內涵,展現出更加廣闊的應用前景[18]。在護理上門服務前,依靠遠程會診,醫護通過視頻的方式在線了解患者的具體病情,共同制訂上門服務方案。在上門服務過程中,上門護士也可通過遠程會診平臺,醫護專家共同在線指導,協助上門服務護士更好地完成患者的護理工作。
2.6 加強第三方機構平臺的構建和完善
第三方機構應構建完善的信息平臺,保持設備的先進性,為護士提供一鍵報警和定位設施配套設備,根據需要配備必要的防身物品。為保障上門服務途中安全,部分平臺開展了與滴滴的合作,平臺可對護士的位置進行核對,并嚴格查看錄像設備,與醫院、滴滴共同保護上門護士的路途安全。同時平臺還應為護患雙方提供保險保障,包括雇主責任險、護理責任險、意外險等。平臺、醫院、政府管理機構合作建立糾紛快速處理通道,在操作中一旦發生糾紛,護士立刻上報平臺與醫院,由醫院和平臺合作進行糾紛的探討和初步處理,然后交予政府管理機構進行糾紛解決與定責。另外還應構建護士上門服務滿意度評價指標體系,由平臺在護士上門服務后,進行患者電話或者線上的回訪,達到持續改進的目的。
3 小結
“互聯網+護理服務” 模式實現了護理服務從醫院延伸到家庭,可滿足老齡化社會的剛性需求,但我國“互聯網+護理”上門服務起步時間較晚,目前仍在初步發展階段,影響其發展的核心關鍵仍然是護患安全的問題[19-21]。為順應時代對上門護理服務的需求,應更加注重上門護士的人身安全,通過政府、醫院及第三方機構平臺的共同努力,降低護士上門執業風險,保障護患安全,推動“互聯網+護理”上門服務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