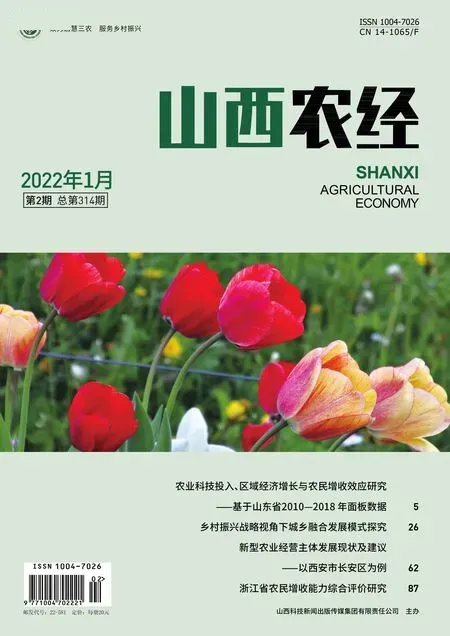生態保護與農戶生態補償的耦合推進機制研究
——以東北地區養殖農戶生態補償為例
□萬 婷,寧 彤
(東北農業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30)
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從“三農”工作的開展到十九屆六中全會的落幕,鄉村經濟的發展一直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經濟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的良性保護也不可忽視。
1 生態保護與農戶生態補償的耦合意義
1.1 理論意義
1.1.1 解決農戶的生計問題
得益于得天獨厚的自然氣候,我國東北地區孕育了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對動植物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動物的養殖和食用產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經過當地居民的代代摸索和傳承,東北地區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養殖業產業結構,這是無數養殖農戶賴以生存的根基。然而,生態保護的失當導致動植物生長環境質量下降,動植物的存活率不高等原因造成農戶獲取動植物的質量與數量都呈下降趨勢,甚至是缺產現象,因此無數養殖業農戶不得不面臨“失業”的處境。為此,如何做好生態補償,怎樣使生態保護與農戶生態補償做到耦合推進,對于解決“失業”農戶的生計問題至關重要,而這也正是文章研究生態保護與養殖農戶生態補償耦合推進的重要目的之一。
1.1.2 破解經濟發展需求和生態保護管控的平衡矛盾
東北地區的養殖業有著數量上規模化、種類上多樣化、品質上高質量化的特征,在我國養殖業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為東北地區的GDP 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環境保護不當、生態資源的過度攫取導致生態失調,對東北地區養殖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沖擊。
不僅如此,從產業之間的相關牽連性可知,養殖業的下流產業如服務業,會不可避免地受到生態失調的影響,諸多產業的發展受到影響,這對東北地區的GDP 帶來一定的打擊。由此可以看到生態保護失調帶來的危害觸目驚心,加強生態保護十分重要,相比經濟發展,良性的生態環境、國民賴以生存發展的“綠水青山”顯然是重中之重。
1.1.3 完善生態保護管控和生態補償機制的銜接
現行法規法律層面涉及6 部法律如《環境影響評價法》,法規層面涉及4 部法規如《環境保護稅法實施條例》,規章層面涉及12 件規章《農用地環境管理規章》,黨的十九大以來,生態環境部門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積極推動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取得新的進展。在過去的生態補償機制中,關注重點多在于自然層面,社會層面關注度較小。而近幾年的法律法規的推進制定,使社會層面的主動性大大加強,推動生態補償機制的完善,實現生態保護管控和生態補償機制的無縫銜接,是研究生態保護與養殖農戶生態補償的耦合推進的重要目標[1]。
1.2 實際意義
1.2.1 有利于東北地區生態保護事業的發展
生態環境是農業養殖發展的重要區位因素,因此,在發展中要重視養殖業發展對生態環境帶來的影響。但是在考慮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勢必會犧牲農戶部分的經濟利益,而通過研究生態保護與養殖農戶生態補償的耦合推進,可以為受到生態保護各項條件限制的農戶提供一定補償,為其生活提供一定保障。在完善的生態補償機制下,東北地區的生態保護事業發展受到的阻力會極大減輕,在加強生態保護管控領域邁出一大步,有利于東北地區生態保護事業的發展。
1.2.2 有利于生態補償機制的制度化、法治化完善
過去,我國各地生態補償機制一直參差不齊,很多地區在立法、政策方面存在著規定重復、漏洞多、不全面、不系統等問題,這也導致我國生態補償機制的不完善。十九大以來法規法律規章的制定與頒布正是整合東北地區生態補償法律、政策,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契機。通過研究實現生態保護與養殖農戶生態補償的耦合推進,有利于實現生態補償機制的制度化、法治化完善。
1.2.3 有利于精準扶貧與生態補償機制的有機銜接,協同推進
東北地區眾多養殖農戶經濟狀況參差不齊,其中存在著大量的貧困人口。當前我國實施精準扶貧,貧困戶得到了極大的關注與幫扶。通過研究生態補償與養殖農戶生態補償的耦合推進,對大量“失業”的養殖農戶進行分類,篩選出其中的貧困人口并給予政策扶持,有利于精準扶貧與生態補償機制的有機銜接,協同推進。
2 生態補償機制的國內外研究現狀
2.1 國內研究現狀
在研究該問題前,有必要梳理生態補償機制的理論及實踐。從實踐情況來看,我國的動物資源集中分布于人口密度稀少的東北部和西南部地區,而這些地區的經濟往往比較落后。同時,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享受著動物資源帶來的生態價值卻無須付出相應代價,難以讓民眾真切地關注并重視動物保護甚至維護生態環境,這也不符合均衡發展、公平發展的理念,不利于生態保護的整體發展。在我國現行的環境法律體系中,所說的補償尚停留在行政補償層面,沒有明確定義為生態補償[2]。而將生態保護補償上升到“生態補償”的意義更符合生態保護的立法主旨和實現生態公平的迫切需要,更有利于落實對生態保護工作中的受損者進行補償,激發人們在生態與環境保護工作中的積極性。
2.2 國外研究現狀
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在立法上很重視生態動物福利問題,甚至有的立法中將動物納入主體地位,動物能夠得到很好的保護。我國雖然將動物至于客體地位,但也認可了動物福利觀點。各國建立了不同的生態保護制度,如生境保護制度、自然保護區制度、生態保證金制度等,但多數集中在動物福利的建設上,關于其中生態補償制度尚沒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也鮮有國外的著作與研究。
3 環境保護與生態補償的研究對象
我國養殖產業發展歷史悠久、規模巨大、種類繁多,馴養繁殖產業有300 多年的歷史。我國政府極為重視生態動植物的保護工作,同時注重野生動物的人工繁育養殖。
此外,野生動物養殖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點,例如東北地區的林蛙、東北虎等。除了具有地域性特點之外,野生動物還具有一定成熟性。以黑龍江省為例,黑龍江省野生動物養殖產業遍及全省,其主要產品多用于觀賞、藥用、肉用以及珍稀物種的保護,全省現有500 多家鹿場,馴養梅花鹿和馬鹿8 萬頭左右,年產鹿茸60 t,馴養毛皮種獸340 多萬只,年產毛皮以百萬計。養殖產業相對于其他產業具有明顯的綠色環保性,產業養殖過程中排放的廢物污染相比一些工業少之又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較小,同時利用這一產業使大批貧困地區農戶實現脫貧致富。養殖產業也具有很大的風險,較為突出的就是“檢疫”工作不到位,從幼種到出欄,長期存在檢查空白,導致破壞自然生態與傳統生產模式產生的消極影響大大增加。
為進一步了解和分析生態保護法規中具體操作程度以及與之具有利害關系的群體的反應和接受程度,相關人員對100 位農戶進行了調查并收取了數據結果。關于農戶對生態保護相關法律法規的了解程度調查結果顯示,有88%的農戶對此關注;關于農戶家庭收入占比調查結果顯示,養殖收入占比最高,超過了打工、務農,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
對農業補償政策滿意程度使用了Logistic 模型,其所需條件相對寬松,適用性更廣。根據調研結果分析,農戶對于養殖退出補償的整體滿意度并不好,其中,表示滿意的農戶占24.7%,表示不滿意的農戶占75.3%。
3.1 個體特征
從理論上說,農戶受教育程度越高,對政策的理解力就更強。但在樣本中,農戶受教育程度差異不大且普遍較低,高中及以下的農戶占75%,而身份上的差異導致了村民和村干部之間的信息差異,村民個體對生態保護的認知參差不齊。
3.2 養殖特征
養殖年限和規模對農戶具有明顯影響。養殖年限越久,農戶對市場需求把握更高,更加敏感,養殖的規模則對農戶有基礎性影響。規模大小決定著農戶投入的程度以及農戶對其的預期。隨著生態保護下政府各種政策的出臺,農戶原本的預期與面臨的實際考驗形成巨大反差,導致滿意程度低。
3.3 認知特征
農戶對生態保護相關條例認知程度明顯對補償滿意程度有著反向影響,同時對其評價程度也隨之下降。農戶面對政策變動時,更多衡量自身利益出發,并且將不利因素歸于政府和政策。
4 生態保護與生態補償耦合推進的建議
4.1 采用多樣化的分析方法進行理論研究
采用文獻分析法將收集到的文獻資料與國家大政方針、中央一號文件等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以此了解其他地區生態保護相關條例頒布后對養殖農戶生態補償的實施情況,進而對東北地區的養殖農戶生態補償進行指導分析。《生態轉移支付——基于生態補償的橫向轉移支付制》詳細闡述了生態補償機制等具有研究意義的概念,在立法上的思考與碰撞更益于推動鄉村生態保護方面的法治建設。提出要將理論轉化為實踐,將試點擴大到全國,結合時事分析農戶生態補償中“誰來補償”與“補償給誰”的核心問題以及國家“輸血型”模式向“造血型”模式的轉變問題。
運用比較分析法將東北地區已落實生態補償的省份與未落實的省份進行對比,考究其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將東北地區養殖農戶的涉及補償主體進行歸納,并將直接養殖農戶補償與涉及多方利益牽涉的補償主體的態度進行對比分析,考究其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
4.2 加強農戶在生態補償機制下的生態保護意識
調查發現,教育程度、養殖經驗規模等方面的差異與農戶生態保護意識有一定的相關性。因此在加強農戶的生態保護意識時應該分類施行,對于教育程度低、養殖規模小的農戶,應用淺顯易懂的方式宣傳鄉村的環保重要性,村委會要加大宣傳,讓生態保護成為農戶的“談資”,潛移默化地影響農戶行為。對于教育程度高、養殖規模大、經驗較為豐富、對生態保護有比較清晰認知的農戶,鄉村應加快制訂處罰規定與生態補償的獎勵制度,從源頭抑制養殖過程中可能造成生態破壞的行為。
4.3 生態補償方式多樣化轉變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提及推進鄉村經濟振興戰略,對農戶進行生態補償,但是生態補償大多只停留在資金補償[3]。這種單一的補償模式并不能調動農戶的積極性,而且由于農戶數量眾多,一方面,規范資金的補償數量是一大難題,較大的資金補償對于國家財政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支出,需要較長時間規劃;另一方面,資金補償的方式對于鄉村經濟、農戶來說并不是可持續的發展方式,一代又一代農戶在這種單一的模式下會極大的缺乏生產積極性。因此,生態補償應該多樣化,可以對農戶進行產業結構轉移的補償支持,前期進行資金幫扶,開展新產業,后期令其自主發展。
4.4 政府應積極引導,承擔責任
長期以來,學界和業界關于“野生動物”的概念一直處于模糊狀態,不同的主體對其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界限難以確定。疫情讓部分養殖業處于停滯狀態,養殖戶處于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4]。一方面,養殖作為農戶重要的收入來源,需要付出極大的成本努力維護和經營;另一方面,“禁野令”的政策以及部分野生動物陸續收錄在重點保護名錄中,農戶不敢貿然擴大經營,只能等待與觀望。
養殖農戶作為弱勢群體,面對保護生態付出了一定代價,為社會的穩定和諧作出了貢獻。為了避免農戶受到二次打擊,承擔不必要的代價,政府應當積極建立引導機制,對農戶提供經濟上的援助和政策上的支持。國務院以及各地政府要提供相應的保障,在落實“禁野令”政策的同時,政府也要提前做好相應的應急方案,對農戶經濟造成的損失和影響進行風險評估,建立有序、健康的退出機制[5]。慎重考慮、兼顧個體養殖戶的經濟利益。政府應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對農戶進行經濟補償。同時養殖產業周期長,在初期資金需求大,農戶大多會采取向銀行貸款的方式獲取資金,現在“禁野令”的頒布導致養殖產品無法投入市場,農戶失去收入來源,還貸壓力增大。政府可以引導銀行降低貸款利率、延長還貸;引導農戶向其他產業方向發展,提供啟動資金、技術以及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實現產業轉型;出臺再就業政策,整合當地資源提供更多崗位。盡可能減少農戶損失,做到保證社會效益,讓群眾滿意,確保整體局面健康發展。
5 結束語
踐行生態保護的可持續發展一直是我國堅持的發展理念,在生態環境損害與農戶的生態補償矛盾問題下,推進二者的耦合更加成為了平衡二者的關鍵。探討科學合理的耦合機制,是為了避免“誤傷”和不必要的損失,實現人和自然的和諧發展。要加大政府政策支持,加強農戶重視意識,并踐行“金山銀山就是綠水青山”的發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