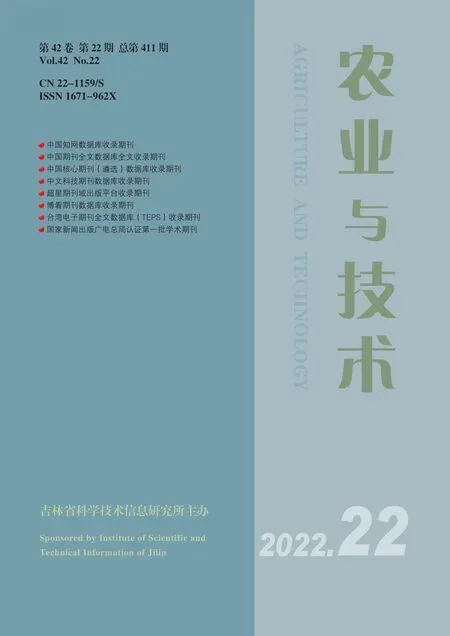我國有機農業發展及其影響因子的驅動響應機制
盧瑜向平安
(1.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4;2.湖南農業大學商學院,湖南 長沙 410028)
有機農業在落實鄉村振興戰略、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改善農產品質量和促進農民增收等方面意義重大,我國政府在歷年政策文件中均大力提倡推廣和發展有機農業[1,2]。然而,盡管發展迅速,但有機農地面積仍然僅占農地面積的很小部分(1.89%)[3,4],有機農業大規模發展仍富挑戰性。學者們基于地區層面的數據分析了區域有機農業發展的影響因子,發現區域有機農業發展差異受到了農業生態因子、農場結構因子、社會經濟因子和政策因子等的影響[5-11]。現有研究雖然做出有益探索,但基于理論分析和文獻研究構建的結構化模型并不足以對有機農業發展及其影響因子間的動態關系提供嚴密的說明;變量內生性問題也將導致有機農業及其影響因子間關系的估計和推斷復雜化,而向量誤差模型(VECM)作為非結構化的多方程模型可以很好地解決上述問題。
基于此,本文基于2004—201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在向量誤差模型的基礎上運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有機農業發展及其影響因子間長期動態關系,力圖從宏觀角度考察我國有機農業發展規模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農業生態條件、政策環境等影響因子間的作用機制與定量關系,以期為促進我國有機農業發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方法
脈沖響應函數分析VECM既可以刻畫有機農業發展及其影響因子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又能同時觀測各影響因子沖擊對有機農業發展的影響效應,因此采用VECM模型:

(1)

依據向量移動平均模型(VMA):
(2)
可得,由yj的脈沖引起的yj脈沖響應函數的矩陣形式:
(3)

1.2 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重點從宏觀角度探討有機農業發展與其關鍵影響因子之間的動態關系及相互作用機理,借鑒國內外有機農業相關研究成果,同時考慮我國有機農業的發展特點,重點從市場需求、生產供給、產業化組織、認證帶動、技術創新、風險保障和政策環境幾個角度研究有機農業發展及其影響因子間動態驅動響應機理。表1歸納了相關影響因子變量與有機農業發展的關系。

表1 用于實證分析的變量說明和描述
鑒于有機農業相關數據的可得性,采用我國2004—2019年時間序列數據展開分析。有機農業總面積及有機產品認證數據來源于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信息中心及我國食品農產品認證信息系統,生態環境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勞動力資源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有機產品加工和貿易數據來源于歷年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的《中國有機產品認證與有機產業發展》報告;農業合作社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居民收入水平和自然保護區占轄區面積的比例等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統計年鑒》,農業保險費收入數據來源于歷年你的《中國保險統計年鑒》。
2 結果與分析
2.1 模型識別和檢驗
2.1.1 平穩性檢驗
表2列出了我國有機農業發展及其影響因子各變量序列對數處理后的ADF平穩性檢驗結果,原序列ADF統計量均大于1%、5%和10%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P值大于0.05,接受原序列非平穩的原假設。而二階差分序列均通過了1%或5%的顯著性檢驗,表明我國有機農業發展及其影響因子各變量序列均為二階單整序列,符合協整分析條件。
2.1.2 協整檢驗
表3列出了我國有機農業發展與其影響因子的協整檢驗結果,結果顯示,我國有機農業發展與其影響因子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其中,有機農業發展與市場需求因子之間具有至少存在2個協整關系。有機農業發展分別與農業生態因子、技術因子、認證帶動因子及風險補償因子間至少存在1個協整關系,有機農業發展分別與勞動力因子、資本投入因子及產業化組織因子間至少存在2個協整關系,有機農業發展與政策環境因子間至少存在3個協整關系,有機農業發展至少存在1個協整關系。

表2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
2.1.3 格蘭杰檢驗
表4列出了我國有機農業發展與其影響因子間的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有機農業發展各影響因子變量的Granger因果檢驗以及聯合檢驗均通過顯著性檢驗,拒絕原假設,說明各影響因子均是有機農業發展的格蘭杰原因。
2.2 脈沖響應分析
選擇10期的沖擊響應,運用Eviews 12.0軟件生成有機農業發展與影響因子之間的脈沖響應函數圖,見圖1~6,橫軸為響應期,縱軸為有機農業發展的響應值,實線表示有機農業發展對各影響因子沖擊的脈沖響應或累計脈沖響應,虛線為±2倍的標準差偏離值。
2.2.1 有機農業發展對市場需求因子的脈沖響應
分別給居民消費水平和有機產品出口貿易量一個正的沖擊,圖1給出了采用廣義脈沖法得到有機農業發展對于市場需求的脈沖響應結果。反應期內,居民收入水平對有機產品出口貿易量的脈沖響應均表現為小幅上下波動,見圖1a、圖1b,1~10期的累計沖擊反應值分別為0.16和0.14,見圖1c、圖1d,表明居民收入水平和有機產品出口貿易量對有機農業總面積的動態沖擊響應效果整體上表現為遞增促進作用,且整體效果并不顯著。

表3 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
2.2.2 有機農業發展對生產供給因子的脈沖響應
圖2匯報了基于廣義脈沖法的有機農業發展對于生產供給因子的脈沖響應結果。有機農業面積對生態環境質量的脈沖響應第2期為負值,而3~10期為正值,見圖2a;1~10期的累計脈沖響應值為0.13,見圖2b,表明生態環境質量對有機農業面積具有正向影響且具有較長的持續效應,但長期持續效應并不顯著。有機農業面積對勞動力資源數量的脈沖響應在反映期內小幅上下波動,見圖2c;1~10期的累計脈沖響應值為0.85,見圖2d;表明勞動力資源數量對有機農業面積具有遞增促進作用。
對有機產品加工量施加一個單位的沖擊,有機農業面積的脈沖響應表現為先升后降并逐步收斂的趨勢,見圖2e,反映期內的累計沖擊反應值為0.46,見圖2f,表明有機加工對有機農業發展整體上具有較為顯著正向促進作用,但響應持續性在第6期后逐步收斂。

表4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圖1 有機農業發展規模對市場需求因子的脈沖響應
2.2.3 有機農業發展對產業化組織因子的脈沖響應
圖3給出了有機農業發展對于產業化組織的脈沖響應結果。反應期內有機農業面積對農業合作社數量的脈沖響應先升后降并于第7期后趨于平穩,見圖3a;1~10期的累計沖擊反應值為0.65,見圖3b;表明農業合作社對有機農業發展的動態沖擊響應效果整體上表現出較為顯著促進作用。
2.2.4 有機農業發展對認證帶動因子的脈沖響應
圖4給出了有機農業發展對于認證帶動因子的脈沖響應結果。反應期內有機農業面積對產品認證的脈沖響應先升后降并于第3~4期達到最大值,隨后于第6期開始趨于平穩,見圖4a;1~10期的累計沖擊反應值為0.61,見圖4b;表明有機產品認證對有機農業發展的具有較為顯著的正向影響。

圖2 有機農業發展規模對生產供給因子的脈沖響應

圖3 有機農業發展規模對產業化組織因子的脈沖響應
2.2.5 有機農業發展對政策環境因子的脈沖響應
圖5給出了有機農業發展對于政策環境的脈沖響應結果。有機農業面積對自然保護區的脈沖響應也呈現先升后降趨勢,并于第5期開始趨于穩定,第8期逐步收斂,1~10期累計響應值為0.16,表明自然保護區面積份額雖然對有機農業發展具有正向沖擊,但沖擊效果并不顯著。

圖5 有機農業發展規模對政策環境因子的脈沖響應
2.2.6 有機農業發展對風險保障因子的脈沖響應
給風險保障因子施加1個單位的沖擊擾動,有機農業面積的脈沖響應先升后降,隨后小幅回升并于第8期后趨于穩定,見圖6a;1~10期累計響應值為0.59,見圖6b;說明農業保險對于有機農業發展具有正向作用,且較為顯著。

圖6 有機農業發展規模對風險保障因子的脈沖響應
3 討論
3.1 市場需求因子對有機農業發展的影響
本文發現居民收入水平和有機產品出口貿易量對我國有機農業發展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但整體市場需求因子帶動效果并不顯著,且我國有機農業發展更多依賴于出口。市場需求是有機農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有機產品上的預算份額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10],高收入將增加有機產品的需求,從而帶動有機農業發展。歐洲和北美市場居民收入高,有機食品市場需求巨大,有機產品出口歐美市場能夠實現優質優價,從而提高農戶有機生產積極性,帶動有機農業發展,因此我國有機農業發展得益于出口需求帶動,然而我國有機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占比仍然較低,且國內市場需求受制于購買力限制,因此整體市場需求帶動效果并不顯著。
3.2 生產供給因子對有機農業發展的影響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農業生態條件和勞動力供給對有機農業發展變化的解釋貢獻度最大,這和部分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7,8]。由于有機農業發展的前提是區域自然生態環境達到有機生產的環境標準,因此有機農業發展受制于自然生態條件約束;此外有機農業所需勞動力成本明顯高于常規農業,勞動力供給對有機農業發展具有顯著影響[4,5,7,8]。本文發現有機產品加工對有機農業發展具有一定帶動效果。這可能源于有機加工可提高有機產品的附加值,促進銷量和經濟效益提升,從而帶動生產者轉型有機農業。
3.3 產業化組織對有機農業發展的影響
本文發現我國有機農業的發展依賴于產業化組織驅動,這部分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14]。我國農業生產主體主要為分散化的小規模農戶,各類農業組織可通過利益、合作和產業化機制等將分散農戶有機整合,實現規模化經營,提高生產銷售效率,從而推進有機農業的發展。
3.4 有機認證對有機農業發展的影響
信息不對稱條件下有機產品認證通過形成約束和激勵機制來促進有機市場健康有序發展進而帶動有機農業發展[15],這與本研究得出結論一致。通過建立國家標準對有機農業進行認證,可規范市場準入、帶來溢價、提高有機產品市場認可度和市場競爭力,從而促進有機農業發展。
3.5 政策制度對有機農業發展的影響
現有研究表明,政策和制度因子是有機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4-7],這和本研究結論一致。政策和制度通過正向激勵(農業補貼、信貸支持和技術培訓等)或反向抑制(農業環境規制:化肥農藥使用量零增長和農業農村污染治理等)來引導生產主體轉型有機農業,從而實現有機農業的發展。
3.6 風險保障對有機農業發展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風險保障對于有機農業發展具有較為顯著的帶動效果,這可能源于有機農業相比常規農業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如產量低、易受病蟲害及自然災害影響),限制使用農藥、化肥和合成藥物將增大風險,同時在我國大量小規模生產農戶的市場風險承擔的能力弱,因此有機生產環節的風險保障支撐尤為重要。
4 結論與啟示
基于2004—2019年我國有機農業的時間序列數據,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基礎上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法探究有機農業發展與各影響因子之間的動態沖擊效果和相互作用機理。得出如下結論。
有機農業發展與市場需求、農業生態、勞動力供給、農業科技投入、資本性投入、產業化組織、認證帶動、政策環境和風險保障等影響因子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且各影響因子均是有機農業面積Granger變動的原因,適宜于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基礎上進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脈沖響應分析表明,有機產品出口貿易、農業合作社、有機產品加工、有機產品認證、勞動力資源數量以及農業保險對有機農業發展的帶動效果較強,居民收入水平、生態環境質量和自然保護區占比的帶動效果較弱。
據此,本文建議公共部門推進有機農業發展的政策可以促進有機產品出口貿易、支持有機農業合作組織發展、支持有機產品認證示范創建項目、擴大有機農業保險覆蓋面和提高有機農業相關的政策性補貼等為重點支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