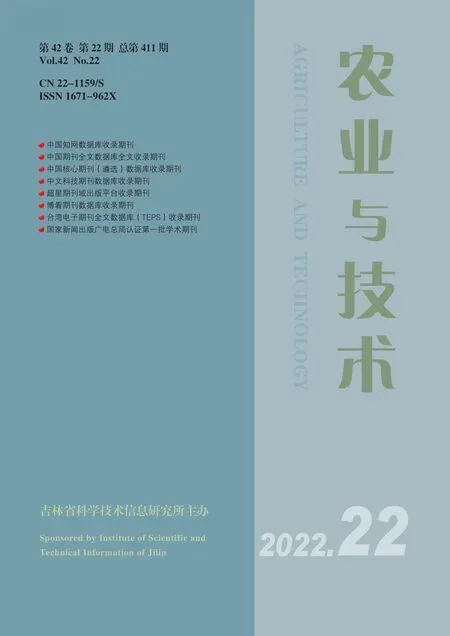基于原型理論的傳統村落文化空間分析
吳浩浩 尹建強
(湖南農業大學,湖南 長沙 410000)
中國自古是一個傳統的農耕文明社會,在上千年的發展過程中,農耕文明社會下的中國形成了有別于其他國家以及文明的文化意識形態與珍貴的歷史印記,傳統村落是農耕文明下的實踐者與歷史時代的經歷者,每一個傳統村落都有其獨特的文明底蘊以及魅力,面對不斷城鎮化的發展,在南方傳統村落的歷史延綿中,不斷面對如古址被人遺忘而逐漸破敗、文化獨特性的無奈失傳、人口搬遷而帶來的傳統村落空間蕭條等眾多外部因素以及內部因素不斷影響的大環境下,如何將傳統村落本真的歷史文化內涵與公共空間等進行有效的提煉與分析,從而對村落進行優化更新,留住最為質樸的記憶成為了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基于原型理論與文化分析的理論基礎
1.1 原型的形成
西方著名心理學家榮格提出了“集體潛意識”的概念,認為人類在歷史和進化過程中累計出來的類似于本能的一種機體經驗,這種“集體潛意識”是一種抽象概念,囊括的內容相當廣泛。
原型概念也是對“集體潛意識”這一概念的補充與加深,其是承載集體潛意識的、能被對象化的概念,一種“典型的領悟模式”[1],通過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在原型基礎上將個人情感與時代需求注入,從而喚起人們的集體記憶[2],因此,集體潛意識必須通過其特殊的載體——“原型”來顯現,要了解具體的集體潛意識,需要從原型中去分析[1]。原型概念在實際中可以理解為是一個地域當中的文化、歷史、環境、自然地理經過時間的地域性發展通過一定的形式被一個群體所傳承成為該地域中所獨有的原始意象或者實體事物,原型對最終形成于當地的空間實物起影響作用。
1.2 原型與文化的關系
原型可以滿足人們對于物質文化的需求以及精神文化的渴望,是一種可以被一個群體永遠傳承的記憶,其組成可以分為2個層面。物質層面即物質性原型,物質性原型是實體空間形成的結果與空間肌理、形制結構的外在顯現,空間肌理實體如人工再造加工的空間形體材質,各類紋路肌理、繪畫、雕刻圖騰等空間具象形態;非物質層面即非物質性原型,非物質層面為指導實體設計的思想意識觀念層面,是村民在歷史實踐中選擇的結果,其與生活相關聯密切,如宗族關系、儒家文化、客家文化中對空間形成起決定影響作用的文化因素。2種層面的原型都是基于一定的地理環境要素與居民生活以及精神需求互相交融的結果,對空間的形成、空間層次的完善與提升起著深遠的影響作用。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由一定文化創造出來,并成為該文化思想基礎的東西[3],任何群體所塑造的空間都具有文化寓意性,物質性原型以及非物質性原型一種是外顯一種是內涵,兩者都具有可遺傳的文化寓意性且相互關聯,對于地域性傳統村落景觀的設計有著歷史性的作用。
1.3 原型與空間肌理的邏輯關系
原型的形成是多方面的,物質性與非物質性原型都是居民通過歷史、自然環境、人文內涵、特色性材料材質經由村民繼承與發展通過不斷實踐互相選擇的結果,在構建空間肌理當中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經由歷史的發展,村民的不斷繼承形成了可遺傳的群體記憶,可遺傳的群體記憶也是原型的核心要點,見圖1。

圖1 原型與肌理的內容形成
非物質性原型即文化要素對于賦予空間功能與意義有著深刻且關鍵的作用,任何空間的功能性都離不開非物質性原型,功能空間的差別在于其外在的表達以及文化內涵的不同,這種群體記憶通過一種具象的形式永久的傳承下來,見圖2。

圖2 原型、肌理與空間的關系
2 應用案例
地處湖南湘西地區懷化辰溪縣的五寶田村,坐落于湖南雪峰山余脈之中,景色秀美,群山環抱,建筑占地面積約6000m2。
2.1 基于原型理論以宏觀角度對五寶田村的文化與空間進行分析
2.1.1 風水文化的分析與提取
風水是人們處理人與自然、社會、文化關系的一種經驗性總結,是古時勞動人民在生產生活當中依據經驗,不斷總結出來的,是一門綜合天文、地理、歷法、水文等理論要素的綜合性體現[5]。五寶田村的各個設計環節在風水文化上的具象體現尤為突出,居民根據對風水文化的內在理解與外部環境的信息提取,將選址的自然地理環境與風水文化一一對應,對當地的環境進行了嚴格的勘察與文化分析,也就是說風水文化作為村落選址的核心思想參考之一,風水文化作為一種文化體系內容極為豐富而居民從中對空間格局的構建起直接指導作用且賦予空間寓意的這一部分文化便是非物質性原型也稱之為文化內涵要素,五寶田選址意義與目的與其原型也有著很深的關聯。
在古代村落之中,山水相依,背靠龍脈,視覺與空間廣闊豁達,居住之地,以大地山河為定居選址的上佳之所,五寶田村將這一文化元素進行了充分的實踐與運用,背靠龍脈的東面是連綿的山巒,西面是既有呈懷抱之勢的案山在空間上相對矗立又有空間開闊的耕地,村落格局中間為形如彎鉤的玉帶溪河流,這樣獨特的環境與出自風水文化的《陽宅十書》這本書中所寫道的:“凡室左有流水,謂之青龍,右有長道,謂之白虎,前有汗池,謂之朱雀,后又丘陵,謂之玄武,為最貴地”[4],青龍、白虎、朱雀、玄武4神相互影響、共生,共同構成了村落建構的整體基調方向與寓意,這種以文化寓意和自然地理環境相互結合的設計對五寶田村獨特的宏觀空間格局形成起到了直接影響作用,基于特殊的地理環境村民以這種文化寓意為非物質性原型作為設計指導形成了五寶田村的村落空間格局及初步功能,這種空間格局是一種實體空間符號,便是物質性原型,其是對環境與非物質性原型寓意性相互作用表達的結果與具象體現。
基于原型理論從風水文化要素以及自然環境進一步分析探討五保田村修建于此地的原因與目的。當地地勢眾山環抱具有其獨特的地勢,能夠聚集陽氣,在這種空間下,發自山勢的陰氣會順著山勢下滑至谷底,也就能匯聚在山谷之中,西邊的水體也能夠起到聚集陰氣的作用,從風水文化寓意的角度稱為“山環水抱必有氣”,也是居民從風水文化當中提取出的非物質性原型,該文化寓意與自然環境相互對應為后續村落空間肌理的形成創造了條件。“氣”是萬物的本源,萬物由“氣”而生,生水,生山川,“藏風聚氣”的根本是四靈之地的思想理念,“四靈”為山,河,路,池的自然環境要素[4],以四靈之地的文化寓意為非物質性原型,村落居民對其進行貼近自然的設計與再造,使其元素整體融入進村落的肌理空間當中形成了物質性原型,這些基于自然環境村民所提取出的文化寓意即非物質性原型對空間的形成起設計指導意義。其深深地烙印在居民的記憶當中,形成了具有傳承性的集體記憶,這種集體記憶具有獨特性,即原型具有獨特性,設計具有獨特性。
村落格局的設計體現了居民對風水文化的注重與敬畏,可以得出居民對于文化、人居與自然相生、包容、上善若水的一種相互協調自然和諧的價值取向,古人在風水文化強調“天人合一”的價值觀理念,人與自然環境的融合與發展,這種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反饋之于自然,趨利避害,因勢利導的價值觀念是五寶田村居民的核心價值觀之一,也是最為重要的情感要素之一。
不同文化要素內涵的運用目的之一便是服務于人,在農耕文明上千年歷史演進過程當中農民與土地有著不可斷絕的情節,農耕土地是農民生存與發展最為根本的物質保障之一,農民對土地、對財富的祈求也深深烙印在了文化當中,所以在運用文化以及選址定居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考量便是是否適合農耕生產生活的健康進行,風水文化要素中對土地耕作的文化要素內涵有“負陰包陽,背上面水”“地無曠土,坦坦平夷,泗澤交流,滔滔不絕”以及“山可樵,水可漁,泉可汲”的描述便是對農耕文明下農耕空間的總體描述與實踐定論,這些文化要素也凝固在了五寶田村的總體發展格調之中,有著充足的陽光與水源的利用,對于農田作物的生長與可持續發展有著天然的促進作用,農耕文明對于自然環境的依賴是極為深刻的,五寶田村做到了小農經濟下自給自足的生活狀態,基于風水文化的影響,這種基于生產生活的需要而促進村落選址進行的現實推動力稱之為生活意向。
2.1.2 宗族文化的分析與提取
宗族文化歷史深遠,在我國可以追溯到古代氏族部落文明時期,群居先人的遠古宗教孕育了宗法觀念的萌芽,宗族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內容、內涵相當廣泛,不同地域的宗族文化存在差異性,經過儒家文化的影響宗族文化的核心便是強調禮、義、忠、孝,五寶田村落居民根據實際生產生活需要在歷史的發展中不斷對宗族文化進行內容的提取與實踐運用,形成了根植于宗族文化當中的非物質性原型,這些以建筑空間塑造、選取以及宗族文化生產生活內容為目的的原型賦予了五寶田村落建筑空間的形制、空間結構布局,并且直接影響了村落空間肌理的形成、文化具象內容的形成與傳承,總而言之原型起著重要且核心的作用。非傳統宗族文化所形成的村落空間與傳統宗族文化形成的空間存在較大的差異性,非傳統宗族文化所構成的村落空間布置格局上體現為具有混居性、分散性,以宗族關系所構成的村落空間布局中體現為群居性與宗法性的獨有特點。
“禮”核心思想的要素內涵。“禮”代表的是一種社會生活中由于某種特定的文化風俗習慣而形成的為大家共同遵守的儀式,“禮”的形成符合某一群體整體利益的行為活動原則,在詞語中有“禮儀”“禮制”“典禮”等具體寓意。宗族文化強調“禮”的思想,這促使居民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建筑功能,空間布局要凸顯“禮”的核心與重要性,文化要素內涵需體現“禮”,在五寶田村的建筑中存在眾多富含且體現“禮”意義明顯的公共活動性建筑,如祠堂,祠堂是單獨某一族群,處于某些宗族聚集性活動而構成的村落空間中的一部分建筑,宗族文化是姓氏的文化根源之一,五寶田村以蕭氏家族為主,祠堂起到了維護蕭氏宗族關系,使蕭氏家族文化得以延續以及鞏固自身宗族文化特色的作用,該建筑是維護以宗法為核心的家族血脈傳承的重要場所之一,在五寶田村祠堂為最古老的建筑,突出了尊老尊祖的“禮制”思想,在這個空間中莊重感與禮節感會顯得相當重要,宗族文化中的血脈親情的交流、思想文化的繼承是該空間的非物質性原型,也是對該建筑空間“禮”文化的深刻詮釋和文化要素內涵的體現,在當地居民中其主要具體活動功能有祭祀、婚嫁、祝壽等宗族重大文化活動,而這些便是非物質性原型即文化要素的具象體現與表達。
“義”核心思想的要素內涵。“義”有遵循倫理原則之意,即要遵循尊卑長幼的思想觀念,在研究中發現五寶田村并沒有獨立設置的核心宗祠建筑空間,所以蕭氏宗族人們用作宗祠功能的建筑單體會選擇村落中最古老的建筑單體,也就是祖屋,祖屋在宗族文化中的建筑群落中的位置處于關鍵地位,是建筑群落當中最為核心、地位最為崇高的獨棟構筑物,祖屋始建于清朝是五寶田村內唯一一棟清代最為悠久的單體構筑物,根據當地老者描述祖屋與祠堂即是選用同一棟建筑單體,兩者在功能上也是重合的,之所以蕭氏族人將祖屋與祠堂重合使用,是因為在蕭氏族人的宗族文化當中存在著對祖先的崇拜與敬仰之情,在祖屋的空間布置上可以明顯看出整體建筑群落是以祖屋為中心進行擴散性排布設計的,建筑等級高向等級低呈階梯型演進,祖屋的堂號為“鄰閣家聲”,其周圍被“師儉清風”“攢侯家聲”環繞包圍突出其地位,這種根植于蕭氏宗族文化當中的尊古重道、尊重祖先的敬仰之情便是非物質性原型,同樣也是直接作用于空間與生產生活以及“禮”的文化內涵要素之一。這種以“義”為核心作用于空間的秩序之美在體現了宗法文化的內聚性、穩定性與傳承性的同時也體現了倫理關系與宗族的等級制度,使得血緣之間的紐帶、宗族歸屬觀念更加的堅固,也表達出不斷促進宗族內部信念團結,不斷傳承發展的宗族價值觀念。
“忠”核心思想的要素內涵。“忠”有忠厚、忠心不二之意,宗族觀念的思想同時也延申到了五寶田村日常生產生活當中,所以村落居民的生活當中宗族活動占有重要地位,“忠”思想也不斷影響著族人,宗族活動在村落歷史的發展當中繼續傳承發展著,受其文化的影響村落居民群聚思想根深蒂固,“忠”的發展促使居民在生產生活中團結意識較強,促使居民互相忠誠、協力奮進,衍生出了具有積極影響的集體主義攻克難關的思想及生活意向,由此體現在思想與生活發展實踐上,各個文化思想的傳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思想教育,在傳統農耕社會當中,五寶田村的文化居民之所以能夠形成一種集體文化記憶,便是出于對長輩和對自身文化根脈的“忠”。村落的建筑設施與形制設計、內部道路材料采集與鋪設等關乎村落形成與發展的一些重大基礎性事項大多依靠居民集體出力建設而成,農田的選地與開荒,居民集體耕作互相幫助意念一致共同發展,在舉行大型宗族活動時,不同家族的成員都會出席活動,共同幫助活動的操辦與正常舉行,這些在宗族文化影響之下的具象生活意向表達亦充分體現了蕭氏家族團結一致共同發展的情感價值觀念。另外,五寶田村居民受其宗族文化的影響有著和諧統一的價值理念,其體現在秩序井然的人居空間上,建筑形制統一為南北長,東西窄,且朝向一致。
2.2 基于原型理論從非物質性原型角度對五寶田村進行歸納
五寶田村中非物質原型要素分類如表1、表2所示。

表1 五寶田村中非物質原型要素分類(風水文化)

表2 五寶田村中非物質原型要素分類(宗法文化)
3 總結
空間與自然地理人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其在不同的空間上被居民選取運用,并在最終塑造而成的肌理與內涵上體現出了不同的原型,原型理論在研究村落空間中具有豐富的學術價值,同時也為鄉村振興戰略農村空間的設計與規劃提供了新的設計角度與思維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