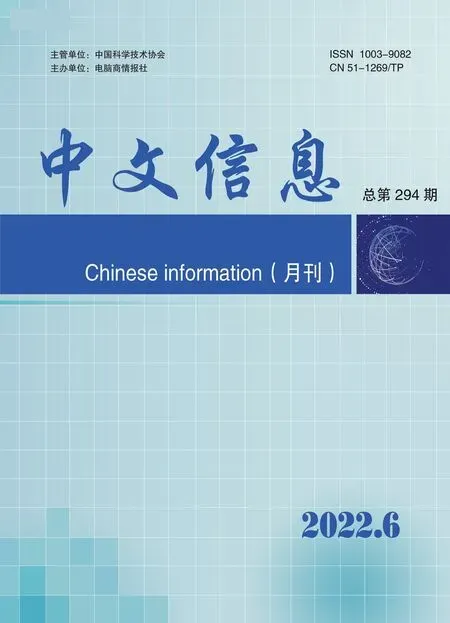賽博空間的共謀:《王者榮耀》機制與主體關系探究
鐵彥輝
(深圳大學,廣東 深圳 518000)
自20世紀80年代中國逐漸普及計算機教學,國內玩家群體經歷了從“娛樂和學習者”到 “文化消費者”的身份轉向。此時,玩家的身份認同、共同體意識逐漸形成,數字游戲的商品性開始顯著于游戲性[1]。而后以《王者榮耀》為代表的MOBA類游戲崛起,它結合與利用現實社會時代的競爭意識,并改變游戲內部消費方式,向外發展游戲資本產業,將玩家的身份變成商品消費者。數字游戲是工業技術與資本主義市場合力的一種商品,從傳統紙媒到新媒體、電子游戲機到移動游戲、網癮青少年到全民電競,數字游戲玩家的主體交往與認同不斷延展,外界對數字游戲發展的評價也更加理性。
一、文獻綜述與問題提出
在數字游戲“去污名化”之前,美國哲學家伯爾納德·舒茲就傳統游戲便已思考游戲與生命的哲學,認為玩游戲的行為“就是人們自愿去克服非必要的障礙”[2],對于這種自愿參與的游戲行為,學者將重點置于玩家與數字游戲之外的現實行為關聯,建構模型、統計分析玩家的參與狀態和游戲體驗,并關注數字游戲里存在的性別歧視等社會問題。
對于主體的思考,巴特勒將福柯的權力話語與精神分析相結合闡釋主體理論,指出權力與主體是雙向共謀的關系,以及主體面對的悖論和反抗可能。鑒于福柯[3]的影響以及對外部話語、精神欲望和生命倫理之間長期以來的哲學思辨,巴特勒相信主體只能被說明——因為維護支撐人類的脆弱,需要主體借助委托話語條件的“可理解性”和“承認規范”。與此同時,她還闡釋了福柯沒有解答的“為何人們會服從權力”,以及后期關注的主體與他者關系。
通過觀察與分析中國本土背景的數字游戲機制和玩家群體經驗,探討代表性手游《王者榮耀》背后的娛樂異變、玩家失去思考、價值迷失等危機;梳理批判游戲內部的邏輯關系,探尋數字游戲領域的癥狀和問題,探索游戲空間與現實世界的平衡塑造路徑。
二、重構與形塑:從欲望到共謀的玩家主體
2015年《王者榮耀》多人在線戰術競技游戲機制上線,持續刺激玩家的參與熱情,賦予玩家主體性。黑格爾認為,“欲望”是“主體”的化身,玩家對游戲投入的動力主要由娛樂欲望構成,游戲活動則能夠滿足人類此欲望。玩家作為欲望主體,游戲機制對其產生作用,被賦予形式與存在;長期追求保持存在,則是為了克服它的“短暫性”。合作與競爭的數字游戲中,玩家獲得的“勝利”是被代碼編輯的數字內容[4]。同黑格爾筆下的奴隸勞動與產品類似,這種“數字的勝利”能夠在游戲機制設置中被輕易褫奪:《王者榮耀》每年大約四個賽季,平均三個月更新一次,每次更新都會進行“段位繼承”,也就是降低所有玩家的段位以開始新的晉級比賽,且段位越高的玩家下一個賽季段位下掉越多。除了最核心的游戲段位,《王者榮耀》還設置各類排行榜單,由全體玩家內部競爭產生變動,欲望成為玩家參與游戲開始與持續的動力。鄧劍把“王者峽谷”這類玩家活動的數字空間比喻為“游戲車間”,打游戲變成流水線的重復勞動[5]。
1.數字規訓:游戲榜單對欲望與主體的塑造
如今,玩家不僅出于娛樂欲望而參與游戲,而且愈發關心游戲通過數字媒介平臺提供的社交屬性、身份認同,以及游戲產業繁榮發展所獲得經濟收益,非生產性和以娛樂為中心的舊游戲范式面臨挑戰[6]。《王者榮耀》包括排位、巔峰以及匹配等娛樂模式,玩家主要通過“排位賽”和“巔峰賽”提高段位與排名,一局游戲結束后,每位玩家的界面都會顯示一份自己游戲表現的數據和符號印記。玩家在數字游戲的賽博“魔圈”內形成主體,欲望驅動玩家參與。巴特勒認為正是人類的“脆弱依附”使主體被外部權力塑造。
另一方面,《王者榮耀》沒有采用曾經流行的買斷制或內購等收費模式,而是設置不影響玩家游戲平衡的消費機制。玩家無須支付任何費用即可玩這款“免費”游戲,提供的虛擬商品如 “英雄皮膚”“改名卡”等主要是滿足玩家的外觀審美價值需求,無關或者隱性相關游戲競技水平。金錢不再是玩家滿足欲望的阻礙,有助于游戲廠商對玩家的維護,也意味著更容易控制玩家的游戲參與活動,產生更多的利潤[7]。
2.主體矛盾:服從與掌控的較量
在經歷了幾個賽季的變化后,《王者榮耀》游戲用戶數量不斷提升,玩家明顯感受到“大家游戲水平都上去了”[8]。社交平臺的游戲分區涉及教學類的內容數量增加,玩家愈發追求對游戲意識和技術要求,打游戲似乎變成了“掌握一門技術”,可以收獲經濟收益,甚至發展為工作或一門職業,例如“電競陪練師”“游戲主播”以及“電競職業選手”等;另外一個重要的面向則是促進情感交流:《王者榮耀》具備便利的社交功能,如線上玩家在游戲或其他社交平臺中可以添加游戲好友,玩家在游戲互動中通過獲得親密度建立“戀人”“閨蜜”“死黨”和“基友”四種關系;線下許多玩家也因接觸便利、時間短、效率高等因素,相約朋友在“王者峽谷”展開娛樂活動,增進情感;一些因游戲結交的線上好友發展為線下好友,實現了從虛擬關系到現實關系的連接。
此時,游戲主體既“服從”又“掌控”(這種掌控是符合游戲機制的管控下產生),可見主體形塑的過程的矛盾——服從與掌控是同步發生的。這恰恰印證了阿爾菲·鮑恩(Alfie Bown)對數字游戲的批判:在賽博空間內數字游戲不是滿足了我們的欲望,而是重塑和改變了夢想與欲望。表面上,玩家在“王者峽谷”中操控所選英雄戰斗,獲得數據排名,其實真正保持玩家黏性的是依靠游戲機制管控所獲得的主體,玩家與游戲機制產生共謀。
三、理解與承認:依附于簡化的游戲框架
如果說接受游戲機制管控,是通過與游戲自身以及其他玩家的互動,從而塑造主體身份;那么,就玩家之間的關系網絡而言,虛擬社交的建構則是一個理解與承認的過程。《王者榮耀》擁有廣泛的用戶群體,且積極地向其他社交媒介與商業、文化資源發展,鼓勵玩家對外在社交平臺輸出游戲相關內容,聯名商業品牌、文化機構或作品展開創作,不斷維持游戲生命的鮮活、刺激玩家參與,這就為游戲話語提供了足夠的前提條件——“他者”,玩家群體的“能動性”數字活動正是在游戲機制與他者的共同作用下產生與維持。因此,脫離了游戲語境,玩家獲得的數字成就將不被理解或承認,也就失去了價值與意義[9]。
1.被理解的消遣社交
“交往在云端”已經成為現代人習慣和接受的日常社交方式,新媒介技術壓縮了人際交流的物理時空距離,減少了聯絡阻礙,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的現實交往意愿。而巴特勒表示主體是由交往關系建構,也會被關系褫奪,它依附于人際交往,卻無法避免面對受到傷害的風險[10-11]。
《王者榮耀》的游戲機制為玩家鋪開了一張虛擬空間的關系網,完善的社交功能與合理的游戲分工安排滿足了玩家們的社交娛樂需求。“不是一個人的王者,而是團隊的榮耀”,這句宣傳語表明玩家并非是某種獨立的主體,而是處于“一系列活動變化之中的相互關聯”。
《王者榮耀》通過內外搭配的“掌控”和“傳播”運作框架,塑造玩家的感知和社會中的游戲氣氛,“可理解性”讓玩家對游戲產生黏性。主體需要理解才能生存,主體也只能在現實生存,數字游戲為玩家創造新的理解,但已有的現實話語也絕不能因此被忽視。
5)構件信息未達到標準化和多樣化,現如今BIM技術中的族庫符合中國建筑產品的構件還不夠廣泛,不能滿足信息化模型的所需要的所有的建筑構件,因此對于信息化模型的表達不會百分百還原。
2.追求承認的數字競技
當情感社交不再是首要目的,玩游戲將回歸到競技的本源:“自己玩就特別‘上頭’,和朋友打就無所謂輸贏。”約翰·赫伊津哈和伯爾納德·舒茲分別把游戲目標理解為“獲勝”和“前游戲目標(the prelusory goal of a game)”,赫伊津哈首先認為獲勝是一種虛假的優越,權力與統治的欲望并非游戲競爭的首要目的,戰勝他者獲得贊譽才是游戲目標。另外,舒茲定義“達成一種特定的事件狀態”(他對前游戲目標的概括描述)要按照建構的游戲規則來,因為接受規則游戲才能得以進行。規則就是框架,它不僅單純地限制游戲方法、呈現真實的游戲結果,同時積極地發揮控制作用,游戲等級應運而生。
數字游戲作為第九藝術,具有典型的多模態傳播特征:圖像、聲音、文字等要素構成具備召喚玩家主體功能的數字符號。《王者榮耀》給予玩家“榮耀稱號”、段位排名等為共同目標,此類游戲符號同時滿足了“贊譽”與“達成”,并試圖以此制造和維持某種類型的幻想主體。玩家群體內對一個現象存在共鳴:高分段的巔峰賽玩家更愿意開麥交流“打配合”。巔峰賽的匹配方式與其他模式不同,它沒有“好友組隊”的游戲形式,玩家只能“單排”參與,并且進入游戲后每位玩家的游戲昵稱被系統隱藏。相比之下,巔峰賽的玩家主要以競技為參與目的,玩家的競技水平和活躍程度緊密相關[12]。
此外,社交媒介有助于游戲框架加強承認的影響力。以抖音和B站為代表的互聯網平臺成為游戲內容生產的主要輸出領域,玩家主動尋求承認的渠道被拓寬,媒介平臺對游戲領域的內容創作持鼓勵態度。此類激勵活動本身也是一場游戲,多元媒介相互合作,增強主體參與游戲的欲望。主播、UP主以及職業參賽選手等新型職業,滿足了玩家物質與精神雙重層面的需求[13]。
相比《英雄聯盟》《DOTA2》等其他MOBA類游戲,《王者榮耀》是一個簡化后的MOBA類游戲產物,這成為玩家選擇或轉向它的重要原因。
四、數字共生:控制與轉換的游戲圖景
1.競爭狀態的轉換
即對玩家游戲成果的褫奪;ELO匹配機制的系統制裁,即根據不同玩家的歷史戰績、對局表現以游戲時長操縱組隊陣容,水平較高的玩家會在幾局游戲后遇到戰績較差隊友,玩家或被扶持或被制裁,以此控制玩家游戲體驗的張力以維持參與黏性。
2.游戲場景轉換:固定到移動、延時到即時、賽博到社會
從端游到手游、視頻到直播、游戲到社交平臺或現實生活,游戲場景已經隨技術發生轉換。技術與資本合力在人類生活中充實數字游戲,幫助個人有機身體與媒介延伸假體“夢幻般”的連接。而《王者榮耀》的問題在于,在一個創新開放的元宇宙世界里,它卻規訓玩家形成單一的競爭意識,約束玩家的創造力。
游戲相關的媒介想要時刻帶動大眾的激情與熱情,以至于這個時代沉默的評判與理解太少了。面對可移動的數字化進程,我們要保持自己的內心,在算法的娛樂時代重新認識和把握自己的主體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