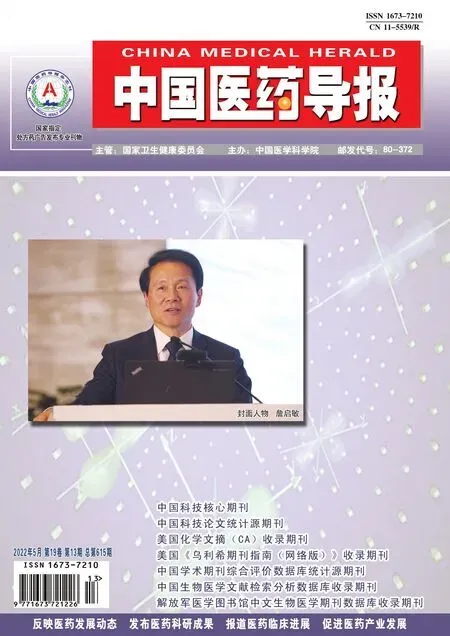人工智能背景下高等醫學教育的改革現狀與探究
王 艷 初 紅 梁靜靜 盧祖能 肖哲曼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神經內科,湖北武漢 430060
醫學不僅是一門治愈疾病的學科,更是不斷與時俱進的科學。人工智能領域的進步,推動著醫學衍生出更多的技術與創新。“人工智能+醫療”的新型醫學發展模式帶動著相關分支學科層出不窮。信息數據轉化為臨床醫療實踐的課題屢見不鮮。而在這新時代、新科技、新市場下,“人工智能+X”的教育模式應運而生。醫學教育領域中,“人工智能+醫療”復合型人才的需求使得國內外人工智能人才市場被打開。但國內各大高校對于“人工智能+醫學”的復合型人才培養欠缺,導致了如今人才數量供不應求的局面。如何將人工智能的個性化、智能化、即時性、開放性融入醫學教育改革,推動高校治理現代化建設,實現精準醫療成為一大難點[1]。
1 人工智能時代的醫學發展
1.1 輔助醫療
“人工智能+輔助醫療”是目前運用較為廣泛的一項技術,可協助醫師進行疾病識別、改進臨床決策并開展后期隨訪。其強大的數據挖掘和圖像識別技術主要應用于影像學讀圖和病理學閱片[2]。人工智能技術將眾多病例影像和病理標本信息轉為云資源共享,進行大數據整合,通過圖像識別技術對患者影像學特點或病理切片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作出臨床診斷,提高醫師診療效率、精準度[3]。但醫師仍需結合患者臨床特征來辯證看待人工智能算出的決策[4]。此外,人工智能系統可開展自動化、智能化的線上隨訪,詢問患者預后情況,以最少的人力資源,收集最多的隨訪信息,極大地減少醫務人員的工作量,同時也節省患者來回奔波于醫院所花的精力[5]。
1.2 醫療機器人
自達芬奇手術機器人問世,手術機器人逐漸應用于神經外科、腫瘤外科等領域[6]。手術機器人集多項人工智能技術與醫療大數據于一體,其三維視野及操作靈活性實現了精準化醫療,使患者創傷達到最低,同時節省手術時間,緩解醫務人員手術疲勞。醫療機器人作為一種新興產業,受到國內外醫療企業的極大重視。現已相繼研發出用于胃腸道疾病輔助診斷的納米靶向機器人、智能靜脈輸液的醫療服務機器人和協助患者訓練保健的康復機器人等高端機器人。但由于國內關于手術機器人等醫療機器人的手術風險、法律和倫理問題有待解決,其臨床應用比較有限[7]。
1.3 智能健康管理
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數據平臺,智能健康管理系統可結合患者日常生活習慣、生命體征及生理指標,對患者進行冠心病、阿爾茨海默病等疾病的風險評估,并提出健康指導意見[8]。針對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可通過人工智能技術開展遠程監督及管理,實現個體的精準管理,實現真正的家庭醫療[9]。尤其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影響下的后疫情時代,基于這一技術,開展網上康復培訓教程,并通過網絡對話等多種線上模式指導患者進行簡單且專業的康復訓練,這對于廣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痊愈患者的預后和功能重建有著重大意義,同時達到預防交叉感染的作用。
2 人工智能時代的醫學教育改革現狀
2.1 人工智能相關的醫學復合型人才需求量大
人工智能的發展為打開國內外人工智能醫療領域市場提供了重大機遇。2019 年一篇關于我國醫療行業對人工智能相關人才的需求分析中發現,國內各企業對于人工智能領域人才需求量大且待遇高[10]。而中國人工智能人才約5 萬人,醫療領域少之又少。國內醫療人工智能市場亟須人工智能相關的多學科復合型人才,并對于其學歷、工作經驗以及對人工智能技術的理解有一定要求。國外的人工智能產業起步較早,走在人工智能前沿的頂尖企業很早便開始招聘人工智能領域人才。人工智能領域市場中,擁有醫療和金融背景的人才需求度相對較高,而同時擁有多學科背景,具備數據分析與創新實踐能力的復合型人才成為了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型人才[11]。
2.2 人工智能醫學課程體系建設尚不完善
國內人工智能醫學教育起步較晚,經驗不足,機械化、形式化嚴重,仍處于探索階段[1]。近年來,國內各類學科陸續進行人工智能融合的教育改革,開設相關多元化課程,但面向醫學生的極少。國內醫學專業的人工智能通識課程教時嚴重缺乏、課程建設滯后等突出問題導致醫學生普遍缺乏人工智能基礎知識[12],且人工智能醫療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定位不明確、培養方案不完善、創新實踐不重視、反饋機制不科學[13]。國外發達國家對于人工智能醫療人才的培養已形成自己獨特的課程體系和經驗。例如美國的斯坦福大學以“實用”為培養核心,根據市場需求和實踐要求,不斷進行技術革新,貫徹以開發為導向的人才培養,不僅設立人工智能中心嘗試將人工智能技術融入臨床,還開設人工智能實驗室,為師生打造頂尖的實踐平臺[14]。同時,美國各大高校通過校企聯合,精準引進高端企業人才,建設了一流的人才團隊,形成了“以學生為中心”的個性化培養[15]。同樣為發達國家的日本針對各年齡階段學生制訂了人工智能相關的通識教育課程計劃,增加跨學科的綜合型人才培養,以“實踐+科研”為理念培養創新型人才[16]。
2.3 人工智能輔助醫學教學需要普及
人工智能技術開放了教育生產力,將教學活動數據化、教學環境智慧化、教學評估智能化并做到人機常態化[17]。傳統的教學以理論教學為主導,而臨床操作大多在人體模型上進行,缺乏在真人操作的實際場景。而人工智能的虛擬現實技術,大大改善了這一不足。人工智能通過整合多種病歷數據,形成標準化虛擬患者,模擬診療過程,可供學生們進行常規問診,同時收集學生的教學反饋,提出新的教學意見[18];其次,強大的圖像識別功能和教學資源,讓學生在學習解剖、影像學等知識時,更加直觀、全面。甚至在技術允許下,醫院可提供虛擬培訓室,模擬臨床真實場景,讓學生身臨其境[19]。訓練者可同時結合人工智能及時科學地反饋,不斷改正所學不足,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人工智能時代的醫學教育改革舉措
3.1 完善醫學教育改革頂層設計與政策
2017 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的通知中強調“面對新形勢、新需求,必須主動求變應變,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將人工智能融入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中,實現公共服務的精準化水平”。此后,國務院又發布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教育部也陸續提出關于加強人工智能在各領域人才培養的措施。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推動為人工智能醫療復合型人才培養提供了重要保障。基于這一契機,各大高校應加快培養一流的交叉學科教師團隊、建設跨學科交流平臺和創建多學科復合型實驗體系[20],在重視學生培養的同時,更要加強高校本身對于人工智能專業的建設和專業教師團隊的培養。此外,各大高校可適當增加醫學與人工智能的跨專業研究生招生,為復合型人才培養提供機遇。
3.2 人工智能帶動“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
傳統的醫學教學模式多以老師為主導,學生被動式學習,忽略了學生本身的能動性。而人工智能醫療復合型人才恰恰需要多學科的知識背景和核心素養來滿足社會市場的需求。首先,“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讓學生成為能動主體,開展問題導向型學習,重點觸發創新思維、頭腦風暴,促進團隊協作性學習。其次,基于案例的應用型實踐教學可幫助醫學生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在醫學的創新應用,并提高學生解決問題能力[21]。然后,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打造“以學生為本”的線上線下一體化理論實踐教學平臺,記錄學生日常學習情況,提出反饋意見,為每位學生打造個性化學習[22]。最后,強化對創新實踐能力的培養,建立以“競賽與創客交融、實踐引導創新”為主導的創新實踐能力培養體系,鼓勵醫學生與其他學科學生組隊共同參與跨學科競賽,在知識碰撞中交流學習[22-23]。
3.3 完善多元素融合培養模式
結合社會需求導向,本科階段的人工智能醫療復合型人才培養方向可分為研發型人才和運作型人才。研發型人才在課程設置方面注重人工智能技術、創新實踐能力培養,塑造為能自主研發新型人工智能醫療設施的高端人才;運作型人才主要以臨床醫學知識為主,人工智能運作技術為輔,能熟練利用人工智能輔助技術進行大數據分析和診療工作。課程設置方面,人工智能主要包括基礎算法、核心技術和創新應用三個板塊,而醫學主要包括基礎課程和臨床課程兩大類[24]。通過早期分流的方式,結合學生意向和市場需求,盡早確立培養方向,建立以人工智能和醫學類課程為主導,其他通識課程為輔的多學科相融合培養模式[25-26]。由于人工智能技術革新快,培養模式可根據市場導向,出現彈性變化。除了交叉學科培養,國內外高校聯合培養和校企聯合培養也同等重要[27]。國內外高校聯合培養,讓學生集中利用各高校優勢專業資源,為缺乏工科專業的單一醫學院校學生提供跨學科學習的機會。而校企聯合培養可讓學生更早接觸市場現狀,不僅擁有更多實踐機遇,更能與優秀的人工智能醫療人才面對面交流[28]。對于已經開始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研究生而言,可以開展嵌入式教學,以操作培訓為主,使其適應人工智能輔助診療的新型醫療模式。
3.4 完善師資隊伍建設
培養優秀的人工智能醫療復合型人才需要一流的多學科師資隊伍為支撐。首先,針對復合型人才的培養方向,通過高校聯合、校企聯合的模式,選拔和引進優秀的專業教師、跨學科教師和企業導師,成立專一的人工智能醫療教學團隊,其中企業導師主要負責引領學生盡早接觸人工智能醫療市場,分享自身經驗[28]。其次,深入完善教師培訓工作,思想上跳出傳統的教學思維,倡導以學生為主的教學理念,同時鼓勵教師前往其他高校、企業深入交流學習,共同探究培養方式。此外,各大高校可聯合建立頂尖的教師資源庫,共享教師資源。最后,單獨組建指導創新實踐的導師團隊,開展“1+1 團隊”指導模式,帶領學生團隊實踐各類項目,并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教學內容,引領學生敢于創新,敢于實踐[29-30]。
3.5 完善倫理與法律問題
人工智能醫療的倫理和法律歷來是敏感問題。自2009 年原衛生部發布了《關于人工智能輔助治療技術規范(試行)》后,再無新的相關法規出現。而近年來,人工智能醫療的應用呈井噴式增長,出現了新的倫理和法律問題。人工智能下的大數據時代,造成個人醫療數據和隱私無法得以保護,對于利用人工智能開展醫療工作的資格認證未出臺相關規定,甚至對于手術機器人用于治療的法律問題仍無明文規定。以往的技術規范無法滿足現行需求。人工智能醫療的倫理和法律需要進一步明確人工智能在醫療中的定位、醫生以人工智能作為治療手段時的潛在性責任以及出現意外后的責任歸屬[31-32]。基于這一背景,在培養人工智能醫療人才時,注意強化其對倫理和法律問題的認識。
4 總結與展望
人工智能領域的發展勢如破竹,其帶動的“人工智能+醫療”的新型診療模式也將深入到未來的日常需求中。人工智能醫療設施擁有的大數據平臺,以及其自動化、智能化的特性能給予病患更舒適的就診體驗,提出更優、更精準的治療手段。精準化醫療的需求必將打開新型的人工智能醫療人才市場,而多學科融合型高素質人才也必將成為市場的主流。這已成為高等醫學教育的改革新契機。國家應盡快出臺人工智能領域相關政策及法律法規,解決人工智能帶來的一系列倫理和法律問題,同時鼓勵和支持全國高校、各大領域培養“人工智能+X”的復合型人才。而各大醫學院校也應結合市場需求,建設一流的多學科教師團隊,打造一流的跨學科交流平臺,建立一流的復合型實驗室體系,培養出一流的人工智能醫療復合型人才,助力我國精準化醫療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