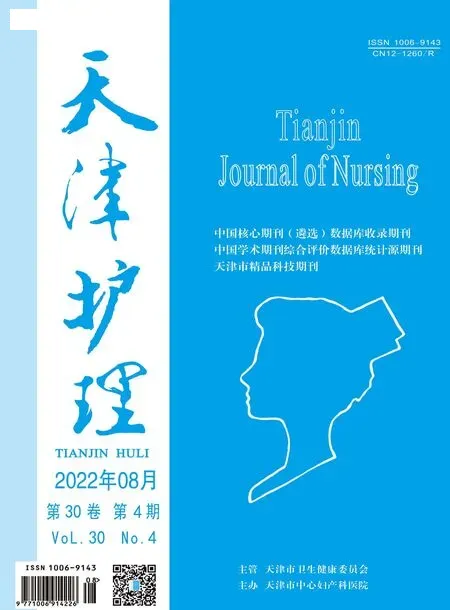住院精神分裂癥患者孤獨感與自我效能感的相關性分析
陳佳偉 許金龍 沈蒙召 艾永豪 陳全 翟超
(中山市第三人民醫院,廣東 中山 528451)
精神分裂癥是一組常見的病因未明的重型精神疾病,臨床上常伴有幻覺、妄想、情感和行為等多方面的功能障礙及精神活動與周圍環境的不協調的特征,一般無意識障礙和智能障礙,具有易復發、易致殘的特點[1],多起病于青少年時期[2],給患者和家屬帶來巨大的壓力。隨著生物-醫學模式的發展和治療技術水平的提高,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癥狀大多能夠得到積極有效的控制,但社會功能等方面的恢復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康復效果不佳。有研究指出[3],孤獨是患者在治療及康復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多項研究[4-6]結果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存在較低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對患者的認知功能和陰性癥狀有著重要的影響[7]。患者的孤獨感與自我效能感的關系如何,二者是否存在著某種聯系,國內鮮見報道。本研究旨在分析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孤獨感與自我效能感現狀,并探討二者之間的相關性,為臨床制定針對性干預措施提供參考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8年3月至2019年12月在中山市第三人民醫院住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納入標準:①符合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DSM-5)診斷標準的精神分裂癥患者[8];②經藥物系統治療后病情穩定,處于恢復期,自知力基本恢復;③小學及以上文化。排除標準:①精神分裂癥外的精神障礙患者或處于急性期的精神分裂癥患者;②伴有其他嚴重的軀體性疾病,如急性心肌梗死、腦卒中等;③不能正確表達自己意愿的患者。本研究已征得患者及家屬的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且得到醫院倫理委員會的批準。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資料調查問卷 自行設計,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職業、受教育程度、家庭經濟水平、居住地、總病程、住院次數、家族史、醫療費用支付方式、被歧視經歷、家屬探訪次數、疾病分型等。
1.2.2 UCLA孤獨量表(UCLA Loneliness Scale) 該量表最初由RUSSELL等[9]于1978年編制,1987年進行修訂。主要用于評價對社交的渴望與現實水平存在的差距而產生的孤獨,在一般人群中得到廣泛應用。該量表共有20個條目,采用4級評分法,從不=1,很少=2,有時=3,一直=4,總分20~80分,其中條目1、5、6、9、10、15、16、19、20為反向計分,總分越高說明孤獨感越嚴重。總分≤39分為無孤獨感,總分40~59分為輕度孤獨,總分60~79分為中度孤獨,總分80分為重度孤獨。該量表中文版被證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4[10]。
1.2.3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 該量表最早于1981年由德國柏林大學的著名臨床和健康心理學家SCHWARZER教授等[11]編制,最先在大學生人群中應用,后被廣泛應用于其他人群。原始量表共有20個條目,后修訂為10個條目。目前該量表已至少被翻譯成25種語言,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應用。采用4級評分,1=完全不正確,2=不正確,3=正確,4=非常正確。總分為10~40分,分數越高,自我效能感越高。該量表中文版被證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內在一致性系數為0.81[12]。
1.3 資料收集方法 研究者使用統一的指導語對量表進行解釋說明,原則上所有的量表應由患者獨立完成,但若有閱讀困難或視力模糊者,可由研究者逐條閱讀,但不得用語言或心理暗示,待患者完全理解后獨立做出選擇,由研究者代其填寫。量表完成后當場檢查并回收,若發現有缺項或疑問的量表要求當場補填或核實后再回收,確保問卷的真實有效性。本研究為描述性相關性研究,樣本量由所采用量表的條目數決定,本研究量表中條目數最多的是UCLA孤獨量表,樣本量為量表中最大條目數的5~10倍,計算得到本研究最少樣本量為20×5=100例。本研究共發放問卷136份,回收有效問卷130份,有效率95.6%。
1.4 統計學方法 數據采用SPSS 21.0錄入并分析。計數資料采用例數、百分比表示,計量資料采用±s表示。孤獨感和自我效能感之間的關系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P<0.05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130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一般資料 男86例,女44例,年齡18~60歲,平均(37.3±9.6)歲。文化程度:小學6例,初中38例,高中或中專56例,大專及以上30例。病程1~32年,平均(12.67±7.46)年。住院次數:1次24例、2次30例、3次30例、4次及以上46例。
2.2 患者孤獨感得分情況 130例患者的孤獨感得分為(47.87±4.46)分。其中無孤獨感的患者35例(26.9%),得分為(31.88±5.34)分;輕度孤獨的患者81例(62.3%),得分為(47.72±4.89)分;中度孤獨的患者14例(10.8%),得分為(64.00±3.16)分。
2.3 患者自我效能感得分情況 130例患者的自我效能感得分為(24.25±6.92)分,與全國常模[13]得分(28.67±5.21)分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7.283,P<0.001)。
2.4 患者的孤獨感與自我效能感的相關性分析 患者的孤獨感與自我效能感呈負相關(r=-0.464,P=0.038),提示患者自我效能越低,孤獨感程度越高。
3 討論
3.1 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孤獨感現狀 “孤獨”是指當個體親密人際關系的需要不能得到滿足或缺乏穩定的社交關系時產生的一種不愉快的情緒體驗,是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心理現象[14]。本研究采用UCLA孤獨量表對住院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孤獨感進行調查研究,結果顯示:輕度孤獨的患者有81例,占62.3%;中度孤獨的患者有14例,占10.8%;研究中并沒有發現重度孤獨以上的患者,說明大多數患者具有輕度以上的孤獨感,這與國內外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15-16]。國內有學者采用情緒-社交孤獨問卷(ESLI)對住院男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孤獨感調查發現,患者的情緒孤獨與社交孤獨程度都偏高[17]。長期以來,由于精神衛生專業知識的缺乏造成人們對精神疾病患者的誤解與偏見,認為精神病患者是充滿危險的,不值得信任的,因此不愿與他們來往,常避而遠之;反之,患者由于缺乏良好的人際關系和社會支持,內心充滿了孤獨。STAIN等[16]在澳大利亞關于精神疾病對生活質量的影響調查研究中,通過半結構式訪談法發現,在1 825例患者中有80.1%的患者反映經常感到孤獨,渴望有更多的朋友;僅有56.7%的患者表示跟家庭成員幾乎每日都有交流聯系;而在過去的1年,有69%的患者沒有參加任何社交活動;43%的患者反映由于“病恥感”而不愿與他人接觸;且僅有29.5%的患者在過去的1年中獲得過他人的幫助。結果表明,孤獨與社會隔離是患者康復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在護理中可定期開展認知行為治療、健康教育,深化患者對疾病的認識,坦然面對他人的歧視和各種困難、挫折,降低內心的孤獨感。
3.2 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自我效能感水平 自我效能感是指人們成功地實施和完成某個行為目標或應付某種困難情境能力的信念[18]。有研究發現[16,18],低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可加重患者的陰性癥狀、降低生活質量。本研究結果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自我效能感低于國內常模(P<0.05),這與慕晨陽[19]的研究結果一致,提示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自我效能水平較低。自我效能水平高的人會增強自己的努力,完成目標任務,提高自豪感與成就感;自我效能感水平低的人會逃避任務、阻礙計劃的實施、降低自己的動機水平[20],遭遇更多的痛苦。
3.3 患者的孤獨感與自我效能感的相關性 本研究結果顯示,患者的孤獨感水平與自我效能呈負相關(P<0.05),提示自我效能水平越低,孤獨感程度越高。精神分裂癥常呈慢性退行性發展,使患者長期遭受疾病的折磨,導致對環境的適應能力下降,對自身成功或失敗的行為經驗產生持續消極的影響,這種消極的影響使得患者對有效作用于環境的自我效能產生了懷疑,這種挫敗感給患者帶來嚴重的消極體驗,可能導致孤獨的產生;出院后患者在工作、學習及其他一些社會活動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挫折和打擊,較少感受到成功帶來的喜悅,同時家庭成員的漠視、人們的歧視和社會支持的不足使得患者自信心受挫、自尊水平下降、自我認同感降低,從而使自我效能感下降,影響自身水平的發揮,進一步加重患者的孤獨感。PRATT等[21]在對85例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橫斷面調查研究中發現,自我效能感作為行為與健康的中間變量,與認知功能、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關。MORIMOTO等[22]認為,自我效能對人際行為變化的預測判斷比通過測量神經認知功能更直接有效;自我效能不僅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影響,對物質依賴患者的治療結局也有一定的影響[23]。在一項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研究中發現[24],通過激發性干預措施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感。護理人員可鼓勵患者參加工娛治療,通過剪紙、繪畫等簡單的手工勞動,鍛煉動手動腦的能力,提高工作技能;對患者的積極行為予以肯定,幫助其意識到自身的優點,激發患者的自信心,提高自我效能感。
4 小結
本研究結果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孤獨心理,自我效能感水平越低,孤獨感程度越高。但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①樣本的來源單一,僅1所醫院的住院精神分裂癥患者,可能會產生選擇性偏倚,應擴大調查范圍,同時納入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和其他類型的精神疾病患者;②孤獨感主要反映的是內心的主觀感受,本研究未實施質性研究,使研究結果比較單一;③未據此結果制定出相應具體的干預措施,因此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孤獨感的干預措施應成為今后研究的一個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