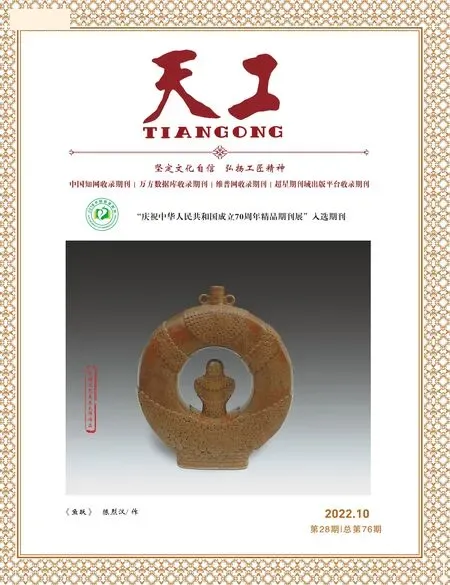淺析漆器工藝的現代化探索與問題
——以艾琳·格雷作品為例
鞏孝天 魯迅美術學院人文學院
漆藝作為東方的獨特藝術形式,無論是造型還是色彩都極具東方韻味,尤其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漆器家具設計,其實用性和審美性和諧統一。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大工業發展的背景下,藝術家為減小機械生產對傳統手工業的沖擊,率先在法國對新材料、新技術下的當代工業美展開了全新的探索。其中,以艾琳·格雷為代表的藝術家不但對新材料進行了發掘,而且將富有東方情調的傳統工藝融入現代設計中。在東西方商業往來日益頻繁的20世紀,東方的大批藝術家隨之來到歐洲。由此,東方的純正的大漆工藝也傳到歐洲。東方大漆原材料以及傳統工藝的到來,使得歐洲對東方大漆工藝的了解愈發深刻。歐洲一些知名的設計師也從中得到了相當大的啟示,使得大漆工藝得到不斷的探索。在此期間,裝飾藝術運動時期的知名女性設計師艾琳·格雷被東方漆器藝術深刻吸引。在機械化大背景下,艾琳·格雷將東方漆器工藝融入其作品之中,不僅對傳統美學進行了現代化探索,創作出了基于傳統漆藝的現代化家具,而且在其家具作品中透露出現代材料與傳統漆藝的融合。筆者認為,我國傳統漆藝在現代社會發展中也許可以找到某種機遇,尋求到漆藝家具與現代工業的融合方法。
一、新型材料的融合
“漆材料的使用從最初便體現為一種思維活動,而大漆材料則是人們各種漆藝創造思維活動的物質基礎。”(李明謙、胡秀妹,2015)。漆藝在歷史層面本身就是一門藝術,在當代設計的大背景下,藝術家在探索大漆的美學特征的過程中,應注意大漆材料的美學特征。
大漆在家具設計中擁有較為強烈的文化特質,因此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更應當注意其審美品格與當代社會的契合。在裝飾藝術運動的設計思想中,設計師尋求著傳統工藝在當代藝術審美背景下復蘇的曙光。從艾琳·格雷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對大漆工藝全新的探索。據筆者觀察,在其獨特的探索精神下,現代材料與美學體系在大漆工藝中不斷綻放異彩,其中筆者提取了其內在的設計語言,并試圖從中尋求現代漆器發展的道路。
在艾琳·格雷的作品中,我們可以從其的創作材料中尋求漆器家具當代發展的可能性。東方傳統漆器工藝的胎體最早多為木胎和陶胎(長北,2015),少量運用到金屬等胎體。從歷史的角度看,漆器的發展受到其特殊的自然屬性的影響。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金屬等人工材料無法做到大批量生產,木胎便成為古代最易得且用處最廣的胎體材料。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發現,東方其他的傳統工藝,如建筑、家具等的建造與制作也都以木制為主。
進入現代社會,漆器工藝的傳統技術面臨著新的挑戰,即現代工業社會與傳統漆器工藝對時間要求的沖突。由于大漆天然材料的局限性,漆器用品由制作到成品往往需要較長的周期,在這樣的背景下,筆者通過對艾琳·格雷漆器作品的分析,發現其作品在追求傳統漆器材料的前提下,對現代化材料進行了不斷的探索。艾琳·格雷早期的設計大多以木材作為最直接的材料。而到20世紀20年代,她開始大量使用鍍鉻管狀鋼材、穿孔金屬片、軟木及纖維膠等現代材質(何振紀,2014)。艾琳·格雷的眼光始終緊隨潮流,她的家具設計不但越來越注重作品的形式感,而且對鋼管、玻璃等材料的應用,表明她對新材料的潮流趨勢相當敏感。
1919 年,她 為 馬 蒂 厄·列 維 夫 人(Mme Mathieu-Lévy)設計了一個公寓的室內裝潢。其公寓位于巴黎洛特街,艾琳·格雷一手包辦其中的室內設計,包括家具、地毯等等。這個公寓有一個長廳,艾琳設計了一款名為《磚》(Block)的漆屏風(如圖1),由黑漆格子以關節式連接而成,盡顯艾琳·格雷驚人的獨創性。這件漆屏風既可以當作墻鑲板又可以分隔空間,即當它閉合時,漆屏風可以當作室內墻面;當它打開時,可以微妙地分隔室內空間。除此之外,艾琳·格雷所設計的漆桌也可以明顯看出漆器對其設計思路的影響(如圖2)。艾琳·格雷不僅對漆器有著濃厚的興趣,而且在她的設計中,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其在現代工業環境中的獨特思考。
批量化生產是現代工業環境的產物,而漆器長期作為高端手工藝,其作品的創作便與現代工業生產產生了必然的沖突。而艾琳·格雷的作品卻給我們展示了兩者相融的可能性。在其作品漆屏風《磚》中,漆器的部件與現代的鋼架形成了一種“安裝”形態,雖然漆器的創作需要一定的周期,但傳統的漆器更多以一種獨立的工藝品形式出現。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漆器的創作是“獨一性”的,即每一件漆器作品都無法復制,這也就決定了漆器的創作周期與現代工業生產方式的背離。而艾琳·格雷的作品給我們帶來了一種全新的啟示,在其作品漆屏風《磚》中,艾琳·格雷對傳統漆器的形式進行了創新:漆屏風的部件采取了全新的幾何形態。雖然單獨部件的創作周期沒有改變,但相對于傳統漆器來說,幾何形狀使其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漆屏風將現代的鋼架結構融入其中,使其充當了“框架”的作用。鋼架結構作為工業化產品,其形態以及產量都可以進行靈活的變化,而艾琳·格雷的漆屏風中幾何狀漆塊與鋼架結構形成了一種完美的契合,幾何形狀本身并沒有其固定的作用,而鋼架結構可以對空間進行預留,從而將漆器與其進行組合安裝。這種安裝形式使漆器不再局限于其“獨一性”,每塊幾何狀漆塊都可以進行多種方式的解構與重組。除了漆屏風《磚》之外,我們從艾琳·格雷的其他作品中也可以找到漆器對她的影響,如艾琳·格雷設計的茶幾(如圖3、圖4),其以紅、黑色為主,并配以簡潔的鋼管支架,雖然茶幾并不是漆器,但其配色也顯示著漆器對艾琳·格雷創作的影響,傳統漆器色彩與現代幾何形狀的融合,不僅僅是設計師對傳統漆器新形式的探索,也向我們展示了傳統漆器應該如何融入現代審美,以及與現代工業生產方式相結合的新方向。
二、幾何美學下的現代化嘗試
在艾琳·格雷的漆器作品中,幾何形狀得到了全新的運用。無論是從作品的形狀還是其質感上,都透露出幾何形狀展示的現代審美傾向。
在 1922 年時,荷蘭風格派(De Stijl)就深深影響到了艾琳·格雷。當年,她在參加在阿姆斯特丹舉辦的法國設計師作品展時結識了風格派的成員楊·維爾斯(Jan Wils)。之后,艾琳·格雷便嘗試設計了不少方直的家具,漆屏風《磚》便誕生于此前后。艾琳·格雷以這件漆屏風參加了當年的秋季沙龍(Salon d’Automne),并受到了羅伯特·馬萊·史蒂文斯(Robert Mallet Stevens)及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贊賞。艾琳·格雷的幾何設計與其早期迷戀的象征題材、神秘主義相關,而風格派正與之關系密切。因而,艾琳·格雷對幾何形狀的運用與杜南德用于表面裝飾的幾何紋樣設計截然不同(如圖5),這在艾琳·格雷日后的設計取向上得到更為明顯的展現。
風格派幾何抽象創作意念是對形式純粹的追求,從艾琳·格雷的漆器作品中,我們可以找到十分豐富的內涵,簡單的幾何形體不僅關注理性主義美學,而且重視藝術與生活的聯系。而在幾何美學的視角下,漆器的天然推光工藝為我們找到了幾何美感的契合,無論是從漆屏風《磚》中還是茶幾作品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其對幾何形狀進行了傳統的純色推光處理。
由此,光滑的平面透露出了簡潔的美感,漆器的傳統審美與現代材料的簡約審美形成了完美的契合。在現代漆器家具設計中,我們是否可以從中尋求到現代漆器的工業發展方向,對于此問題,筆者認為仍然值得從中深入探尋。
三、問題與啟示
筆者從裝飾藝術運動時期說起,從艾琳·格雷的作品中,介紹了現代化審美的新思路,但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漆器作為東方傳統工藝,其表面圖案以及內在含義都有著極高的文化價值。
現代工業的沖擊是諸多傳統工藝沒落的重要因素,在艾琳·格雷的作品中,雖然其尋求到了漆器材料與工業審美的融合,但在對其理論的運用中,現代設計師也應該注意到漆器的文化精神與現代審美的沖突。漆器擁有著獨特的傳統文化符號,其傳統紋樣、器物造型都蘊含著東方的傳統審美,在對其進行現代化創作時,設計師也不應該對傳統審美進行完全摒棄,雖然艾琳·格雷的《磚》在形式上體現了現代幾何美感,但在內容上,其簡潔的造型以及無裝飾的圖案也體現了現代工業的某種弊端,即對傳統裝飾內容的摒棄。因此,現代漆器設計師應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傳統文化進行提煉,并對其內在含義與意境進行充分的吸收,對傳統文化與現代產品設計進行重新思考和詮釋,從而設計出具有現代社會需求價值和傳統意義的作品(王亦敏、劉元寅,2015)。
艾琳·格雷的漆器創作大多采用天然東方大漆。由于大漆材料的性質,漆器的創作需要較長的周期。對于傳統手工藝來說,人力與時間始終是限制其發展的重要因素。雖然漆器融入工業的方式可以提高漆器創作者的效率,但是也只是相對而言,相較于鋼架材料的機器大生產方式,漆器部件的創作周期較長,也就決定了其在價值上始終無法擺脫高端工藝品的定位。
筆者由此提出思考,漆器的發展不僅僅需要漆器形態的創新與發展,對其本身的天然性質也應進行充分的創新。天然的組成成分決定著大漆材料的屬性,也決定著大漆獨一無二的美學特征。大漆的文化性質也在一定程度上附著于其天然的自然屬性上,因此,在對大漆原料進行創新的同時,其天然性質的保留也顯得尤為重要。可以說,沒有天然大漆的漆器無法命名為漆器。
因此,雖然現代漆器出現了諸多的材料創新,但其創新始終需要遵循一個度,即對大漆的歷史文化的尊重。
四、結語
本文就傳統漆器藝術在當代社會環境下的發展前景與問題進行了研究。以艾琳·格雷的漆器作品為切入點,分析了其漆器作品在創作材料以及審美風格上的現代化傾向,并將其融入傳統漆器創作中,試圖尋求當代工業生產與傳統漆器創作的融合方法,以探求傳統漆器在當代發展的可能性。通過本文對艾琳·格雷作品的研究,筆者提出了以下幾個觀點:首先,當代漆器的發展應從材料入手,通過對現代化材料的融合,解決傳統漆器在時間和成本方面的桎梏;其次,現代審美方向也決定著漆器在當代社會的生命力,在追求傳統漆器現代性的同時,設計師仍需要在其中找到合理的界限,使傳統漆器的文化內涵與現代審美相結合,從而尋求漆器的創新發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