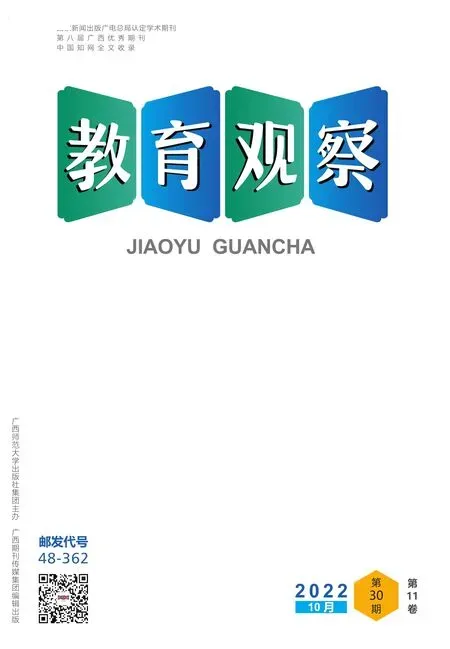基于CiteSpace可視化分析的我國教師情緒勞動研究熱點與趨勢
梁倩雯,畢 妍
(天津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天津,300387)
一、研究問題的提出
教師是職業倦怠的高發群體。已有研究發現,有相當比例的教師曾感覺到壓抑、焦慮,教師的情緒問題日益凸顯。[1]在與情緒相關的研究中時常涉及“情緒勞動”這一概念,此概念來源于社會學家霍赫希爾德的《被管理的心靈:人類感受的商品化》一書,其研究對象聚焦空乘人員、收銀員等以人際互動為基礎的服務性行業,提出了“這些雇員主要做的工作并不是體力勞動,也不是腦力勞動,而是情緒勞動”這一頗具洞察力的觀點。[2]已有關于情緒勞動的研究特別關注文化、社會與組織中的規范體系對個體“感受法則”的影響。教師在教學工作中需要不斷調整情緒以展現給學生合適的情緒狀態,保證課堂活動的順利開展。[3]哈格里夫斯提出情緒是教學的中心,教學是一種情緒勞動。[4]由此可見,教師在教學工作中需要常常檢視自己的情緒感受與表達是否適合當下的情境。本文運用CiteSpace研究工具,梳理教師情緒勞動領域的研究現狀,以期為后續研究提供參考。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工具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學術期刊數據庫(CNKI)。通過在高級檢索的“主題”一欄中輸入“教師”和“情緒勞動”,時間限制為2007年1月至2021年12月,共獲得研究文獻339篇,剔除會議、成果等非學術文章53篇,共保留286篇。與此同時,鑒于高校教師與幼兒、中小學教師的差異性,本研究僅保留幼兒和中小學教師相關文獻,剔除46篇高校教師相關文獻,共有240篇文獻進入計量分析范圍,符合運用CiteSpace進行可視化分析的基本條件。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通過文獻計量分析方法,對“教師情緒勞動”這一關鍵詞相關的文獻進行整理和綜述。基于CiteSpace 5.8可視化軟件,進行關鍵詞共現圖譜顯示、熱點詞突顯等對收集到的文獻進行可視化分析。
三、教師情緒勞動研究的計量分析
(一)年度發文量分析
一個學科在一段時間內的發文量可以反映出該領域的學術研究熱度和趨勢。[5]本文統計了2007—2021年教師情緒勞動研究的年度發文量并繪制成折線圖。如圖1所示,自2007年以來教師情緒勞動研究發文量總體上呈增長狀態,但增速緩慢。
(二)文獻來源分析
有關教師情緒勞動的240篇文獻樣本中期刊所占篇數為129篇,其中50篇來自核心期刊。如表1所示,《教師教育研究》《全球教育展望》《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外語教育研究前沿》均為專業領域內核心期刊,其中《教師教育研究》發文量為7篇,位居首列。由此可見,教育學、心理學領域是教師情緒勞動研究的主要陣地。

表1 教師情緒勞動研究的主要來源期刊
(三)研究機構情況
為直觀顯示教師情緒勞動的研究機構情況,本文將研究機構作為分析單位生成了共現視圖。如圖2所示,我國2007—2021年教師情緒勞動教育研究主要是在各師范高校或各高校的教育學院中進行的。各高校研究教師群體類型各有不同,沈陽師范大學學前與初等教育學院研究群體多為幼兒教師、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的研究主題大多與特殊教育教師有關、廣州大學教育學院的研究對象多為中小學教師。值得關注的是,暨南大學管理學院的發表文章數量也緊隨其后,而且對教師情緒勞動這一主題的研究開展較早,集中在2011年,其切入視角也與師范類高校有所不同,更注重組織層面因素對教師情緒調節的影響。
(四)被引核心文獻分析
分析引文是文獻計量分析的關鍵部分之一,通過被引頻次的數量可以判斷文獻質量水平的高低,高被引文獻是該領域研究發展的重要參考。[6]本文統計出了引用排名前十的代表文獻,并根據排名對篇名、作者、來源、發表年份和被引用次數進行歸納。如表2所示,文獻被引次數較多的作者是尹弘飈、吳宇駒、劉毅、周厚余等學者,被引次數較多的文獻多為實證研究,主題一般聚焦情緒勞動機制與策略。

表2 教師情緒勞動研究被引頻次排名前十的核心文獻
四、研究熱點分析
(一)關鍵詞共現圖譜與詞頻圖譜
關鍵詞是整篇文章研究主題的概括,也是研究內容的高度總結與凝練,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教師情緒勞動領域的研究熱點。[7]本文利用CiteSpace 5.8軟件對所選240篇研究樣本進行可視化分析,得到教師情緒勞動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和關鍵詞詞頻圖譜,如圖3所示。關鍵詞頻次越高,說明研究者在一定時間內對其關注度越高,越有可能成為研究熱點;中心性數值越高代表著關鍵詞在網絡節點中具有越強的中心地位。關鍵詞的共現頻率越高,中心性數值越高,表明此研究主題在該領域越重要。[8]因此,本文列出了頻次大于10和中心性大于0.02的關鍵詞,并視該詞為熱點詞,如表3所示。由表3統計結果可知,排名前三的關鍵詞“情緒勞動”“幼兒教師”“教師”頻次分別為147、38、22。根據可視化分析結果,教師情緒勞動研究的熱點內容可以概括為三部分,即教師情緒勞動的基本內涵與結構、影響因素、產生的效應。

表3 教師情緒勞動高頻關鍵詞一覽表
(二)教師情緒勞動的基本內涵和結構
學界關于教師情緒勞動的研究,一般都先對其概念做出界定。隨著國內對教師情緒問題的研究熱度越來越高,教師情緒勞動的基本內涵也逐漸豐富。國內對教師情緒勞動的定義,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側重于工作要求,強調教師情緒勞動是根據學校要求和教學需要來表達情緒。例如,田學紅將教師情緒勞動界定為教師在教學工作與人際互動時,表達組織以及教學工作所要求的情緒過程。[9]第二類則側重于心理加工過程。例如,劉衍玲認為教師的情緒勞動是指在教學的師生互動情境中對自己的情緒進行必要的心理調節加工,以表達出適合教育教學活動情緒的過程。[10]目前國內外對教師情緒勞動結構的測量尚未達成共識,國內研究大多基于國外情緒勞動問卷展開修訂與編制工作。例如,鄔佩君于2003年翻譯了Gramdey編制的兩維度量表,包括表面行為和深度行為。[11]通過梳理文獻發現,我國學者對教師情緒勞動結構的研究大致分為兩個方向。一是以教師本身為導向,即基于個體層面的情緒調節。例如,劉衍玲基于教師的個體層面提出包括表面行為、主動深度行為和被動深度行為的三維結構。[10]二是綜合導向,在教師個體基礎上增加“工作中心”的角度,在具體的教學情境中提出教師情緒勞動結構。例如,吳宇駒等人編制的中小學教師的情緒問卷,包括四個維度,即知覺、深層行為、表層行為和自然行為。[12]綜上可見,在對教師情緒勞動的結構維度研究中,無論是以個體為導向,還是以綜合為導向,都包含表層行為與深度行為。
(三)教師情緒勞動的影響因素
國內學者對教師情緒勞動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從個體、組織、環境三個方面展開。在個人因素方面,性別、年齡、教齡和學歷方面是研究者普遍考慮的因素。研究表明,女性會比男性展現出更多的情緒勞動,因為女性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會形成較好的情緒管理能力,更善于表達情感。[13]在組織和環境因素方面,林嬌嬌通過對幼兒教師的研究表明,薪酬待遇是影響教師使用情緒勞動策略的主要影響因素。[14]學校環境也會對教師情緒勞動產生一定影響,張一楠在對幼兒情緒勞動影響因素的研究中發現,學校工作氛圍會對教師情緒勞動產生一定的影響。[15]
(四)教師情緒勞動產生的效應
對教師情緒勞動產生效應的早期研究以負面結果為主。學者大多關注的是情緒勞動帶來的情緒倦怠、工作壓力及對身心健康等方面的消極影響等。毛晉平等人對湖南省部分地市中小學校教師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教師表面行為正向預測工作倦怠。[16]周厚余通過訪談和問卷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情緒勞動的表面表現與情緒倦怠、離職意向有非常顯著的正相關。[17]情緒勞動是一把“雙刃劍”,教師情緒勞動帶來的積極影響逐漸得到學界的關注。安丹丹等人通過對幼兒教師進行調查發現,教師的深層扮演對幼兒教師職業幸福感的各個維度均有正向影響。[18]
五、教師情緒勞動的研究趨勢
關鍵詞的突顯代表著該研究領域的前沿動態方向。為進一步探討教師情緒勞動研究的演變趨勢與未來動向,本文使用突現詞的功能得到2007—2021年教師情緒勞動的關鍵詞突現情況,如圖4所示,教師情緒勞動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2007—2011年為初步萌芽階段。在這一時期,“表層行為”“深層行為”“情緒智力”為主要研究對象,且這一階段的突顯詞持續時間較長。自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發布《關于大力推進教師教育課程改革的意見》以來,教師情緒問題所獲得的關注度逐漸提高。[19]在萌芽期,教師情緒勞動的研究主題較為模糊,部分研究圍繞教師情緒勞動結構展開,相關理論基礎也在這一時期逐漸構建起來。
2012—2015年為深入探索階段。這一階段出現的突顯詞較多,研究內容逐漸豐富,尤其是在2012年這一年出現了許多相關研究,其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工作倦怠”“職業倦怠”“心理健康”和“心理資本”等主題。這個階段的文獻大多是通過實證研究方法探究情緒勞動給教師帶來的消極影響,尤其是教師情緒勞動與情緒耗竭、心理資本,工作倦怠之間的關系研究,說明學界越來越關注教師個體的心理健康狀態。
2016年至今為蓬勃發展階段。“教師”“影響因素”“工作投入”“情緒管理”“師幼互動”等成為研究熱點。此階段的研究現狀體現出學者從探究情緒勞動的作用機制逐漸轉向如何提供適切的組織資源和政策支持以幫助教師更好地進行情緒管理這一趨勢。在這一時期,幼兒教師格外受到學者關注,“師幼互動”得到越來越多情緒勞動研究者的關注。
六、結論和展望
(一)結論
在研究視角方面,教師情緒勞動研究涉及的領域比較廣泛,除教育學和心理學領域兩大主要陣地外,管理學、經濟學和哲學等領域的研究也不斷涌現。教師情緒勞動的研究者多為高等學校教育學領域的教師和科研人員,從事幼兒及中小學一線教學的教師較少。關于教師情緒勞動的理論研究在實踐中的應用成效應是未來研究的重點。
在研究內容方面,根據教師情緒勞動的關鍵詞詞頻一覽表和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教師情緒勞動研究的熱點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教師情緒勞動的基本內涵和結構、教師情緒勞動的影響因素、教師情緒勞動產生的效應。隨著研究的不斷推進,研究關注點也從情緒勞動給教師帶來的消極影響轉變為探索情緒勞動給教師帶來的職業認同、正念、幸福感等積極方面的影響。目前關于教師情緒對學生影響的研究較少,教師情緒把控和管理能力能否及如何影響學生情緒調節能力和學生的學業發展等方面還存在較大探索空間。
在研究方法方面,目前對教師情緒勞動的研究多采用量化研究方法,通過對教師進行自陳式問卷調查獲得數據并進行統計分析。量化研究范式可以檢驗情緒勞動的生成和影響機制,但難以揭示教師情緒勞動表達的內在過程以及不同的情境因素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未來可結合量化與質性研究的優勢,采用混合研究設計,更加深入地挖掘教師情緒勞動過程和相關情境因素。
(二)展望
教師在工作中需要開展大量的人際互動,他們會更多地感知情緒并受到情緒的影響,在面對不理性的家長或有行為問題的學生時經常會產生情緒的波動。[20]而基于職業要求,教師需要長期保持積極且穩定的情緒,始終以熱情的態度面對學生,因此教師需要為管理自己的感受與情緒表達付出大量努力。國內關于教師情緒勞動的研究成果不斷豐富和完善。基于上文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可視化分析,本文從以下兩方面提出建議,以應對教師情緒勞動帶來的問題。
一方面,學校應將教師情緒識別與管理能力作為教師教育的重要目標。心理學家戈爾曼認為情緒管理能力是可以通過后天習得或培養的方式逐漸形成的。[21]教師要經常自省,及時察覺自身情緒狀態的變化,養成管理情緒的意識,積極參與情緒管理培訓中的實踐活動,如討論、互動、角色扮演等方式,形成終身受益的情緒管理技能。職前職后教師教育應為教師識別并管理自身情緒提供場所和學習資源,增強教師調節消極情緒的能力,為教師積極開展教育教學工作提供技能支持。
另一方面,學校應創新管理制度,為教師“減負增能”。學校應創造條件,使教師把精力集中在教學育人核心任務上,同時充分發揮教師的主體性地位,使教師專注于教學,產生職業歸屬感,不斷提升工作的勝任感和獲得感,以疏解工作中產生的負面情緒。學校還應重視教師職業發展通道中面臨的障礙,為不同階段的教師提供適切的交流和發展機會,增強他們追求職業發展的內在動機和心理能量,促使其以更積極的態度投入教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