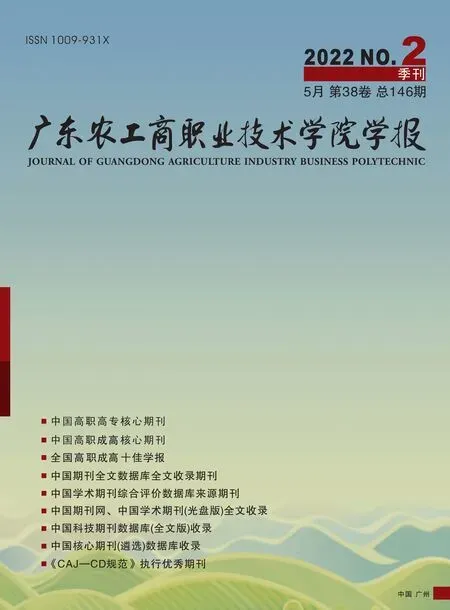兩宋之交陳與義詩歌的流變
侯本塔
(華南師范大學,廣東 廣州 510006)
陳與義是兩宋之交杰出的詩人,他的一生與佛結緣,并被《續傳燈錄》等禪宗典籍列為臨濟宗大圓洪智禪師的入室弟子。但當前有關陳與義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學杜成就及其對江西詩風的變革等方面,對陳與義詩歌與佛禪關系的考察成果相對較少。據筆者所見,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寧智峰《簡論禪宗對陳與義的影響》(2008 年)、吳倩《陳與義詩歌論》第四章《禪宗對陳與義詩歌創作的影響》(2010 年)、張云《禪宗對陳與義思想及其詩文創作的影響》(2015 年)、沈童《佛禪思想對陳與義文學創作的影響》(2020 年)等。其中,前三篇文章所論較為淺顯,沈文則認為陳與義詩論與漸修、頓悟的參禪方法相通,并指出簡齋作品的題材、語匯和詩境均受到佛禪思想的影響。不過,更深一層地看,陳與義的佛禪認知主要來自盛行于兩宋時期的臨濟宗,該宗“峻烈活潑”的宗風、“觸目是道”的宗旨對陳與義的詩學觀念具有指引作用,并被詩人運用到詩歌創作中,進而催生出全新的簡齋詩風。有鑒于此,本文擬對陳與義的人生態度、詩學思想與詩歌風格所受臨濟宗的影響進行考察。
一、人間似夢,悠然休心:佛禪思想與陳與義心態之演變
根據現有文獻考察,陳與義與佛禪之關涉主要表現在出入佛寺、結交禪僧、閱讀佛書等方面。具體來看,陳與義曾游歷汝州天寧寺、洛陽龍門諸寺、汴京慧林寺、汴京天清寺、陳留八關寺、潭州岳麓寺、江陵長沙寺、樂清云峰寺等寺廟,結識覺心、超然、洪智、印老、祕典座、勝侍者等僧人,并閱讀過《楞伽經》《楞嚴經》《華嚴經》《法華經》《圓覺經》《維摩詰經》《景德傳燈錄》等佛禪典籍。除此之外,陳與義和友人的交往也常常與佛禪有關。如葛勝仲,陳與義在居汝守喪期間曾多次與其酬唱,其中《承知府待制誕生之辰輒廣善懷菩薩故事成古詩一首仰惟經世之外深入佛海而某欲托辭以寄款款適獲此事發寤於心似非偶然者獨恨荒陋不足以侈此殊慶耳》即借善思菩薩與葛仙公之故事為葛勝仲祝壽;又如與簡齋之師崔鶠齊名,曾作《織佛圖》詩的陳恬,陳與義有《陳叔易賦王秀才所藏梁織佛圖詩邀同賦因次其》;再如吳使君,他曾托畫史為陳與義畫像,陳與義則以《楞嚴經》“我真文殊,無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于中實無是非二相”[2]65之言立意,作《甘泉吳使君使畫史作簡齋居士像居士見之大笑如洞山過水睹影時也戲書三十二字》。生活在這種濃厚的佛禪語境下,陳與義的人生觀念勢必受到佛教的深刻影響。從歷時性的角度出發,陳與義與佛禪之間的聯系可以分為靖康之亂前、戰亂流離中和晚年為官后三個階段。
首先,陳與義作于二十五歲的《題劉路宣義風月堂》便大量使用禪門典故,如“北窗舊竹短,南窗新竹長”“明當攜麴生,往問安心方”[3]15等。汝州為母守孝時,他更是結交僧人、出入佛寺,該時期的詩歌甚至有堆砌佛典的嫌疑。如《聞葛工部寫〈華嚴經〉成隨喜賦詩》《陳叔易賦王秀才所藏梁織佛圖詩邀同賦因次其韻》等詩,幾乎句句使用佛典。佛教觀念認為人生如夢,世間的一切皆是虛幻,“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2]268。陳與義無疑接受了這種觀念,他認為仕途如夢,寫出“從來作夢大槐國,此去藏身小玉山”[3]142;認為世事如夢,說到“世事紛紛人老易,春陰漠漠絮飛遲”[3]219;更認為人生如夢,所謂“人間似夢風旌出,佛子何之宰樹悲”[3]167。總的來說,陳與義這一時期的人生觀念是相對消極的,他不止一次地在詩歌中流露出年華易老、功業難成的看法。從《對酒》《若拙弟說汝州可居已卜約一丘用韻寄元東》等詩可知,個人的憂愁與處境的困窘是詩人的主要關注點所在,他對人生的態度和對佛禪的接受也往往由此而來。
其次,靖康之亂后,陳與義自陳留南逃,一路經過湖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最終到達會稽行在。這時的陳與義達到了詩歌創作的巔峰,他在旅途中寫下了大量的被稱為“以雄渾代尖巧”的優秀篇章,佛禪的影響似乎隱而不彰。但需要注意的是,陳與義的南渡詩歌并非一味地感時撫事、憂心家國。如《得席大光書因以詩迓之》:“也知廊廟當推轂,無奈江山好賦詩”[3]270。他在走出個人悲愁的小圈子后,同時走向山林,陶醉于大好河山之中。像《晚晴》說:“人生如歸云,空行雜徐疾。薄暮俱到山,各不見蹤跡。念此百年內,可復受憂戚。林木方翳然,放懷陶茲夕。”[3]341人生就如同流云一般,不管怎樣選擇,無論是快是慢,最終的歸宿都是走向虛無。這也是佛教人生如夢的觀念,但詩人這一時期的態度卻已悄然發生改變。他認為既然無術可救時弊,不如暫且放寬情懷,陶醉在這美麗的夕陽之中。再如《寒食》:“竹籬寒食節,微雨澹春意。喧嘩少所便,寂寞今有味。空山花動搖,亂石水經緯。倚杖忽已晚,人生本何冀。”[3]288年少時喜愛喧鬧的生活環境,如今悠游于空山細雨中,已能從寂寞里品出滋味,這樣的人生還需要什么希冀呢?
最后,晚年的陳與義更是在禪學中找到了自己的心靈歸屬,所謂“百年鼎鼎雜悲歡,老去初依六祖壇”[3]419。對佛禪思想的深入認識讓詩人的心態更為達觀,他為自己的詞集取名《無住詞》,又稱自己的住處為“無住庵”。“無住”出自《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指的是沒有任何所緣執著。陳與義這一時期甚至還寫出了近乎徹悟的詩句:“無住庵前境界新,瓊樓玉宇總無塵。開門倚杖移時立,我是人間富貴人。”[3]462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認為,“他(陳與義)跟蘇軾一樣,也具有達觀的人生哲學”[4]。我們可以說,在詩人的心態由消極悲觀向超然達觀轉變的過程中,禪學思想的影響不可忽視。
更進一步地看,陳與義這種逐步深入佛禪的經歷還為其詩歌創作心態帶來了不小的影響。早年的陳與義十分喜愛作詩,在喝醉酒之后,他說“海棠脈脈要詩催,日暮紫錦無數開”[3]202;在漫天大雪時,他認為“密雪來催詩,似怪子不作”[3]30;他甚至還聲稱不愿與不會作詩之人交往,所謂“寧食三斗塵,有手不揖無詩人。寧飲三斗醋,有耳不聽無味句”[3]317。但自紹興二年(公元1132 年)四月遷中書舍人至紹興八年(公元1138 年)十一月病卒期間,除了兩次因病奉祠外,陳與義約有七年時間并未作詩。關于這一點,用詩人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自得休心法,悠然不賦詩”[3]464。白敦仁先生曾指出,陳與義是因為“入朝見忌”,擔心以言獲罪,故而“以‘不賦詩’為‘休心法’”[5]。但實際情況并不止此,對于“休心法”,天如惟則《示大休永庵主》曾說:“古者謂:‘不學佛法,惟務休心。休得一分心,學得一分佛法。休心至于究竟,即是學佛法至于究竟。’然則佛法別無可學,惟以休心為學也……休心之法須具頂門正眼,照破塵勞業識,然后盡情放下……”[6]。據此來看,陳與義所謂“休心法”應當也是用以指代學佛參禪,于是以上兩句詩便可以理解為:由于在佛禪世界里獲得了心靈的安頓,詩人便不再將作詩視為不可或缺之事。禪宗向來主張“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認為語言文字是對清凈自性的遮蔽。陳與義年輕時也說過“小詩妨學道,微雨好燒香”[3]242,此時更是時常流露出不愿賦詩作文的心態,如《宿資圣院閣》說“欲與僧為記,今年懶作文”[3]444。總之,從早年“投老詩成癖”到如今“休心不賦詩”,禪宗思想的影響具有顯著作用。
除詩歌創作心態外,佛禪觀念對陳與義的影響主要來自哪些方面,又產生了什么樣的具體效果,尚且需要進一步地分析。
二、拔俗求新,不強不肆:臨濟宗風與陳與義的詩學思想
北宋以來,臨濟宗自第六世汾陽善昭禪師開始迅速振興,其弟子石霜楚圓禪師門下更分出黃龍、楊岐二支,禪宗遂有“五家七派”之稱,臨濟宗也逐步成為禪門“一花五葉”中影響最大的派別。而就陳與義的個人經歷來看,他早期接觸佛教的洛陽、開封、汝州、鄧州等地既是宋代禪宗的發展中心,同時也大都是臨濟宗的弘法重鎮。以汝州為例,臨濟宗南院慧颙、風穴延沼、首山省念、葉縣歸省、廣惠元璉等禪師曾先后在此傳法。再如陳與義游覽過的汴京慧林寺,臨濟宗黃龍慧南禪師的弟子慧林德遜禪師就曾在此院擔任住持。陳與義晚年主要活動在兩浙路,與大圓洪智禪師之間的交往頗為密切,并被《續傳燈錄》列為洪智禪師的嗣法弟子,而后者便是臨濟宗黃龍派開山祖師黃龍慧南的三傳弟子①據《五燈會元》可知,大圓洪智禪師的法系為:黃龍慧南—隆興法居—道林了一—大圓洪智—陳與義。。
臨濟宗的禪風特色被前人歸納為“臨濟將軍”,寓意單刀直入、殺伐決斷。南宋智昭《人天眼目》對此有十分形象描述:“臨濟宗者,大機大用,脫羅籠,出窠臼,虎驟龍奔,星馳電激,轉天關,斡地軸,負沖天意氣,用格外提持,卷舒擒縱,殺活自在。”[7]這種殺活自在的風格反映到禪門傳法之中,往往體現為以剿絕對方情識為目的的機鋒對答。臨濟宗師徒在機鋒問答之際,常常易賓為主,棒喝齊施,從而打破固有的思維習慣,將對方逼向絕路,借以勘驗其體悟境界之高低。如《臨濟錄》:“黃檗因入廚次,問飯頭:‘作什么?’飯頭云:‘揀眾僧米。’黃檗云:‘一日吃多少?’飯頭云:‘二石五。’黃檗云:‘莫太多么?’飯頭云:‘猶恐少在。’黃檗便打。飯頭卻舉似師。師云:‘我為汝勘這老漢。’才到侍立次。黃檗舉前話。師云:‘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師便問:‘莫太多么?’黃檗云:‘何不道來日更吃一頓。’師云:‘說什么來日,即今便吃。’道了便掌。黃檗云:‘這風顛漢,又來這里捋虎須。’師便喝:‘出去。’”[8]黃檗禪師以“來日”答復“多少”,臨濟禪師以“今日”回應“來日”,都是對執著于數量多少的破除,也是對常人慣有思維的駁斥,反映出求新求異的思想特征。臨濟義玄是黃檗希運的弟子,卻對其師加以“掌”“喝”,并曾說“造五無間業,方得解脫”②五無間業指: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壞和合僧、焚燒佛經佛像。,展現出臨濟宗蔑視權威、鄙棄流俗的精神風貌。
陳與義的詩歌亦不乏臨濟宗風的影響,如《葉柟惠花》說:“無住庵中老居士,逢春入定不銜杯。文殊罔明俱拱手,今日花枝喚得回。”[3]472據《古尊宿語錄》記載:“世尊在靈山會上,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于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同之。文殊繞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敕罔明出此女人定。罔明卻至女人前鳴指一下,女人于是從定而出。”[9]陳與義以詼諧的語調說文殊、罔明菩薩均不能令自己出定,只有葉柟的花枝才能將自己喚回,這里雖然沒有呵佛罵祖,但也并無對菩薩的恭敬之意。陳與義還在自己的詩歌中塑造出不畏流俗、瀟灑隨性的居士形象。如《散發》說“藜杖不當軒蓋用,穩扶居士莫相違”[3]411,《題江參山水橫軸畫》稱“萬壑分煙高復低,人家隨處有柴扉。此中只欠陳居士,千仞崗頭一振衣”[3]462等。這位“陳居士”主要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吟詩”,二是“不俗”,正如《題趙少隱青白堂》所說,“使君堂上無俗客,白白青青兩勝流。添得吟詩老居士,千年一笑澤南州”[3]421。他不愿讓俗人閱讀自己的詩歌,“馬健莫愁歸路遠,詩成未落俗人看”[3]68,也不喜與俗人往來,“敲門俗子令我病,面有三寸康衢埃”[3]323。詩新則不俗,故而他作詩力求出新,所謂“千丈虛廊賏明月,十分奇事更新詩”[3]163。這里的“新”指的是:立意拔俗求新,出語字字驚人。對此,陳與義曾說“莫道人人握珠玉,應須字字挾風霜”[3]511,又說“如今未有驚人句,更待秋風生桂枝”[3]418。這種意新語異的詩學觀點固然與其師承有一定的關聯,如《卻掃編》就記載了他向崔鶠學詩之事,“陳參政去非少時學詩于崔鶠德符,嘗請問作詩之要。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10]但同時也是臨濟宗風的影響所致,如《題趙少隱青白堂》說:“雪里芭蕉摩詰畫,炎天梅蕊簡齋詩。它時相見非生客,看倚瑯玕一段奇。”[3]417陳與義所謂“炎天梅蕊”與王維筆下的“雪里芭蕉”大體相類,也是將兩種難以并存的事物并列放在一起,借此來表現詩作的新奇不俗,而其中顯然不乏佛禪思想的影響。
此外,臨濟宗風對陳與義“拔俗求新”“意新語異”詩學觀念的影響,還體現在如何學習杜詩方面。自北宋以來,杜甫的詩學地位逐步提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均曾學杜,甚至將杜詩奉為圭臬。其中,蘇軾詩學思想通達,審美趣味廣泛,在對杜詩的學習上既有內容與精神方面的繼承,也有字詞句法和意象體式方面的模仿。按照蘇軾的觀念,學習杜詩應當“巧會”,但他常因才大隨意而為,從而失于草率。黃庭堅則更多地是從杜甫的詩歌技法入手,他認為學習杜詩的關鍵在于“句法”,因此對杜詩的構思立意、章法句式乃至對偶拗句等均有獨到認識。蘇、黃二人的學杜之法成為文人的仿效范式,尤其黃庭堅的作法因其操作性強而得到更多人的模仿。如陳師道便認為要通過學習黃庭堅來學習杜甫,“然學者先黃后韓,不由黃韓而為老杜,則失之拙易矣”[11]。曾幾將杜甫、黃庭堅比作達摩與惠能,所謂“老杜詩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12],也是由學黃而學杜的觀點。
陳與義同樣主張學杜,但他并不迷信權威,而是要跳出蘇、黃學杜的藩籬,以自己的方式學習杜詩。朱熹《陳去非詩集引》引轉述陳與義之言說:“學蘇者乃指黃為強,而附黃者亦謂蘇為肆,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為,然后可以涉老杜之涯涘。”[3]4學習杜詩要能認識蘇、黃尚未發掘處,才能真正窮盡杜詩之精華。這同樣是臨濟宗風影響下陳與義“拔俗求新”詩學觀念的體現。趙齊平認為“‘必識蘇黃之所不為’,就是在詩歌創作上‘能卓然自辟蹊徑’,而‘不為流俗所移易’”[13]。不僅如此,劉克莊《后村詩話》曾說:“元祐后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煅煉精而性情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為師。”[14]57這里的“始以老杜為師”指的是直接師法杜甫,而非借蘇、黃而窺老杜詩法。直接學習杜詩如何才能做到“不強不肆”,陳與義有自己的思考: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蟾蜍影里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髪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逸步。后之學詩者,儻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15]。
根據前文分析可知,“語工”“句奇”恰是陳與義受臨濟宗風影響而主張的詩學觀念。但他在這里卻對此加以否定,認為僅僅做到“語工”“句奇”并不能“參少陵之逸步”,其中原因就在于字句層面的學習“韻格不高”。在陳與義看來,由“韻格”入手是不同于蘇軾重“巧會”、黃庭堅重“句法”的全新的學杜方式,至于“韻格”的獲取則需要借用杜詩的法度規矩對唐人“工語”“奇句”進行重新組織編排,而這種畢肖杜詩之法的提出顯然也不乏臨濟精神的影子。
三、觸處新詩,光景明麗:臨濟宗旨與陳與義的“新體”詩風
在禪宗五家分派后,各家各派除了門庭設施與宗風特色的不同外,在根本宗旨上也存在一定的傾向與側重。關于這一點,呂澂曾結合法眼文益《宗門十規論》中的說法談及臨濟宗與曹洞宗的分別:“由臨濟傳下來的南岳一系的特點,是他們逐漸發揮出來的‘觸目是道’;而由曹洞傳下來的青原一系,其特點則發揮為‘即事而真’。臨濟比較重視從主觀方面來體會理事的關系,由理的方面體現到事,也就是說,以理為根據來見事,所以所見者無不是道。曹洞的‘即事而真’重點則擺在事上,注重客觀,在個別的事上體會出理來。”[16]換句話說,就臨濟宗的觀念而言,世間萬物均系自性的顯現,觸目所見,皆是菩提。也正因如此,臨濟宗禪師常常指引后學從眼前的森羅萬象中去發現真理,如晦堂祖心禪師便曾作詩說“風卷殘云宇宙寬,碧天如水月如環。祖師心印分明在,對此憑君子細看”[17]。陳與義在與大圓洪智禪師一起坐禪時,所寫詩歌《與智老天經夜坐》同樣也有類似的展現:“殘年不復徙他邦,長與兩禪同夜缸。坐到更深都寂寂,雪花無數落窗前。”[3]461深夜在燈下參禪,四周靜寂無聲,此時只見雪花無數,片片飛落窗前。在陳與義眼中,這雪花中透露著禪機,正是真如本性的自然呈現。
實際上,以圓滿自足的自然景物入詩,借以呈現佛禪旨趣,是宋代文字禪的慣用手法。而就臨濟宗旨對陳與義的影響來看,則主要體現在創作靈感的生發上,如《赴陳留》:“點點羊散村,陣陣鴻投陂。城中那有此,觸處皆新詩。”[3]192目光所及之處,事事皆可入詩。詩人曾在詩中多次表達此意,像“蛛絲閃夕霽,隨處有詩情”[3]240,“新詩滿眼不能裁,鳥度云移落酒杯”[3]189,“落日留霞知我醉,長風吹月送詩來”[3]190等。陳與義十分重視“興”的創作手法,并有意識地到自然界中尋找詩興,如《又用韻春雪》說“急雪催詩興未闌,東風肯奈鳥烏寒”[3]521,《與王子煥席大光同游廖園》稱“三枝筇竹興還新,王丈席兄俱可人”[3]372。“興”原是古典詩歌的慣用表現手法,不過宋代詩人卻更加重視“以學問為詩”,其主要代表便是蘇軾與黃庭堅。陳與義生活的北宋晚期,正處在以蘇、黃為代表的江西詩派籠罩下,此時詩壇學習蘇、黃詩歌已然成為一種風氣,所謂“師坡者萃于浙右,師谷者萃于江左”[18]。這種學習無疑是將“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等“以學問為詩”的手法作為重點,但江西后學卻往往因為才情有限,從而拘泥蘇、黃詩歌的成法,以至于詩情僵化。如《庚溪詩話》說:“山谷之詩,清新奇峭,然近時學其詩者,必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澀,曰江西格也,此何為哉?”[19]從這個角度來說,陳與義對“興”的崇尚實際上是不滿江西后學的流弊,試圖從自然景物入手來突破蘇、黃藩籬以求新。
若就陳與義詩歌創作的具體情況來看,重視“詩興”的主要影響是其“新體”詩風的產生。關于這一點的論述主要有兩處:
會兵興搶攘,避地湖廣,泛洞庭,上九嶷、羅浮,而以山川秀杰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詠尤工。縉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遍,號稱“新體”。(葛勝仲《陳去非詩集序》)[20]
客有誦陳去非《墨梅》詩于余者……予誦其一曰:“‘潔白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是緇塵染素衣。’世以簡齋詩為新體,豈此類乎?”客曰:“然。”予曰:“此東坡句法也。”(陳善《捫虱新話》)[21]
論者常將陳與義雄渾壯闊的學杜之作稱為“新體”,這或許是受到劉克莊“建炎以后,避地湖嶠,行路萬里,詩益奇壯”[14]26之說的影響。但實際上,葛勝仲對此早已言之甚明,所謂“新體”是指那些益以“山川秀杰之氣”的“賦詠尤工”之作。陳善同樣也認為陳與義早期的《墨梅》等詩是東坡句法,并非“新體”。南渡以來,陳與義寫出了大量明麗流暢的作品,如“日落潭照樹,川明風動花”[3]288,“春風浩浩吹游子,暮雨霏霏濕海棠”[3]318,“客子光陰詩卷里,杏花消息雨聲中”[3]476等。劉辰翁評價此類詩歌有“光景明麗,肌骨勻稱”之語。筆者據此認為,這才是陳與義的“新體”詩風所在。而這些以悠然之心表現自然之美的詩歌,恰是詩人采用“興”的手法所進行的創作。至于“光景明麗”之詩風形成的淵源,在陳與義自己詩作中也已有所透露,如《題向伯共過峽圖二首》(其一)說:
旌旗翻日淮南道,興罷歸來雪一船。正有佛光無處著,獨將佳句了山川。[3]420
此詩大約作于建炎四年冬天,陳與義這時正處在將要入川的南逃途中。該詩首句追想旌旗獵獵的戰爭前線之場景,次句以眼前所見江上雪景加以對照,三句大約是指嘉州峨眉山之“攝身佛光”,末句則自顧自地說不如用詩句來為這難得的佛光景象作結吧。據此詩可以看到,在陳與義的筆下,“詩興”“佛禪”“山川”三者之間有著十分微妙的聯系,正反映出詩人在走出書齋后、從自然風光中發現與找尋“詩興”的佛禪因子。
作為南北宋之交最具盛名的詩人,陳與義受到了佛禪思想的極大影響。禪宗思想一方面令其人生觀念由消極悲觀逐漸轉變為超然達觀,另一方面卻也影響到詩人晚年作詩的積極性。具體而言,臨濟宗“峻烈活潑”的宗風促使他提出“拔俗求新”的詩學思想以及重視“韻格”的學杜方法,“觸目是道”的宗旨則令其更加崇尚“詩興”的創作手段,進而催生出“新體”詩風。更進一步地說,宋代臨濟宗所啟示的詩學思想及作詩手法,為陳與義跳出江西詩風的圈圚提供了較大的助益,這是研究陳與義詩歌特色必須要注意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