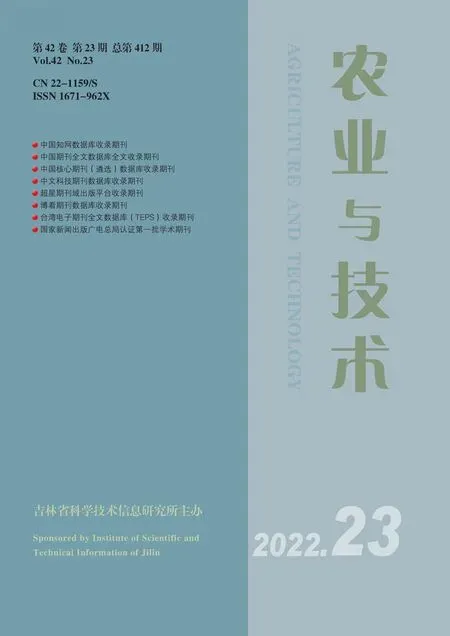鄉村振興視角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社會風險識別
——基于云南大理的實踐調查
付光輝 朱佳宇
(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1800)
目前,我國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然而城市快速發展的背后是鄉村的相對落后,即城鄉二元結構。城鄉二元結構使得集體土地被排斥在用地市場之外,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所有權地位不對等,于是導致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隱性流轉。隱性流轉市場在20世紀90年代達到頂峰,造成鄉村土地資源的粗放利用,對耕地生態用地存在占用,為了減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隱性流轉的危害,國家展開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的試點工作。從2015年開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制度的試點改革取得了極為顯著的改革效果,截至2018年底,入市地塊1萬余宗,總成交價款約257億元,成交666.67hm2以上。
然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地區的改革并非一帆風順,仍暴露出了一些的問題。如收益分配機制不健全[1]、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分布零散,價格低[2]、改革利益是否真正落實到農戶等問題,因此系統地對入市全過程進行風險的識別尤其重要。
當前,學者們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研究集中于入市的障礙、收益分配問題[3]、農戶入市意愿[4]、政府在入市中的角色與定位[5,6]、入市政策與制度[7,8]等方面。然而鮮有研究系統地涉及到了入市的社會風險與形成機理的研究,本文以云南大理市為例,運用扎根理論,對入市社會風險識別與梳理,并分析其形成的內在機理。這有助于獲知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下各方主體的利益訴求及承擔的風險,并降低風險發生的概率乃至化解風險,同時也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順利推進提供建議,更好地促進鄉村振興。
1 研究設計
1.1 研究方法
扎根理論研究方法是一種自下而上,從實際客觀資料上建立理論的定性研究方法,其最大的特點是客觀。研究者通過深度訪談、實地調研等過程對原始資料進行提煉概括具有隱蔽性、潛伏性、難以量化、相互影響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社會風險。
1.2 數據來源
本研究調查區域為云南省大理市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的村鎮,調研對3位政府工作人員,12位村干部,29位參與入市農戶,3位企業負責人進行了訪談。訪談時以“您對入市政策的了解程度”“入市收益分配情況”“入市對您生活的影響”等問題入手,逐步深入。調研完成,整理獲得47份訪談報告,隨機選取40份訪談報告,對其進行編碼。
2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社會風險識別
2.1 資料分析過程
2.1.1 開放編碼
開放式編碼是一個從原始資料中發現概念類屬,并將其整理、命名、概念化、歸類化和范疇化的過程。在訪談結束后,運用Nvivo12軟件中的編碼功能對概念整理分析,共建立46個一級編碼。

表1 概念提取過程
2.1.2 主軸編碼
主軸編碼也稱之為二級編碼。主軸編碼是進一步歸類的二次分析的過程。將開放編碼得到的初始概念進行整合,將原有的開放編碼提煉出24個主軸編碼。

表2 范疇發展與質性編碼過程
2.1.3 選擇編碼
選擇性編碼是通過資料與初步成型的理論互動進一步獲取范疇之間的聯系,最終提煉出研究的理論模型。本文對24個主軸編碼進行整理,得到7個選擇編碼。
2.2 理論飽和度檢驗
對剩余的7份訪談記錄進行編碼和概念的提煉,沒有涌現出新的概念或范疇,這說明上述編碼的40份訪談記錄已經完全容納了相關的概念和范疇。由此可以認為,本文形成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社會風險模型通過了理論飽和度檢驗,具備一定的現實解釋力。

圖1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社會風險基本模型
3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社會風險影響機理分析
入市涉及到政府、集體經濟組織、用地企業和農戶4個主體,各方利益沖突,各類社會風險相互影響,形成了一個復雜的風險系統,作用于風險承擔者,這些風險的形成也有其內在原因,見圖2。

圖2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社會風險識別及影響機理
3.1 城鄉二元化結構是根本原因
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時,必然會出現鄉村相對落后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即城鄉二元結構。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影響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主要表現為城鄉之間資源配置、戶籍壁壘、基礎設施不完善等。經濟的發展不平衡,農民沒有太多收入來源,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收益權和宅基地是其最大資產和身份的保護與認可,導致農民對入市收益的“斤斤計較”和對宅基地征收的抗拒;雖然法律規定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享有和國有土地權利,但是由于基礎設施不完善,在入市市場上很難被平等對待;鄉村封閉的發展模式使鄉村天然具有“排外”屬性,同時自身能力的限制,法律知識和權利意識的匱乏使其利益訴求很難被表達,為村干部權力尋租埋下隱患。
3.2 鄉村自身局限性是內生因素
自身局限性主要體現在農民自身素質、管理方式、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農民自身受教育水平、職業技能都深刻影響著其自身權益保障,也影響了其對于入市的意愿;不同于城市街道辦,鄉村的管理是由其人口、財力以及領導者思維決定的,在管理上缺乏統一的標準,在住房和基礎設施建設上參差不齊。對企業施工造成的污染、入市是否影響村民正常生活也都取決于領導者的思維。其自身局限性也使其在與入市企業進行博弈時,處于劣勢,利益被企業攫取。
3.3 法律法規體系不完善是外部誘導因素
新《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多在宏觀層面上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做了規劃,但是各省市自治區乃至于各縣基礎情況不同,留下了一定的騰挪空間。如新《土地管理法》第45條確立的征地公益條款雖有利于縮小征地范圍,但該條款所確定的“成片開發”征地情形又為政府土地征收留下了巨大空間。當地政府可以利用“漏洞”將原本可以入市的土地征收為國有土地掛牌入市,侵害了農戶利益。
3.4 利益沖突是直接原因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涉及到政府、集體經濟組織、用地企業和農戶4個主體,各主體的利益訴求存在既對立又統一的現象。地方政府可以在集體經濟組織入市過程中獲得增值收益調節金,增加財政收入,但是地方政府更希望由自身征收為國有土地入市,獲得更大利益;入市農戶需要依靠集體經濟組織的領導者去實現入市,村干部也可以獲得政績。但是實際中村干部的權力尋租活動時常發生,使農戶利益受損;集體經濟組織與用地企業存在同樣目標,即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成功入市,集體經濟組織獲得收益,用地企業項目順利實施。然而用地企業更希望以低價取得土地使用權,以此獲得更大收益,集體經濟組織則相反。
4 風險控制與規避
本文運用扎根理論的質性研究方法,以云南省大理市試點時期參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村鎮為例,建立入市社會風險基本模型。通過上述風險及產生機理的識別梳理,為地方政府和集體經濟組織的入市工作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風險管控措施,也促使人們進行自我反思,增強風險意識,尋求規避風險的方法,促進鄉村社會的穩定與經濟的發展。
4.1 健全收益分配機制
在收益分配過程中,協調好農戶—集體經濟組織—政府三方的利益,確保收益分配的合理公正,必須健全收益分配機制,而收益分配機制的首要問題即處理好收益分配各方比例。對于調節金比例、收益中集體經濟組織所占比例、分配依據、分配方式與形式等都應通過村民代表大會、村小組會議商討決定后,合理確定分配機制,并及時進行公示。入市所得收益除了直接的資金分紅之外,還可以通過諸如收益再投資進行分紅,也可以成立集體經濟合作社給予農戶股份,形成多渠道多類型的收益分配機制[9],增強農戶積極性。
4.2 村集體要引導消費,提升農民自身素質,優化產業結構
村集體要加強對農民的理財思維培訓及消費引導,避免農民獲得一次性大額收益后,出現不理性消費,從而使家庭返貧情況;集體經濟組織要加強對農民自身素質的培養,如職業素質與工作技能,特別是由于入市或宅基地征收會導致家庭收入減少的農戶。更重要的是,集體經濟組織應該借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這股“東風”壯大自身經濟實力,成立合作社或者股份制公司,打造適應各地情況的產業支柱,使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成為“有源之泉”。
4.3 加強鄉村及周圍的基礎設施建設
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出資改造鄉村的綠化、環境衛生、村民住宅等,對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存在的小、零散且周邊環境差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優化入市地塊周圍環境。同時村集體也可以將零散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附近的荒地開發成可利用的土地,或者征收部分宅基地,將這些地塊進行合并,擴大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可使用面積,使原本不適合入市的地塊通過整理能夠入市,緩解當前集體土地供給制約困境。地方政府也可以設置專項財政資金,逐步完善各項基礎生活服務設施向農村延伸。
4.4 規范和優化入市流程
規范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確權登記,入市的前提是將土地確權,但是由于確權資料匱乏,確權過程低效而漫長。地方政府應當制度規范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確權流程和步驟,入市之前協助村集體解決“確地”和“確人”2個問題。“確地”即厘清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基本資料,如面積大小、界址范圍等。“確人”即厘清集體經濟組織的組織成員,避免產權主體虛置和重疊,最后也要明確收益分配者。引導集體經濟組織參與入市,地方政府要優化簡化集體經濟組織申請入市的基礎流程,避免繁瑣復雜的手續,盡可能縮短審批時間,必要時可以組成專業小組,派遣專業人士對入市環節諸如手續準備、土地審核、土地確權[10]、土地的估價定價、與用地企業聯系與談判等方面進行指導與幫助,盡可能降低村民的入市成本,減小入市過程中耗時時間長,花費資金大等造成推動入市難,成本高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