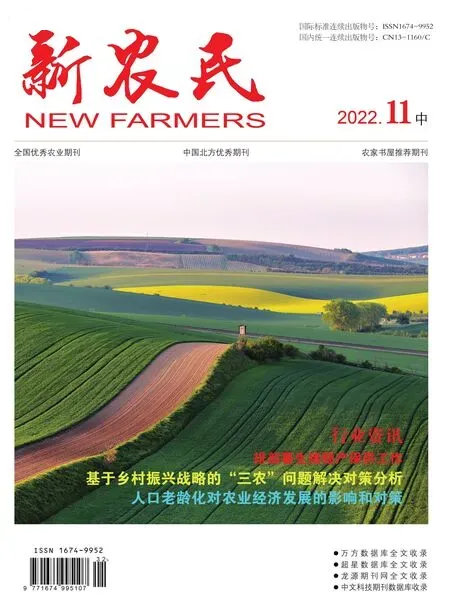山西某地區由出血性大腸桿菌引發麋鹿死亡的分析報告
張 卓,李金邦,孫樂天,霍占鎖
(太原動物園,山西 太原 030009)
大腸埃希氏菌(E.coli)通常稱為大腸桿菌,是埃希菌屬中的一類,為革蘭氏陰性無芽孢的直桿菌,兩端鈍圓、周身鞭毛,為兼性厭氧菌,常見于溫血生物的下腸。大腸桿菌廣泛分布在自然界,大多數是不致病菌,附生于腸道內為正常菌群。某些血清型的致病性強,大致分為5類:致病性大腸桿菌(EPEC)、腸產毒性大腸桿菌(ETEC)、腸侵襲性大腸桿菌(EIEC)、腸出血性大腸桿菌(EHEC)和腸黏附性大腸桿菌(EAEC)。其中,腸出血性大腸桿菌(Enterohemorrhagic E.coli,EHEC)是一種人畜共患病,被感染的病人、帶菌動物等均可傳播本病,較常見的易感動物為牛、羊、雞、狗、豬等家畜,也有從鵝、馬、鹿的糞便中分離出此菌的報道。出血性腸炎在我國大部分鹿類園區時有發生,成為對我國養鹿業威脅較大的傳染病之一[1]。
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隸屬偶蹄目(Artiodacty)鹿科(Cervidae)鹿亞科麋鹿屬,原產于中國長江中下游沼澤地帶。2021年2月份,山西某養殖鹿場死亡2只麋鹿,通過臨床癥狀和病理變化的分析,以及實驗室診斷等,明確死因,為今后麋鹿的飼養和疾病預防工作提供參考。
1 發病情況
該鹿區共飼養20頭麋鹿,分3個圈,發生疾病的是其中一個圈舍,內飼養有6頭麋鹿。據該場人員介紹,2021年2月12日上午突然發現兩只麋鹿狀態不佳,其中一只♂7歲麋鹿走路時出現跛行的癥狀;一只♀6歲麋鹿出現精神沉郁、少食的癥狀。后于13日及15日這兩只麋鹿先后出現不食,精神不振、頭垂地常臥、拉血便的癥狀,排泄物為帶有黏液和暗紅色血液的坨狀糞便。15日上午♀麋鹿死亡,20日上午♂麋鹿死亡。發病期間圈內剩余4只麋鹿精神狀態一般,采食較平日減少,但未發現拉血便情況。
2 剖檢情況
對病死的兩只麋鹿病理解剖時發現:
心臟明顯腫大、心冠脂肪處有少量出血點、心房內壁有出血點(圖1A);
肝臟邊緣鈍圓,輕微腫大(圖1B);
肺臟表面輕微出血;腎臟包膜不易剝離,質脆(圖1C),皮質與髓質間的邊界不清;腸系膜廣泛性點狀出血,淋巴結腫大;
小腸彌漫性出血壞死,內有血性內容物;部分腸段脹氣,小腸內容物呈暗紅色液體(圖1D)。

圖1 麋鹿尸體剖檢結果
3 實驗室診斷
3.1 細菌分離培養及鏡檢
在超凈工作臺內,無菌操作,使用接種環在心、肝、腎和腸道等病變組織取樣,劃線接種于血平板和中國藍瓊脂培養基(購于上海廣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37℃需氧條件下培養18~24 h,觀察菌落形態,相互對照后發現,菌落在血平板和中國藍培養基上均生長良好,血平板上出現圓形,稍凸,灰白色不透明菌落,在中國藍平板上出現藍色菌落,挑取單個菌落進行革蘭氏染色、鏡檢后,顯微鏡下可見細菌為革蘭氏陰性,菌體中等大小、兩端鈍圓短桿菌,基本符合腸出血性大腸桿菌的特點。
3.2 細菌生化特性鑒定
在超凈工作臺內,利用細菌微量生化反應管,對所分離的菌株進行生化指標測定。結果表明該細菌能分解葡萄糖乳糖與靛基質、鳥氨酸、賴氨酸、衛矛醇反應;不與苯丙氨酸、枸櫞酸鹽、尿素、硫化氫反應。這些生化鑒定結果與大腸桿菌生物學特征相符,表明該菌極有可能是出血性大腸桿菌。
3.3 藥敏試驗
3.3.1 方法
采用紙片擴散法,按K-B法要求操作,35℃溫箱中培養18~24h后,測抑菌圈直徑。判斷標準,參照K-B法藥敏試驗標準,抑菌圈直徑≧18mm者為敏感(S);抑菌圈直徑13~17mm者為中敏(M);抑菌圈直徑<12mm者為耐藥(R)。
3.3.2 結果
實驗結果表明該分離株對頭孢噻肟和慶大霉素中敏,頭孢曲松、奧美拉唑和慶大霉素等敏感,詳見表1。

表1 腸出血性大腸桿菌對抗生素的敏感程度
4 治療
(1)由于病鹿于2月12日發現少食、精神沉郁,口服健胃消食片(4.8g/次),2次/d。飲水中添加電解多維(5g/10kg),喝完再續。
(2)母鹿于2月1 3日發現拉血便后單圈飼養,治療藥物更換為:肌內注射酚磺乙胺注射液(1.25g∕次),2次/d;肌內注射維生素k1注射液(50mg∕次),2次/d;肌內注射鹽酸林可霉素注射液(10mg∕kg),2次/d。由于病情較為嚴重,在及時治療的同時,采集帶血糞便進行實驗室檢查,但因病料從地面采集,污染嚴重,未培養出有效菌種。
(3)母麋鹿于2月14日,對其進行補液治療,靜脈滴注0.9%生理鹽水,輸液中添加鹽酸林可霉素注射液(10mg/kg),2次/d。并肌內注酚磺乙胺注射液(1.25g∕次),2次/d;維生素k1注射液(50mg/次),2次/d。
發現母麋鹿血便后,公麋鹿采取預防性治療,鹽酸林可霉素注射液(10mg∕kg),2次/d。
(4)母麋鹿病程較快,治療效果不佳,于2月15日死亡。采集心、肝、腎及腸道等病變組織重新進行細菌培養和藥敏試驗。
同時,為預防其他5只麋鹿不受感染,飲水中添加鹽酸土霉素可溶性粉(1g/500ml),飼料中添加電解多維(1g/kg)。也為減少治療期間麋鹿的應激反應。飼料也將苜蓿顆粒更換為易消化的谷草、槐樹葉和東北草。
2月18日,根據藥敏結果治療藥物更換為:肌內注射慶大霉素(400mg/次),2次/d;酚磺乙胺注射液(1.25g/次),2次/d;維生素k1注射液(50mg/次), 2次/d。但治療效果欠佳,公麋鹿1月20日死亡。
5 討論
本病在我國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場及動物園的斑馬、象、鹿中均有發生,被稱為“猝死癥”[3]。因此,早期發現,及時診斷和治療是控制該病的關鍵[4]。文中兩只麋鹿發生死亡,原因分析可能是早期癥狀不典型,未出現水樣腹瀉和出血性腸炎,對其重視程度不夠,錯過了治療的“黃金時期”,也可能是天氣寒冷食欲減退等多種原因混合引發。圈內剩余4只麋鹿由于治療及時,配合良好的飼養管理,均已好轉。
在飼養中要以預防為主,防重于治。具體的發病機制大體可以總結為4點:
多雨季節,雨水未及時清理,飲到不潔凈水;
季節溫差較大,氣溫驟變,如寒冷、炎熱、干燥等;
突然大量變換飼料種類或飼喂方法,如在北方冬草和青草的轉換上,應慢慢遞增或遞減;
有應激刺激如換舍,斷奶,換環境等。盡量避免上述發病原因,可以有效減少患病的幾率。
在診斷時,也應與產氣莢膜梭菌及巴氏桿菌引起的鹿出血性腸炎區分清楚,避免誤診。由于死亡速度較快,治療時抗生素的選擇需要根據藥敏試驗的結果。本報告中,藥敏試驗結果對頭孢噻肟和慶大霉素中敏,頭孢曲松、奧美拉唑和慶大霉素等敏感,而有些地區對養殖場送檢的病死動物進行細菌分離之后,阿米卡星的敏感度最高,與本實驗結果不同,原因分析可能是不同地區用藥不同導致的敏感性存在差異[5],或是動物品種的不同導致敏感性也不盡相同。
EHEC主要會通過糞口途徑傳播,動物之間可以通過相互接觸、共食共飲污染的草、水等進行相互傳播,鳥類和禽類也是攜帶者。當懷疑或診斷出此類疾病后,首先選取針對性的方法進行消毒,可以減少患病動物與健康動物之間的傳播;我們使用1%的次氯酸鈉對運動場和食槽、水槽、糞便等重污染地區噴刷消毒,30分鐘后用清水沖洗干凈。因為消毒比較及時所以成效也明顯,對圈內剩余麋鹿并沒有造成感染和死亡。其次,將患病2只麋鹿放入隔離圈舍治療,也能有效地控制傳染源,減少動物應激,方便治療和投喂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