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jìn)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時(shí)代價(jià)值、思想淵源與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
萬華穎
(中共江西省委黨校 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江西 南昌 330108)
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以中國式現(xiàn)代化全面推進(jì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使命任務(wù),強(qiáng)調(diào)“中國式現(xiàn)代化是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xié)調(diào)的現(xiàn)代化”[1],并將“豐富人民精神世界”納入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本質(zhì)要求。在主持召開中央財(cái)經(jīng)委員會(huì)第十次會(huì)議時(shí),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通過多種方式“促進(jìn)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2],一方面強(qiáng)調(diào)了物質(zhì)生活共同富裕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另一方面對(duì)扎實(shí)推動(dòng)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促進(jìn)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為新時(shí)代的一個(gè)大課題,對(duì)于推動(dòng)共同富裕具有極其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當(dāng)前,學(xué)術(shù)界側(cè)重于研究共同富裕的物質(zhì)生活層面,對(duì)其精神生活層面的研究不多、認(rèn)識(shí)較模糊,有關(guān)如何在實(shí)踐中促進(jìn)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也亟待加強(qiáng)。立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學(xué)理意蘊(yùn)和現(xiàn)實(shí)意義,從理論和現(xiàn)實(shí)的雙重視域系統(tǒng)梳理其時(shí)代價(jià)值、理論淵源,構(gòu)建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探尋其內(nèi)在邏輯和關(guān)鍵點(diǎn)位,能夠?yàn)樾掳l(fā)展階段扎實(shí)推動(dòng)共同富裕提供理論指導(dǎo)和經(jīng)驗(yàn)借鑒。
一、促進(jìn)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的應(yīng)有之義
習(xí)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huì)主義的本質(zhì)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具體地,共同富裕是全體社會(huì)成員生活上的全面富裕,“物質(zhì)財(cái)富要極大豐富,精神財(cái)富也要極大豐富”[3]323,這不僅是對(duì)物質(zhì)貧窮的否定,也是對(duì)精神空虛和思想愚昧的否定。因此,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不只是物質(zhì)層面的生活富裕,也是包含精神在內(nèi)的人本身的發(fā)展的全面富裕。從理論和實(shí)踐、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相結(jié)合的角度,立足歷史的反思、現(xiàn)實(shí)的選擇、未來發(fā)展的需要,不難發(fā)現(xiàn),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必然組成部分和內(nèi)在構(gòu)成。
(一)共同富裕是物質(zhì)生活與精神生活質(zhì)與量相統(tǒng)一的全面富裕
共同富裕不僅包括物質(zhì)方面的豐厚,還包括經(jīng)濟(jì)、政治、生態(tài)、文化等各個(gè)方面,體現(xiàn)出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生活全方位的質(zhì)與量的統(tǒng)一。當(dāng)前,有的人對(duì)物質(zhì)生活與精神生活發(fā)展時(shí)序問題存在著認(rèn)知偏差,認(rèn)為必須在實(shí)現(xiàn)物質(zhì)追求之后再考慮精神追求問題,把精神追求看成是獨(dú)立于、外在于人們現(xiàn)實(shí)活動(dòng)的存在。然而,實(shí)際上,人的物質(zhì)追求與精神追求具有內(nèi)在統(tǒng)一性,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物質(zhì)生活共同富裕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guān)系。
一方面,物質(zhì)生活共同富裕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前提,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基礎(chǔ)和條件。馬克思主義認(rèn)為,物質(zhì)資料生產(chǎn)方式是社會(huì)發(fā)展的決定性力量,“物質(zhì)生活的生產(chǎn)方式制約著整個(gè)社會(huì)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4]8。這也充分表明,人的物質(zhì)生活狀況掣肘著人的精神生活。物質(zhì)貧困的長期存在會(huì)導(dǎo)致或加劇精神貧困,精神貧困又會(huì)反過來加劇物質(zhì)貧困。然而,真正的社會(huì)主義不僅要有高度發(fā)達(dá)的生產(chǎn)力,還要有高度發(fā)展的精神文明。若僅僅只是物質(zhì)生活富裕,但是精神生活卻很空虛,并不是真正的富裕。因此,我們必須清楚地認(rèn)識(shí)到,只有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生活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才能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絕對(duì)不能用物質(zhì)生活的富裕去掩蓋精神世界的匱乏和精神生活的貧困。
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更加聚焦于精神層面,是富裕的更高狀態(tài),也是個(gè)人發(fā)展和社會(huì)發(fā)展的更高歸宿和奮斗目標(biāo),為物質(zhì)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動(dòng)力支持和精神保障。進(jìn)一步地說,它既是社會(huì)公眾所應(yīng)具備的一種精神生活狀態(tài),又是一個(gè)需要不斷實(shí)踐、與時(shí)俱進(jìn)的奮斗目標(biāo)。雖然衣、食、住、行等直接物質(zhì)需要的滿足和社會(huì)物質(zhì)財(cái)富的豐富是解決人生產(chǎn)問題的關(guān)鍵,是促進(jìn)人的發(fā)展和推動(dòng)社會(huì)進(jìn)步的首要問題,但這絕對(duì)不是說追求物質(zhì)生活富裕是人類生活的全部意義。豐富多變的精神需求才是人區(qū)別于動(dòng)物的重要標(biāo)志,是人作為社會(huì)的“人”的本質(zhì)特征。當(dāng)然,有時(shí)物質(zhì)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產(chǎn)生、供給和滿足程度并不完全對(duì)稱,會(huì)呈現(xiàn)出不同于一般規(guī)律的特殊情況。比如說,在一定的環(huán)境和條件下,人的精神需要可能會(huì)不同程度地先于物質(zhì)需要的發(fā)展,或者是超越物質(zhì)需要而上升為首位需求。因此,我們既要遵循人的物質(zhì)和精神需要發(fā)生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也要承認(rèn)特定環(huán)境條件下的特殊規(guī)律;既不能只注重滿足物質(zhì)需要而忽視精神需要,也不能只注重精神需要而對(duì)物質(zhì)需要置之不理,要力求兩者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否則共同富裕的目標(biāo)就難以真正實(shí)現(xiàn)。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實(shí)現(xiàn)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的重要前提
物質(zhì)富裕、精神富裕,是馬克思主義關(guān)于人的全面發(fā)展理論的基本要義和重要內(nèi)容。人的全面發(fā)展內(nèi)在包含物質(zhì)層面的發(fā)展和精神層面的發(fā)展兩個(gè)方面。在物質(zhì)生產(chǎn)快速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人的物質(zhì)需要逐漸得到滿足、物質(zhì)生活不斷實(shí)現(xiàn)增長,但這并不能構(gòu)成人的真正發(fā)展。唯有滿足精神需要和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才是人全面發(fā)展的真正目的,才是社會(huì)發(fā)展進(jìn)步的精神動(dòng)力。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精神生產(chǎn)理論的重要體現(xiàn)。人的精神生活是決定人發(fā)展程度的關(guān)鍵因素[5]。馬克思主義精神生產(chǎn)理論提出,精神生產(chǎn)活動(dòng)的目的是滿足人的精神需要,實(shí)現(xiàn)人的能力發(fā)展,從而更大程度上實(shí)現(xiàn)人的精神愉悅和精神享受。一方面,從人的全面發(fā)展維度來說,馬克思強(qiáng)調(diào)精神生產(chǎn)作為“人的自由的有意識(shí)的活動(dòng)”,是人的本質(zhì)的充分體現(xiàn)。精神生產(chǎn)的發(fā)展程度是人類自由實(shí)現(xiàn)程度最為重要的標(biāo)志[6]139。作為現(xiàn)實(shí)的人,可以通過有目的、有計(jì)劃的實(shí)踐活動(dòng),達(dá)到滿足人的物質(zhì)需要、改善人類生產(chǎn)環(huán)境的發(fā)展目的。同時(shí),在這個(gè)過程中,人可以通過實(shí)現(xiàn)和發(fā)展各種能力,不斷超越主觀精神的制約,從而實(shí)現(xiàn)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另一方面,從社會(huì)進(jìn)步的維度來說,精神生產(chǎn)是社會(huì)進(jìn)步(包括物質(zhì)文明進(jìn)步和精神文明進(jìn)步)的重要標(biāo)志和衡量尺度。在精神生產(chǎn)發(fā)展的過程中,精神生產(chǎn)力的提升能夠通過物質(zhì)生產(chǎn)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或者能夠轉(zhuǎn)化為物質(zhì)生產(chǎn)力以推動(dòng)社會(huì)生產(chǎn)力的提升,從而促進(jìn)社會(huì)的全面發(fā)展進(jìn)步。
習(xí)近平總書記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發(fā)展以人的發(fā)展為歸宿,人的發(fā)展以精神文化為內(nèi)核”[7]150。這也充分表明,“人的全面發(fā)展”必然離不開精神生活的富裕。如果人們過分追求物質(zhì)利益,被物欲蒙蔽了雙眼,失去了作為人最寶貴的精神支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將遭受到嚴(yán)峻挑戰(zhàn)。同時(shí),隨著人民物質(zhì)生活質(zhì)量和水平的不斷提高,人民的文化水準(zhǔn)、精神追求、主體意識(shí)也隨之提高,人民對(duì)物質(zhì)文化的需要程度不斷加深,而且產(chǎn)生了更高層次的需要。因此,盡可能地把人從來自物的和人的各種束縛關(guān)系中解放出來,在更大程度上改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生活質(zhì)量,促進(jìn)人的全面發(fā)展,關(guān)注人的精神世界和社會(huì)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已成為時(shí)代強(qiáng)音。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高速發(fā)展以及大規(guī)模的貧困治理,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171元提高到2020年的32 189元(1)數(shù)據(jù)來源于:國家統(tǒng)計(jì)局。中國統(tǒng)計(jì)年鑒2020[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0/indexch.htm。國家統(tǒng)計(jì)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0年國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統(tǒng)計(jì)公報(bào)[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絕對(duì)貧困群眾長期存在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性需求得到較大程度的滿足。我國社會(huì)主要矛盾已經(jīng)轉(zhuǎn)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相較于物質(zhì)文化需要而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領(lǐng)域更寬、層次更高、形式更多,而這些都與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緊密相關(guān)。因此,推進(jìn)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要從物質(zhì)和精神、客觀和主觀多個(gè)方面發(fā)力,既要有數(shù)量上的增加,更要有質(zhì)量上的提升甚至飛躍;既要有客觀條件的改變,更要有良好的心理體驗(yàn),從而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主要是解決人的精神需要問題。富裕是與“貧困”相對(duì)應(yīng)的,而貧困被普遍認(rèn)為和人的需要相關(guān),本質(zhì)上表現(xiàn)為個(gè)人或社會(huì)的某種需要無法得到滿足。從需要的歷史序列和體系來說,人主要是通過社會(huì)實(shí)踐過程中的生產(chǎn)和創(chuàng)造來滿足自身需要,而需要的滿足會(huì)催生新的需要,新的實(shí)踐又會(huì)滿足新的需要,如此循環(huán)反復(fù),呈現(xiàn)出“需要→實(shí)踐→新的需要→新的實(shí)踐”這種由低級(jí)系統(tǒng)向高級(jí)系統(tǒng)螺旋上升的動(dòng)態(tài)發(fā)展過程。從歷史唯物主義視野出發(fā),人在社會(huì)實(shí)踐中會(huì)產(chǎn)生物質(zhì)性需要、交往性需要與精神性需要。人的需要的豐富性使人的本質(zhì)得到新的證明,充實(shí)著人的本質(zhì)內(nèi)涵。當(dāng)然,不可否認(rèn),人的需要的滿足程度會(huì)受到人自身、經(jīng)濟(jì)文化條件、社會(huì)發(fā)展程度等因素的制約。馬斯洛將人的需要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shí)現(xiàn)需求等由低到高的5個(gè)層次。現(xiàn)階段人們已經(jīng)滿足了溫飽需求,生存性需求退居從屬地位,此時(shí)人們更加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愉悅,因此發(fā)展性需求被提到更為重要的位置。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滿足人民對(duì)美好生活的需要作為出發(fā)點(diǎn)和落腳點(diǎn),進(jìn)一步增進(jìn)民生福祉。
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實(shí)現(xiàn)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人民群眾對(duì)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全方位的、多層次的,雖然美好生活的實(shí)現(xiàn)依賴于美好的物質(zhì)生活,但是人民對(duì)美好生活的定義已經(jīng)不再局限于此,而是更為注重對(duì)精神維度的追求。過去我們處于擺脫貧困、追求溫飽、實(shí)現(xiàn)小康的時(shí)期,現(xiàn)在我們處于促進(jìn)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時(shí)代,以前不突出、不迫切的需要,現(xiàn)在已然成為最突出、最迫切的需要。人們不再僅僅滿足于收入提高、衣食無憂,止步于物質(zhì)生活層面的豐裕,而是更為追求接受各種開闊眼界、豐富素養(yǎng)、怡情養(yǎng)性的教育,更為追求提升認(rèn)識(shí)世界的能力、欣賞美好的品位、立身為人的道德。當(dāng)然,人民精神境界的富足,不僅需要提高人民的科學(xué)文化素質(zhì),還需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zhì)。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提供較為豐富的精神文化食糧,正如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8]34。盡管我們知道精神文化所依賴的是肉體生命,但是它所追求的卻是高于肉體生命、超越現(xiàn)實(shí)世界的意義世界,而在這個(gè)追求的過程中生命的價(jià)值才能夠得以實(shí)現(xiàn)、生命的境界才能夠得以提高。只有通過不斷豐富精神文化生活以實(shí)現(xiàn)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才能使人擺脫物質(zhì)主義、消費(fèi)主義的束縛和枷鎖,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所在,從而以崇高的意志品質(zhì)、高尚的道德情操引導(dǎo)自身的生活,在真正意義上實(shí)現(xiàn)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擁有真正的美好生活[9]。
(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提出是對(duì)社會(huì)實(shí)踐的理性反思
當(dāng)前,我國已經(jīng)進(jìn)入了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關(guān)鍵期,人們的自主開放意識(shí)活躍、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秩序變化迅速,呈現(xiàn)出許多不確定的矛盾與挑戰(zhàn),充滿了許多變革的因素和發(fā)展機(jī)遇。
首先,物質(zhì)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是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到現(xiàn)階段的最佳選擇。經(jīng)過多年努力,中國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從1952年的679.1億元躍升至2020年的101.6萬億元,經(jīng)濟(jì)總量占全球經(jīng)濟(jì)的比重超過17%,穩(wěn)居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人均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從1952年的幾十美元增至2020年的超過1萬美元,實(shí)現(xiàn)從低收入國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歷史性跨越[10]。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zhì)生活總體上已經(jīng)達(dá)到了一定的富裕程度,積累了一定的物質(zhì)基礎(chǔ),為解決精神貧困問題、實(shí)現(xiàn)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目標(biāo)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其次,應(yīng)當(dāng)清楚地認(rèn)識(shí)到,“共同富裕”不僅僅存在于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經(jīng)濟(jì)的增長、人們物質(zhì)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代表就是堅(jiān)持了“共同富裕”。經(jīng)濟(jì)建設(shè)是中心,但絕不能“唯經(jīng)濟(jì)是瞻”而不顧其他,我們無法用單純的物質(zhì)手段和經(jīng)濟(jì)措施代替人們的精神生活或是解決社會(huì)發(fā)展過程中的所有問題。諸如GDP(或GNP)這種經(jīng)濟(jì)指標(biāo)其實(sh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并不能反映自由、閑暇等問題,也無法反映出快樂、幸福等非物質(zhì)性的精神因素。另外,不可否認(rèn)的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之初帶給人們的幸福感是最強(qiáng)的,但是等到經(jīng)濟(jì)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時(shí)候,人們的幸福感會(huì)減弱。這是因?yàn)槿藗兯非蟮哪繕?biāo)并不是單一的,除了物質(zhì)財(cái)富以外,人們對(duì)實(shí)現(xiàn)自我價(jià)值、提升社會(huì)地位等非物質(zhì)的目標(biāo)也有所追求。此時(shí),增加物質(zhì)財(cái)富并不能夠滿足人們所有的期待和追求,他們?cè)谛碌母邔哟紊嫌辛诵碌母叩哪繕?biāo)。從這個(gè)意義上來說,“隨著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幸福的邊際效應(yīng)會(huì)遞減”[11],無論物質(zhì)手段如何豐富、物質(zhì)生活水平如何提高,人們精神生活中的所有問題都無法完全得到解決,幸福指數(shù)也有可能會(huì)下降。那么,既然物質(zhì)手段并不能解決經(jīng)濟(jì)快速發(fā)展中的全部問題,我們就不得不及時(shí)思考“富而思源、富而思進(jìn)”的問題,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與物質(zhì)生活共同富裕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否則,人們?cè)诓粩嘧非笊踔脸撩杂谖镔|(zhì)生活的過程中,可能會(huì)缺乏動(dòng)力、迷失方向、錯(cuò)失機(jī)遇,最終還會(huì)阻礙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速度,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制約社會(huì)發(fā)展的進(jìn)程。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風(fēng)氣如果壞下去,經(jīng)濟(jì)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huì)在另一方面變質(zhì),反過來影響整個(gè)經(jīng)濟(jì)變質(zhì),發(fā)展下去會(huì)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12]154因此,我們?cè)谧⒅厝嗣裎镔|(zhì)生活富裕的同時(shí),絕不能忽視其精神生活,要使兩者相互促進(jìn)、協(xié)調(diào)并進(jìn)。
再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對(duì)精神方面不良現(xiàn)象的回應(yīng)。西方發(fā)達(dá)國家推行“從搖籃到墳?zāi)埂钡母吒@鐣?huì)保障模式,然而實(shí)際上這種模式受到資本邏輯的制約,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在經(jīng)濟(jì)危機(jī)的沖擊下更加無法持續(xù)下去。一方面,資本和市場不斷促進(jìn)人民群眾整體上物質(zhì)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它們對(du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卻沒有起到相同的促進(jìn)作用。在資本邏輯的推動(dòng)下,勞動(dòng)喪失了自主性,在一些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較高的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物質(zhì)財(cái)富豐富的同時(shí),各種腐朽的思想也相繼出現(xiàn),精神空虛、價(jià)值偏離、理想失落等現(xiàn)象層出不窮,這些都是資本邏輯制造出的物質(zhì)財(cái)富與精神財(cái)富之間的矛盾。發(fā)達(dá)國家現(xiàn)代化道路的教訓(xùn),我們應(yīng)引以為戒,積極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口袋鼓起來,精神空下去”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中國把社會(huì)主義與市場經(jīng)濟(jì)有機(jī)結(jié)合起來,通過改革開放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騰飛,并在快速發(fā)展中注重解決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城鄉(xiāng)區(qū)域發(fā)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等問題,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改善。然而,近年來由于工具理性和功利原則被大力推崇,極端的物欲充斥著人們的精神家園,導(dǎo)致人的物化和片面發(fā)展,如“飯圏文化”的產(chǎn)生就使得大眾精神生活充滿污濁之氣,對(duì)社會(huì)精神領(lǐng)域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這些不良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及演變,說明一部分人的精神生活失去了健康的方向,這是文化市場上秩序失序、標(biāo)準(zhǔn)失范的結(jié)果,不是社會(huì)主義共同富裕目標(biāo)下應(yīng)該出現(xiàn)的。因此,促進(jìn)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需要優(yōu)質(zhì)豐富的精神文化資源的繁榮發(fā)展,也需要對(duì)現(xiàn)有精神文化資源進(jìn)行合理配置和均衡供給,更需要全體人民對(duì)先進(jìn)精神文化成果進(jìn)行主動(dòng)內(nèi)化與積極外化”[13]。而此時(shí)中央提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生活“雙富裕”,是社會(huì)實(shí)踐的必然要求,也是對(duì)共同富裕理念的豐富和充實(shí)。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思想淵源
馬克思在《1844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中提出“通過私有財(cái)產(chǎn)及其富有和貧困——物質(zhì)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貧困——的運(yùn)動(dòng),生成中的社會(huì)發(fā)現(xiàn)這種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14]83,這里“精神的富有”的概念可視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最早提法。這也表明他在強(qiáng)調(diào)人類社會(huì)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強(qiáng)調(diào)人的精神世界及其精神生活的充裕和滿足。當(dāng)前,學(xué)術(shù)界對(du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關(guān)注程度與日俱增,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對(du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思想淵源作出進(jìn)一步科學(xué)嚴(yán)謹(jǐn)?shù)奶接憽?/p>
(一)中國共產(chǎn)黨百年來關(guān)于精神富裕的重要論述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論提供了思想指導(dǎo)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并非憑空產(chǎn)生的抽象命題,而是始終扎根于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的偉大實(shí)踐之中,貫穿于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百年歷程之中。中國共產(chǎn)黨關(guān)于堅(jiān)持物質(zhì)富裕和精神富裕相統(tǒng)一的認(rèn)識(shí)來源于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實(shí)踐,是新時(shí)代中國共產(chǎn)黨在共同富裕實(shí)踐發(fā)展基礎(chǔ)上推動(dòng)思想認(rèn)識(shí)持續(xù)深化的結(jié)果[15]。近代中國的問題不僅體現(xiàn)為物質(zhì)方面的“貧”,更體現(xiàn)在精神方面的“弱”。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dǎo)下,中國人民不僅在經(jīng)濟(jì)上和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而且在文化生活方面擺脫了相對(duì)貧乏的境地,人民的精神境界逐漸豐盈起來,在精神上也成為了自己的主人。在社會(huì)主義革命和建設(shè)時(shí)期,我們黨尤為重視“科學(xué)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設(shè),毛澤東同志指出要“將我國建設(shè)成為一個(gè)具有現(xiàn)代工業(yè)、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和現(xiàn)代科學(xué)文化的社會(huì)主義國家”。鄧小平同志圍繞“什么是社會(huì)主義”“怎樣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這一根本問題,提出“我們堅(jiān)持走社會(huì)主義道路,根本目標(biāo)是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12]155,并且強(qiáng)調(diào)“我們要建設(shè)的社會(huì)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zhì)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6]367,只有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發(fā)展,國家物質(zhì)力量和精神力量才能同時(shí)增強(qiáng),這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江澤民同志也十分注重人民的精神富裕狀態(tài),提出“物質(zhì)貧乏不是社會(huì)主義,精神空虛也不是社會(huì)主義”[17]621的科學(xué)命題,并采取一系列有效舉措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社會(huì)持續(xù)發(fā)展,使人民的物質(zhì)生活不斷豐富、精神生活不斷充實(shí)。胡錦濤同志也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我們要建設(shè)的現(xiàn)代化,是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發(fā)展的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18]589,從而進(jìn)一步推動(dòng)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論和實(shí)踐的發(fā)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xí)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jiān)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把帶領(lǐng)人民創(chuàng)造美好生活、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擺在更為突出的位置,歷史性地解決了我國的絕對(duì)貧困問題,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zhì)條件和思想保證。當(dāng)前,我國已轉(zhuǎn)向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新階段,更為注重經(jīng)濟(jì)增長與社會(huì)進(jìn)步的有機(jī)統(tǒng)一、物質(zhì)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之際提出來,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diǎn)[19]。立足于中國的實(shí)際情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顯示出更為寬廣的理論空間和現(xiàn)實(shí)意義,更加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強(qiáng)國的奮斗目標(biāo)。習(xí)近平總書記強(qiáng)調(diào):“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shù)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2]社會(huì)進(jìn)步的內(nèi)在驅(qū)動(dòng)力包括追求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一方面要讓人民過上比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學(xué)文化水平”[20]111。總之,這些關(guān)于物質(zhì)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論述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對(duì)精神富裕的追求更為自覺,為我們解決好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生活發(fā)展不平衡不協(xié)調(diào)問題,實(shí)現(xiàn)人民物質(zhì)生活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同頻共振、相得益彰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jù)。
(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論提供了重要來源
“共同富裕”思想自古有之,具有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基因。作為治國理政思想理念的重要元素,共同富裕不僅是經(jīng)濟(jì)表述,而且是文化展示;不僅有經(jīng)濟(jì)上的滿足,而且包括思想文化上的充實(shí),它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間存在著天然的基因聯(lián)系。自古以來,中國就較為重視精神世界的建設(shè),注重精神生活的追求。一方面,物質(zhì)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礎(chǔ),漢代董仲舒、王符曾經(jīng)說過,“先飲食而后教誨,謂治人也”“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xué)為基”。“既富且教”,這是古代傳統(tǒng)社會(huì)真正的“治人”標(biāo)準(zhǔn)和社會(huì)治理理念。另一方面,精神富有也是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維度,孔子說“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禮記》講“圣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于約,貴不慊于上,故亂益亡”,管子曰“倉廩實(shí)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等等,這些都體現(xiàn)了對(duì)追求道德精神的重視。只有物質(zhì)和精神都富裕,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大同社會(huì)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由天下人共有,不僅體現(xiàn)在物質(zhì)生活方面,擁有“天下為公”的社會(huì)管理制度和“安居樂業(yè)”的社會(huì)保障制度;而且體現(xiàn)在精神生活方面,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至高理想,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愛哲學(xué),人們誠實(shí)守信、和諧相處,具有良好的社會(huì)人際關(guān)系,實(shí)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當(dāng)然,這里所說的大同社會(huì)與當(dāng)代共同富裕、共產(chǎn)主義理論有著本質(zhì)區(qū)別,由于當(dāng)時(shí)落后生產(chǎn)力的限制,中國古代人民對(duì)平等和諧生活的追求以及對(duì)理想社會(huì)的構(gòu)想只能停留在萌芽階段,不過這仍然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來源。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論是對(duì)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論的繼承和發(fā)展
現(xiàn)階段所提出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論是對(duì)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論的繼承和發(fā)展,與馬克思主義精神生活理論的相關(guān)思想一脈相承。馬克思在追求共同富裕的社會(huì)理想中,始終把實(shí)現(xiàn)精神生活與物質(zhì)生活的共同富裕作為社會(huì)發(fā)展的終極目標(biāo)。他認(rèn)為“人雙重地存在著:從主體上說作為他自身而存在著,從客體上說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這些自然無機(jī)條件中”[21]484。具體而言,在社會(huì)實(shí)踐中,人類不僅創(chuàng)造了滿足肉體生理需求的物質(zhì)文化世界,而且創(chuàng)造了滿足主體精神需求的精神文化世界。因此,馬克思在關(guān)注人們物質(zhì)生活狀況的同時(shí),對(duì)人們的精神生活、精神世界也非常重視。他尤其強(qiáng)調(diào)精神力量對(duì)人們改造自身以及改造世界的作用和意義,即我們?cè)谧非笪镔|(zhì)富裕、發(fā)展生產(chǎn)力的過程中,絕對(duì)不能忽視實(shí)現(xiàn)精神富有以及精神文明建設(shè)。他深刻揭露和無情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丑惡,“在一極是財(cái)富的積累,同時(shí)在另一極……是貧困、勞動(dòng)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22]708。如同物質(zhì)財(cái)富被資本家壟斷占有一樣,精神財(cái)富也被資本家所壟斷,他們甚至將占有的精神財(cái)富轉(zhuǎn)變?yōu)閴浩群团廴嗣竦墓ぞ撸箯V大勞動(dòng)者精神生活也極為貧乏,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huì)不僅存在著物質(zhì)生活兩極分化,精神生活也存在著兩極分化。與此同時(shí),馬克思主義科學(xué)構(gòu)想了未來的社會(huì),認(rèn)為由于消滅了剝削階級(jí),人們成為國家和社會(huì)的主人,“在人人都勞動(dòng)的條件下,生活資料、享受資料、發(fā)展和表現(xiàn)一切體力和智力所需的資料都將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歸社會(huì)全體成員支配”“……而且使每個(gè)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shí)間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xué)、藝術(shù)、交際方式等等——中間承受一切真正有價(jià)值的東西;并且不僅僅是承受,而且還有把這一切從統(tǒng)治階級(jí)的獨(dú)占品變成全體社會(huì)的共同財(cái)富和促使它進(jìn)一步發(fā)展”[4]478-479。恩格斯也指出“社會(huì)生產(chǎn)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huì)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zhì)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fā)展和運(yùn)用”[23]757。在他們所構(gòu)想的理想社會(huì)中,全體勞動(dòng)者平等、自由地接受教育,參與國家經(jīng)濟(jì)、政治、科學(xué)文化等一切活動(dòng),人人團(tuán)結(jié)友愛、和諧相處,充分享受著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從而實(shí)現(xiàn)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雙富裕。當(dāng)前,在生產(chǎn)力極大發(fā)展后,人們必然會(huì)追求不可或缺的精神享受,要求更高質(zhì)量、更高品位的生活,此時(shí)我們應(yīng)該在增長物質(zhì)財(cái)富的基礎(chǔ)上,以馬克思主義關(guān)于精神生活的思想為指導(dǎo),努力發(fā)展物質(zhì)生產(chǎn)力和精神生產(chǎn)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方面多層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最終實(shí)現(xiàn)更高階段、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
相對(duì)于物質(zhì)生活共同富裕來說,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們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和現(xiàn)有生活的主觀感受和反思,具有深層性、隱蔽性。就評(píng)價(jià)內(nèi)容而言,滿足各種“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主要包括享有政治權(quán)利和依法參與政治的民主需要,參與文化活動(dòng)、享受文化產(chǎn)品和服務(wù)的文化需要,享有公共服務(wù)、接受教育、充分就業(yè)的社會(huì)需要,享有美好宜居環(huán)境的生態(tài)需要等。因此,在深刻理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內(nèi)涵的基礎(chǔ)上,科學(xué)探索構(gòu)建我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以此多維度、多主體、多視角全面評(píng)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發(fā)展程度,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構(gòu)建原則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主要表現(xiàn)在個(gè)人和社會(huì)精神需求的不斷充實(shí)、滿足和提高上,對(duì)個(gè)人和社會(huì)的全面發(fā)展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我們應(yīng)該采取何種指標(biāo)去衡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程度高低,絕非易事。作為較為抽象的精神層面,選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存在一些難度,而解決問題的首要環(huán)節(jié)就是我們必須確立好選取指標(biāo)的原則。
1.主觀性與客觀性相結(jié)合原則。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主要是測定人們?cè)谖幕⑶楦小⒌赖隆徝酪约吧畹囊饬x、價(jià)值觀念等方面的發(fā)展變化,很難確定統(tǒng)一的、不變的、客觀的標(biāo)準(zhǔn);另一方面,人們內(nèi)心的體驗(yàn)和感受都是基于客觀發(fā)展?fàn)顩r所體現(xiàn)出來的,所以體驗(yàn)和感受的好壞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人的精神生活的客觀發(fā)展?fàn)顩r。因此,我們?cè)谶x取衡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指標(biāo)時(shí),要有一定的理論支撐和事實(shí)依據(jù),充分把握其主觀性和客觀性的特征,以客觀性指標(biāo)為主、主觀性指標(biāo)為輔,兩者相結(jié)合以此衡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發(fā)展程度和實(shí)際狀況,這樣才是較為科學(xué)合理、全面客觀的。
2.定性與定量相結(jié)合原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定的社會(huì)物質(zhì)生產(chǎn)方式反映的生存樣態(tài),是社會(huì)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相互作用的結(jié)果,是動(dòng)態(tài)的、發(fā)展的。在不同的社會(huì)制度下,由于社會(huì)主體的價(jià)值參照不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樣態(tài)也會(huì)有所不同。即使是在相同的社會(huì)制度下,其構(gòu)成因素也會(huì)有所差別,不僅呈現(xiàn)出量的差別,而且也會(huì)有質(zhì)的飛躍。有時(shí),我們可以使用具體的數(shù)字來表現(xiàn)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程度,例如一周(一月、一年)內(nèi)學(xué)習(xí)的時(shí)間比重、閑暇的時(shí)間數(shù)量等等。但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狀況并不是指具體準(zhǔn)確的數(shù)字,而是特指個(gè)人或社會(huì)精神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反映人們對(duì)積極健康價(jià)值觀的認(rèn)可程度和精神生活的層次高低。另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實(shí)現(xiàn)需要具備綜合性的條件,既包括主觀條件,又包括外界客觀條件。因此,我們?cè)诎盐掌湓u(píng)價(jià)指標(biāo)時(shí),要注意概括性和全面性相協(xié)調(diào),質(zhì)與量的統(tǒng)一。
3.簡潔性與操作性相結(jié)合原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全面性,它不是一種功利性的精神生活富裕,而是追求精神生活的完善,不僅求知、而且求善求美;不是局限于個(gè)體自我的精神生活感受,而是具有群體意識(shí)、民族意識(shí)、人類意識(shí);不是單一的精神生活類型,而是在科學(xué)和人文、邏輯和情感、計(jì)算和倫理的均衡中,享受精神生活的完美;也不是僅僅依靠個(gè)人的生活能力就能提高精神生活水平,而是還要有國家文化建設(shè)、社會(huì)精神生活產(chǎn)品等保障。然而,我們?cè)谶x取衡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指標(biāo)時(shí),必須把握簡明扼要、方便實(shí)用、可比性強(qiáng)、符合情理的原則,不能過多過細(xì),否則不但操作困難,而且還可能會(huì)操作失靈。因此,要盡量選取有代表性的、可信度高、容易獲取的、信息量大的國內(nèi)外通用指標(biāo),以反映某個(gè)地方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發(fā)展?fàn)顩r。另外,也要充分考慮到該指標(biāo)體系中各個(gè)指標(biāo)之間既要獨(dú)立體現(xiàn)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某一方面,又要相互聯(lián)系、全面綜合地反映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總體水平,在量化的過程中要易于理解、便于計(jì)算,最大限度地使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與實(shí)際情況相適應(yīng)、相吻合。
4.靜態(tài)性與動(dòng)態(tài)性相結(jié)合原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連續(xù)性、穩(wěn)定性,一旦形成后就會(huì)滲透到社會(huì)生活的各個(gè)方面,體現(xiàn)在社會(huì)個(gè)體的言談舉止中。同時(shí),當(dāng)一定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確立后,只要能夠滿足生產(chǎn)力在一定時(shí)期發(fā)展的需要,它就可以保持相對(duì)靜態(tài)的穩(wěn)定態(tài)勢,只是在這種生產(chǎn)關(guān)系所規(guī)定的區(qū)間內(nèi)或累積或減弱。也就是說,在某個(gè)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選取的靜態(tài)指標(biāo),能夠反映某個(gè)地方特定時(shí)期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程度。另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結(jié)構(gòu),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受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呈現(xiàn)出動(dòng)態(tài)發(fā)展的趨勢。在不同的時(shí)代、不同的發(fā)展階段,人們對(du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標(biāo)要求和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有著不同的理解。因此,我們?cè)跇?gòu)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時(shí),要具有一定的針對(duì)性和彈性空間,統(tǒng)籌考核歷史數(shù)據(jù)、現(xiàn)實(shí)數(shù)據(jù)和預(yù)期數(shù)據(jù)。
(二)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的具體構(gòu)建
與“物質(zhì)富裕”評(píng)價(jià)體系相對(duì)應(yīng),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評(píng)價(jià)體系涉及人的精神生活領(lǐng)域,主要傾向于對(duì)主體精神生活、精神需求有無和多寡的衡量。當(dāng)前,國內(nèi)部分學(xué)者基于中國情境對(duì)共同富裕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作了探討,但大多側(cè)重于物質(zhì)層面的指標(biāo)研究。不過,也有的學(xué)者提出可以用受教育程度、情感需要的滿足狀態(tài)、文化生活質(zhì)量、價(jià)值觀念取向、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24],社會(huì)保障能力、科教文衛(wèi)服務(wù)[25],文化建設(shè)、法治建設(shè)[26],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國民素質(zhì)、文化生產(chǎn)供給、公共文化服務(wù)、精神文化消費(fèi)[27]等具體指標(biāo)來測度人民精神生活富足的狀況,這為我們構(gòu)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提供了參考。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一個(gè)意義重大的價(jià)值體系,又是一個(gè)十分復(fù)雜的要素組合和實(shí)施過程。因此,我們?cè)跍y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程度時(shí),要從兩個(gè)維度進(jìn)行考量,具體而言:一是客觀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用于衡量人們擁有精神文化資源的富裕程度,主要包括社會(huì)總供給和人們實(shí)際能夠享有的程度;二是主觀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用于衡量人們內(nèi)在精神生活是否充實(shí)、精神境界是否更高,主要體現(xiàn)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質(zhì)量。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嘗試對(du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的架構(gòu)(圖1)及具體指標(biāo)結(jié)構(gòu)(表1)進(jìn)行初步探索。

圖1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的總體架構(gòu)

表1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的具體結(jié)構(gòu)

續(xù)表(表1)
(三)指標(biāo)模型應(yīng)用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具有描述功能、解釋功能、預(yù)警功能和決策功能。它不僅能深刻描繪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現(xiàn)有樣貌,而且能基于客觀測量對(du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設(shè)的狀況和水平進(jìn)行評(píng)估,同時(shí)也能夠進(jìn)行區(qū)域?qū)Ρ取⒚鞔_定位。具體來說,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可以應(yīng)用在如下方面:
一是能夠及時(shí)監(jiān)測各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建設(shè)狀況,不僅可以客觀分析比較縱向時(shí)間序列上的數(shù)據(jù)變化,以此反映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建設(shè)成效;而且可以客觀分析比較橫向全國范圍內(nèi)的數(shù)據(jù)變化,以此反映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總體變動(dòng)趨勢。總之,構(gòu)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的目的在于,讓它成為當(dāng)前和未來衡量、監(jiān)控我國人們精神生活發(fā)展?fàn)顩r的晴雨表。
二是通過常態(tài)化建設(sh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指標(biāo)數(shù)據(jù)庫,明確各指標(biāo)對(duì)應(yīng)的部門,改變定期報(bào)送的數(shù)據(jù)傳輸方式,打破各數(shù)源部門信息傳輸?shù)谋趬荆M(jìn)行部門間的數(shù)據(jù)共享,及時(shí)挖掘抓取相關(guān)指標(biāo)的數(shù)據(jù),實(shí)現(xiàn)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指標(biāo)的實(shí)時(shí)生成與完善。
三是通過客觀數(shù)據(jù)的分析,科學(xué)研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設(shè)的成效,精準(zhǔn)找出其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為地方政府的社會(huì)治理實(shí)踐提供準(zhǔn)確動(dòng)態(tài)的數(shù)據(jù)支撐,為地方政府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設(shè)中的統(tǒng)籌規(guī)劃、精準(zhǔn)施策提供科學(xué)有效的決策依據(jù),從而推動(dòng)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整體水平邁上新臺(tái)階。
四、結(jié)語
黨的二十大報(bào)告指出,“物質(zhì)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的根本要求”[1]。也就是說,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的本質(zhì)要求,也是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重要特征。因此,我們既要在物質(zhì)生活共同富裕上做文章,更要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上下工夫,把精神變成物質(zhì)、讓物質(zhì)升華精神,從而實(shí)現(xiàn)人民群眾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生活雙富裕的目標(biāo)。從實(shí)踐路徑來說,一是要以經(jīng)濟(jì)高質(zhì)量發(fā)展為重點(diǎn)鞏固物質(zhì)基礎(chǔ),包括堅(jiān)持改革創(chuàng)新、貫徹共享發(fā)展理念等,努力實(shí)現(xiàn)物質(zhì)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平衡發(fā)展。二是要加強(qiáng)頂層設(shè)計(jì),健全管理保障機(jī)制,堅(jiān)持黨的全面領(lǐng)導(dǎo),強(qiáng)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證;堅(jiān)持以人民為中心,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標(biāo)價(jià)值,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豐富精神食糧、培塑良好主體條件、營造有利環(huán)境空間。三是要以提供高質(zhì)量精神文化產(chǎn)品與服務(wù)為依托創(chuàng)建美好文化生活,包括完善文化基礎(chǔ)設(shè)施、創(chuàng)新公共文化服務(wù)方式、優(yōu)化公共文化服務(wù)結(jié)構(gòu)等,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四是要以加強(qiáng)宣傳教育為關(guān)鍵,激發(fā)內(nèi)在動(dòng)力,包括堅(jiān)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的指導(dǎo)地位,強(qiáng)化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引領(lǐng),加強(qiáng)教育扶貧,注重用社會(huì)主義先進(jìn)文化、革命文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培根鑄魂等,將全社會(huì)奮斗意志、必勝信心轉(zhuǎn)化為干事創(chuàng)業(yè)、促進(jìn)共同富裕的實(shí)際行動(dò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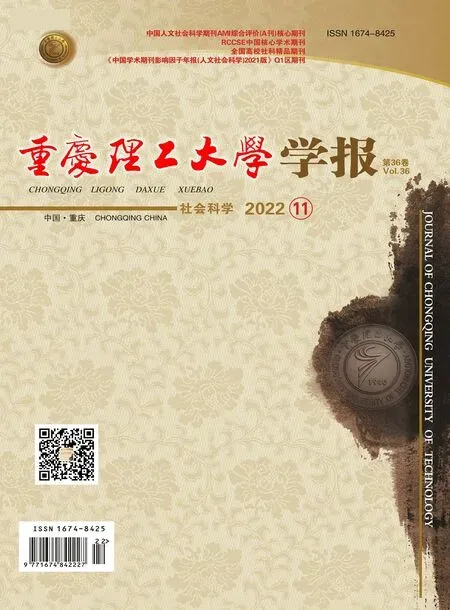 重慶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2022年11期
重慶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2022年11期
- 重慶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的其它文章
- 資本市場開放與審計(jì)投入
——基于“陸港通”的經(jīng)驗(yàn)證據(jù) - 成渝地區(qū)雙城經(jīng)濟(jì)圈農(nóng)業(yè)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時(shí)空特征及驅(qū)動(dòng)機(jī)制研究
- 環(huán)境規(guī)制異質(zhì)性、溢出效應(yīng)與我國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jí)
- 居民負(fù)債與綠色消費(fèi)
——以新能源汽車為例 - 中國城市老齡友好型社區(qū)建設(shè)狀況與優(yōu)化策略
- 多元利益衡量視閾下瀏覽器廣告屏蔽行為正當(dāng)性判定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