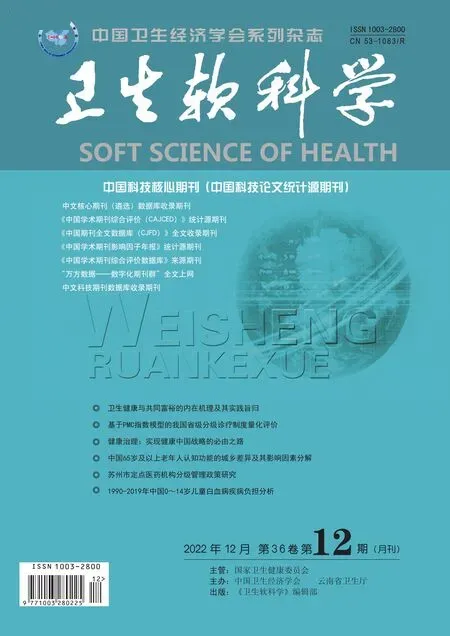基于PMC指數模型的我國省級分級診療制度量化評價
徐萍萍,趙 靜,李春曉,劉森元,李林峰
(北京中醫藥大學管理學院,北京 102488)
分級診療制度是化解“看病難,看病貴”這一社會普遍關注的民生問題的重要手段,是新一輪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主要抓手。2009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中首次提出健全醫療服務體系,逐步建立基層首診、分級診療、雙向轉診的就醫新格局。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中提出:“到2020年,分級診療服務能力全面提升,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的分級診療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建立符合國情的分級診療制度。明確各級醫療機構診療范圍及服務功能定位。”然而,分級診療政策執行至今,我國仍未形成科學合理的就醫格局[1],在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進程中,各方對分級診療制度的政策信心、建設思路以及操作方法,尚存優化空間[2]。
目前我國學者對分級診療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國外制度建設經驗與啟示[3]、民眾認知研究[4]、實施成效[5]、現狀分析[6]等,在政策評價角度較為缺失,有學者對政策效力與效果[7]、政策歷程、困境及建議[8]以及利用政策工具對政策內容[9]進行了分析,但沒有學者利用研究工具聚焦到具體政策層面對各份政策進行定量評價。本文基于PMC(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指數模型,對省級層面出臺的28份關于分級診療的政策進行逐一評價,以定量研究的方法客觀分析政策優劣,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促進我國分級診療制度進一步有效高質量發展的對策和措施,助力健康中國戰略建設。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北大法寶數據庫為主要檢索平臺,以“分級診療”為檢索詞進行標題檢索,選取地方層面文件,為避免遺漏,輔以地方政府網站進行檢索,得到127份標題中含有“分級診療”的政策。按照以下標準進行背對背人工篩選:一是發文機關為省級層面;二是為本省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通知、意見、規劃等正式規范的政策文件;三是政策時效為現行有效狀態,按照以上標準全文閱讀后,每省選取一項最具有代表性的政策進行分析,其中寧夏回族自治區未出臺省級層面的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相關政策,江蘇省與西藏自治區的省級政策未公開,因此最終選定28份省級分級診療政策,覆蓋除以上3個省份及港澳臺的28個省(區、市),政策目錄見表1。
將28份政策文本導入ROSTCM 6.0軟件進行文本挖掘,首先去除無意義詞后提取出相關的高頻詞,頻數前10位的詞為“醫療”“醫院”“分級診療”“醫療機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慢性”“資源”“制度”“基層”“醫保”,然后將高頻詞形成社會網絡圖。高頻詞表及社會網絡圖是本文變量分類參數確認的主要依據。
1.2 研究工具與方法
PMC(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指數模型是Ruiz[10]等基于Omnia Mobilis假說提出的。認為一切事物都是動態的、相互關聯的,應當盡量注意各個相關變量的作用,因此二級變量的數目不受限制,并具有相同的權重。PMC指數能夠從多個角度對政策的異質性和優劣進行多維度的分析,同時也能通過曲面圖直觀地顯示出政策各個方面的優缺點,從而對政策進行科學的定量評估[11]。

表1 部分省級分級診療政策文件
1.2.1 變量分類及參數確認
本研究依據社會網絡圖譜的情況,綜合Mario Ruiz Estrada的變量設計方法[12]及已有學者的研究結果,構建分級診療政策PMC模型,見表2。包含10個一級變量和39個二級變量,同時設置每個二級變量的權重相同。

表2 分級診療政策量化評價變量設置表
1.2.2 PMC指數計算
根據PMC指數的計算方法[17],首先根據公式(1)和公式(2)對39個二級變量進行賦值。其次再根據公式(3)計算10個一級變量的得分,一級變量的分值為二級變量總分與二級變量數目的比值。最后根據公式(4)計算分級診療政策的PMC指數值,即加總各政策所有一級變量的得分,因此PMC指數得分的取值范圍為[0-10]。其中i表示一級變量,j表示二級變量,m表示一級變量的個數,n(Xij) 表示某一級變量下的二級變量個數。
X~N[0,1]
公式(1)
X~{PR∶[0,1]}
公式(2)
公式(3)
公式(4)
根據Estrada[12]的評價標準,將政策具體劃分為以下4個等級:0~4.99分為不良政策,5~6.99分為可接受政策,7~8.99分為優秀政策,9~10分為完美政策。
1.2.3 PMC曲面構建
PMC曲面圖可以直觀清晰的展示某項政策內部的各維度情況從而分析其優劣。由于本研究中均為公開發布的政策,因此在構建矩陣時為了保證矩陣均衡性,不考慮一級指標X10的得分情況,建立如公式(5)所示的矩陣表,從而繪制某項具體政策的PMC曲面圖。

(公式5)
2 結果
計算各份政策的PMC指數得分,并依據評價標準對各項政策進行等級排序和分析,見表3。

表3 各份政策的PMC指數得分
2.1 分級診療政策整體評價
從PMC指數得分及政策等級來看,28份政策得分均在4.72分及以上,排名為P1>P3=P8=P11=P16=P20=P26=P28>P6=P13=P17=P19=P22>P18>P4=P14=P23=P27>P10>P5>P12=P21>P7=P9>P15>P24>P2>P25。28份政策的PMC得分均值為6.08,屬于可接受范圍。本研究所選取的政策中P1為優秀等級,P2和P25政策為不良等級,其他政策為可接受等級。說明政策內容的覆蓋面較為廣泛,政策較成熟,制定政策這一環節絕大部分達到了可接受及以上等級。
從政策評價一級變量的平均得分來看,X1政策性質得分均值為0.75,所有政策均涉及到了建議、描述和引導,但預測性質缺失,部分政策涉及監督性質。X2政策時效得分均值為0.25,在一級變量中得分最低,大多數政策為中期發展規劃,其他政策為長期和短期發展規劃,未涉及到當年發展規劃。X3政策目標得分均值為0.75,基本全部政策在基層首診和雙向轉診等方面提出了較為具體的發展目標,在急慢分治和上下聯動方面略有欠缺。X4政策內容得分均值為0.97,除X10政策公開變量外在一級變量中得分最高,說明各項政策的內容覆蓋基本全面,對分級診療制度的內容做出了明確的要求與規劃。X5政策領域得分均值為0.51,各份政策基本都涉及到了社會和科技領域,僅1份政策涉及政治領域,經濟領域未涉及。X6激勵方式得分均值為0.40,在一級變量中得分較低,基本涵蓋了人才培養、政策支持兩種激勵方式,在財政補貼、法律保障和土地供應方面有缺失。X7政策工具得分均值為0.35,在一級變量中得分較低,各份政策都涉及到了環境型政策工具,供給型政策工具使用較少,需求型政策工具沒有被使用;X8作用方式得分均值為0.44,在一級變量中得分較低,基本使用了強制型的作用方式,其次是激勵型作用方式,沒有使用市場型和服務型的作用方式;X9政策評價得分均值為0.67,各份政策都做到了目標明確和內容詳實,部分做到了權責清晰;X10政策公開得分均值為1,所選取的政策均為公開發布。
2.2 分級診療政策具體評價
由于本研究樣本數量較大,所以選取排名第一的P1、排名中等的P18和排名末位的P25 3份政策,根據量化評價結果及PMC曲面圖進行具體分析。
P1政策量化評價結果為7.07分,排名第1位,等級為優秀,PMC曲面圖見圖1。P1政策性質涉及到監管、建議、描述和引導;時效為中期,政策目標涉及了基層首診、雙向轉診和急慢分治;政策內容覆蓋全面,政策領域涉及了社會、政治和科技;激勵方式有人才培養、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使用了環境型和供給型的政策工具,強制型和激勵型的作用方式;認為該政策目標明確、內容詳實和權責清晰。

圖1 P1政策的PMC曲面圖
P18政策量化評價結果為6.08分,排名14位,等級為可接受,PMC曲面圖見圖2。P18政策性質涉及到建議、描述和引導;時效為中期,政策目標涉及了基層首診、雙向轉診和急慢分治;政策內容覆蓋全面,政策領域涉及了社會和科技;激勵方式有人才培養和政策支持;使用了環境型政策工具,強制型和激勵型的作用方式;認為該政策目標明確、內容詳實和權責清晰。

圖2 P18政策的PMC曲面圖
P25政策量化評價結果為4.72分,排名末位,等級為不良,PMC曲面圖見圖3。P25政策性質涉及到建議、描述和引導;時效為中期,政策目標涉及了基層首診和雙向轉診;政策內容未涉及建立基層簽約服務制度,其他均涉及;政策領域涉及了社會和科技;激勵方式僅涉及政策支持;使用了環境型政策工具以及強制型作用方式;認為該政策做到了目標明確。

圖3 P25政策的PMC曲面圖
通過PMC曲面圖和對3項政策各維度的橫向對比分析可知:P1政策PMC曲面圖起伏不大,各維度得分均處于較高水平,其優勢在于通過法律保障的激勵方式,引導和加強基層衛生治理工作。P18政策PMC曲面圖起伏較大,各維度得分的水平不均衡,處于中庸位置。P25政策PMC曲面圖起伏不大,各維度得分均處于較低水平,劣勢在于政策目標不全面,激勵方式和作用方式單一。
3 討論
3.1 發揮多種作用方式與政策工具的效能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目前我國省級分級診療政策所采用的政策工具主要是環境型,作用方式集中在強制型和激勵型,缺乏需求型及供給型政策工具與服務型及市場型作用方式的使用。主要原因在于分級診療政策為政府主導推進建設,社會力量參與度小,造成政策工具和作用方式使用單一,后續執行效果不如預期。一方面,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動作用能與供給型政策工具的推動作用、環境型政策工具的影響作用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政策的有效執行,合理均衡使用這三種政策工具可以作為達成政策目標,實現政府的有效治理的有效抓手。建議通過全面推行基層首診制度等強制措施形成需求,拉動分級診療制度階段性目標的實現,逐漸形成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的局面。另一方面,當前作用方式結構性失調,忽略服務型與市場型的作用,影響政策發揮效果。建議應積極探索服務型與市場型在分級診療制度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與其他作用方式形成耦合力量,如將民營醫院納入分級診療體系中,利用市場型作用方式,豐富分級診療內涵,擴寬民眾的選擇。
3.2 豐富激勵方式形式,提高醫務人員積極性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當前我國省級分級診療制度的激勵方式集中于人才培養和政策支持方面,在財政補貼、法律保障和土地供應方面非常缺失。主要原因在于配套措施尚不完善,政府財政壓力較大,激勵的覆蓋面和層次不足,方式單一,造成制度建設各方主體的積極性下降。首先,建議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或規章制度,一方面能為政策的執行提供強有力保障,明確利益相關者各方的權利與義務,起到監督與約束作用,完善規范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為醫務人員的法律責任做出界定,有利于規避一定程度的風險,解除其后顧之憂,激勵其投入到工作中去。其次,在人才激勵方面,建議引進優秀人才到基層醫療機構,提供培訓與進修機會,在職稱評定與職級晉升方面進行適當的調整,拓寬其職業發展道路與前景[5];對現行考核方式與體系進行適當調整,讓工作回歸到醫療本身。最后,在完善相關配套政策方面,建議加大財政補償力度,提高基層醫療服務能力;推進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吸引患者到基層就醫;加強信息化建設,促進信息互聯互通。
3.3 有機結合政策長期、中期和短期目標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目前我國省級分級診療制度的時效主要為中期和短期規劃,缺少長期與當年的規劃與指導,未能有機結合長、中、短期目標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分級診療政策前瞻性功能的發揮[18]。自2015年明確提出建設分級診療制度的的目標模式后,當前分級診療在實施過程中仍存在著醫療資源分布不合理、醫院系統功能越位、雙向轉診渠道不暢通、醫保引導力度不夠等問題[19]。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合理適度的調整政策目標與時效,而其是實現政策預期效果的前提基礎。因此建議,未來應將分級診療政策長期、中期和短期目標進行有機結合、科學規劃。一方面,制定明確的長期目標,在按照“近細遠粗”的原則制定一段時間的計劃,按照計劃實施的效果和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對今后的計劃進行調整和修改,將短期、中期和長期計劃相結合,及時根據環境變化做出調整。另一方面,應注重政策目標的完成度,監測政策實行與既定目標的偏離程度,加強監督與考核評價,及時修正偏差,保證既定總目標的高效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