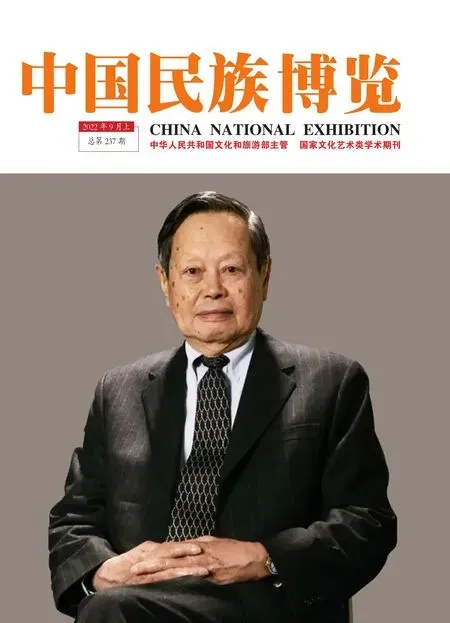以文化社會學視角看《中國繪畫變遷史綱》的敘述結構
石 菲
(南京師范大學,江蘇 南京 210023)
一、 《史綱》的敘述分期
繪畫史的分期是繪畫史撰寫前必須解決的技術性問題,是繪畫史的敘述結構最直接的體現。在《史綱》的開篇部分,傅抱石從美術教材的教學功能以及現代形態繪畫史寫作的角度出發,提出“中國繪畫有沒有斷代的可能?記賬式和提綱式,哪種另讀者易得整個的系統?”并答道,“斷代的太破碎了!記賬式的太死氣!”問答間體現了傅抱石試圖“打破機械歷史斷代的破碎史料羅列,找出中國繪畫發展的線索‘正途’的研究方法”。將其分為文字畫與初期繪畫、佛教的影響、唐代的朝野、畫院的勢力及其影響、南宗的全盛時代、有清二百七十年六個部分。從分期節點的選擇看來,這種分期方式帶有明顯的藝術社會學研究的特點,傅抱石對復雜的社會因素加以提煉,將佛教的傳入以及政治對繪畫發展的影響作為分期依據。究其緣由,或與20世紀20年代藝術社會學在中國廣泛傳播有關,當時國內相繼出版了丹納、盧那察爾斯基、弗里契、居友等人的藝術社會學論著,這與《史綱》的創作時間是相互契合的。
(一)以社會文化因素——佛教的傳入為分期依據
傅抱石將文化因素,尤其是外來的佛教藝術視為對六朝畫風形成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以佛教的傳入為界確立了“佛教影響”“中原繪畫的產生與發展”兩個章節。傅抱石認為中國在接受佛教、模仿佛畫與佛塑創作的過程中,中國繪畫從原有的“趨于線條變化的追求”的基礎上“穎悟了暈染的方法,和背景的運用”。因此,“這時的畫法,與周、秦、漢不同。是含有印度風味,而趨向便化的裝飾。后來慢慢擴充而滲入民眾的嗜好,成了極堅固的壁壘。如衣服摺紋,及肩背的弧度,線與線的聯合和展布,邊緣所綴菱花麻葉的模樣,都充量容有特殊的格調!”傅抱石采用“夾敘夾議”的敘述方式交代佛教的傳入對繪畫風格形式產生的影響,然后以畫家傳記為主體整理魏晉六朝時期的繪畫,所涉史料包括《貞觀公私畫史》記載的四十七處佛畫名跡,包含寺名、作者、寺址,魏晉南北朝時期畫家的繪畫作品、繪畫理論以及繪畫相關的奇聞異事。
傅抱石并非是將佛教的傳入作為繪畫史階段性分期依據的第一人,1887年法國學者巴遼洛(M.Paleologue)在《中國美術中》將中國繪畫史分為七個部分,第一、第二部分“自繪畫起源至佛教輸入時代”“自佛教輸入時代至晚唐”即是以佛教對中國繪畫的影響為分期依據。德國學者希爾德(Hirth)亦將佛教的傳入對中國繪畫的影響考慮進繪畫史的分期中,將繪畫史分為不受外來影響獨自發展時代、西域畫風侵入時代、佛教輸入時代。很顯然,上述分期方式是立足于民族交流過程對本民族繪畫風格造成的影響。相較上述兩位外國學者,傅抱石除了關注外來佛教文化對繪畫的影響之外還關注魏晉玄學對繪畫的形式與風格影響。
“然天才的暴露,有相當環境是增加力量的。固然是需要所有印象做自己的依歸,而‘骨法’的美備,也需要更切的參考。”
“骨法”為南陳謝赫提出的最早的關于繪畫實踐與品評具體標準——“六法”的第二法“骨法用筆”。六法的影響力并未隨著時光的流逝而褪去色彩,宋代美術史家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指出: “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至今仍是品評國畫的主要標準。“骨法 ”這一概念的提出與盛行與六朝時期的玄學關系緊密,謝赫將人物品藻中的常用概念借以品評人物畫,流行于南朝時期的“秀骨清相”的人物畫風格不能說與當時提倡玄學的社會風氣沒有關聯。可見,佛教與玄學在六朝時期同樣對繪畫的發展產生了影響,傅抱石卻選擇將佛教的影響作為分期依據,除了傅抱石在書中提到的“但影響最大的,還是佛教的輸入”以外,恐怕還與這一時期傅抱石審視中國繪畫史的“民族國家”觀念有關。這種分期方式被張學峰歸類為“民族學分期模式”,認為“民族學模式關注起源與盛衰,并在邏輯上與進化論較近,吻合中國學者對民族文化和社會進化變革的期待。它提供了一種中西繪畫的比較視域和旁觀者角色,容易讓人看到中國繪畫的基本特征和西方繪畫的優勢”。
(二)以政治因素——帝王貴族對繪畫的影響為分期依據
傅抱石在文中在引用了《家語》中的一段話論述了政治在繪畫發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家語》載:‘孔子觀乎明堂,睹四門擁有堯舜之容,桀紂之相,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但人類的進化,歷史自然非常幽遠,變遷也漸而不覺突然。當文智不太啟展,一切政教憲章,只求其備,遑論‘美’‘善’!某種東西,他直接或間接若能輔助政教之一部,它的發展必然迅速。姑認它的結果,它將來的結果和‘輔助’差得不可以道里計,而這段過程,藝術也是必經之途……因此,孔子觀乎明堂的故事,也就大足驚人,煞是可觀;然不能說不是中國繪畫發達的原因內強有力的原因了。”
首先從孔子的“游于藝”入手討論繪畫發展過程中的功能轉化,初為“補文字之不足”,后起到“鑒善勸惡”的教化功能,指出其中的某些繪畫因直接或間接“輔助政教之一部”得以迅速發展,在這一外部條件的支撐下,繪畫向著更深層次的“美”與“善”發展。除此之外,傅抱石在《唐朝的朝野》言:“若是帝王不歡喜這樣東西,這樣東西其倒霉無疑了。”又言,“民眾思維,實以帝王為樞紐而隨其輪回。有些盲從地不能辨別應當不應當,但完全為迎合大人公卿而借作進身之階者,占了全部的極多數。”政治在繪畫發展中產生的不容忽視的作用早在唐朝《歷代名畫記·敘畫之興廢》中,張彥遠就闡述得十分明了:“儻時君之不尚,則闕其搜訪,非至人之賞玩,則未辨妍蚩。”然而,兩者對這一繪畫史現象所持態度與觀點卻大不相同,張彥遠憑此觀點極力強調繪畫的教化功能,引起統治者對繪畫的重視以實現繪畫的繁榮,傅抱石則是極力強調統治者對繪畫風格的控制與壟斷,使繪畫失之真正獨立之精神價值。對同一現象的不同觀點源于傅抱石與張彥遠不同的思想觀念與價值取向,相較于張彥遠與王朝正統思想及價值取向的一致性,傅抱石則持有相對獨立的學術思想,站在繪畫本體發展的角度看待繪畫史的發展,表現在繪畫史的書寫上即為突破了以朝代更迭為分期節點的繪畫史分期,將文化、政治等社會因素作為繪畫本體風格演變的重要因素,并以此為分期依據。
二、 《中國繪畫變遷史綱》的敘述線索
(一)對“南北宗論”的再思考——“朝野對峙論”
繪畫史上的“南北宗論”是晚明董其昌、莫是龍、陳繼儒等人“為了掃蕩偽逸品、院體末流和浙派流弊”提出的有關山水畫的分類方式與品評標準,將禪宗的“南北宗論”借用到繪畫中,將自唐以來的繪畫分為南北二宗,視李思訓為“北宗之祖”,視王唯為“南宗之祖”。傅抱石以“南北宗論”為撰述基點,“突破了一些南北宗畫史研究者只注重不同宗派畫家歸屬的做法”,依據畫家的階層身份、畫理、畫法的層次對“南北宗論”做了更深層次的推進,并在繪畫題材、內容以及時間上做了延伸,將繪畫分為“在朝的”繪畫(北宗)和“在野的”繪畫(南宗)兩種不同類型。
首先,是對繪畫受眾階層身份的考量,在《唐代的朝野》一章的開頭部分,傅抱石提及三種身份的繪畫受眾群體:一為帝王貴族,為鞏固權勢地位將繪畫用于政教或以個人好惡影響控制繪畫的創作及品評標準;二為“性靈未泯的高人野士”,在繪畫中彰顯“性靈思理”;三為“人民”,其思維“以帝王為樞紐而隨其輪回”。上述分類暗含了政治因素在繪畫發展中起到的作用,為“朝”“野”的繪畫分類做了初步的鋪墊。再者是從畫理層面對“南北宗論”的深入探究。在畫理層面,傅抱石繼承了“南北宗論”的理論主張,歸結在朝(北宗)的繪畫特點歸納其特點為:“面目一律”“皆有所自鉤摹”“圖作客觀的描述”“缺少個性的顯示”,“在野的”(南宗)繪畫特點為:“境界高遠”“不落尋常窠臼”“充分表現個性”“主觀重于客觀”“有自我的表現”。
其次,傅抱石在傳統的“南北宗論”的畫理層面上增加了對政治因素的考量,先是引用宗炳的《畫山水序》以及王微的《論畫》,認為宗炳所提倡的“意求”“心取”是“做自我的主張”,王微“更進而說明繪畫的特有精神,脫盡‘畫教’的羈絆”。其間包含著的強烈的自我覺醒的意識,被傅抱石視為畫理上的進步。這種進步的第一效能“就是反對以繪畫做政治的副物。以為繪畫應當獨立存在,不能附有政治宗教及其他色彩。”此處可以看出,傅抱石主張繪畫應該獨立存在,考察繪畫是否獨立存在的標準為是否體現了創作者思想精神上的自主性,而影響繪畫獨立存在的主要因素為政治因素。這一主張成為“朝野論”的理論基礎,為“朝野論”提供了理論支撐。再者是在畫法層面的考察,歸結為“在野的”繪畫(南宗)“不專事技巧的講求”“注重水墨渲染”;“在朝的”繪畫(北宗)為“作家之畫,乃專心形似的工致”,“注重顏色骨法”。
最后,傅抱石在董其昌、莫是龍“南北宗論”已存系統上加了新的鏈條,將“南北宗論”擴大至花鳥畫,擴展了原來“南北宗論”所能涵蓋的繪畫史范圍。傅抱石談論山水畫家時,延續了董其昌的觀點,認為北宗“注意顏色骨法”和南宗“注重水墨渲染”;談論花鳥畫時,認為“黃筌好比李思訓,徐熙好比王摩詰”。徐黃之后的花鳥畫家,則分別歸入徐(熙)派和黃(筌)派,將花鳥畫在“南北宗論”中找到合適位置,在董其昌“南北宗論”的基礎上做了題材與內容上的延伸。傅抱石在“南北宗論”基礎上延伸而來的“朝野論”體現了他對自魏晉六朝至清代這一歷史階段繪畫史的重新理解與展示。
(二)“朝野對峙”線索對內容的組織方式——“主干+枝葉”
在線索對內容的組織方式上,傅抱石注重“史”與“論”之間的結合,在文人畫思想的指導下,篩選支持預設理論的史料結纂史實情節,“以論串史”設計敘述線索,以實現繪畫史的系統性書寫,闡述繪畫史的發展規律。“主干”,指的是“歷史事件的動態演進”。傅抱石在《史綱》中明確了“提倡南宗”的主張,在文人畫精神的指導下確立了以“南北宗論”為基礎的“朝野論”,并以“朝野對峙”關系建構《史綱》的主干線索。用近四十種古代畫史畫論資料呈現了繪畫史動態演進過程中,縱向發生的重要歷史場景與歷史細節以及發生在不同時空同時又與主干產生橫向關聯的特定的歷史事件。縱橫相交的系統闡釋了“在朝的”與“在野的”繪畫的發生、發展、相互爭斗的演變歷程。值得一提的是,現今的研究一致認為《史綱》中的“朝野對峙”關系的起止時間為自唐朝至清朝,筆者認為這種對峙關系可延伸至魏晉六朝時期。我們以《史綱》自魏晉六朝至清朝的繪畫史發展線索為例,直觀地認識一下《史綱》“主干+枝葉”的敘述線索的構建。
在《史綱》敘述主干的構建上,文人畫理論擔任了重要的角色。傅抱石首先從宗炳與王微的山水畫理論入手,指出畫理產生了倡導“意求”“心取”“做自我的主張”的新主張,這一進步使繪畫開始擺脫對政治宗教的依附“獨立存在”。這一轉變促使了繪畫的分野,即“在朝的”繪畫與“在野的”繪畫二元對立的局面。傅抱石視東晉時期的顧愷之是調劑“朝”“野”的一員大將,唐朝的李思訓代表了朝廷的繪畫,王唯為在野繪畫的代表且占據了上風。繪畫發展至五代時期,以李思訓為代表的“在朝的”山水畫風中斷,“在野的”繪畫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荊浩、關仝的水墨山水畫成就斐然。五代時期花鳥畫領域形成了以黃荃的“黃家富貴”為代表的“在朝的”繪畫,成為此后“在朝的”繪畫的主要力量。與之相對峙的“在野的”花鳥畫派是以徐熙為代表的“徐家野逸”。北宋徽宗時期畫院的勢力達到高峰,以“黃家富貴”為代表的畫風占據畫壇主流。花鳥畫領域“在野的”繪畫受到“在朝的”繪畫的壓制,直到宋代中期以崔白為代表的畫家才打破了“皇家富貴”一統天下的局面。從山水畫領域來看,宋代時期只有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等少數畫家可“撐北宗的門面”,到了元代靠帝王苦心經營的院體畫壽終正寢。與之相對的“在野的”山水畫無論是人才數量、繪畫精品還是畫法畫學上都勝過“在野的”繪畫,獲得了勝利。明代時期,宮廷繪畫在帝王的支持下得以復興,明代中葉以后隨著皇權的衰微,院畫勢微,被蘇州地區“在野的”吳門畫派所取代,繼吳門畫派之后的是以董其昌為代表的“華亭派”。對清代畫壇的分析,傅抱石認為“有清二百七十年的繪畫,其勢力均屬于“南宗”,此處“南宗”的概念與“在野的”概念完全重合,因此直接以“南宗”稱之。上述即為《史綱》的敘事主干線索。
法國結構主義者羅蘭·巴特在《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中道:“理解一部敘述作品,不僅僅是弄懂故事的展開,也是辨別故事的‘層次’,把敘述‘線索’的橫向連接投射到一根垂直的暗軸上。”此處與橫向線索相垂直的暗軸即“在歷史事件動態的演進過程中,縱向生發出來的具體的歷史場景與歷史細節,也包括發生在不同時空同時又與主干產生橫向關聯的特定的歷史事件”,即枝葉。如在構建唐代繪畫史時,在橫向的唐代朝野對峙關系的初現線索上縱向生發出了兩派代表畫家生平、家世背景、師承關系、作品風格以及個人的軼聞事跡,其中尤以吳道子與李思訓在明皇宮殿的墻上同畫嘉陵江兩岸山水在時間與畫風方面的對比最具戲劇性效果,增加了文本可讀性的同時,也突出了“在朝的”和“在野的”兩種畫派繪畫風格的差異性特征。傅抱石將中國古典小說中常用的草蛇灰線法這一敘述方法應用于繪畫史的寫作中,使各篇章內部以及篇章之間的連接流暢自然,開啟了一種將繪畫史“情節化”的寫作方法,在同時期的繪畫史著作中獨樹一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