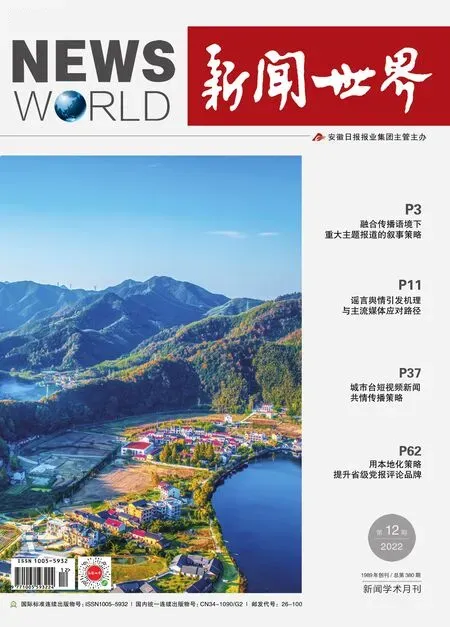從小舞臺到大銀幕:現代傳媒視域下戲曲文化的活態傳承
○王傳琪
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傳統文化與現代審美的融合碰撞頻繁,讓傳統文化恢復了生機與活力。近兩年,如粵劇電影《白蛇傳·情》《南越宮詞》、以越劇文化為最大亮點的《柳浪聞鶯》在口碑與市場推廣上均獲得了空前的好評。從小舞臺走向大銀幕,傳統戲曲似乎找到了發展的新方向,但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活態傳承,仍需要創作者們共同努力。
一、年輕化、青春化的戲曲電影
戲曲電影是中國民族戲曲與電影藝術相結合的片種。戲曲,融合了“唱、念、做、打”等表演形式,是深受歡迎的娛樂形式之一。古時的戲曲題材大多涉及人們喜聞樂見的家事或是與英雄人物和歷史事件相關,多宣揚封建倫理道德觀念,與當下受眾的思想觀念脫節。另外,戲曲的唱腔等形式也與當代的審美觀念有隔閡,動輒數小時的完本演出也不符合當下人們的文化消費習慣。而如《白蛇傳·情》一類的戲曲電影,則順應了當下年輕人的審美觀念,無論是有新美學風格的視聽語言,還是電影中的戲曲表演形式,或是電影敘事手法,都是在傳統戲曲的“唱、念、做、打”與故事情節基礎上作了改編,用當下年輕人眼中的“美”去解構傳統故事,重新編碼了戲曲的藝術表達方式。
戲曲反映著中華民族的含蓄的審美心理,無論是越劇的“寫實風格”,還是昆曲的“寫意風”,抑或是戲曲電影中頻頻出現的科技樣貌,戲曲人總是在虛實結合中,尋求“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以情訴情、以景塑人”的境界。以往單純對戲曲舞臺進行拍攝的紀錄片式的戲曲電影,只能滿足老戲迷的需求,而流行的實景拍攝方式不僅耗時耗力,也會與戲曲中細膩又顯得浮夸的肢體動作產生違和感。
戲劇電影《白蛇傳·情》的導演張險峰決定“用西方的電影技術,來建立東方文化的美學體系”。《白蛇傳·情》以精彩的特效搭建了一個宋代宮廷工筆畫風格的煙雨江南,給觀眾以古風之奇幻體驗。這種“眼到處皆是景,各異景映不同情”的“國風新美學”手法,用抽象化、符號化的布景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之絕美,也襯托了《白蛇傳·情》的“一切景語皆情語”。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對于動畫場景設計和游戲美術設計風格元素的借鑒,并不是一味照搬,而是依據戲曲表演的場景需要有針對性地進行提煉創作。如電影中的昆侖山與金山寺一段,遠近的夢幻對比,讓年輕觀眾有進入修仙游戲般的代入之感,也讓人們聚焦于演員的唱詞與動作。這些現代電影技術的背后,是制作團隊運用的堪比動畫電影設計的分鏡圖數量與細節。
《白蛇傳·情》成為年輕群體中的“爆款”,豆瓣8.0 的評分也離不開新的戲曲電影沉浸表演方式。“戲曲者,謂以歌舞演故事也。”[1]在以往的劇院演出中,戲曲演員為了讓后排觀眾能感同身受,達到互動效果,常會將“歌舞表演”夸張化,并且多采用“明星”唱法,而粵劇作為少有的將實用性武術融入各個行當的劇種,對于演員“四功五法”的要求較為嚴苛。將舞臺戲曲表演搬上大銀幕,伴隨觀演方式的變化,觀眾的審美需求也會發生改變。同時由于電影的獨有美學特征,它更注重演員的細節表達。以往在傳統舞臺演出時常會被觀眾忽略的眼神、臉部等細微表情動作,在電影剪輯的配合下將被多次放大。“戲曲電影首先要忠實于演員的表演、唱腔、對白、身段、包括演員的功法,既不能損害它,又要忠實地呈現表演藝術。”[2]《白蛇傳·情》的戲曲表演不僅保留了戲曲藝術的本真,更襯托出人物角色的特點。以粵劇的招牌動作表演為例,舞臺版的白素貞在“水漫金山”一段中,與十八羅漢打斗以“水袖功”“踢出手”相互配合進行表演,其中“踢出手”雖然只有一瞬,但卻需要演員有極好的身體素質和爆發力,這也考驗演員的戲曲舞臺水平。但在戲曲電影中,導演去掉了“踢出手”這一電影中不夠突出的動作,單獨使用了多種翻花水袖技巧,配以慢鏡頭與“水漫金山”特效的展示,更顯得白素貞的法力高強和內心的堅定。“水袖”將山傾覆、法海“立杖定水”等緊密又不重復的細節,運用現代技術將觀眾對于戲曲動作的想象變為現實,這是之前的舞臺表演所不能達到的效果。再加上快速剪輯與美景的襯托,甚至讓其頗有東方暴力美學的視覺感受,延伸了戲曲電影的美學意味。
隨著文化強國建設的穩步推進,當下的影片也越來越多從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柳浪聞鶯》就融合了越劇文化、扇藝文化等傳統文化元素,以著名唱段“梁祝”為敘事母本,講述了上世紀末國有劇團變遷中一對姐妹花和畫扇師關于愛情與人生的故事。影片雖不是傳統的戲曲電影,但全片因戲而起,因戲而落,長達二十分鐘的越劇唱段也成為了最出彩的段落。這種以戲曲文化為重要敘事題材的電影創作,為傳統戲曲增添了新的表達方式。不斷有年輕演員加入到有戲曲元素的電影中,更使得戲曲文化在大銀幕市場“出圈”。
“思想性與藝術性是衡量戲曲劇目優秀與否的重要準則,而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融合甚至相互轉化則是戲曲藝術獲得較高審美價值的必要條件。”[3]對于《白蛇傳·情》來說,電影表現形式上的創新不是單一的,而是與現代精神主題相輔相成的。主創人員將白素貞對于自我的執著追求與掙扎充分外化成了可聽可看的戲劇語言,給予觀眾超越時空的觀影體驗。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所塑造的敢愛敢恨,不畏強權,積極爭取的大女主形象也順應了當今“女主熱”的創作潮流。[4]同時,影片不過分追求電影的好萊塢“救貓咪”式的敘事手法,而遵循中國傳統戲劇的回目結構,即采用折子戲般的段落式作為影片結構,讓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都能更快理解故事。
影片《柳浪聞鶯》改編自茅盾文學獎得主王旭烽的中篇合集《愛情西湖》,它細膩傳神地刻畫了畫家工欲善、越劇女小生垂髫和花旦銀心這三個各具個性的小人物,以及大時代下三人命運的糾葛與變遷。垂髫是一個戲癡,演的“梁山伯”人人叫好;銀心表面單純內心卻頗為鉆營,但與垂髫一直同窗長大在這個越劇劇團,雖只有個“祝英臺”的丫頭名,卻是獨屬于垂髫戲中女扮男裝的“祝英臺”。而越劇逐漸落寞,劇團因市場化運作不善被迫解散,工欲善的加入使得這對“梁祝”的人生更加縹緲。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無疑是最為知名的戲曲之一,戲曲中“十八相送”的經典片段在全國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而“梁祝”故事在千百年的歷史中通過多種媒介的傳播,已成為傳統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元素,也是民族情感共同體的符號之一。
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的通本注重描述二人感天動地、生死相依的愛情,從愛情電影的敘事角度來說未免有些單薄,階級與性別上的缺陷也會讓一些年齡偏小的觀眾難有代入之情。《柳浪聞鶯》成功地選取了文化母題中的核心情感共同體來進行人物關系的建構與人物情感的表達,多次以“梁祝”唱詞代以日常對白,如工欲善質問因事故變盲不再演戲的垂髫為何不辭而別時,曾經在臺上玉樹臨風的“梁山伯”,在盲人按摩店里悠悠唱起了“想山伯無兄又無弟,亦無妹也無姐,有緣千里來相會,得遇仁兄心歡喜”。全片以戲中戲的橋段,升華了傳統戲曲的敘事結構,更借伶人的離合之情抒發越劇的興衰之感。在兩個女性人物在舞臺上下性別轉換的過程中,影片借工欲善之口提出了越劇女小生“第三性”的概念。在戲曲文化中,越劇女小生是行當中獨特的存在,“他”不似古代的嬌弱女子,也更不是同學三年仍辨不出形影不離的同學性別的男人,“他”是女性想象中的男性,擁有幻想中的一切美好。《柳浪聞鶯》作為一部借用戲曲探討時代與性別的電影,能如此深刻地為戲曲行當以及傳統“梁祝”故事的文本帶來具有時代性與創新性的解讀并進行正面傳播,是難能可貴的。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戲曲+”建設
美國馬薩諸塞州理工大學的伊契爾·索勒·普爾教授在上世紀最早提出了“媒介融合”的概念,他認為媒介融合必將經歷組織融合、資本融合、傳播手段融合、媒介形態融合這四大階段。學界也普遍認為后期的融合就是文化融合。可以說,融合是當今傳媒藝術發展的重要特征和傳媒藝術生態格局變化的重要背景,主要體現在技術融合、媒介融合和平臺融合三個層面。[5]在短視頻等便攜的大眾娛樂方式的裹挾下,傳統的戲曲電影面臨種種困境。陳舊的藝術表達尚且可以通過跨媒介敘事與科技技術的引入來革新,盡管這對于部分創作者來說是極其艱難的。如中國戲曲學院副教授黃迎所說:“戲曲電影的被邊緣化,是時代進步的必然結果。面對這種時代必然,我們更應該去著力開掘戲曲電影在歷史變遷中不變的東西。”[6]媒體融合背景下,傳統文化傳承需要全媒體傳播和全行業的支持,需要大家一起打開新思路,才能真正讓戲曲電影綻放新生,做到戲曲文化在新時代的活態傳承。
值得借鑒的是,《白蛇傳·情》探索了戲曲跨平臺傳播繼而實現破圈效果的可能性。電影預告片一經播放后,便登上B站等平臺的熱搜榜,“驚艷”“美爆了”等溢美之詞瘋狂刷屏,網友紛紛要求增加排片,并在多個媒體平臺進行“自來水”似的“打CALL”。截至2022年8月,電影豆瓣評分高達9.0,且一直呈穩定高分;更有許多人表示,因為這部電影對粵劇和廣東充滿了向往。2021年,《白蛇傳·情》第一輪放映時,不到20天便打破戲曲電影《李三娘》的票房紀錄,成為中國影史戲曲類電影票房冠軍,加上2022 年5 月的第二輪放映,現已總計2700 萬元票房。根據貓眼專業版數據,《白蛇傳·情》29 歲以下的觀眾占比65%,35歲以下占比更高達80.7%。[7]

如前文所述,《白蛇傳·情》在戲曲故事新編、戲曲電影形式結構上的創新,不僅契合國內年輕觀眾的審美需求,承擔了文化傳承的責任,更在多個國際電影節上獲得榮譽,入選第76 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第75 屆戛納國際電影節的展映環節,好評如潮,成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尤其是戲曲文化“走出去”的代表。
這一次的破圈與《百鳥朝鳳》有異曲同工之處,也源于戲曲電影創作者合理運用現代媒體的優勢。傳統戲曲難免有曲高和寡之嫌,單純“說教”和再現已不符合文藝作品的發展趨勢。困于老觀眾的“一畝三分地”,更不利于戲曲文化的活態傳承。應靈活選擇大眾社交娛樂平臺,利用媒介與平臺優勢進行聯動宣發,如短視頻話題、B站的二段創作、微博與豆瓣觀影群等。
這一點上,講述越劇文化的《柳浪聞鶯》深諳此道。對于大部分年輕人來說,戲曲是長輩電臺中聽不懂的鄉音,但也是無法割舍的鄉愁。該片由鄭云龍等具有音樂、戲曲功底的年輕演員出演,在網絡營銷上更加青春化,以與越劇票友和演員對談為主要看點,結合時代變遷下戲曲生存空間的逼仄,影片吸引更多青年人由愛聽愛情和歷史故事轉而自發了解越劇文化。另外,積極搶占新媒體渠道,獲得觀眾及時的評論與意見反饋,也有利于促進作品質量和后續制作水平的提升。
長久以來,戲曲電影的制作多由政府財政撥款、公立電影制片廠主持,對國有院團的經典戲曲進行改編、拍攝。由此,題材和內容方面受到了很大的約束,同時資金的匱乏也導致很難進行科技化、產業化的電影拍攝。號稱首部4K全景聲粵劇電影的《白蛇傳·情》,基于梅花獎演員主演的劇目改編,保證了劇目質量,更積極引入社會募集資金,依靠更加純粹的市場機制,請來了大導演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深圳三地頂尖特效團隊共同完成,將中國的戲曲電影推動到“戲曲大片”時代,構建了良好的商業化循環機制。
近些年,江蘇、廣東等地的戲曲電影知名度和精品率逐漸提升,也打開了“戲曲+”的新概念、新思路。比如江蘇省演藝集團錫劇團整合全省戲曲資源,聯合南京電影制片廠建立起專業的戲曲電影攝影棚,孵化并拍攝了多個劇種的戲曲電影,加強不同類型的藝術融合。安徽再芬黃梅劇團積極利用短視頻等跨媒介平臺,吸引更多年輕觀眾了解戲曲文化,促進傳統戲曲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同時,戲曲電影的發展除了專業戲曲創作者的努力外,也離不開電影評論界和影迷的參與與反饋。上海國際電影節、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等國內重要節展紛紛開設戲曲電影論壇,以多重視角探討在新時代的媒介傳播環境中戲曲電影的創作、傳播發展的跨媒介新路徑。
從小舞臺到大銀幕,戲曲電影不斷涌現的“出圈”作品為傳統文化的活態傳承打開了新方向。創作者應積極響應促進民族文化復興的號召,利用更多的媒介渠道進行現實且青春化的表達。而伴隨著電影產業化水平提升、市場的蓬勃發展,戲曲電影也將呈現出更旺盛的生命力。
注釋:
[1]王國維.宋元戲曲史[M].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10.
[2]顧春芳.意象生成——戲劇和電影的意象世界[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300.
[3]馮冬.從小劇場戲曲《玉天仙》看黃梅戲藝術的當代探索[J].中國戲劇,2020(03):62-64.
[4]《白蛇傳·情》:新式戲曲電影的成功還是試錯?[EB/OL](2021-05-30)[2022-08-31].https://mp.weixin.qq.com/s/DoeEHrOMqHHm_4oCVEIsqg
[5]胡智鋒,陳寅.融合背景下傳媒藝術生態格局之變[J].社會科學戰線,2021(04):173-179.
[6]黃迎.當代戲曲影視導演創作漫談[J].電影文學,2021(01):114-116.
[7]羊城晚報.《白蛇傳·情》重映倒計時 唯美粵劇再傳情[EB/OL].(2022-05-17)[2022-09-0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3032602174929247&wfr=spider&f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