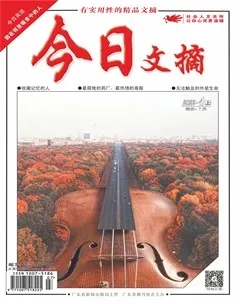豬血豆腐

黑暗里,所有的聲音都被放大,每一個聲響都驚心動魄。
我不敢起床。母親說,小孩子看了殺豬,念不好書。
多年后,我終于見識了殺豬的場面,知道了豬血豆腐的來歷。
幾個身強力壯的男子,哼哈哼哈地把大肥豬抬到四尺長、二十公分寬的長凳上斜放好。母親事先準備了一個可裝近二十斤水的大缽頭,放進一把鹽。這個缽頭,坊間叫豬缽頭。
只見刀光一閃,尺把長的尖刀已經進入豬的下脖。殺豬佬用腳把豬缽頭往豬脖下一放,刀一撥,鮮血濺,帶著熱氣的豬血如注而下,準確地進了豬缽頭的肚子。
殺豬佬胖乎乎的,說出的每句話似乎都淌著油。但他有殺豬的手藝,主人家都敬著他。豬血豆腐能不能做好,殺豬佬沖入的水量是一個關鍵因素。看起來他舀水很隨意,多年的經驗讓他有斤兩有底氣。
加了鹽的鮮豬血,很快就呈現結凍的樣子。母親將大鍋的水燒開,用尖刀在豬缽頭里劃“井”字,凝固的豬血被劃成方方的一塊塊,倒入大鍋。母親將稻稈或者麥稈折成一圈,慢慢地添進土灶。若用硬柴燒,就容易火力過猛。倘若燒豬血時熱水溢出了鍋,那一鍋的豬血豆腐就幾乎毀了。
在以往的農家,殺豬是一年里的大事。鄰里之間你幫我我幫你,你送我一碗,我回你一碗,這種點滴流淌的禮尚往來,豬血豆腐是主角。要用稻稈文火煮,煮到一定的時候,就不再續柴。用母親的話說,叫養。養熟的豬血豆腐嫩滑如玉,柔和的紫紅流淌著生活的溫度。
把一塊厚滑的豬血豆腐裝進盤子,鄭重地端起往鄰家走。一連端上幾趟,每一趟都能收獲樸素的贊美和感謝。鄰家小孩把彈珠揣進衣兜,麻雀一樣蹦來蹦去,或者小尾巴一樣跟著家人走來走去。
這天中午,必定有一個菜是咸菜滾豬血豆腐。那年頭,豬肉是賣給殺豬佬的,家里每個角落都等著花錢,哪里舍得自己吃呢?只有豬血豆腐,送了人后,總要留下一兩塊。咸菜是母親自己腌的,它和豬血豆腐的組合,和諧而簡單。那份低調的氣場就像門口的石板路,給人踏踏實實的感受。熱氣騰騰的咸菜豬血豆腐,把孩子們的目光像小貓的尾巴梢一樣纏繞在一起。夾一塊放進嘴里,滑嫩的豬血豆腐哧溜一聲竄了下去,沉睡的味蕾倏然活躍起來。
前幾天,我在一個攤位的角落見到了豬血豆腐。它們安靜地待在塑料大盆里。風淡淡的,陽光也淡淡的,豬血豆腐的目光也是淡淡的。我接過排骨,賣肉的喊:“豬血豆腐是白送的,喜歡的隨便拿。”
往事嘩啦啦涌到面前,我的心莫名地疼了一下,曾經盛裝出場的豬血豆腐,在幾十年后的今天,失去了江山和格局。
可我,總覺得它應該是有底氣的。豬血豆腐的胸中激蕩過風和雷,理應經得起熱鬧,也受得了沉靜。晚上,我燒了一個豬血豆腐燉黃豆芽,清爽可口,讓人胃口大開。我曬出的圖片,把一群煮夫和煮婦攪得蠢蠢欲動。
生活從來不是簡單的加和減,人生也從來不是簡單的高潮和低谷。豬血豆腐,不會因為某些冷落而消失。
(劉珊珊薦自《東陽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