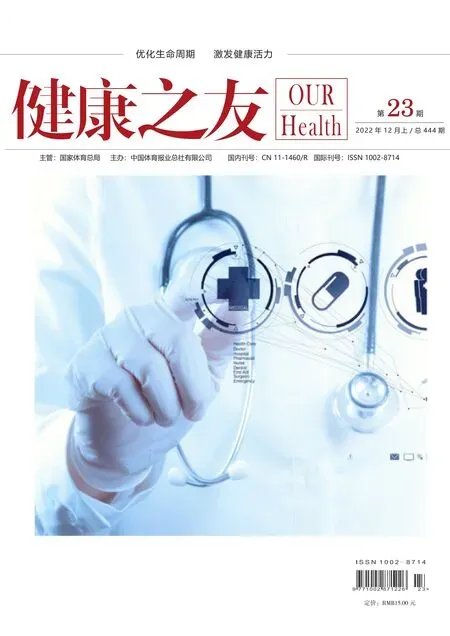青少年系統性硬化癥合并肺間質病變1例及文獻復習
夏 蓉 郭 潔
(蘇州大學附屬兒童醫院 江蘇 蘇州 215000)
系統性硬化癥(Systemic Sclerosis,SSc)是一種以組織纖維化為特征性表現的復雜多基因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平均發病年齡在35-50歲,女性多見,25歲之前發病少見,而兒童更為罕見。系統性硬化癥往往起病隱匿,臨床表現不典型,在臨床診療時容易被誤診、漏診及不正確的處理,影響患者預后。目前對于JSSc仍沒有統一的治療方案,處理方法存在較大差異。現報道1例我科收治的JSSc患兒,討論其臨床表現、診斷及治療,并進行相關文獻復習,總結該病的臨床特征、診斷、治療及預后,以提高臨床醫生對該病的認識,現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1.1患兒女,13歲10月,因“雙手足發涼三年余”于2018年10月12日入住我科。三年前,患兒出現雙手足發涼,伴雙手手指不能伸直,無疼痛、麻木、腫脹,無晨僵,無皮疹,無發熱,無肌肉酸痛,雙手指尖時有蒼白,無花紋,保暖或休息后手指科逐漸變紅,緩解后無不適,無出血,無破潰,無硬結,無蛻皮。近一年來,患兒雙手足發涼、雙手手指不能伸直癥狀較前加重。
該患兒患病以來精神可,飲食、睡眠可,體重無明顯變化,無發熱、咳嗽、嘔吐、腹痛腹瀉等不適癥狀。既往體健,否認“乙肝、結核、麻疹、水痘”等傳染病史及接觸史,無食物及藥物過敏史,無手術及重大外傷史,家族史無特殊。
入院查體:神志清,精神可,雙手指無法伸直,雙足拇外翻畸形,髖關節活動度輕度受限,四肢端皮膚顏色蒼白,無杵狀指及多指畸形,雙下肢無浮腫,無壓痛,雙肘、雙腕、雙膝關節無腫脹,脊柱無畸形,四肢末梢皮溫較低,全身未見皮疹、出血點,頸軟,無抵抗,雙肺呼吸音粗,無啰音,心律齊,心音有利,心前區可及3/6級收縮期雜音。腹軟,無壓痛及反跳痛。

圖1 JSSc患兒雙手指無法伸直,指端皮膚顏色蒼白;肺部高
輔助檢查:類風濕因子:陰性;自身抗體初篩:抗核抗體、抗Scl-70、抗著絲點抗體、抗PM-ScL、抗U1nRNP/Sm、抗Ro-52均陰性;ANCA:陰性;左手正位片:骨齡相當于14-15歲左右;雙足正側位:雙足諸骨密度減低;腰骶椎正位:未見明顯異常;胸部高分辨CT:兩下肺可見毛玻璃樣影;心臟彩超:二尖瓣輕度狹窄伴中度反流;三尖瓣中度反流;主動脈瓣輕度反流;食道鋇餐造影:上消化道造影未見明顯器質性病變;心血管CTA:未見明顯異常;頭顱MRI:左頂葉局部皮層絮片狀信號影;右手MRI:右手月骨信號異常。
JSSc最常見的臨床表現是雷諾現象、皮膚水腫和硬皮病,該患兒主要臨床表現有:肢端蒼白、發涼,雙手指伸直受限,雙足拇外翻畸形,右足2、3趾關節畸形、僵硬,髖關節活動度輕度受限,雷諾現象,心前區可聞及3/6級收縮期雜音。胸部高分辨CT:兩下肺可見毛玻璃樣影;心臟彩超:二尖瓣輕度狹窄伴中度反流;三尖瓣中度反流;主動脈瓣輕度反流。結合患兒臨床表現,可診斷為JSSc。
1.2治療方法 入院后予甲潑尼龍琥珀酸鈉40mg靜滴,1次/d,環磷酰胺 0.2g
1次,硝苯地平片5mg口服,3次/d,鹽酸貝那普利5mg口服,1次/d,右旋布
洛芬口服混懸液8ml口服,3次/d,白芍總苷膠囊0.3g口服,3次/d,積雪苷外
涂。治療10d,患兒雙手較前轉暖,握持有利,無活動困難。后定期行環磷酰
胺沖擊治療半年。
2 討論
以“Juvenile Systemic Sclerosis”為關鍵詞在PubMed進行搜索,以“青少年系統性硬化癥”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萬方、維普數據庫進行檢索,檢索2002-2018年國內外關于JSSc的病例報道。納入標準:所有經臨床確診的JSSc的病例報道。排除標準:報道的患者病史不全;在不同期刊或以不同形式重復報道的病例;對其他多家醫院的多例病例進行總結分析的文獻;因不能除外重復報道的情況且無法獲得詳細的臨床資料。共找到滿足條件的英文文獻2篇,收集病例4例,中文文獻2篇,收集病例2例,加上本文所報道的1例,共7例。見表1。

表1 JSSc患兒臨床資料和血清學特征
7例JSSc患兒年齡越大,發病率越高,女性發生率明顯高于男性,首發癥狀多為雷諾現象,實驗室檢查中抗核抗體多為陽性,少數患兒抗SCl-70可為陽性,食道功能障礙在JSSc患兒中多見,少數患兒可有肺纖維化及心臟損傷,腎臟損傷不常見。治療方法上,可口服或靜脈用激素,存在肺纖維化者可行環磷酰胺沖擊治療。
JSSc是一種罕見病,兒童該病的發生率是0.27/100萬[1],女性發生率高于男性,兩者之比大約為4:1[2]。一個大型的多中心回顧表明平均初發年齡是8.1歲[1]。系統性硬化癥(SSc)是一種血管疾病,表現為不同程度的皮膚及主要器官纖維化以及大、小血管病變[3]。
JSSc主要是根據其臨床表現、相關實驗室檢查來進行診斷,目前沒有明確的診斷標準。有研究表明,70%的JSSc患者以雷諾現象為首發表現,其中10%的患者可并發指尖潰瘍、壞死,第二常見癥狀是皮膚硬化;另外10%的患者在發病時可出現甲襞微循環的改變[2]。JSSc經典的特異性抗體如抗拓撲異構酶1(Type I topoisomerase,Scl-70)抗體、抗著絲點(anti-centromere,CENP)抗體、抗RNA聚合酶(anti-RNA polymerase,RNAP)抗體已經廣泛應用于其診斷分型和預后判斷中,但對于JSSc致病機制的研究仍在不斷拓展和深入。有研究表明,一些功能性抗體靶向于SSc重要致病環節,如抗血管緊張素Ⅱ-1型受體(Anti-angiotensin Ⅱ-1 receptor,AT1R)和內皮素1受體(Endothelin 1 receptor,ETAR)抗體,抗血小板源性生長因子受體(Anti-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PDGFR)抗體;而新發現的SSc自身抗體,如抗干擾素誘導基因16(anti-interferon inducible gene 16,IFI16)抗體、抗RuvBL1和RuvBL2抗體、抗真核起始因子-2B(anti-eukaryotic initiation factor 2B,eIF-2B)抗體,與SSc特定臨床表型相關,有望成為治療SSc的方向[4]。
SSc可導致多器官纖維化,而肺間質病變是其最嚴重的并發癥。肺部受累是JSSc患兒死亡的主要原因,其初期可無明顯癥狀,及早查高分辨CT有助于早期診斷,并可及時干預,改善患兒的近遠期預后。目前SSc合并肺纖維化并無統一的治療方案,但對于存在肺纖維化的SSc患者主張早期使用免疫抑制劑或激素治療[5]。在一個多中心大安慰劑對照試驗表明每日口服環磷酰胺一年,可有效穩定SSc病情的進展[6],并改善預后。但長期的免疫抑制劑治療帶來的毒副反應,如感染、生長發育落后、缺血性骨壞死等,使其生活質量下降。因此,需要尋找更加安全的、有效的治療方法。有研究表明,在SSc模型組小鼠肺組織中,通過上調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可能誘導肺纖維化[7]。鑒于TGF-β在肺纖維化的進展中起著核心作用,阻斷TGF-β可能是潛在的治療方案。亦有研究表明,SSc患者皮損組織、體外培養的SSc成纖維細胞及硬皮病動物模型均表現為TGF-β1、TGF-β受體、Smad2/3表達上調和Smad7的明顯不足[8]。Hizal等[9]及Brown等[10]發現,低LL-37水平可能導致肺中血管生成和上皮增生,最終引起肺纖維化。Bhattacharyya等[11]證實在SSc患者皮膚和肺活檢標本和原代皮膚成纖維細胞中Toll樣受體4(toll-like receptor 4,TLR4)表達增加,潛在的TLR4內源性配體的組織染色也增加。這些研究提示JSSc患者發生肺纖維化的可能危險因素,在這些領域的進一步研究有利于為JSSc合并肺間質病變的診療提高最新臨床思路,尋找新的治療靶點。
JSSc患兒早期臨床癥狀不典型,易漏診、誤診,需尋找特異性指標進行早期診斷,合并肺間質病變需早期診斷,及早干預,改善患兒的近遠期預后,對于JSSc合并肺間質病變發病機制的研究為其治療提供了新靶點,促進了新藥的研發,關注疾病進展涉及的多條信號通路間的相互聯系,采取針對不同部位和不同靶點多種藥物的聯合治療,可能是未來抗JSSc合并肺纖維化治療的方向。